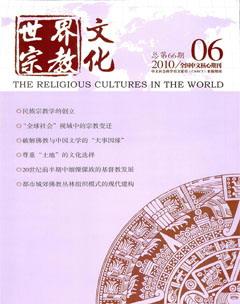20世纪前半期中缅傈僳族的基督教发展

内容提要:傈僳族是跨中国、缅甸、泰国、印度而居的跨界民族,在19世纪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中国面对帝国主义威胁并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先后接踵在中国与缅甸傈僳族中传播基督教,从此,两国傈僳族之间又增加了基督教文化互动的内容。本文重点探讨20世纪前半期处于不同国家政治场域与文化场域中的傈僳族基督教发展的背景、特点,并以傈僳族为个案说明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以及基督教在重构区域文化中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缅甸傈僳族基督教
作者简介:高志英,云南大学西边中心副教授。
20世纪前半期基督教在中国和缅甸傈僳族中得以传播和发展,在此过程中也伴随着各教会在中缅间傈僳族主要分布地区彼此的复杂关系。本文拟勾勒此一时期中缅两国傈僳族基督教的发展状况,并就中缅边界傈僳族地区基督教发展的地缘关系、教会间的关系和传教策略与得失等问题进行讨论,以求抛砖引玉,望各位方家不吝赐教。
一、跨界而居的傈僳族基督教信仰的特殊地缘关系
20世纪40年代,“傈僳民族之中心分布地带,多在云南西北部横断山脉中之高原及澜沧江、恩梅开江之峡谷地带中。”傈僳族在20世纪前半期独居之中心地带向异地迁徙路线,其一为沿怒江、澜沧江南下散布于保山、德宏,其二为翻越高黎贡山向西进入中缅未定界,最终形成东部以中国怒江为核心南达德宏与临沧、西部以缅甸密支那为核心的跨国界傈僳族大三角分布区。傈僳在这一带广泛迁移分布的原因之一,是因该区域在现代国家形成之前,云南地方土司“遥领”之故。中缅边界在历史上因中央王朝势力鞭长莫及,且远离土司统治核心区域而仅“遥领”,使得边界较为模糊,便于傈僳等族跨界迁徙流动与分布。在对缅甸伊洛瓦底江与中国怒江、澜沧江中下游傈僳族的调查中,皆发现保留着故乡为“怒迷哑哈巴(怒江石月亮)”,即傈僳“独居之中心地带”的共同历史记忆,并孕育了区域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傈僳传统文化。
傈僳族跨界分布格局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元代丽江路高黎贡山以西至今缅北地区已有傈僳先民“卢蛮”居住。明以后傈僳大量迁居于此。20世纪30年代恩梅开江与小江流域“有茶山、浪速、俅夷、傈僳四种,约计数百寨,人口数万户,浪速最多,茶山、俅夷、傈僳次之。其习俗多同。…‘俅夷、傈僳杂处,……两种人生活大同小异。”20世纪40年代“上帕(福贡)夷民,虽分三种(傈僳、怒、勒墨),而性质则互相传变,习染成风。”可见,同处于傈僳族分布的大三角区域内的以上诸族,历史上就存在的相近地缘、共同族源以及具有共享区域文化一致性的历史传统,与后来出现跨国界、跨民族的基督教信仰不无关联。
鸦片战争以来,分属西方列强的基督教不同力量先后传至中国与缅甸。缅甸傈僳信教与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有关。1824年至1885年,英国发动三次战争逐步吞并缅甸,使之完全沦为殖民地。“第一次英缅战争以后,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对缅甸侵略的深入和缅甸国家主权的进一步丧失,西方传教士得以深入内地,尤其是在少数民族中传教。”以缅甸傈僳族浸礼会与克钦族浸礼会文献记载互证,缅甸傈僳族接受基督教早于滇西傈僳族。19世纪80年代,美国传教士开始在克伦族中传播基督教。1880年,美国浸礼会牧师到克钦族地区传教。1898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格斯(Grorge J.Geis)在密支那克钦族中传教时接触傈僳族。1902年开始,密支那马肯村傈僳族夫妇俩受洗,缅甸傈僳信教由此开始。之后全缅浸礼会总部派克伦族青年学生巴托(Ba Thaw)到密支那专门给傈僳族传教。同时,还有神召会、内地会等外国传教士在缅甸景颇、克伦等族中传教,与其杂居的少量傈僳族也加入这些教会,但在20世纪前半期缅甸傈僳族地区的教会主要是浸礼会。
1909年,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昆明总会的英国牧师傅能仁(J.O.Fraser)从上海途经新加坡,到达缅甸仰光,又经曼德勒、八莫,进入滇西,以腾冲作为传教窗口,在古永、明光等傈僳村寨传教。腾冲历史上是南方丝绸之路要冲,近代因地处滇西濒临缅甸而被英帝国觊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英续订《中缅条约附款》,规定开腾越为商埠并设海关。傅能仁进入腾冲前,已有9任英领事驻腾越海关,另有多名英传教士在腾冲县城传教。在半殖民化的历史背景中凭借腾冲特有的孔道,英传教士进入云南傈僳族地区传教,腾冲傈僳族由此而率先信教。之后傅能仁在与腾冲相邻的木城坡、苏典等地傈僳族中传播基督教。
1912年,在密支那傈僳中传教的格斯听说傅能仁在腾冲传教,派巴托前往与之见面。其后创制傈僳文字、翻译《圣经》、编纂《赞美诗》及在两国傈僳等民族中发展基督教、建设教堂等。1919年,木城坡傈僳族传道员胡大(后改名胡保罗),受英国牧师麦克西主持的八莫内地会派遣到耿马贺永山传教,1921年,成立内地会龙陵木城坡教会。1922年,杨思慧(A.B.Coore)夫妇被内地会派往木城坡接替傅能仁。内地会牧师美籍加拿大人杨志英(Mr.John Kuhn)从上海到云南,先后在龙陵、腾冲、耿马等地傈僳族中传教,1924年被派到贺永山建立内地会教堂。
1927年,杨思慧从缅甸运进钢筋水泥等建材建成礼拜堂,成为内地会贺永山总堂,贺永山亦改名为福音山。该堂先后在21个村寨(其中有岔沟、明子山、平河3个村寨属缅甸)建立礼拜堂,还把胡大、亚比斯、根地那等送到缅甸深造。可以看出滇西傈僳族基督教发展与缅甸傈僳等族有密切的地缘关系。
基督教在怒江地区傈僳族中的传播,也是与缅甸傈僳族的地缘、族源关系密切相关的。杨思慧于1929年进入怒江泸水县大兴地托基村开拓新教区,同年派遣傈僳族传道员旺友毕等到碧江传教,成立里吾底教会。1933年杨思慧到里吾底传教,次年建立里吾底内地会主教基地,统管碧江全县教会,培养教职人员,怒族步傈僳族之后开始信仰基督教。泸水教区因杨思慧夫妇北上碧江而出现空缺,杨志英就于1930年从福音山到泸水大兴地,次年建立麻栗坪村基督教会,泸水成为其传教范围。为了巩固教会,杨志英于1934年开始开办每年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圣经培训班。1947年泸水内地会迁于称戛村,直到1950年止,共办了16年之久,培训马扒(傈僳语,传道员)约有50余人,其中泸水一个县内培训出了24个马扒。不仅泸水、碧江的教牧人员参加,还有腾冲、维西、福贡、贡山、永胜等地,甚至缅甸传教士也前来培训。短短20余年间,滇西、滇西北大部分傈僳族居住地皆成为内地会传教范围。
1920年,维西神召会派遣传道员到福贡县进行试探性传教,1929年维西神召会美国传教士马道民派遣汉族助手昆明人杨雨楼进人福贡传教,1930年,马道民亲自到福贡上帕村传教。因出示了政府签发的入境证件,设治局局长保维德对其传教与携带枪支无可奈何,马道民就在福贡稳住了脚跟,并派遣傈僳族教徒到中缅未定界传教。1926年莫尔斯(J.Russell Morse)脱离原所属美国“联合基督教
会中华传教会”,成立“滇藏基督教会”,从1938年开始不断从维西派遣传道员到贡山传教。1940年莫尔斯派遣傈僳族传教士用傈僳语与傈僳文《圣经》在中国独龙族中传教,并将教会推进中缅未定界。到1949年已发展信徒2193人,其中独龙族信徒500多人,约为当时独龙江独龙族人口的1/4。
二、多种教会在中缅傈僳族中的跨界并存与发展
20世纪前半期,分属不同国家的基督教各种教会在缅北与滇西傈僳族中形成了多种教会并存的局面。内地会是英、美等国基督教新教对中国派遣传教人员的差会组织,该会直接在中国设立教会,因而系由内地传入。而进入滇西傈僳族地区的浸礼会、神召会与基督会,有各自不同的背景和各自的传播路线。
在滇西,浸礼会从美国传至缅甸,再由缅甸传入德宏;神召会即“五旬节派”,或称“灵恩派”,由法国传至缅甸,再从缅北南桑阳传人德宏。
在怒江地区,除了内地会外,基督会与神召会也皆从其中国内地经维西传来。怒江地区基督教各教会之间的关系,正如李道生在《福贡县基督教情况调查》中所说:“解放前怒江的基督教分属不同教派,各教派的外国传教士为了各自的利益,都竭力想要争夺群众,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各派外国传教士既互相利用,又相互排挤,……如福贡是马道民的教区,属神召会教派;碧江是美国传教士杨思慧的教区,属内地会教派;贡山是美国传教士莫尔斯的教区,属滇藏基督教会派。三个外国传教士各自划分势力范围,谁也不能到对方的教区内传教。”几个教会在滇西、滇西北傈僳族中虽然规模不同,但能够并存,而且在事实上形成了各自主要的传播区域与势力范围。而从这些外国传教士与所属国家教会及其国籍看,基督教各教会之间势力的消长、传教区域的伸缩,即是西方列强在滇西傈僳族地区“宗教版图”的变化。各教会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关系俨然是当时各西方列强在中国复杂关系的缩影。

内地会、神召会、基督会在1949年以前是从中国傈僳族地区向中缅未定界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傈僳族信徒迁徙缅甸,而把各自教会“搬”到缅甸,中国基督教会在缅甸得以延续、发展。因此有学者就认为,“(缅甸)各个教会的前身居在中国”。缅甸傈僳族基督教各教会在缅甸境内的发展,与在中国傈僳族中的发展一样,因为分属不同政治力量和不同教会等原因,加之从中国境内“移入”缅甸的教会也不可避免地将以往彼此之间的竞争与矛盾带去,导致缅甸傈僳族多教会并存中矛盾与竞争同在的格局。
基督教多种教会的并存,实现了跨地区、国界、教会的傈僳族宗教区域文化的重构。通过傅能仁与巴托等人的传教活动,使滇西与缅甸两地的傈僳族内地会与浸礼会联系在一起。该区域内更多不同教会随后在傈僳、景颇、拉祜、克伦等族中推广基督教方面亦长期存在相互交往与合作,显现出超越教会的文化认同与超越民族、国界的宗教认同相互纠葛的发展特征。泸水、碧江、腾冲、龙陵、潞西、耿马等地傈僳族教会信众多为单一民族;而陇川、瑞丽等地傈僳族多依附于景颇族为主体的教会中;缅甸傈僳族既有傈僳族为主的教会,也有多民族共同参加的教会,显现出傈僳族聚居、杂居不同区域基督教教会组织的特点。从总体上看,在中缅傈僳族分布的大三角地带形成了新的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区域文化,这是同一区域内多民族信众的共同选择,也是区域文化传统的延续与重构。
三、基督教会在中缅跨界傈僳族地区的传教策略与得失
作为内地会在傈僳族地区传播基督教的开创者,傅能仁在传教过程中探索出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是学习傈僳语、创制傈僳文字并用傈僳语文传教;二是培养本民族传道员;三是行医济贫,扶助孤弱;四是寓教于乐,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傅能仁以此在腾冲顺利立足,并往四境平稳发展。
傅能仁进入腾冲傈僳族地区宣教后,曾经住在苏典(时属腾冲,今属盈江)邦别(巴比)村的柯武家,学习了半年傈僳语后,开始用傈僳语传教。他请柯武为伴,先后到盈江苏典、陇川户撒与腊撤、龙陵木城坡等傈僳族地区传教。他“一面宣教,一面学习各地方(傈僳族)的不同语言,了解傈僳族的民俗民情。”柯武作为他培养的第一个傈僳族传道员,不仅是旅伴和翻译,其在场更有助于消除傈僳人对傅能仁的排拒心理。借本民族传道员把西方基督教传播到更多信众中,是外国传教士屡试不爽的手段之一。
1912年,巴托与傅能仁在腾冲见面后,两位在传教过程中意识到了创制傈僳文字作为传教工具的重要性,约定各自创制一套文字方案试用比较。巴托依据克钦(阿普)文字设计了傈僳族文字方案,但因傅能仁创制的BPD方案单音节多,易读、易写、易记,而被广泛认可。之后经两人共同修改完善,于1919年定案。两国、两个教会的共同努力,终结了傈僳族无文字的历史,对于傈僳族宗教认同的强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傈僳文字的创制,不仅便利了传教,更使傈僳人可以与区域内相对强势的汉、彝、纳西等族在文化传播与引进上展开竞争,有利于激发其民族自信心,民众也因而更向往能够使其认字识文的基督教。
傈僳文给内地会的传教工作插上了翅膀,其影响从腾冲一隅扩展到滇西各地。傅能仁被任命为滇西基督教区监督,以肯定其贡献。木城坡教会的成立,实现了传教区从腾冲(保山)到德宏的突破,为英国内地会在滇西最为辉煌之时。之后,中缅边界傈僳族地区“基督教版图”随内地会传教士的足迹而扩大,以腾冲为起点,南到德宏,东至临沧,北达怒江。傅能仁与巴托一面传教,一面审定已翻译的四卷福音,新译了《新约全书》中的《使徒行传》,翻译与编纂了《赞美诗歌曲集》。1937年,傈僳文《圣经》新约全书共33万字194本终于在烟台付梓。以傈僳族易学想学的傈僳文《圣经》与《赞美诗》传教,使内地会在傈僳族中的影响与日俱增。
内地会对于培养傈僳族传道员极为重视,用其减少民众对外来宗教、外国传教士的排拒心理。内地会在滇西的每个教会每年都开办圣经培训班,并以此为核心,将基督教扩散到周围。1926年,杨思慧在木城坡、福音山派出傈僳族传道员到各地传教。旺友毕等人来到泸水上江,一路北上到碧江,将基督教传播到怒江中上游地区。杨思慧夫妇到碧江后,每年举办两期讲经班。即一、二月举办普及班,主要学习文化和讲授圣经常识;七至九月举办高级班,主要培训对象是马扒(教士)、密支扒(教主)、教牧人员。不仅培养了许多本土本族的传教士,而且在翻译傈僳文《圣经》、编译《赞美诗》的过程中培养出一大批傈僳族教牧人员,由此傈僳族也有了识文认字的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使内地会的传教事业发扬光大。
外国传教士对基督教文化与傈僳族传统文化的“嫁接”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在高黎贡山至恩梅开江一带诸民族中有个古老的传说:野人(景颇族)与汉人、焚夷(傣族)是同祖先的弟兄三人。野人为老大,气力莽壮,阿公阿祖不喜欢,令其远居耕山种地防边,故野人皆居深山老林;焚夷为老二,令起半耕半读,故僰夷多种水田,亦有知书识字者;汉人系老三,阿公阿祖最钟爱,令其在内地读书做官。故汉人皆知书识字做大官。在“传教士进人边境民族地区后,为了扎住根,对这一传
说进行了锯解,说景颇族、傈僳、汉人、洋人是一娘所生的四兄弟,洋人是老大,过去出门走远了。老大很有本事,会造飞机,现在回转来了。”以基督教信仰作为确定兄弟关系的标准,将洋人添列其中,不但使傈僳、景颇、汉人与洋人因为相同血缘和宗教而有了亲近的关系,而且传说中不在“兄弟”之列的傈僳族也荣列其中。无疑地,传教士为了传教对民族渊源关系的文化再解释却给了傈僳族以民族自信心。
传教士在以附会历史促使傈僳、景颇民众信教的同时,制定“不准唱民族歌曲”、“不准讲故事”的教规,迫使民众放弃传统文化,用新创的历史叙事颠覆民族传统历史记忆,从而形成以基督教为核心或标志的区域文化,使此区域内原来信仰万物有灵原生宗教的民族文化向基督教文化靠拢。而且,传教士所谓信教后不怕鬼神、不需频繁祭祀的宣传也对傈僳族群众有吸引力。
内地会传教士的诸种努力,使其传教事业发展迅速。到1949年,内地会在怒江泸水、碧江培养教徒11759人,数量超过基督会与神召会教徒总数的2456人;内地会在保山、临沧也占优势,在德宏居第二位。
四、傈僳族对基督教的“迎合”与基督教在同一区域内不同民族中的境遇
内地会信众以傈僳族为主,之所以能够发展兴旺,不仅与内地会传教士不断借鉴与完善传教经验有关,也和傈僳族自身的原因有关。
20世纪前半期,僳僳族社会尚处于政治管理真空、半真空状态,中国政府控制力量薄弱,是基督教进入和扩展的重要因素。当时中缅傈僳族分布地带多远离政治中心,虽然边疆危机后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傈僳族地区的管理与控制,但终究鞭长莫及,尚未形成严密的政治管理网络,基督教的进入有较大空间。从傈僳族自身来看,民间政治制度发育还不完善,村寨头人组织尚不完备,且头人们也因遭受异族强权压迫而往往率先入教。其次,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弱势地位也是傈僳民众皈依基督教的内因之一。因土司、国民党设治局官员、异族汉族商人层层压迫剥削,傈僳族处于社会最底层,与上述群体隔阂很深。作为区域内的弱势群体渴望寻找外界力量作为靠山,而外国传教士一方面给傈僳族传福音,创文字,看病送药,扶助贫弱,使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尊重感;另一方面在长期以来只能以迁徙来逃避压迫的傈僳民众面前,凭借教会势力,可以以此与官员对峙。杨思慧1929年就为碧江县设治局长干涉里吾底圣诞节捐献事件而与其对簿公堂,由此在群众中赢得威望,认为终于有了政治靠山而围拢在其周围。第三,教会的出现,使傈僳族有了以宗教为连结纽带的统一组织,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与周围具有较为完备的政治组织的民族相抗衡的政治动员机构,除了精神信仰上的皈依之外,宗教组织作为集体动员力量,弥补了原有宗教分散、非制度化的欠缺和以家族为主要社会组织而在更大规模组织结构上的缺失,对在区域政治中处于弱势的傈僳族颇具吸引力。
傈僳族对于基督教的“迎合”,往往体现出主动性的集体选择。1912年,傅能仁被山区傈僳族主动相邀到家做客,才有了第一家傈僳族教徒在他讲经布道后,拆除神坛皈依基督教的行为。1919年,胡大迎接杨思慧去其家乡寒地传教,又主动将家里拜鬼的器物摧毁、祭拜神树的架子拿掉、水碗打破,又将存放香火的小栅付之一炬,从此基督教也在怒族中发展起来。1956年,怒江地区教徒的分布,以内地会所在的“碧江、福贡二县接壤的32个乡最多,占32个乡总人口的90%。”
不过,传教士在同一区域其他民族中的境遇也有差异。1920年维西白济汛人阿夫贾(纳西族)到福贡传教,颇为成功。因为傈僳族对纳西族具有历史上延续下来的认同感,而且阿夫贾会说傈僳语,还借用万花筒、图片,吸引群众驻足围观。但此后汉族与美国传教士进入福贡则时有坎坷。据付阿伯《福贡基督教传播史略》记载,1929年,杨雨楼到福贡鹿马登村一面传教,一面向村民买地准备修盖教堂,因受设治局局长保维德干涉抵制,只好跑到今缅甸境内的俅江木拉斗发展。1930年,马道民亲自到上帕村传教。首先住在傈僳族保长家里发展教徒。次年,在上帕筹建神召会,并在上帕与腊乌交界地亚马尼坡租地盖房作为据点,向福贡四境传教,人教者日渐增多,势力逐年扩大。之后,神召会经历了诸多波折,最后被绝大部分教徒所离弃。而莫尔斯在藏族、纳西族聚居区与傈僳、独龙族地区遭遇了截然相反的命运,则说明即便是教会、传教士及传教方法相同,但基督教在不同民族中的境遇却完全不同。
总之,宗教信仰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及表现,基督教认同与民族认同往往相互交织、彼此促进,在特定情境下也可成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20世纪初西方基督教在中缅傈僳族中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基于中国与缅甸先后沦为西方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是长期处于迁徙中的傈僳族处在政治管理真空,并在区域内居于弱势地位所致;此外,亦与基督教在傈僳族中传教策略有关,与区域文化一致性传统有关。基督教在20世纪前半期中缅傈僳族中的并存、竞争与消长,伴随各教会国际背景的变化,与西方列强在中国与缅甸势力消长相对应。傈僳族经历了从地域性传统宗教到制度化基督教的变迁,基督教成为傈僳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并重构了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跨国界、跨民族的区域文化。
(责任编辑唐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