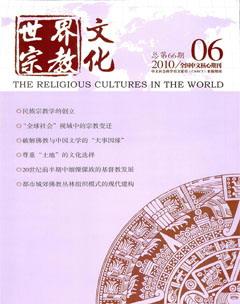可能与必然
内容提要:弥勒图像渊源于古印度,流经西域,盛极于中土。其图像的演变经历了“仙佛模式”、“交脚弥勒菩萨”、“倚坐弥勒佛”,最后定型于“布袋弥勒”的形象。那么弥勒图像为何最终定型于布袋弥勒?本文从可能性和必然性两方面,对弥勒图像的转型与定型作了具体分析。
关键词:布袋弥勒布袋和尚图像转型与定型
作者简介:王忠林,《中国佛教艺术》编辑,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生。
一、问题的提出:“布袋弥勒”并不等于“布袋和尚”
弥勒图像渊源于古印度,流经西域,盛极于中土。其图像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第一、早期“仙佛模式”的混融阶段,这时的弥勒图像既不是古印度的弥勒造像范式,也没有完全中国化,而是与中国古代传统信仰中的仙神混融的形象。如梁沈约因皇太子造弥勒像而著《弥勒赞》中云:“道有常尊,神无恒器,脱屣王家,来承宝位”之句,即把弥勒称之为神。此阶段的弥勒图像具有不成熟性和过渡性的特点;第二、中期“交脚弥勒菩萨”和“倚坐弥勒佛”图像的圆融阶段。弥勒图像具体表现为弥勒经典中的“上生菩萨,下生佛”的形象。从十六国一直到隋代,弥勒像基本以交脚或思维坐姿弥勒为主流。倚坐弥勒尊像则为唐代弥勒图像的典型特征。第三、晚期“布袋弥勒”的定型阶段。北宋之后,各式各样的弥勒图像均让位于布袋和尚的形象,至此弥勒图像的发展走向了完全世俗化与中国化的终极。
那么弥勒图像最后何以定型于“布袋弥勒”的形象呢?学界和民间一般皆以“布袋和尚”——“契此”为依据。其依据的有关史料如下:
首先是北宋初年(988)赞宁所作的《唐明州奉化县契此传》。由传中“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焉。”说明最迟在北宋初年,布袋和尚的图像就已经开始流传于世了。
其后是1004年的道原所著的《景德传灯录》。道原在《宋高僧传》的基础上加入了若干典故,补充了一歌二偈,四次问答,特别是写下了布袋和尚示灭的时间、地点和临终前说偈的情况和内容。说明“竞图其像”缘起于“他州有人见师亦负布袋而行”。由《景德传灯录》中:“……四众竞图其像。今岳林寺大殿东堂全身见存”可以确定,在北宋中期的11世纪左右,布袋的画像在汉传佛教造像中已经非常普遍了。
此外还有较为重要的《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释氏稽古略》、《神僧传》等书中的布袋传,以及《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中的《明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布袋和尚后序》、《重刻弥勒传略记》等。
南宋志磐所著《佛祖统记》卷42所载布袋和尚篇幅虽少,但却加入了《景德传灯录》所没有的记载,且和后世所见的布袋和尚像构图有密切的关系。如“十六群儿哗逐之,争掣其袋”的典故;以及蒋见师背一眼抚之曰:“汝是佛”。师止之曰:“勿说与人”典故等等。
由以上资料可知,学界和民间之所以认为“布袋弥勒”的定型是以“布袋和尚”契此的形象为依据的,可归纳为以下几个理由:
第一、时间上的吻合。从时间上讲,现存的布袋弥勒造像都是北宋之后的作品,这与上述资料所记载的契此和尚生活的大致年代是吻合的,而且契此和尚与图像关系的记载也很明确。
第二、空间上的吻合。以上资料记载布袋和尚为明州(浙东地区)人氏,而最早的“布袋弥勒”造像也正是流传于江浙一带的。如现存的杭州飞来峰36窟著名的大肚弥勒。
第三、形象上的吻合。二者都是“散圣”的形象。头如比丘、袒胸露腹,以布袋为行囊。
但是,如果由此我们就认为“布袋弥勒”就等同于“布袋和尚”契此,就值得商榷了。
第一、从记载契此和尚的传记来讲,如《景德传灯录》、《宋高僧传》、《佛祖统纪》等本身就充满神化与传奇的色彩,并不是对历史人物的真实描写。如“曾于雪中卧而身上无雪,人以此奇之”、“他州有人见师,亦负布袋而行”等都是民间的神通。
第二、从契此和尚的相貌上来讲,“形裁服腰蹙额”中“服腰”即“肥貌”,缺乏神采。“蹙额”即“皱缩鼻翼”,为“愁苦貌”。显然这样愁苦丑陋的相貌与喜眉乐目的“布袋弥勒”图像的形象是不一致的。此外,虽然二者都打破了佛像“不现腹、不出脐”等诸多相好,但布袋弥勒造像还没有彻底脱离佛相的基本特征,如“大耳垂肩、耳垂丰满”等相。
第三、从弥勒“笑”的表征来看,以上所有传记中并未见契此和尚的笑,哪怕是微笑。而现存的“布袋弥勒”造像基本是笑口常开的。
第四、从布袋和尚的性格上来讲,《宋高僧传》和《景德传灯录》中所描述的就不一致。《宋高僧传》中的布袋和尚是一个能测人凶吉——“示人吉凶,必现相表兆”、预知天气——“亢阳,即曳高齿木屐。市桥上竖膝而眠。水潦,则系湿草屦”具有类似罗汉的神通。而《景德传灯录》中有了禅宗偈诗的出现,应答也完全是禅宗公案的行为模式,这说明此处布袋和尚的性格已经具有了禅宗高僧的成分。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在形象上还是在精神与性格上,“布袋和尚”契此与“布袋弥勒”图像都有很大的差距。尤其在精神层面上二者不但毫无相通之处,而且是相悖的。一个是“苦”相,一个是“乐”相。因此,传统观点认为“布袋和尚”是“布袋弥勒”定型的依据之说,是不成立的。那么“布袋弥勒”的定型究竟以何为依据呢?。
法国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文艺批评家丹纳认为,每一种美学思潮、艺术品种及流派只能在特殊的精神气候中产生,“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这一点已经由经验证实: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的各个重要时代,就可以看到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习惯同时出现的。”
因此,我们要探析弥勒图像的转型与定型,也应该在其历史与文化的气候中解读。
二、弥勒图像转型的可能性
1、从弥勒经典角度来看,佛经中已有弥勒多种形象的出现,这为弥勒的转型提供了宗教心理接受的可能。
在《阿含经》中,弥勒的身份就不是固定的,有时是比丘,有时是菩萨,而早期的菩萨其实多指白衣居士。《中阿含经》卷十三《说本经》说释迦告诉弟子们:“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当时佛名称弥勒如来……”在《长阿含经》中说:“有佛出世,名为弥勒如来。”在《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中,佛弟子优波离便指责:“世尊,世尊往昔于昆尼中及诸经藏说阿逸多次当作佛。此阿逸多具凡夫身,未断诸漏,此人命终当生何处?其人今者虽复出家,不修禅定、不断烦恼。”此阿逸多即弥勒,这表明弥勒似乎未得阿罗汉果,不像是一个严格的出家僧人。在《弥勒菩萨所问经》(元魏菩提留支译于509至537年间)、同本同译《大宝积经弥勒菩萨问八法会第四十一》(同经111卷)、同本异出未完本《佛说大乘方等要慧经》,(后汉安世高译于148年至170年间)等弥勒经中,弥勒还只是单纯地以一个佛弟子的身份出现。在《慈氏菩萨所说大乘缘生稻秆喻经》,(唐代不空译
于746年至771年间)、同本异出《了生本死经》,(吴代支谦译于223年至253年间)、同本异出《佛说稻秆经》,失译者,人名附东晋录、同本异出《大乘舍黎娑担摩经》,(宋代施护译于980年后)等经中,弥勒虽然还是一佛弟子的身份出现的,但其地位已比舍利佛更高一层了。在《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西晋竺法护译于303年)、异本《大宝积经弥勒菩萨所问会第四十二》,(唐菩提流支译于693至713年间)中,经典的前半部分中还在讲只是佛弟子的弥勒,到了后半部分,则讲述作为未来佛的弥勒事迹了。在所谓的“弥勒六部经”中,作为佛弟子的弥勒已全然隐没于背后,弥勒开始以未来佛的身份出现。同时弥勒菩萨自身也时不时地以佛的身份出现在“前台”对大众说法。
可见,即使在经典的弥勒经中,其形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在弥勒图像发展的历史上,就出现过交脚弥勒和倚坐弥勒等多种尊像。随着佛教和社会的发展,弥勒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化。
2、从佛教发展史角度来看,佛教义理的转型为弥勒图像提供了形象转型的可能。
宋之后佛教的儒学化已经成为佛教发展的新趋势。“儒家思想虽也浩瀚广博,但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是强调人本,二是注重人世。自孔子、孟子而明清之际儒者,概莫能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儒家学说,其思想旨趣,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一言以蔽之——“人”。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重点就是“仁学”。孔子赋予“仁”以道德属性,用来论述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这种“重人伦,远鬼神”的审美倾向一直是儒学思想的主流。儒家的人世思想也贯穿于整个儒学的发展历程中。孔子的“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而成”,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董仲舒的“圣人之为天下者,兴利也”,等主张皆注重人世。儒学发展到宋代与佛教互补渗透,产生大交融。佛教在理论上吸收了儒家的人本与人世的思想,走向儒学化和世俗化。赖永海先生在其文《宋元时期佛儒交融思想探微》中精辟地论述了佛儒思想交融的有关情况。
佛教造像是佛教精神的载体,所以佛教思想与义理的转变也必然带来佛教造像形象的转型。弥勒从佛和菩萨的形象向世俗的人的形象转型也是佛教在宋元之后的儒学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弥勒转型后的形象既出世、又人世,既神奇、又平常的风貌不仅吸引了民间众生,还逐渐受到官方的尊崇,这表明中国人既不喜欢高高在上、不可触及的真佛,也不甘心承认庸俗堕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假佛,真正喜欢的是处于中道位置的高贵而平凡、庄严而亲切的可近可仰的世间佛。如果脱离宋元后的佛、儒交融的大背景,我们很难理解弥勒造型在此历史时期的转型,何以为可能?
3、从民间百姓角度来看,美好的象征为弥勒的转型提供了契合民间愿望的可能。虽然庄严而高大的弥勒佛令人仰视震颤,华丽而高贵的弥勒菩萨令人向往迷恋,但是这些图像与普通老百姓距离遥不可及,凡人“若无戒行,追空念善,也不得生”,现实中人们期盼的是喜乐、祥和与宽容。喜乐祥和是人们真实的心理满足,而大肚弥勒正是弥勒这种愿望的表征。
如果说弥勒菩萨和弥勒佛像是一种对彼岸的向往,那么大肚弥勒像则是对现实的期盼。它集民间多种美好的渴望于一身。如布袋和尚游戏坐,圆腹如鼓,头大耳垂。两侧各一童子,左侧还有一驯服伏卧的家犬。富态的布袋与童子、家犬组合在一起,表现了人们希冀生活富足,人丁兴旺。六子布袋则反映了人们对子孙繁衍的期望。其富态的造型与祥和表情只是符号的能指。其所指却是民间对生活的热望、包容与谦让。所以,这种弥勒造型的象征性是中国人心态的物化形式,其意指和象征意义是非常清楚的。
三、弥勒图像定型的必然性
1、从文化发展角度来看,宋之后中国文化的全面世俗化,使弥勒从神的形象走到了人间。
赵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的繁荣兴旺,促使城市诸行百业的繁兴和广大市民阶层的壮大,多层次的社会生活状况,带来了多层次的文化艺术的发展,除正统的诗词、书画、音乐、建筑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歌舞、杂艺等通俗的文艺一时也得到极大的繁荣。这造就了世人对生活美、自然美、艺术美的认识幅度的扩大和欣赏能力的提高,从而奠定了佛教造像表现世俗化的现实生活内容的社会基础。
弥勒佛是“现世佛”释迦牟尼灭度之后下降人世的“未来佛”。《佛说法灭尽经》说:“弥勒当下世间作佛,天下泰平,毒气消除,雨润和适,五谷滋茂,树木长大人长八丈,皆寿八万四千岁,众生得度不可称计。”这样的理想世界,自然受到人们的热烈向往。
宋代之前的弥勒佛图像有上生菩萨形和下生佛形两种,以下生佛形造像最为多见。弥勒佛形图像和其他佛教图像一样,必须严格遵循经论中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造像仪轨来塑造,诸如“广长眼”、“鼻直高”、“面净如满月”、“手足赤自如莲花色”等。这些细节特征集中了人类想象出的一切优点,以便来塑造这位至尊至贵的未来佛形象,借以突出他超越人间的“神性”特征,使人们产生敬仰之情而皈依佛门。
迨至五代,尤其是两宋时期,随着佛教世俗意识的高涨,出现了与前代迥异的面带笑容的大肚弥勒佛,神圣的弥勒佛图像异化为世俗化的高僧。
这位肥头大耳的弥勒佛与早期端庄秀美的弥勒上生菩萨像及庄严静穆的下生成弥勒佛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大足宝顶至杭州飞来峰等处的弥勒塑像,其“蹙额皤腹,笑容满面,箕踞而坐”的丰厚形象已完全摆脱了佛教造像“绝对高于人间”的程式化造型。江西赣州有通天岩石窟,其中也有着布袋和尚的雕像。高不可攀的弥勒佛祖成了小孩子都可以爬满全身与之嬉戏的乐呵呵的大肚子和尚。这一“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的皆大欢喜的佛教图像,标志着宋代佛教神祗造像已深深地融入了世俗生活,从而取得了全新的艺术生命力。
总之,随着宋之后中国文化的全面世俗化,弥勒图像也必然从形象到精神都走向民间化、世俗化。这样的弥勒图像才能成为中国人心中最为熟知又极为亲切的佛像。
2、从禅宗发展角度来看,后期禅宗从佛教内部废除了设象传教的法统,并赋予了布袋弥勒形象更多的禅意。
唐经安史之乱和会昌法难后,佛典散佚,中原义学失去质的凭藉,日趋式微。相反“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禅宗在南方悄然崛起,以“见性成佛”、“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思想成为质朴利行的大众化佛教。随着禅宗在宋代的勃兴与发展,中国佛教出现了一种由繁而简、由博而约的世俗化发展趋势。由祖师禅到分灯禅,心的宗教逐步取代了对佛陀的崇拜。禅宗倡导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自性平等,众生是佛”、“即心即佛”的佛性说,直接消解了佛教的神圣思想,打破了世间与出世、家与出家、生死与涅槃之间的界限。佛教至后期禅宗更强调“混俗和光”、“随缘任运”的“无证无修”的思想,这不但导致禅宗本身的变革,而且对佛教图像也产生了必然的影响。
第一、从“呵佛骂祖”到对“设象传教”法统的废除。在禅宗语录中,“呵佛骂祖”的公案比比皆是。如佛是“干屎橛”“佛不如曹山”、“他是阿谁”等。佛教也叫“象教”,“象”即“佛
像”。所谓“象教”也就是强调寓教于像。由于佛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读懂的,尤其普通的信徒根本不会去读那些高深而晦涩的佛经。但佛教为了扩大传教范围,于是便借助佛像来“方便说法”。由于佛教“以像传法”,此后“象教”也逐渐成为佛教的代名词。正如释道高所云:“夫如来应物,凡有三焉:一者见身,放光动地;二者正法,如佛在世;三者像教,仿佛仪轨。仿佛仪轨,应今人情,人情感像。”此后,像教的力量常为世人所称道,李白云:“乃再崇厥功,发挥像教”。杜甫也曾云:“方知像教力,足可追冥搜”。但佛教发展到禅宗则由“象教”走向了“破相”,正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尤其是到“后期禅宗由不求佛祖,到呵佛骂祖,甚至要‘逢佛杀佛、逢祖杀祖、‘蒸佛、‘蒸祖,标志着禅宗已经反对一切偶像;而主张纯任自然、做本然天真自在佛。”石头希迁的弟子丹霞天然禅师竟然把佛像劈了烧火取暖。
第二、变神殿为人间。《勒修百丈清规》中明确规定:“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者,表佛祖亲嘱受当代为尊也。”就是不在佛殿中供奉诸佛菩萨等偶像,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原来的弥勒佛和弥勒菩萨失去了偶像崇拜的空间。
第三、赋予弥勒图像更多的禅意。在后期禅宗的思想影响下,弥勒造像作为神的形象被废除了,但却赋予了更多的禅意。其禅意主要表现在“笑”、“布袋”和“大肚”之中。禅宗常常把“笑”的意象当做一种禅机。如在《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中就有“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的公案。迦叶的破颜一笑,应是佛陀知其开悟了,了然于他的拈花妙旨,道可悟,可会而不可说。到了后期禅宗更把“呵呵大笑”当作开悟禅机。“布袋”表示包罗乾坤、遍及十方虚空,象征着无边无际、森罗万象的表象分别,即“有住”;而放下布袋,则表示将纷杂的万象分别全行脱去,即“无住”。如《五灯会元》中所引之偈:“我有一布袋。虚空无罣碍。展开遍十方。入时观自在”,以及《希叟绍昙禅师语录》中所云:“紧布袋头,森罗及万像一时收……”等语。“大肚”象征着呵骂。如希叟绍昙布袋图赞中有“一肚皮恶毒”、“肚里千机万变”、“肚皮无窖”等语。当然,大肚的更多禅意是豁达,如“宽却肚皮常忍辱,放开泆日暗消磨。若逢知己须依分,纵遇冤家也共和。要使此心无缝碍,自然证得六波罗。”“宽却肚皮需忍辱,豁开心地任从他”此外,禅宗还偶用大肚比喻大量之意,如断桥妙伦:“上下相依不相怪,由来彼此肚皮大”。
由上可以看出,在后期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宋代之后弥勒造像已从宗教的圣坛走向世俗的人间。而布袋弥勒像被赋予更多的禅意,也是后期禅宗带来的自然转型。
3、从政治需要角度来看,民间利用弥勒口号起义及“赞扬弥陀,贬抑弥勒”思想的盛行使弥勒信仰失去了生存的政治土壤。
晋释道安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名言,是对十六国时期佛教传播条件的总结。事实上,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也从没有出现过任何一种宗教超越皇权的时代。一方面,统治者利用宗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另一方面,当一种宗教危害皇权的统治的时候,必然要招到到镇压,从而导致信仰的转变,弥勒信仰亦如此。
南北朝以来就有不少人打着弥勒的旗号掀起暴乱,这不仅败坏了佛教的形象,还使佛教本身受到直接打击。早在北魏末年,就有沙门法庆领导的大乘起义,口号是“新佛出世,除去旧魔”。“新佛”即指“弥勒佛”。以弥勒下生相标榜的邪教多以白衣长发的面目出现,如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汾州等地冯宜都、贺悦回成等惑众作逆,即“服素衣,持白伞白幡”。隋代民间的弥勒信仰,以下生信仰为主,突出地表现在利用弥勒诸经中有关“弥勒即将出世”的预言,并以此为号召暴力反叛。据《隋书》卷三《炀帝纪》载,在隋朝短短的三十多年中,以弥勒出世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就有三次。
在弥勒净土信仰传播中,还出现了许多“赞扬弥陀,贬抑弥勒”的言论,这是弥勒信仰衰落的又一原因。阿弥陀净土信仰早在汉魏之际就已传人中国内地,到南北朝后期,由于昙鸾的大力提倡而影响剧增。弥陀净土学说因其简单易行,而更容易为广大信众所接受。入隋之后,又得到智者大师、道绰等的弘扬。道绰在其《安乐集》中从多方面比较了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的优劣,盛赞弥陀净土之优,贬抑弥勒净土为劣;智者大师《净土十疑论》中也有“扬弥陀,抑弥勒”的说法。这些言论有的固然有宗派贬斥异己的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般看法,同时又对民间信众的信仰取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样,弥勒信仰逐渐衰落,而弥陀信仰则迅速普及,流行日广。至初唐,《净土十疑论》、《往生安乐集》、《净土论》问世之后,弥勒净土思想更加没落。这三论作者有意无意地贬低了弥勒净土的价值。
宋元之后弥勒佛像失去神圣的偶像地位,也正是弥勒信仰的衰落的必然结果。
4、从佛教造像角度来看,罗汉、高僧和祖师造像的兴起,为弥勒图像定型提供了直接参照物。
禅宗与禅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佛教教旨的局限,致力于心的开发,由此表现在佛教造像上则从佛、菩萨的形象向世俗的罗汉、高僧和祖师像转变。所谓“诸佛、菩萨之应世也,亦犹哲王之抹弊,或忠、或文、或质、虽制治不同,其趋一也……彼达磨大士,方以妙元明心,亲提教外别传之印,则于有为功德,不无抑提,是亦因时求弊耳,非实贬也”。
罗汉的形象本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随着禅宗思想的抬头和玄奘翻译的《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略称《法住记》)的流行,罗汉逐渐在中国得到普及。罗汉造像初法绘画,初唐发其端,经五代贯休和尚与北宋初赵光辅的发展定型。盛唐时期两京罗汉绘塑已经盛行。五代时期由中原而南方,尤其护持佛教的浙江钱塘一带地区发展显著,两宋时期波及全国,其中东南地区达到相当水平。江苏吴县的保圣寺罗汉彩塑,为唐代塑造宋代整修的珍品,原18尊,现尚存9尊,罗汉比例适度,表现出不同的人物性格与气质,衣褶线条流畅,细节刻画极精,是中国罗汉塑像中的精品。山东长清县灵岩寺的40尊罗汉塑像,把喜怒哀乐的内心世界展观得淋漓尽致,塑像袒露的胸骨、锁骨和青筋脉络清晰可见。江苏苏州紫金庵内的18尊罗汉塑像,重彩描绘,色泽古朴明快,服饰塑造精致,远看疑是丝绸,近看才知是彩塑。陕西蓝田水陆庵壁塑《佛教故事》,场面宏大,内容丰富,为500罗汉和十神王像,罗汉穿插于亭台楼阁建筑之中,构思精巧,塑工细致。石刻罗汉造像如杭州灵隐寺飞来峰诸刻、重庆大足县宝顶J挛崖造像,俱细致精巧,栩栩如生。
高僧像、祖师像如北宋杭州灵隐寺飞来峰玉乳洞六位禅宗高僧像,南宋嵩山少年寺的达磨只履西归图,广州光孝寺元泰定元年(1324)碑绘制的六祖慧能像,四川大足北山佛湾北宋靖康元年(1126)宝志像和僧跏像等。
在中国大众看来,这些罗汉、高僧和祖师像是亲近的、富于人情味的,比起那威严的、高高在上来自印度的佛陀偶像,要亲切得多。从宋元明清罗汉、高僧和祖师造像的相延不衰中,中国佛教偶像才真正从天上走向人间、融入人间。而布袋和尚的形象出现也正顺应了佛教造像转型的潮流。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弥勒图像之所以由弥勒菩萨、弥勒佛的形象转型并定型于布袋和尚的形象,其依据是多方面的,但总体上来讲,契此和尚的原型只是其转型与定型的契入点,而历史、文化、宗教等语境的变迁才是其转型的可能性与定型的必然性。
(责任编辑周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