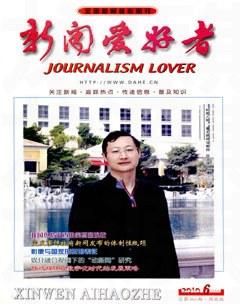公文写作中常见的形式主义文风问题
郑彦离
这里所称的形式主义文风是指公文行文时不注意切合实际和实用效果的态度与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各单位的公文行文总体是走着一条注重实用之路,但也有曲折的情况。“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了我国第一轮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高潮。改革开放以后,全国的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全局务实的风气影响了公文写作,在公文写作中体现了这一务实的时代风貌。然而2005年以来,在不少的中下层单位,却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情况,特别是在一些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文件方面,至2009年这种不良文风的泛滥达到高潮。形式主义文风的泛滥毫无疑问地导致公文效能的下滑,但遗憾的是虽然社会上大多人痛恨这种情况,却很少有人真正努力去做纠正的工作,至今学术界也未见对之的专门研究。
形式主义文风泛滥与公文效能下滑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这种曲折既决定于党的力量与敌对势力的状态对比,也决定于党自身所使用的处理问题的路线、方针,尤其是后一方面对党的事业的发展影响更大。不管党面对什么样的局势,不管其当时采用了什么具体的路线、方针,凡是秉持实事求是精神的,事业就可能获得转机和发展;凡是违背这一精神的,事业就可能遭遇曲折甚至损失。这种经验教训使党的各级领导者有痛彻的体会,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内洋溢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公文中有很好的体现,并由之使公文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良好的效用。但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背离实事求是精神的思潮浸染了公文写作,盲目的个人崇拜思想和狂热的极端片面政治意识充斥并弥漫于当时的公文中,突出特征是几乎每一篇公文不管是否必要与恰当,都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大喊所谓的革命口号。并且这种做法几乎是一种要求,导致几乎人人写公文都照此的局面。至于这种状态的公文到底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效用,能否真正实现公文意图,既不得而知,也难见人去考究,于是形成这种形态的公文泛滥成灾的局面。在这个新中国成立后首轮公文写作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高潮中,由于发出的大多公文没有实在的内容,致使人们不愿对之细阅,公文的有益效能自然较此前的务实公文下滑。“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全国逐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风气,公文写作回到了务实的轨道上来,公文再次成为推动实际工作的有益有力工具,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效能。但是从2005年起,这种状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某些地方的中下层单位,尤其是在其发行的思想政治文件方面,务实的精神逐渐淡漠,虚浮的成分愈益增加,形式主义公文泛滥,至2009年达到了高潮。这新一轮的公文写作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表现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一轮不同,虽然仍有空喊政治口号的成分,但却不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的内容与形式随意,而是不仅行文程序合规,并且内容构成也不违背规范,形式上更是按标准制作。如安排活动的文件,内容中不仅有指导思想,而且活动的具体任务、标准、实施办法、时间安排等正式公文的应备项目全部具备,从表面看,属于内容充实、形式符合要求的文件。但是,现实工作是否确需发这样的文件?它的指导思想看似正确,到底是否符合实际?布置的任务、标准、办法、步骤等是否可行?这些都有待检验。从现实的情况看,某些写文件者着意写成这样的状态,至于这样的文件是否切合实际并产生应有的效益,则并不认真去考虑。因为在他的心里,他的任务就是写文件,写像“样”的文件,文稿审核人、签发人等也不对之细究。收文者对这样的文件简单一阅了之,甚至是一眼扫视了之,然后应付性执行一点,甚至根本不当回事,将之搁置一边。因为他知道,这样的文件没多少实在有用的内容。这种收发方都不太当回事的文件效能可想而知了。但它的确是像“样”的文件,却又是真正的没有实际效能的文件,应算是“高级的”形式主义文件了。这种写作文风应称作“成熟的”形式主义文风了。这大概应算是新一轮形式主义文风较“文化大革命”时的第一轮形式主义文风的“进步”吧!
形式主义文风是社会形式主义作风在公文写作中的体现
公文写作中的形式主义文风不是孤立的现象,更不是凭空产生。一定的行为总是由一定的思想支配的,而一定的思想又是由一定的社会实际影响和激发的。公文写作中的形式主义行为主要与写作人的思想态度有关,而他的这种思想态度又是受社会现实中的形式主义风潮所影响的,否则他得不到社会的容忍,没有生存的土壤和施展的环境。
“文化大革命”时的公文写作中的形式主义文风是当时社会形式主义作风的一种反映和体现。不管恰当和有用与否地引用毛泽东语录,正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到处滥引毛泽东语录的一种表现,我们现在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盲目的个人崇拜。所谓个人崇拜,应是十分崇敬的意思。认为毛泽东思想正确,崇敬毛泽东个人,应全面认识毛泽东,把握其成功的本质,认真分析毛泽东思想组成部分的各具体言语发出时所针对的情景,研究其适用情况,真正按其原理办事,而不是断章取义地滥引。这种滥引,既是盲目的崇拜,也是偏重形式上的崇拜。至于公文中的滥喊政治口号,也是当时社会到处狂喊政治口号的一种反映。当时的本来精神是“抓革命,促生产”,但实际作为却是满眼“抓革命”,难见“促生产”,所以这种“革命”实际是空头政治,也就是形式主义的政治。2005年以来的第二轮公文写作中的形式主义文风泛滥,是这几年一些地方和单位流行形式主义作风的一种结果。这几年来,一些地方和单位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热衷于搞哗众取宠的没有实在价值的活动。工作明明应是能做多少做多少,却偏要凑一个数字,而且可能每年都是这个数字。每年的客观情况本来是不一样的,不同年份却执意做同样数量的事,使人不得不怀疑其到底是勉力而为,还是在做数字游戏。特别是搞那些没有实际内容和意义的活动,有布置,有检查,布置当然要发文件,检查则主要不是查活动的实际成效,而是检查有无该方面文件材料,评价结论主要凭文件材料齐全与否来定。至于文件的内容如何,是否切合实际与产生成效如何,甚至是否有成效则不考究。这些被检查的单位本来知道搞那种所谓的活动没有实际价值,且可能削弱实际工作,于是在上级布置时应付性接受,到上级检查时以虚空的文件材料来应对,无材料或虽有但不齐备时,匆忙补做,结果形成了做假文件材料的怪象。对这些假文件材料检查组虽心知肚明却不点破,甚至作为符合检查指标的证据,没有补做达到齐全的则以不符合要求评价,这自然助长了做假文件材料之风,形式主义文风的形成与泛滥成为必然。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单位的活动设计看起来相当周密而充实,从组织领导,到具体活动内容安排,再到责任划分,都十分明确,但就是没有真正地与实际工作挂钩,没有实在价值意义,以至于群众讥之为“认认真真走过场”。这种一些地方和单位的自上而下的普遍的形式主义活动做法,无疑刺激并助推了公文写作中的形式主义文风更加泛滥和严重。
还要特别说明的是,形式主义文风的形成与泛滥和这几年社会上流行的一种不良做事风尚有关。这种不良做事风尚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圆滑。遇事不触矛盾,说话绕过来绕过去,就是不涉及真正的实际,不表明自己的真实意见,不提出解决问题的真正有用的办法。因为这样可以不伤及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利益,不树敌,不得罪人,也不会落下可能经实践检验自己不对的把柄,免得事后承担责任或丢面子。体现到公文上,就是写作时回避矛盾,不明确责任,不写有实际意义的内容。但公文有时又是必须写一定内容的,于是以空话、套话充任。其二是偷懒。偷懒不是明目张胆的不做事,而是投机地做事,尽可能少地投入与付出,但也不让人看出偷懒的迹象,这样自己还能获得期望的评价与报答,与时下流行的“装忙族”的做派和心态相似。反映在公文写作上,就是抄袭别人现成的公文内容,而不是真正调查所写公文应对的现实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思考,提出有效的处理办法,只是做出一个公文的样子。这两种做事风格表现,从本质上说也是做人的风格和品质体现,从工作的角度看则是工作作风的展现,属于形式主义作风的类型,它也实际引发了公文写作中的形式主义文风的生成与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