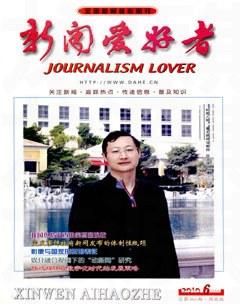读《中国新闻社会史》有感
李 漫
初读李彬老师的《中国新闻社会史》大约是在2007年冬,其后此书迭经裁汰增订,数易其稿,光目录就精心修改了多次。这次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插图版第二版面世之后,又读一遍,有些所思所得,虽不见得成熟,却是由这本书所激发的,因而借此机会略作一粗疏的清理。
对于这部书,作者枕典席文孜孜趷趷,用力之勤恐怕在其所著诸书中最为突出。该书第一版即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与最新一版插图本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的差异之大是一目了然的。除了图片、排版、文字校对等编辑事务的精益求精,除了对史料的挖掘增补、锦上添花,除了作者一贯的晓畅通达而典雅剀到的叙事风格……笔者关心的则是增补史料之外,删除了什么?为什么删除?并且除了这些删除和增补外,什么才是这本书真正的意义所在?或者说,作者以搏虎之力而擒羊,究竟背后有何深意?因为,如果仅仅把《中国新闻社会史》看做一本叙事生动的新闻史教科书,想来对于花了如许精力的作者而言,是并不能满意的,也是不客观的。虽然作者自己说:“严格说来,本书既不是专著,也不是教材,而是一部根据授课内容记录整理的讲稿。”事实上,真正的课堂讲授和将讲授内容写成文字,其实是两种工作。正如利科所说:“‘写把‘说的偶然性去掉了。”显然,作者这么用心去做这本书,绝不简单地只是为了在众多新闻史教材中再添一种选择。因此,不管这个文本是学术专著,还是教材,或者两者都不是,都无关紧要,文本本身的独特性是什么,它存在的意义才是我们所要探讨和追问的。也因此,对于这个“既非专著又非教材”的独特文本,这篇“读书所感”同样既不会是一篇非常学术性的问题讨论,虽然毫无疑问会涉及学术性的话题;也不会是一种非常感性化的好恶表白,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有主观的判断。所以,毋宁说这篇阅读感想,正是一个读者与该文本所进行的午夜倾谈式的对话。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从这部书的第一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以下简称上交大版)到插图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以下简称插图版),再到最新出版的插图版第二版(以下简称插图第二版),到底哪些内容被删除了?或者至少说在目录上被删除了?对于一个诠释者而言,删除的恰恰是最值得注意的东西之一。按照诠释学派的观点,一个文本产生以后,文本的生产者对文本的诠释并不天然具有权威性。多重的解读可能会揭示原文本更多连作者都没有想到的意义。那么在这个视野里,我们可以认为,该文本其实是三个独立而又相关的文本。因为每一个文本都有其历史阐释的意义。不能简单地将它看成一个文本的修订完善。如果将它们合起来读,并作简单比较,会得到与分别读每一个版本不同的体会。庶几可以体味作者这一写作过程中的心境变迁。
从上交大版到插图版,再到插图第二版,变化最大的有两章,一章是“范式嬗变:横看成岭侧成峰”,一章是“文化政治:放眼全球谈新闻”。“范式嬗变”在上交大版中作为专门的一章,到插图版就没有了这一章而是被隐入文中,但同时插图版比上交大版中多了一篇代为序言的论文“‘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以及“文化政治”这一章;而插图版到插图第二版又将这篇代序和“文化政治”这一章也都隐去,内容散入文中。这显隐之间有什么秘密?难道仅仅是编辑技术上的原因吗?至少笔者的解读是否定的。目录可以说是一本书的骨架,目录的变动就意味着书的结构的调整。对于这种结构的调整,除了叙事学角度的思考之外,笔者更关注的是其历史哲学角度的意义。
我们应该暂时不考虑书中展现出来的精巧叙事的能力、文采飞扬的表达和旁征博引的学识,因为这是作者一贯的风格。那么,这样看时就会发现:该书第一版即上交大版的亮点是“范式嬗变”这一章的内容,应该说它是作者对新闻史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因为作者在这一章里将新史学的观点引入到新闻史的写作中,区别了三种范式下的历史叙事,即:革命化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并将这三种范式在新闻史中各自的特点总结为:“革命化范式突出舆论动员、宣传引导,现代化范式强调新闻自由、思想启蒙,民族国家范式讲究国家认同、专业主义等。”且对这三种范式主导的新闻史各自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反思,可惜由于每个章节的篇幅所限,反思并没有得到深入。对于上交大版而言,民族国家范式似乎是其所依从的范式,以此来将自己区别于一般“教科书”新闻史和官方新闻史所具有的革命化范式的倾向,以及一般“公共知识分子”新闻史和“自由派”新闻史所具有的现代化范式的态度。但是作者此刻同时也在思考和忧虑的是,这三个范式的共同特点都是西方的线性历史观。如何才能“真正把中国传统自身的特性纳入考察视野”?而这也正是插图版将要做的工作。
在讨论插图版之前,需要指出,在笔者看来,这三种范式的划分,本身是有一定问题的,如果不说是“范式”而说是叙事、方式、修辞等,可能更妥当。因为按照库恩所谓的“范式”概念,这三种“范式”只能算是两种范式:政治化范式与非政治化范式。因为无论是“革命化‘范式”(毋宁称为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是一种政治化范式。正如书中所概括的“革命化范式强调宣传,现代化范式突出自由,民族国家范式讲究认同”。宣传与自由、革命与改良(现代化)、救亡与启蒙都是政治化范式。而民族国家范式,其实质就是国家化范式,是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范式。因此这三种范式(叙事)的前两种是政治立场相反的政治化叙事,但它们的相反相争正合了库恩范式的定义:观点不同却遵循同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反映在新闻史的范式上就是政治立场。前两种“范式”虽然政治立场相左,但都一定是有政治立场的,这是前提。然而民族国家范式(这个名称也许换成国家化范式更妥当)在本质上其实是取消政治立场的,在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之前,没有政治上的善恶。不过,在分析新闻史的叙事时,用这三种“范式”来归纳,显然要比用政治化与非政治化范式来归纳要清晰很多。只不过范式这个词用得不够准确。但是在范式已经被滥用得失去原意的情况下,就权且继续沿用“范式”这个词吧。
插图版的问世,表明作者多少意识到了上述问题的存在,而且并不满意于依从本质上是非政治化的“民族国家范式”的新闻史叙事,因为可以看得出文本的内容的确是有比较鲜明的政治立场的。因而,很自然地,本来就已经有很大意义创新的“范式革命”的一章在这里却被大刀阔斧地芟除,将内容化入第五章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版本中,添加了论文“‘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代序,通过这篇论文明确提出了这个插图版的书写目标是:社会史范式与叙事学方法相结合。将社会史范式引入新闻史写作,无疑也是一项值得注意的创新。而这种引入才使得这本书的题名《中国新闻社会史》真正具有了社会史的意味,这是上交大版所不具有的。更重要的变化出现在插图版的第六章,即“文化政治:放眼全球谈新闻”这一章。将文化政治作为一章,是很醒目而且具有深意的。对于没有政治立场的新闻史叙事,即非政治化的“民族国家范式”的新闻史叙事,作者在这个版本中也刻意想要避免受其影响。因而,特意添加了文化政治这一章。在这一章里,着重讨论了去政治化的现代政治社会中,如何重塑政治的、文化的权力与信心。抵抗这种名义上非政治化、本质上政治化,正是插图版的意指所向。而这种将政治(文化政治)的重要性以书中专门一章的形式,更显示了作者对这个问题尤其的关注与忧虑。寄希望于激起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此通过争取“文化领导权”来转换西方的线性历史观对当代中国历史叙事的宰制。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插图第二版的目录中竟又取消了序言和文化政治这一章,而将原先的“风雨苍黄”和“红日初升”两章经增补各分为上中下三章。乍一看目录,作者似乎将自己的立场取消了,采取了非政治化的叙事模式。然而,细读之后才发现,在全书的各个角落,似乎都回响着一种犹如呢喃独语的声音,一刻也不停地激发着读者去思考,什么是中国历史,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虽经数千年的沧桑沉浮却始终“其命维新”的原因何在。在阅读中,读者如果不自我提醒一下,几乎会忘了这是一本新闻史学的论著。就像是通过一位名叫“新闻”的导游来阅读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来阅读中国社会,来阅读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和奇闻逸事。这本插图第二版,在完全延续了插图版以社会史的范式与叙事学的方法来写作的特色之外,又增加了一种特色,那就是历史/政治观的进一步“内在化”,然而却是一种一目了然的内在化。将政治观与历史哲学观,用叙事学的方法,春秋笔法的论述,蕴涵在更容易让现在的年轻读者们接受的文本中,使得他们在获取技术知识的同时也得到了价值判断的能力。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篇代序被删除了,因为社会史范式的提出,是与政治史范式相对应的。政治史范式从上到下的视角、关注历史趋势与总体结构,与之相反,社会史范式则关注从下到上的视角,关注历史细节与个体经验。然而,可以看出,虽然在文本中一位位具体新闻人的个体经验鲜活地表现了出来,一个个独特而重要的文本重新得到展示,但《中国新闻社会史》仍然是一部从上到下的历史论述,这里新闻史的解读仍然没有脱离试图对结构变迁的把握和描述,因而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一个社会史范式的论著。因而将这篇代序言删去,也许就出于这种考虑。但是社会范式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整体观与通史观使得文本自身具有了单纯政治史范式的论著所不具有的独特魅力,那就是在描述历史迁演的同时,展示了一幅活生生的历史社会画卷。作者一再引用钱穆所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在这一文本庶几得到了作者个体性的实践。
插图第二版同时被删除的文化政治这一章,事实上其核心观点早已化为青烟散入字海。虽然没有独立成为章节,但是对于文化政治的关注,对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取,对于文化自觉的激发,对于文化自信的培养,书中比比皆是,甚至大段的表述也随处可见。因而要不要这专门的一章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能将其本质得到传达,所谓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此之谓欤?因而,序言和文化政治这一章的取消并非一种非政治化的表现,而是出于一种修辞学的思考。从非政治化到再政治化,再下一步如何走?再政治化的方式分两种,一种也许可以用施特劳斯所说的“显白的教诲”来作比喻,施特劳斯常常引用伏尔泰的一句话:“勇者的天命就是将他的所思所想自由地表白出来。”这种直白的表达是坚决而明确的,如阳光一样烛照人心。另一种也许可以用歌德所说的“音韵袅袅”来作比喻,歌德有咏月诗曰:“你洒入丛林与河谷/静默而迷朦的清晖/而我的灵魂/化为清光把你追随。”这种让人不知不觉的温和,如月光一样润泽灵魂。这两种方式,这本书似乎都有所采用,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以歌德的月光式体现出来。
因而,也许我们可以作一个不恰当的概括,《中国新闻社会史》的文本所体现出来的符号实践,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文本自身成长的历程:由对新闻史普遍存在的两种政治化(革命化与现代化)的现状不满意,而产生了一个非政治化倾向的文本(民族国家范式的上交大版);继而由于对上交大版的非政治化倾向的不满意和对“为什么不能政治化”问题的再度思考,文本转向了“新新闻史”的实践(插图版),即社会史的范式加上叙事学的方法,然而社会史的范式不足以容纳文本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视野,因而“文化政治”这一章便自然(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而突兀(文学与史学叙事意义上的)地出现了,文本再度政治化,以一种“直白的”方式;然而在政治化仍然被庸俗地理解为官方的,“文化大革命”式的,意识形态化的,宣传的,愚民的(或者将与之相反的自由主义政治化理解为启蒙的、客观的、真实的),而非政治化与政治化的界线已经模糊不清的时候,伏尔泰式的勇者是无助的,而且关键不在无助而在无效,因而,序言与文化政治这一章又自然(文学与史学叙事意义上的)地消失了,不,毋宁说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以一种更具史学修辞特征,而更有自信的方式存在着了。因而这个文本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恰恰体现在这个似乎不重要的目录——结构的变迁之中,以自身的成长和变动来实践了作者本身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插图第二版)。然而作者的思想究竟如何,只能用王维的一句诗来描述了: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
对话总是有可能出现三类情况,意见不合的争论,相见恨晚的畅谈,以及各说各话的二人独白。笔者学力尚浅,又强作解人,无疑是不能具有与该文本争论或畅谈的资格和能力的,也许这篇读后,仅仅只是一种独白。但这种独白也是一种解释,它至少说明了文本对笔者的言说引起了笔者对它的一种言说,这种言说的存在是由于文本的存在,即便对于文本而言是不相干的,它们二者之间也事实必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