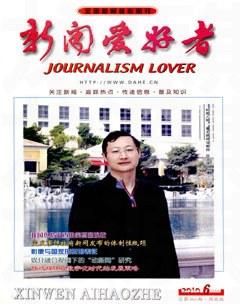民意和司法的冲突及对策
王焕平
民意和司法相对独立、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两者能否实现良性互动,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相互纠结冲撞,使得民意和司法的冲突如此凸显,以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关于冲突的成因及解决对策众说纷纭,相互激荡。综观之,笔者认为,任何社会问题的形成都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认识和解决热点、尖锐的社会问题不能抛开对复杂社会现实的拷问和综合治理。化解民意和司法的冲突也是如此。
民意和司法冲突的现实性
民意和司法的冲突,是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张力与司法不力的冲突,是众多社会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和典型代表,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现实性。
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与法律知识不足、规则意识缺失的冲突。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快速推进,民众参与司法活动的程度不断提高,民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觉醒、高涨。面对突发案件、热点事件,显示出了空前的参与热情。他们通过媒体发表对事件的看法与处理观点,甚至自发组织起来,去探明真象,并希望他们的行动、观点能影响事件,使事件能顺着他们的愿望得以圆满解决。然而,由于法律知识的局限性、对司法活动的非专业性理解,使得他们的观点朴素、感性、情绪化,于是出现了他们的意愿与司法的冲突,这是非专业的理解与专业化司法追求间的冲突,更是民众法律意识的觉醒、法治愿望的高涨与自身法律知识不足、规则意识缺失的冲突。
彭宇案中,不少民众都认为,好人就得有好报,做好事还得赔钱就是不合理,做了好事还赔钱,以后谁还做好事;邓玉娇案中,舆论一边倒,认为身为官员竟强迫良家女子卖淫,死有余辜……民众从道德感情出发,去评判案件,至于法律的规定、案件的细节,等等,在民众那里似乎并不重要。而司法机关要去搜集案件的证据,任何细节都不放过。法官更是要让证据说话,通过案件证据的认证质证进行推断,依据相关法律进行判断,还要考虑判决结果对规则形成的深远影响。很多时候,正是公众缺少这种专业的法律人的思维,缺少对判决结果的规则意义的认识,缺少对法律保持刚性的社会稳定价值的认同,不懂得因法律的刚性而造成个体实质不公是实行法治付出的必要代价,而这种不公也是完善法律的动力之一,才肆意宣泄愤怒,甚至不顺其意愿改变司法审判结果决不罢休,从而使得民意与司法要义剧烈冲突。
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与法律不健全的冲突。这使得他们对法律知识极端渴求。并努力用所学法律知识去评判案件。当法律的不健全伤害到他们的公平心理时,他们愤而鼓呼,向司法施压,从而造成司法与民意的冲突。
许霆案中,民众认为,许霆利用ATM机的漏洞“取”了17.5万元就被判了无期徒刑。而那些令人厌恶的、祸国殃民的贪官贪了几百万上千万甚至几个亿,也不过判了十几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缓。两者相比较,法律对许霆太不公平,法院判决太不合理。于是,对许霆的一审判决在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而且一浪高过一浪。任何对案情的分析,只要对许霆稍有不利,都会招致围攻与谩骂。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法院不得不启动特殊程序,对许霆案进行了重新审理,改变了一审判决。许霆的父亲公开对媒体表示感谢。该案也被称为媒体的胜利。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我们既没有健全的法律可遵从,又缺少敬仰法律的民意来支撑,问题的出现就可想而知。许霆案的判决结果,与其说是媒体的胜利,毋宁说是偷盗与贪污、受贿在定罪量刑上存在着不协调问题的反映,是立法对ATM机等新事物过于迟钝的反映。因而是缺乏引领的民意与不健全的法律的冲突,是法律不健全条件下审判对民意的回应。
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与官方权力傲慢的冲突。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使得他们要求政府行为公开、透明,给他们以知情权。一旦知情权遭到忽视、冷落,他们就会通过自己可以借以使用的渠道,表达不满,并穷追不舍,寻求真相。“70码”案、邓玉娇案、躲猫猫案……之所以从普通的刑事案件发展成为沸沸扬扬的公共事件,无一不与公众知情权被官方忽视、冷落有关。
“70码”案中,官方显然低估了民众的智商,认定的车速70码,与造成的伤害结果不相称,于是公众展开质疑,迫使民众眼里的官方,也就是相关权力部门对胡斌车速进行了重新界定,改变了70码的说辞,还以“84.1~101.2km/h范围”;邓玉娇案中,警方的草率定案,可以说是对公众知情愿望的践踏,于是公众对以强欺弱谴责、对案件细节“较真”,让案件步步逼近真相;躲猫猫案中,官方对民众知情权的忽视,用傲慢至极都不为过,于是“躲猫猫能让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撞死?”“太离奇!”民众恼怒,不懈追问,终于揭出牢头狱霸行凶的事实……凡此种种,都让人觉得官方是在保护某种利益,因而暧昧,不够坦荡,甚至是傲慢。
民意与官方的这种冲突让司法面临窘境,人们对案件真相的怀疑足以影响对案件判决结果的信任。胡斌案审理中,人们对法庭上的胡斌是不是胡斌真身的质疑,就颇值得民众眼里的官方反思。
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与媒体约束不力的冲突。随着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他们获取法律知识的愿望,以及遇事寻求救济的积极性前所未有。通过媒体学法是民众获取法律知识的重要途径,而借助媒体造势,赢得关注,以向官方及相对方施压,被众人认为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在不少人看来甚至是最佳途径。这使得媒体在公众心目中,就主张权利而言,有着特殊的地位。媒体从自身赚取民众关注,吸引眼球,留住读者的利益出发,也乐于维护并不断强化这种地位。
媒体这种特殊地位的存在,在普法、维权方面确实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少可圈可点的作为。但一些媒体自律性的缺乏,一些编辑、记者法律知识的不足、法律意识的淡薄,加上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外部约束的不到位,致使“媒体审判”频频出现。案件还没到法院,法院还没审理,或正在审理还没作出判决。“杀人犯”“贪官”“获刑”之类的词,一些足以引起震撼、影响公众情绪的判断,就出现在报道里了。黄静案中,有媒体直接论证黄静男友就是杀人犯,甚至鼓励黄静家人将此论证结论进行到底,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是黄静男友杀人证据不足,杀人事实不能成立;“70码”案报道中,《富家子弟把马路当F1赛道,无辜路人被撞起5米高》的标题很有心思,“富家子弟”对“无辜”,“马路”对“F1赛道”,加上“被撞”与“5米”的叠加,把富人的飞扬跋扈,没钱人的无奈、惨状,烘托得淋漓尽致,很具有引导舆论、制造轰动的功能;梁丽案中,有媒体的报道标题是这样的:《清洁工“捡”14公斤金饰或被起诉》。“清洁工”、“捡”、“起诉”这样一串词的运用,让读者产生一弱者、无意还可能会被判刑之感,骤然关心起弱者无意间导致的前途起来,很具有对案件定了性的嫌疑……在日常报道中,上述现象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这种带着民意面纱的炒作,无疑使司法审判的压力变大。现实中常常有这种情况的发生:面对“民意”压力,一个案件的判决,若听了民意,专家、专业人士不干了,对法院、法官一通指责;遵从了法律,民意不干了,对法院、法官一通围攻。法院如此左右不落好,但却没有看到监管媒体的相关部门有所反应,进而从追求法律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可预见性,以及民众对法治的信心的高度出发,对炒作,尤其是恶意炒作有个说法,约束制止。
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与“前腐后继”的冲突。这里所说的腐败,不单指存在于公、检、法系统的吃、拿、卡、要、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还包括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贪污腐败、腐化堕落,乃至失职、渎职等。正是这些腐败现象的屡打不止,使“官方”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民意对个案愤怒的背后,是对腐败作祟的怀疑,和“替罪羊”式的发泄,和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
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中,对犯罪嫌疑人以嫖宿幼女罪的认定,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网民把检察院以嫖宿幼女罪提起的公诉,“官官相护”,说成是“当官就可以轻判”。案件判决后,北京大学一专家发表文章,从法律创制角度,依据法律相关规定,阐明法院的判决是恰当的、正确的,旋即引来不少网民的围攻、谩骂,质疑专家是为谁服务的,说该专家是“说客”、“传教士”、“呆子”。不仅热炒的涉“官”案遭遇类似,还有热炒的涉富案、涉贪案、涉强弱案……热议中无不透出民众对腐败作祟的担忧。其实,正是现实中腐败的存在,给了民众联想、质疑的空间。也正是对官腐的愤怒将民意的不满推向高涨,聚焦在一个个个案,把长期激发的对腐败的愤怒,集中于一个个具体的被告。不仅被告成为“替罪羊”,在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罪责的同时,也为众多之前未被清算的类似案件、类似罪行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任何对案件的探究,只要不顺“民意”,作者就会被“民意”当成“坏蛋”“帮凶”。这里,司法审判的结果也未能幸免于难,有时要在民意的胁迫下为腐败埋单,否则,就不能平民愤。
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与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冲突。关于司法含义有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司法”有广狭两义:广义上的司法包括审判、检察、侦查等国家权力的运作行为以及仲裁等“准司法”活动,只要是把书本上的法用于实际生活均为司法;而狭义的司法则指审判、检察机关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
这里,之所以阐述司法含义,是因为,在笔者看来,谈司法公信力用广义的司法概念更为有利于理解现实中民意与司法冲突形成的原因,也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换句话说,就个案展开的司法活动而言,只有侦查的案情翔实、检察起诉内容扎实、判决适用的法律准确,才能使案件的判决结果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赢得公众的信任。令人遗憾的是,在整个司法活动过程中,除了腐败现象的存在、行政权力的干扰、办案过程透明度的不足、民众参与度的不高、司法从业者素质的低下,等等,都使司法的公信力受到挫伤。正是公信力的不足,让民众产生了强烈的自救意识,采取了高涨的自救行为,使民意与司法的关系变得紧张。综观成为公共事件的诸多案件,其中不少案件都是民众从质疑侦查结论开始,聚焦拷问检察起诉的证据和罪名,从而不满或怀疑判决结果的公正性。
化解民意和司法的冲突需综合治理
面对司法面临的困境,有人说,法官要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内心对法律的敬仰,不被舆论所左右,以维护法的权威;有人说,法院要不断提高公信力,让案件办得公平、公开、公正;有人说,要改革司法体制,破除非法干预;有人说,要完善法律;还有人说,在现有体制条件下,无良方法,法官遵从自己的道德底线吧……笔者认为,民意和司法的冲突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交织的结果与反映,应作为系统工程,从复杂的社会背景出发,综合治理。
完善法律。虽然法律具有稳定性,而现实是多变的,立法永远不可能和多变的生活保持同步。但并不表明立法可以对生活过于麻木,尤其对一些已成社会问题的焦点问题,立法应保持足够的敏感性,及时作出反应,以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加强普法。“五五”普法虽然成效显著,但构建法制社会,普法任重道远。普法应不只是停留在让大家懂得一些法律条文,知道依法维权,更重要的是培养全社会的法制氛围、法律敬仰、规则意识,让人们明白法的思维规律,明白为了公共的规则,个体可能付出的代价。
惩治腐败。腐败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公信力。人们对腐败的不满一旦聚集于一点,其势可怖,政府惧之,何况法院?很多时候的事实是,政府迫于民愤压力,施权法院。在现有体制下,法院不能不听命于政府,于是民意审判得逞。因此,应加大反腐力度,给审判一片蓝天。
媒体监管。媒体常常说,没有监督的权力,容易腐败。这也同样适用于媒体自身。自律可用,但不可靠。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就本文的本意来说,就是要给“舆论审判”一个说法,对其有所监管,有所约束。
侦查缜密。案件侦查是起诉、审判的基础环节。缜密侦查、及时向社会进行案情通报,无疑是民意的期待,也是化解民意不满所需要的。从现实看,这个工作做实了,做到位了,可以把很多民愤化解在萌芽状态。
公诉准确。公诉对侦查和审判这两个环节起着制约作用,公诉工作做得越扎实,越有利于案件审判的顺利进行。公诉应有力、有理,并公开、透明。
审判阳光。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民意的检验,因而是阳光的审判。法官要不断提高适用法律的能力、吸纳民意的水平,办出阳光的案件。
(作者单位:人民法院报社)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