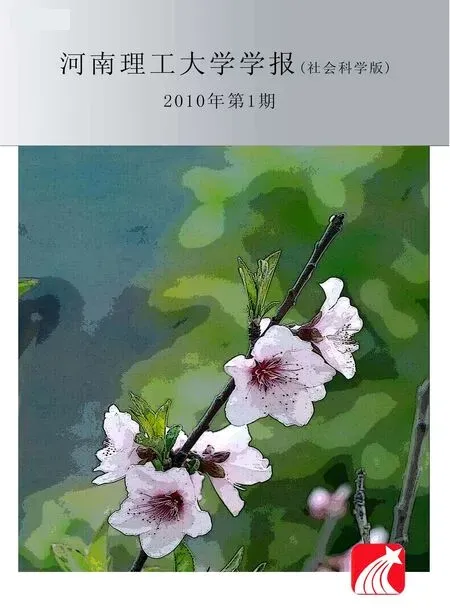山 涛 故 里 调 查
程 峰,李敬平,申华岑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覃怀文化研究所 河南 焦作 454001)
山 涛 故 里 调 查
程 峰,李敬平,申华岑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覃怀文化研究所 河南 焦作 454001)
采取田野调查和资料分析的方法,考查了山涛的故里武陟县西小虹村的历史文化,分析了山公墓祠的碑刻资料,走访了口头文学的传承者,收集了一些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厘清了一些历史史实,为学术界深入研究竹林七贤的游历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山涛故里;西小虹村;山公墓祠
山涛(205-283年),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据《晋书·山涛传》记载,山涛的籍贯在河内怀县,即今天的武陟县大虹桥乡西小虹村[1],学术界对此没有异议。为使读者和学术界对山涛的籍贯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也为了考察竹林七贤游历地的基本情况,本课题研究人员多次调查了山涛故里,并将收集到的一些资料和故事以论文的形式公布出来,以期为学术界提供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一、西小虹村厚重的历史文化
西小虹村位于武陟县城西南的17公里处,北望太行,南临黄河,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以来,西小虹村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并且是人才辈出。
西小虹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基本上体现在文庙、隆寿寺等庙宇的修建以及众多的碑刻上。文庙即孔庙、夫子庙,是我国封建王朝祭祀孔子的场所。一般而言,古代的州县皆有州学、县学,州、县学又皆为文庙。因此,文庙在中国古代具有双重功能:一为祭祀孔子的场所;二为州、县学的学堂。不过,在古代,一些文化根基深厚的村落也建有文庙,西小虹村就是一例。西小虹村文庙创修的年代虽不清楚,但它毁于日本侵华时期却是众所周知的,而文庙的一通石刻《三教图碑》所体现的西小虹村三教合一的文化特征也与覃怀地域文化特征基本一致。另外,从西小虹村的《杨津尊敬图》、《刘宽和睦图》、《秦公生祠记并像赞》、《玄帝像题识》、《白衣大士像题识》、《十八子游山图题识》石刻来看[2],西小虹村的历史文化确实厚重,出现过一些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最具代表性的是魏晋禅代之际的“竹林七贤”之一山涛、明代崇祯年间(1628-1644年)的周万书及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年)的王化鹤。周万书,号鹤台,著名书画家,生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卒于崇祯末年;著名的书画作品有《白衣大士抱小淳》(周万书后人周有中家存)、西小虹村文庙的《三教图》、妙乐寺的《释迦牟尼像》、东小虹村的《祖师吹风》、武陟老城的《关公勒马听风》、西小虹村山公祠的《魁星踢斗》,等等。关于王化鹤,清代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怀庆府志·人物志》记载:“王化鹤,字六翰,康熙丙辰进士,任翰林院编修。甲子典试云南,有得人之誉。性至孝,母病,汤药必亲尝,衣不解带者累月,居丧,哀毁骨立。岁饥,倾资捐赈。大虹桥渡口设义船,捐地养给,榜人至今便之。卒,祀乡贤”[3]1023。

二、山公墓祠
关于山公墓祠(平面分布见图1,图2),清代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怀庆府志·舆地志》载,晋山公墓“在县(武陟)西二十里小虹桥村。……明弘治七年(1494年),建庙祀焉”[3]193。清代道光九年(1829年)的《武陟县志·古迹》亦记,晋山公墓“在小虹桥。明弘治七年(1494年)奉文修理”[4]808。“山公庙,在小虹桥山公墓前。明弘治二年(1489年)奉文重修”[4]764。《焦作文物志》也载[5]:山涛墓,位于武陟县城西南17公里大虹桥乡小虹桥村中,原墓冢高4米,南北长25米,东西宽20米,面积500平方米,1966-1976年之间逐渐被夷平。墓前原有碑刻数10通,其中明代嘉靖五年(1526年)知武陟县事毛验所立的碑刻通高1.78米,上刻双线楷书“晋侍中吏部尚书山公墓”;清代钦加运同衔署武陟县事骆文光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所立碑刻通高1.78米,楷书“晋侍中新沓伯山公之墓”。山公祠之拜殿内,存重修山公祠碑记9通,

记述山涛籍贯、生平及死后葬于此地的史实。山公祠位于墓前,东西宽60米,南北长70米,占地为4 200平方米,现存拜殿、东西配殿等4座古建筑。山公墓与其父、其子孙、其女等12座墓葬组成山公墓冢群(图2)。
关于山公墓祠的整体状况,负责看护山公墓祠石刻的村民王新顺先生(曾担任西小虹村党支部副书记30多年,多次参与焦作市、武陟县文物部门对山公墓冢的调查,掌握有大量的文字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山公墓祠平面分布图(图1、图2)。王新顺先生所提供的山公墓祠平面图极其完整,但现实却是残缺的。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山公墓只是2平方米左右的一个小土丘,比周围高出仅0.5米左右,这也与千平喜同志《山涛墓祠》一文中“山涛墓坐北向南,东西20米,南北25米,占地500平方米”[6]129的记载截然不符。
王新顺先生还介绍:山涛去世后,朝廷出资修建山公墓祠,其后历代均有修葺。清代以前的重修缺乏历史记载,现仅存康熙(1662-1722年)、道光(1821-1850年)、咸丰(1851-1861年)、同治(1862-1870年)年间重修山公祠的部分碑刻。民国21年(1932年),山公祠各殿塑像被拉倒,山公祠改成学校。由于灾荒、战乱等原因,学校时办时停,直到1949年后才又恢复生机。至1965年,山公祠各殿、山公墓冢依然存在。“文革”开始后,山公祠各殿和墓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973年,山公祠东西两厢房被拆除;1997年,拜殿也被拆除。山公祠原有一口大钟,高约1.5米,口径约0.9米,钟钮为虎头,1958年大办钢铁时被投入炼铁炉焚毁。“文革”中,由于山公墓冢被视为“四旧”之列,其墓冢之土陆续被村民拉走垫了地基。
三、山公墓祠碑刻
据王新顺先生介绍,仅在原来山公祠的拜殿之中,就有10余通碑刻,如今已所剩无几。山公墓祠现存石刻9通,其中5通散置于院内,另外4通碑刻集中镶嵌在影壁墙上。由于镶嵌于墙体之内,仅能看到碑刻的一面(石刻的阳面)。
(1)《重修山公庙碑记》(影壁墙左四)。石刻高1.35米,宽0.57米。碑文曰:
从来祀典之设,匪徒隆庙貌以餙(按:当为“飾”,即“饰”字)观美而已,盖所以崇先贤而昭劝勉也。故士生两大间,其德业闻望,苟不足以推重于当时而垂范于后世;毋论穷居下寮,即势位赫奕,亦殁则已耳。或间有传者,甚且从而议之诋之矣,亦安能使千百世下上之人,按籍稽名,考其里居,永隆其享祀;下之人因名征实,慕其行谊,想见其为人,历久而弥显,声施无穷哉?以是知后人之祀先贤,固后人之隆礼先贤也,亦先贤之灵爽实有以凭籍乎?后人而崇祀自不容己(按:似当为“已”字)也。如吾乡之有山公祠,由来旧矣,其重修则见于弘治、万历。在弘治者,建奉朝敕,祀典隆重,彰彰前碑已;在万历者,仅得诸栋上之书,且剥落不可读,岂前人之怠忽从事,以改(按:当为“致”字)考征无由欤?抑费资无几,故略而不载欤?忆余总□时,家居湫隘,尝随伯大人学慱公、叔大人太史公读书,其中每友生道,故握手同览,慨夫风雨漂摇、鸟鼠喙啮,百年之间,颓然徒见瓦落而墙圯,未尝不有志修葺而特恨力未逮也。岁乙亥,乡之人聚族而谋于余曰:“招提梵宫金碧辉煌,先贤瓦屋不蔽风雨,是为吾子忧。”余曰:“唯唯。”又曰:“春秋祀戊,饩羊徒存,栋宇不餙(按:当为“饰”字),将就蓁莽,惟吾子图之。”余曰:“唯唯。”又曰:“宜旧者仍,宜新者增,即故为功,永妥先灵,讵异人任哉?”余曰:“唯唯。虽然,经之纪之,固存乎?余醵金鸠役尚需乎众。”于是乡人皆首肯,踊跃鼓舞,辑薄登名,将十之五者捐赀吾家,十之三者勔输村人,其余则广募化而统□(按:合“力左”为一字)成焉。肇始于乙亥十一月,落成于丁丑四月,约费朱堤百陈力布金并锓碑阴。其年秋,余叔候选州佐公讳化鹓又重修寝宫。越三载,辛巳,余叔太史公官京邸,亦捐俸即拜殿之旧制而完葺焉,前后一新,焕然改观。既成,乡人嘱余为文以记之。余观公在泰始中,甄拔人物,各为品题,拟而奏之,时称山公启事。善乎,李青莲之言!曰公“作冀州,甄拔三十余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则其为冢宰,典铨政且十余年,所举更不知几许矣。其以人事君,视夫后之嫉贤妬能,相距何如也!当其寄迹竹林,诸贤以材,公以识度,虽纵情皆礼如籍,箕踞而锻如康,执筹钻核如戎,公皆与之终始无间。至今读嵇叔夜书云“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则其度量恢宏,无所不容,更何如也!若夫以释吴为外惧内忧外宁之言,何识之远也!以违礼为不祥、废长立少之论,何见之卓也!其于王夷甫也,何以知其贻误苍生也?非具知人之明,能之乎?其议罢郡兵也,若预见夫永宁之后也;非秉先几之哲,能之乎?至于操履谦冲,与物无忤,虽时事变更而嚼然不染;即运际改革,而物议不加;当上下疑忌之会,而能超然独全。谓非晋室之完人,更属史臣之所不及知耶!余既喜之工成,又乐与乡人道公之事,使吾乡之人瞻公之庙貌,即欲效公之行谊安在,古今人不相及也,斯又余之所厚望也夫。是为记。
峕康熙四十三年岁次甲申秋七月蓂飞四荚之辰
庚午科举人候补内阁中书王睿撰文
岁进士候补外翰王肃书丹
岁进士南阳府唐县儒学训导王庄篆额
王宽刊石
该石刻是现存最早的关于重修山公祠的碑刻,它记载了山公祠在明代弘治(1488-1505年)、万历(1573-1619年)年间的重修过程,以及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年)重修的原因和结果。不过,这里存在一个疑问,那就是本次重修的主要工程完成于康熙丁丑年(1697年),三年后又重修了拜殿,然立碑的时间却是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其缘由不得而知。
(2)《重修山公祠记》(影壁墙左一)。石刻高1.43米,宽0.57米,碑额题“山高水长”。碑文曰:
武陟城西小虹桥村,晋新沓伯司徒侍中山公巨源故里也。里故有祠,不详所始。我朝康熙四十年,怀庆太守刘公维世、武陟县主刘公廷用倡捐重修,载在祀典,春秋飨食。惟谨今百余年矣,风雨剥蚀,庙貌颓然。道光三十年,里东西两社士民等,虑无以妥神灵而起乡人之向幕(按:当为“慕”字)也,谋所以修葺之。既成,属予为记。考《晋史》,公“少有器量,介然不群”,尝与嵇、阮为竹林游,有高世之志。年四十始仕州郡,清操远鉴。晋武帝雅知之,受禅后,宠眷日隆。历官称职而深怀退让,每进秩辄恳恳固辞,不得已而后视事。爵同千乘,室无妾媵,所得禄赐尽散亲族,视富贵泊如也。前后领选事十余年,甄拔人物,各当其才,时人称之。吴之初平也,武帝令天下州郡皆去兵,公独论以为不可无武备;晚值后党专权,公时时讽谏,以为不可专任杨氏。深虑远识,有先畿之哲。其尤不可及者,公遭母丧,爵位已崇,年逾六十,古人不毁之年也,乃居丧过礼,躬负土成坟,手植松柏,慎终如此,色养可知。非至性缠绵固结而不可解,何以能此?由是知公之雅操硕德、彪炳一时而俎豆千秋者,精神之不可没,殆皆孝思不匮之一念有以致之,非苟然也。后之生斯土、入斯祠者,考其行事,慨慕流连不忍去,则幸勿徒羡其富贵之崇高,而深致力于事亲从兄之间,以勿为山公之所弃,则关于世道人心者,岂小小乎哉?斯役也,经始于道光三十年之二月,落成于咸丰元年之十月。至其助捐各姓氏,详载碑阴,俾后之人有所考焉。
赐进士出身前太常寺少卿河内李棠阶谨撰并书丹
皇清咸丰元年岁次辛亥冬十月吉日立石
铁笔闫锡玉
该石刻依然是重修山公祠的碑记,它记载了开始于清代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落成于咸丰元年(1851年)十一月的重修过程,其中追述了清代康熙四十年(1701年)怀庆府太守刘维世、武陟县令刘廷用倡捐重修山公祠的事实。正是自康熙四十年重修之后的“惟谨今百余年矣,风雨剥蚀,庙貌颓然”,才出现了开始于清代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的重修。然而,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所立的《重修山公庙碑记》却没有提及康熙四十年(1701年)怀庆府太守刘维世、武陟县令刘廷用倡捐重修之事。而且,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已重修完成,似乎没有必要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再次“倡捐重修”。一种可能是“康熙四十年怀庆太守刘公维世、武陟县主刘公廷用倡捐重修”并没有形成事实,如是这样,就没有“惟谨今百余年矣,风雨剥蚀,庙貌颓然”的前提。另一种可能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十一月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四月对山公祠重新修复以及后来的续修,本身就是一回事。如是这样,则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所立的《重修山公庙碑记》所记述的时间,无论是修复的时间还是立碑的时间都是错误的,这其中必定存在问题,只是一时无法解开而已。
(3)《重修山公祠规例碑》(影壁墙左三)。石刻高1.45米,宽0.48米,篆额题“典则常昭”。碑文曰:
晋山公涛,字巨源,封新沓伯,谥曰康,河内怀人也。事业载在史乘,祠墓坐落县西二十里小虹桥村,创建不知何代。前明宏(按:当为“弘”字)治七年,奉文重修。其时,府尊出库金八十两,县主鲍公克敏、郭公良各出金五十两,协同城官员暨本村绅耆皆出金助修,每岁春秋上戊奉旨致祭。嘉靖五年,县主毛公验建立神道碑。至国朝康熙四十年,县主龙公待建立碑亭,奉文遵依明制典礼办理。康熙四十年,因庙貌颓圯,府尊刘公维世捐廉八十两,县主刘公廷用捐廉五十两,率劝同城官员及该村王太史化鹤、郭孝廉大受、王孝廉睿等,出金重修。康熙五十一年,刘公又书悬匾对;因二月初二日系公诞日,官为送戏;春秋二祭,一遵定例。至乾隆中年,因大虹桥沁水决口,祭戏遂废。嘉庆五年,县主叶公龙官釐正祀典,祭仪全复。道光五年,县主王公荣陛诣庙致祭,又将诞戏补复,迄今未改。每岁年终,县主奉文查考祠墓,恐致损坏。自康熙四十年重修以来,至今又百四十余年矣;风雨飘飖,庙貌复颓。两社绅耆,具禀道宪、府宪。道宪长大人臻捐廉八十两,书悬匾额一面、对联一付;府尊龚公瑞谷捐廉八十两;余公炳焘捐廉五十两;县主许公赓谟捐廉五十两,并书悬匾额一面。道宪又面谕县主,饬令加函,代启五厅捐廉助修。于是北河厅孙公家良捐廉五十两,祥河厅周公树衡捐廉五十两,曹考厅陆公嵰捐廉三十两,黄沁厅王公绪昆捐廉三十两。此外,怀庆府经历张公文耀捐廉十两,武陟县丞姚公元寿捐钱十千,儒学教谕张公敏政、训导王公懋德共捐钱八千,典史于公湘捐钱六千,黄沁协府时公逢午捐钱八千,城守营任公榜元捐钱二千,武荥把总黄公文成捐钱二千,唐郭汛分防杨公立中捐钱一千五百文,莲花池分防宋公守业捐钱一千文。至于远近乐善好义之士所捐输者,勒于碑阴,以并垂不朽云。
附记县主代函 敬启者:顷奉本道宪谕,以敝邑旧有山吏部祠,山公为晋代名贤,载在史乘。今陵庙倾圯,该首事等鸠工重建。惟是工程浩大,经费无资,不能不藉众擎以助其成。除道宪与本府及谟处酌量捐廉外,饬令加函,给该首事、职员王清祺、生员常丽天,特叩台墀,务祈鹤俸宏施,襄成其事。庶几振高风于千古,有所凭依;行祀事于崇朝,咸深景仰矣。肃函代请。敬颂,升祺!统祈,荃鉴不戬。许庚谟谨启。
钦命河南分守河北兵备道长臻,怀庆府知府龚瑞谷、余炳焘,即用同知知武陟县事许赓谟、典史于湘,率小虹桥东西两社首事仝立石
大清咸丰元年岁次辛亥十月之吉日刊
该石刻依然涉及到重修山公祠的问题,但它主要记述了“自康熙四十年(1701年)年)重修以来,至今又百四十余年矣”,山公祠“风雨飘飖,庙貌复颓”,在道宪、府宪以及各级各类官员的支持下,清代咸丰元年(1851年)完成了本次重修。该石刻还追述了明代弘治七年(1494年)奉文重修山公祠的事实,尤其指出了清代康熙四十年的重修事实,但依然与上述碑刻存在矛盾。
(4)《邑侯骆公捐免 山公祭田粮差记》(影壁墙左二)。石刻高1.43米,宽0.53米,篆额题“流芳百世”。碑文曰:
从来惟贤者能尊贤,惟善者能乐善,不以年湮而少阻,不以代远而或移,此声应气求之定理,而并非矫强于其间者也。晋新沓唐伯山公,启事流芳,铨衡著美,卓识宏猷,彪炳史册,其足以动百世仰止之思者,固不仅为七贤之领袖、一代之弁冕已也。祠墓坐落本村,历年春秋上戊,牧兹土者例以羊豕鼓乐致祭。然因公务殷繁,恒以少尉摄行。今春祭期,贤邑侯骆公躬临于兹,周览冢墓,巡视祠宇,载咨载询,指示多方。越数日,复延东西两社绅耆至署,阐杨(按:似当为“扬”字)山公之勋猷,而殷殷以祭田缺如为憾。村中士庶感公之意,因公议捐置祭田四十七亩零,呈禀于公。蒙公蠲免徭役、捐办粮漕,而以此田应征之课施入祠中,为山公香火之资;详明抚宪钱大人,并令该房注册立案,以垂永久。复捐清俸,为公树表墓之碑,改建祠前后门,使合体制。噫!公之尊贤乐善,岂貌为豪举者所能希其万一哉?方公之由临漳而莅兹邑也,未经接篆之,先即微行境内,潜访民间利弊。凡各村之风俗朴漓、人情良莠,无不了了于胸。以故绾篆以来,兴利剔弊,惩莠安良;帮筑堤防,加镶埽坝;约束吏役,节灭差徭;保障偕茧丝,并懋催科,与抚字同殷;善政仁施,指不胜屈,而尤尊礼。名贤至,不惜捐其鹤俸,匡此鸿模,非所谓声应气求、并无矫强于其间者哉?自有公之此举,则名贤之享祀愈着寅恭,盛世之激扬益昭甲令;而公之令誉芳徽,亦与山公而并永千古矣。
戊午科举人拣选知县村人王清植熏沐谨撰
邑庠生王恂之沐手书丹
小虹桥首事王清植、常丽天、王清祺、王清才、常太戊、郭永芳、王谦之、王三甲、常允中、吴元魁
地方王治世、杨继元
大清同治十二年岁次癸酉季春吉日立石
铁笔陈国瑞
该石刻是为表彰邑侯骆公捐免山公祭田粮课的行为特地竖立的,是重视乡贤的举措;同时,它还昭示后人,以起教化之作用。
(5)其他石碑。散靠于学校教室墙外的石碑还有二通,一通为“大清咸丰五年(1855年)岁次乙卯秋月吉日小虹桥仝立”的《重修山涛墓祠的捐资碑》(全为捐资人名,略);另一通为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碑刻,高1.22米,宽0.34米,厚0.17米,碑首题“釐整祀典”。碑文曰:
山公,晋名臣也。祠墓坐落本村,历代崇祀不替。康熙壬辰,邑侯刘公廷用遵宏(按:当为“弘”字)治碑文,二八月上戊日以羊豕致祭,特悬匾曰“风高两晋”,悬刻对□联;又念二月二日系公生辰,献戏致祭。延至乾隆年间,偶因水灾事剧,祭戏俱废。嘉庆五年,邑侯叶公龙光据本村绅士王克哲、常光宗等呈词,究侵吞责书、胥罚礼书补祭,俾山公祭典全复。道光六年,邑侯王公荣陛诣庙躬祭,遍阅碑文,详询祀事,谕村众曰:“祭既复矣,生辰戏不可不献。届期,尔等宜具禀,我为山公撰戏。”次年二月,神戏亦复。今岁二月,署印张公庆昌照例送戏,忽逃去。河内李太史文园闻之,曰:“《礼》云:‘有其举之,莫敢废也。’我为山公送戏,可乎?”遂请于张公,复送戏焉。戏演毕,河内李进士玫、秦孝廉秀抡亦谓“名臣祀典,理不可缺”,又将逃去之戏送来补演。一时村人咸颂李太史、李进士等之高义,嘱余记之,以见山公之德尚不泯于人心云。
敕授文林郎奎文阁典籍年七十四岁王克哲撰
道光十七年岁次丁酉八月吉日东西两社公立
附记:
嘉庆五年,叶堂公釐整祀典,仪注:每年春秋上戊日,供祭猪壹口,重五十六肋;祭羊壹腔,重二十二肋;树果肆盘;主祭官行三跪九叩首礼。颁胙仪注:县公,猪羊肘各一双,主祭官同,东西两社首事同;陪祭及礼相,各一分;东西社地方陪祭、随役、看庙和尚,各一分;礼房,猪首一;屠户,猪脊;听事吏、听差、提垫、濂补、车夫、跟班,各羊肉一分;清唱,羊头一。
该石刻缺乏碑题,但主题鲜明,主要是表彰送戏祭祀山涛的义举。同时,它还列举了祭祀的物品,是研究近代祭祀礼仪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山公墓前,尚立有《晋侍中吏部尚书山公墓》碑一通,见前述。另外,在西小虹村的老年活动中心——小虹桥村大队部的墙基中还砌有几通碑刻。其中,最东边的一块侧立于房基之中,碑阳向外,碑阴向里;碑刻文字清晰,为“清同治癸酉年(1873年)季春月吉日 钦加运同衔署武陟县事骆文光立石”的“晋侍中新沓伯山公之墓”碑,碑高1.78米,楷书碑文。另一块碑刻则碑文向里,碑阴向外,具体内容无法察看。
四、山公墓冢群
山公墓冢群不仅有山公墓祠,而且还有与山涛相关的其他墓冢,包括山涛的父母墓、儿孙墓、女儿墓等,并有一些石刻。这一系列墓冢及石刻并称为“山公墓祠石刻及古墓群”或“墓冢群”。墓冢群原为武陟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焦作市文物志》记载:“小虹桥村墓冢群,位于武陟县城西13公里沁河南大虹桥乡东小虹村东。由四冢组成,均为圆形,其大小相同,每个冢直径23米,占地400平方米。20世纪60年代将冢挖平。据传说此四冢为山涛四个女儿之墓,故称为四女冢。”[5]104
实际上,小虹桥村原为一个行政村,后分为西小虹村和东小虹村。山涛及其儿孙的墓冢在西小虹村;由山公墓祠西隔壁的西小虹村安街口往北走,是山涛父母的墓冢;西小虹村西南1.5公里左右,有山涛乘马的坟冢,叫马冢;西小虹东南1.5公里左右,有为山涛驮运物件的骡冢;东小虹村正东1公里左右,有山涛四个女儿的墓冢,其方位分别是西南向、东北向、西北向、正北向。
(1)山曜墓。关于山涛之父山曜的墓地,清代道光九年( 1829年)《武陟县志·古迹志》记载:“冤句令墓,山公之父墓也。在山公墓西北。”[4]《焦作市文物志》记曰:“冤句令墓,位于武陟县西南17公里大虹桥乡小虹桥村山公墓西北50米处。原冢东西宽15米、南北长20米,占地300平方米,20世纪60年代初村民挖为平地。”[5]81
根据王新顺先生提供的线索,按照图1所示,山公墓与其父山曜墓及儿孙的墓是在一个中轴线上。实际上,就村民所指示的方位,并非如此,而是山曜墓略偏西北。在得知我们调查山曜墓时,村民们立即集拢过来,纷纷向我们描绘昔日的盛景:当时的山曜墓高于如今的三层楼房,上面还建有房子,西边大致至村民安社宅院西侧,东边止于王三保大门东侧;南边始于王三保宅院南墙所在路边,北边齐于王三保三层楼房的北墙。但如今的山曜墓已没有任何遗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民居,其状况、规模也仅存于村民的心中了。
(2)山简、山遐墓冢。清代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怀庆府志·舆地志》记载:山公墓在武陟县西10公里的小虹桥村,其“二子简、遐墓①亦在焉”[2]。《怀庆府志》明确指出“二子”墓为山简、山遐墓。但清代道光九年(1829年)《武陟县志·古迹志》仅仅记载为山涛“二子”①墓。山涛“二子墓①,在山公祠前。二冢上分下连。传为山公二子墓而未详其名”[4]808。这说明在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年),由于某种原因,人们可能还不知道二子为何人,也有可能是县志的编撰者调查不细所致,但现在人们依据《怀庆府志》明确指出“二子”墓①是山简、山遐的墓冢。千平喜同志的《山简、山遐墓》一文指出:“山简、山遐为山涛二子①,其墓位于山公祠前。原墓冢一东一西,上分下连,东西35米,南北22米,共占地770平方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土挖平。”[7]130《焦作市文物志》也记载:“山简、山遐墓位于山公祠前,原墓冢一东一西,上分下连,东西长35米、南北宽22米,共占地770平方米,20世纪60年代起土挖平。”[5]81-82
①在这里,需要修正一个记载错误。无论是清·乾隆年间的《怀庆府志》和道光九年(1829年)的《武陟县志》记载,还是千平喜的《山简、山遐墓》所记,甚至一些当地人的记忆,均存在一个错误,那就是都将山涛墓前的山简、山遐墓冢记为山涛的“二子”墓。其实,山简与山遐并不是兄弟,而是父子关系,山遐是山简的儿子,即山涛的孙子。这一点,《晋书·山涛传》(卷43)、《大清一统志·怀庆府(二)》(卷161)均有明确记载,在此一并说明。当我们提出调查山涛儿孙墓冢情况的要求时,村民郑青云女士热心地陪我们来到位于山公墓冢西南方向、与山公墓冢相距150米的一处低洼空地。该空地100平米左右,南部曾是菜地,北部有明显的塌陷痕迹。郑女士介绍:山涛儿子孙子的墓冢就在这片空地下方,原来这个地方的地势一点也不低,当初山涛儿孙的墓冢有房屋那样高,但在破“四旧”过程中被铲平。原来这儿附近也没有住户,随着农村的扩展,被铲平的山涛儿孙的墓冢四周逐渐住满了农户。而且,农户建房时普遍垫高地基,于是山涛儿孙墓冢的这一片地方就显得更加低洼了。当我们来到山涛儿孙墓冢所在地的时候,遇到了住在附近的几位村民,当他们得知道我们是在整理山涛故里的故事之后,对此他们普遍表示欢迎,并拜托一定要把发生在自己村里的和山涛有关的故事、传说早日宣传出去,让外界更多的人了解山涛、知道小虹桥。同时,他们对山涛儿孙墓冢的一些说法又进行了补充。
王小满,男,35岁,西小虹村村民。他说:据先辈们讲,山涛儿孙们的墓冢与东北方向的山公墓冢之间有砖洞相通。前些年,这个地方突然塌陷下去,连接墓冢的砖洞也因此坍塌并外露,有人出于好奇,曾顺着洞口尝试着走进洞中,但没有结果。后来,县里的文物工作人员闻讯后,也曾来这儿实地考察过。据进洞的工作人员说,砖洞内墙壁上的绘画颜色光鲜,说明古时精湛的漆画技艺已经达到了较为先进的水平。由于当时没有考古发掘计划,随即掩埋了洞口。自此之后,再没有人提起此事。
赵藏富,男,55岁,西小虹村村民,是最早(1992年)到此建房的村民之一。赵藏富介绍:山涛父子墓冢之间有砖洞相连的说法是很可信的,以前,在天降暴雨的时候,因为山涛儿孙墓冢附近地势低洼,所以短时间之内往往能积聚大量的从村里流淌而来的雨水。但是,积聚的雨水又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莫名其妙地被排泄掉,这说明地下的确存在着砖洞。
五、关于山涛的传说
为了解到更多的山公墓群的情况,我们又走访了几位见多识广的老人。
(1)山涛善饮与斗酒。村民杨乃荣介绍:山涛善饮酒,传说有千杯不醉之量。朝中奸臣为陷害山涛,就拿出一个有八斗酒量的小铜人和山涛斗酒,以验证山涛的酒量。据说小铜人脚下有洞,酒从小铜人嘴里灌下去,马上就顺着脚底的孔洞流到地下。最后,山涛喝酒斗不过小铜人而输。山涛善饮是事实,但从《晋书·山涛传》“涛饮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试之,乃以酒八斗饮涛,而密益其酒;涛极本量而止”[1]的记载来看,杨乃荣先生所说的山涛“有千杯不醉之量”不免有些夸大。但与铜人斗酒的传说,在西小虹村很是流行,表达了其故里对山涛本人的敬爱和对奸臣的痛恨。
(2)山涛全家赴难。朝中奸臣使用小铜人和山涛斗酒,结果山涛斗败而输,被奸臣诬告有欺君之罪,三日后处斩。朝中有人透露消息给山涛,山涛举家逃到外地。但朝廷并没有放过他,最终在西小虹村将山涛团团围住,结果:山涛自尽,父亲吊死,母亲撞墙而亡,儿子自焚。关于山涛全家赴难的这一传说,只能看做是山涛故里对山涛的一种感情而已,与史书记载完全不符。
(3)山公祠的修建。杨乃荣介绍:山涛一家人死后,朝廷知道了这是一冤案,就下拨银两给山涛及其家人建立庙祠。因为当时河南(黄河以南)某县也有个小虹村,所以起初是在河南某县的小虹村建造的。工程进行过程中,朝廷派人来督查,发现建的地方根本没有山涛的墓冢,赶紧拨乱反正,将山公祠改建到武陟县大虹桥乡西小虹村。但是,朝廷下拨的银两已用去不少,所以重建的山公墓祠就没有那么豪华和气派了。王新顺先生也谈到山公祠的修建过程:其说法与杨乃荣介绍的基本一致。祠堂修好后,全国各地的大小官员都来祭拜他。来的时候,每人捎来一包土,为山涛的墓冢培土,日积月累,山公墓就成了一个大冢。关于黄河之南还有一个小虹村并误建山公庙祠的说法,村民均信其有,但是在荥阳还是在巩义谁也说不清楚。我们曾委托村民安存玉先生帮忙打听,一旦证实,我们即可前往调查,后来反馈回来的消息是没有查到。所以,黄河以南误建有山公庙祠的这一说法,只能作为山涛故里对山公祠过于简单甚至有些寒酸的一种变相解释和托辞而已。
从《晋书·山涛传》记载山涛“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景帝”[1]的文字资料来看,说明山涛的确和司马懿之妻张春华是表亲关系。司马师对山涛也很是亲近,“魏帝尝赐景帝春服,帝以赐涛。又以母老,并赐藜杖一枚”[1]。后来,司马师对山涛虽有“吕望欲仕邪”的揶揄,但还是“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久之,拜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1]。可以说,司马师对山涛职位的升迁还是尽了提携之力。因此,村民们所说的山公祠堂误建他处的细节并不可信。又如,山公墓之所以成为大冢,是源于山涛死后全国各地大小官员都来祭拜他并为其墓冢培土的说法,同样是民间出于崇敬心情的一种夸大之辞。
(4)山涛儿孙墓下的砖洞。截至目前调查得知,杨乃荣先生是小虹桥村唯一的曾经亲身进入砖洞察看的当事人,其洞中所见,与县里文物工作人员所见大体一致。关于山涛儿孙墓冢沉降为坑的原因,杨乃荣先生的解释是:山涛儿孙墓冢附近地方曾被用做生产队打晒谷物的场地,后来又被复耕为菜地,因为常年浇水,山涛儿孙墓冢附近才发生了塌方沉降,变成了现今的低洼模样。
(5)山涛的名讳与后人。山涛字巨源,名、字之中均有两个三点水作偏旁的汉字。据王新顺先生介绍,山涛出生后,按照阴阳八卦,他命中缺水,所以就取名为“涛”,取字为“巨源”。这样一来,无论是字形上还是字义上,就再也不缺水了。对于山涛名字的由来,我们认为,王新顺先生所介绍的山涛的名、字符合古人命名取字的实际情形,的确算是山涛故事传说中的饶有趣味的一个小情节。关于山涛的后人,王新顺先生介绍:山涛的后人分为两支,一支在山东,一支在辽宁。前些年,山涛后人还来祭拜过山涛,但目前西小虹村及附近村庄均没有山涛后人。
山涛故里关于山涛的传说可能与史实不符,甚至有较大的差别,但这种集体记忆还会继续传承下去。尽管他们中间肯定有人阅读过《晋书》等正史文献,但他们所传播的依然是他们心目中的“事实”。总之,山涛故里保存的有关山涛的碑刻、祠墓以及大量的故事传说,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文献资料和口头史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1] 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 晋书·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山涛(子简,简子遐) [M/OL].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128857.html?from=isnom.
[2] 史延寿.续武陟县志:马集文斋刊本[M]. 1931(中华民国20年).
[3] 焦作市地方史志编辑委员会,沁阳市地方史志编辑委员会.怀庆府志(乾隆五十四年):点校本[M].郑州:解放军测绘学院印刷厂,2005.
[4] 王荣陛修,方履篯纂.武陟县志:影印本[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68.
[5] 焦作市文物局.焦作市文物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6] 千平喜.山涛墓祠[Z]//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武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陟文史资料:第4辑.1997.
[7] 千平喜.山简、山遐墓[Z]//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武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陟文史资料:第4辑.1997.
AnInvestigationofShantao’sNativePlace
CHENGFeng,LIJing-ping,SHENHua-cen
(InstituteofTanhuaiCulture,JiaozuoTeachersCollege,Jiaozuo454001,Henan,China)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hantao’s native place: Xixiaohong Village in Wuzhi county are studied by means of fieldwork investigation. From these materials,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inscription data of Shantao’s tomb and memorial temple, visited the inheritors of the oral literature and collected a lot of folk stories and folk legends so as to clarify a number of historical facts, which provide the first-hand information for the further academic study of the travel activities of Seven Celebrities of Bamboo Grove.
Shantao’s native place; Xixiaohong village; Shantao’s tomb and memorial temple
2009-11-09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竹林七贤游历地调查研究》阶段性成果(2009FLS006)。
程峰(1965-),男,河南济源人,教授,从事地域文化研究。
E-mail:cfjs2004@tom.com
K825.81;K928.76
A
1673-9779(2010)01-0110-08
[责任编辑 杨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