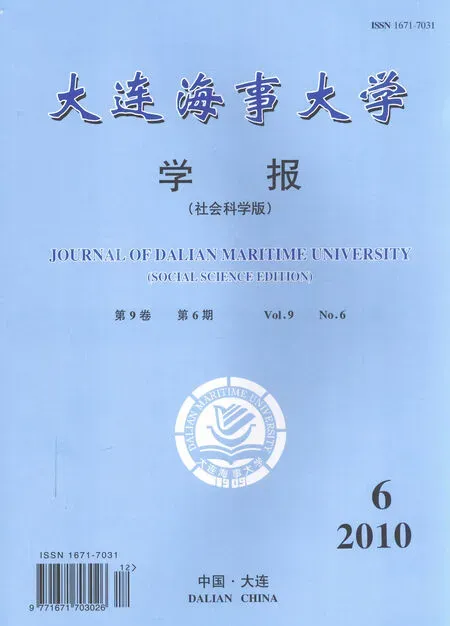“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身份犯性质的质疑
黎邦勇
(武汉大学 法学院,武汉 430072)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身份犯性质的质疑
黎邦勇
(武汉大学 法学院,武汉 430072)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被设定为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密切关系的人员,视为身份犯。不过本罪所欲保护的法益是公务员对自身合法职权的行使的排他性而非受贿罪所要求的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故其不属于身份犯;另外,“密切关系人”这一概念的内涵无法被明确界定,缺乏被界定为身份的可操作性。因此应该合理地将本罪解释为非身份犯。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身份犯;非身份犯;密切关系人
《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388条新增了一款犯罪,根据权威学者高铭暄、赵秉志等人的看法,可称其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立法者将该罪的主体设置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立法者在《刑法》第300条新增条款中的具体规定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从事实上看,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当然属于与国家工作人员密切关系的人;从《刑法》的用语来看,“其他”一词也意味着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包括在与国家工作人员密切关系人之内。由此而言,近亲属应是《刑法》明示的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或者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密切关系的典型人,因此本文中密切关系人的范围涵括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当然,如正文所声明那样,这里没考虑增补条款中所规定的第二种情形。本文暂时不考虑增补条款中规定的第二种情形,姑且将其简称为“密切关系人”。从《刑法》的用语上看,将该罪的主体明确为“密切关系人”似乎明示了本罪属于身份犯;另外从《刑法分则》的体例安排来看,受贿犯罪一般都属于身份犯,这似乎也意味着该罪的身份犯性质。然而,《刑法》的用语形式并不是确立该罪身份犯性质的真正标志,还需透过用语的形式,以其客观的实质含义来探究该罪是否属于身份犯;《刑法》贿赂犯罪的体例安排固然能说明一般贿赂犯罪的身份犯性质,但却不能排除特例的出现。因此,有必要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身份犯性质保持一种谨慎的怀疑。根据笔者的研究,这种怀疑具备两个来源:其一,“密切关系人”缺乏成为身份的法理基础;其二,“密切关系人”缺乏成为身份的实践基础。以下分述之。
一、“密切关系人”缺乏成为身份的法理基础
《刑法》中的身份的意义在于行为人身份是衡量行为对法益侵害的要素,具言之:(1)无特定身份,行为就不可能侵害某些特定的法益——有些犯罪只能由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实施;(2)具有特定身份,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性才能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3)为了保护特定的法益,将某种犯罪作为加重类型,而规定特殊的身份;(4)有些不作为性质的犯罪,由于相关法律只是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义务,故只有具有该特定身份的人不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才可能成立不作为犯罪。[1]128从以上4种情形可以看出,某罪保护法益的特殊性才是将该罪行为主体限制为身份犯的前提和基础,即保护法益的特殊性决定了行为主体的特殊性,进而将其设定为身份犯。因此要判断某罪是否属于身份犯,首先要考察该罪的保护法益是否存在某种特殊性。以此基本逻辑来考察“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否属于身份犯,意味着首先要确认该罪的保护法益,其次判断该罪的保护法益是否具有某种特殊性。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法益,根据《关于〈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说明》,无疑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但经过仔细的推敲,这种观点不无可疑之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顾名思义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身份所设定的义务,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者自有义务维护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非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与国家工作人员合谋当然亦可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但是此两种情形之外,要使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够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须事先设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维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法律义务。有人将这种情形解释为一种身份义务有限度的扩张:“无一定身份者利用无责有身份者实施法定身份的犯罪同样可以对法益造成侵害,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以受贿罪为例,无公务员身份者利用和自己存在密切关系的无责的公务员实施受贿行为,无身份者的行为同样会对公务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造成侵害,所不同的是,这种侵害与公务员直接实施受贿行为是有一定区别的。但是这种区别不是性质上的区别,而是程度上的区别。”[2]然而这种受贿罪身份有限度扩张的观点并没有讲清楚这种身份扩张的实质理据:什么情形下可以扩张,什么情形下不能扩张?身份的扩张与法益侵害之间的联系究竟是怎样的?这些答案在上述主张中要么踪影全无,要么含糊不清。所谓的受贿罪身份扩张其实质在于保持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义务的扩张。细究之下,不难发现这种扩张违反了在宪政国家权力赋予与义务承担对等这一基本原则的要求。在现代宪政国家中,无一不承认国家权力来源于国民的授权,这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而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国家对合法国家权力的授受取得对国家权力的行使。换言之,国家工作人员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国家对权力的合法赋予。为了防止正当拥有国家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将手中的权力作为其他利益的对价物进行交易,国家通过法律给合法的权力行使者规定了必须保持职务廉洁性的要求。从这里可以看出,身份所决定的廉洁性义务只能来源于具有合法来源的权力,任何人,当其不具有这种合法权力时,法律也就不应该为其创设保证权力正常行使的义务。反过来说,法律为非法权力的行使创设相应义务的做法存在荒谬的逻辑矛盾。
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密切关系人”本身并不能合法地拥有行使国家公职的权力,在其实施受贿行为时,其完整的行为过程实质上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凭借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某种密切关系,非法地获得权力拥有的事实;第二步是进而利用这种非法获得的权力收受贿赂。这同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行为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先合法地拥有某种国家权力,尔后将其作为某种利益的对价物加以交易,而前者则先是非法地获取某种国家权力,然后又将其作为某种利益的对价物加以交易。用一个隐喻性类比来讲,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行为人先是窃取了国家权力,然后将窃取的国家权力进行出售。显然,正如人们可以责备财物的合法的暂时保管人将财物进行交易,但是没有必要也无法责备抢劫财物者将抢劫所得的财物进行交易,在后一种情形下值得谴责的是行为人非法取得财物的行为,而不是将抢劫所得财物加以交易的行为。同理,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不能也没有必要为“密切关系人”赋予非法获取国家权力后正确行使这种事实权力的义务,因为正确行使“非法获取的国家权力”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悖论,法律所能做的事情是防止行为人利用所谓的密切关系对国家权力进行非法攫取。以上分析可以简单概括为:合法的权力方能派生出合法的义务,不合法的权力无法派生出合法的义务;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密切关系人”所获得的是非法的事实性权力,无法派生出要求其合法行使这种非法的事实性权力的义务。在《刑法》中身份的设立意味着具有身份者对特定法益存在着特定的保护义务,或者对特定法益存在着较不具有身份者更强的保护义务,但是,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由于行为人所拥有的事实性权力不具有合法性,也就不可能派生出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予以维持的义务。既然无此等义务,也就不可能针对这个不存在的义务而设定特殊的身份。
以上分析揭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保护法益不可能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而只可能是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所授受职权行使的独占性。国家将权力通过职位授受给相应的国家工作人员行使,要保障国家权力正当行使,首先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对自身职务权力行使的独占性,这种独占性要求排除其他任何人对相关职权的非法介入或攫取。那么,“国家工作人员对职务权力行使的独占性”这一法益是否要求只有具备某种特定身份的人才能加以侵害呢?回答之前,不妨回顾一下张明楷教授所提出的疑似身份犯的问题。在身份判断的问题上,张明楷教授曾提出一种疑似特殊身份而并非真正特殊身份的情形。他认为,如果任何人事实上都可以进行某种行为,那么就不存在针对此种行为的身份。对此他举例论证道:“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为例,任何人都可以直接从事生产、销售活动,因而都可以成为《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者、销售者。在此意义上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主体,并无特殊之处。而其他特殊身份则并非如此。”[1]130-131据此,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人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利用各种手段,利用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的种种关系而达到非法介入和攫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权力的目的。因此,“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刑法》在本罪主体的设置上使用“密切关系人”一词,充其量只不过使“密切关系人”成为疑似特殊身份,而并非认定其为真正的特殊身份。
二、“密切关系人”缺乏成为身份的实践基础
“密切关系人”构成身份所面临的与身份对应的义务没有基础的法理难题,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将“密切关系人”认做身份必定会遭遇不可克服的困境。这个困境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无法穷尽作为生活事实的密切关系人的具体种类;其二是无法提炼出作为规范事实的“密切关系人”的一般标准。以下详述之。
1.无法穷尽作为生活事实的密切关系人的具体种类
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工作人员无论是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还是作为普通民众中的一员,除自己的近亲属外,都还存在着广泛的人际交往,并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建立了各种人际关系。字典也为种种人际关系提供了尽可能多的词汇,能够根据某种标准建立归类的特定关系有情人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校友关系、同事关系、战友关系、邻里关系、雇佣关系以及合作关系等。此外还存在着难以特定的关系,如朋友关系。朋友关系的存在本来以交往的双方存在着一定的友情为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的总括。不管归纳列举得如何全面,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密切关系的具体情形,这种归纳列举仍然是无法穷尽其所有情形的。《刑法》在此没有使用“斡旋受贿罪”司法解释所提供的“特定关系人”一词表明,《刑法》在确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时并不主张将其局限于有限的“特定关系人”。故此,虽然上述特定关系人均可纳入“密切关系人”的范围,但“密切关系人”的范围却不仅仅局限于“特定关系人”,二者呈现的是一种“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正因如此,《刑法》使用“密切关系人”一词对上述种种关系进行概括。这种概括不但意味着语言使用的简洁,更有利于克服使用“特定关系人”一词将该罪规定为身份犯所带来的主体范围褊狭的问题,表明立法者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规定为非身份犯的立法意图。
2.无法提炼出作为规范事实的“密切关系人”的一般标准
如果“密切关系人”是一种身份,那么对于何谓“密切关系人”的界定应当从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交往的具体情形进行客观的事实性的判断,即应遵循这样的判断逻辑:首先从事实的角度确定行为人是否属于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然后判断行为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是否以该密切关系为媒介。在这个判断过程中,对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的判断是以行为人确属“密切关系人”为前提的,即用“密切关系人”来说明“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影响力”之可能,而不能以后者来说明前者。然而,如前所述,《刑法》在使用“密切关系人”一词时,只是对种种密切关系人的一个概括,没有也不可能从事实角度提炼出“密切关系人”的一般标准。相反,可以以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是否“足以影响国家工作人员对职务权力的行使”为基准,来确定这种关系是否属于“密切关系”,即完全可以颠倒将“密切关系人”理解为身份而必须遵循的判断逻辑,以行为人是否存在足以影响国家工作人员对职权的行使而判断其是否属于“密切关系人”,只不过这种判断的顺序,彻底否定了“密切关系人”构成身份的可能性。
三、客观解释下的“密切关系人”
“密切关系人”难以构成身份,那么究竟应如何理解“密切关系人”的含义?笔者认为,应当对“密切关系人”作客观的解释。客观解释之基本主旨在于承认文本一旦产生,即具有自身的含义,对文本的解释只能是对文本本身所具有的客观意义的解释,而非寻求所谓的文本作者的意图。[3]根据客观解释的基本要求,《刑法》条文一旦由立法机关写就颁行,其意义只能由鲜活的生活事实来赋予,对《刑法》条文也只能遵循客观的生活的意义进行解释。现实的生活实践告诉人们这里的“密切关系人”实为“任何人”,这个结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论证。
1.从事实出发的客观解释
根据以上的论证,不可能给“密切关系人”提炼出一个事实性的标准,只能以是否“足以导致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影响力”来确定行为人是否属于“密切关系人”。事实上在《刑法》第388条的增补条款中,“密切关系人”和“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影响力”存在着一种相互说明的关系:关系密切者方可实施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影响力之行为,可能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影响力者方为“关系密切人”。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种种手段和方式达至“足以导致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影响力”之事实,即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密切关系人”。以此而论,所谓“密切关系人”的范围在实质上可以扩展到包括任何人的范围。或许立法者的初衷确实欲以“密切关系人”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作出某种限制,但是《刑法》用语的客观解释却赋予了“密切关系人”更为广阔的范围,而这种客观解释更能够使人们避免陷入必须提炼“密切关系人”事实标准的泥沼。
2.立法比较上的客观解释
《刑法》之所以新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除出于遏制国内腐败行为的高发态势的实际需要外,考虑我国反腐败立法与国际立法趋势接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其第18条针对影响力交易犯罪规定:(1)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使其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为该行为的造意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不正当好处;(2)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其中第二款所规定的“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者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的好处,以作为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的犯罪涵括了《刑法修正案(七)》所设立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公约》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的情形与我国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相关规定作一简单的比较不难发现,前者对犯罪主体没有作限制性的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该犯罪行为的主体,而我国将该犯罪主体规定为“密切关系人”,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如果“密切关系人”构成一种特定的身份从而限制了该罪的主体范围,那么相关立法的接轨就还存在着一定的空隙。当然,接轨这一要求本身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相关具体立法必须与《公约》规定完全一致,但是立法规定差异的存在必须是因为我国在此事项上存在着与国际反腐败趋势情形的实质差异。然而腐败实乃政治生活中的毒瘤,各国腐败情形除剧烈程度不同外,腐败之性质与范围并无本质性的差异。我国的腐败情形较国际社会尤为剧烈,有何理由在立法上作出与《公约》存在相当空隙的规定呢?显然,对此只能作出相反的推定,即我国立法者选择了外延并无实质性限制的“密切关系人”作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从而完成了与《公约》规定的彻底接轨。当然,立法者选择“密切关系人”除完成接轨的任务外,也还存在着一种强调的作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密切关系人”中最主要的是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某种特定关系的人员。立法者使用“密切关系人”一词其实质在于强调司法工作人员注意“密切关系人”与“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影响力”所存在的相互说明的关系而已。
四、结 语
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认定为身份犯,除法理上的障碍外,还会给司法实践制造必须提炼出“密切关系人”的事实标准的难题,必然导致我国打击此类犯罪面临无谓的困扰,也不利于与《公约》相关规定的全面接轨。因此明确该罪的非身份犯的性质,做到与《公约》相关规定的全面接轨应当是对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解释的必然选择。
[1]张明楷.刑法学[M].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毛冠楠.影响力受贿罪解读[J].中国检察官,2009(4):13.
[3]安德雷·马默.法律与解释[M].张卓明,徐宗立,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21-223.
Queryonbriberymakinguseofinfluencebelongingtostatus-crime
LI Bang-yong
(School of Law, Wuhan Univ., Wuhan 430072, China)
The subject of bribery making use of influence is the personnel who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overnment staff members like being status-crime. The legal interest of this crime is the exclusiveness of civil servant fulfilling their duty, but not the probity of their duty which is required by bribery, so it is not a status-crime. The close relationship's connotation is not clearly and lacks of the maneuverability to form status. So we should explain this crime to be a non-capacity criminal rationally.
bribery making use of influence; status-crime; non-capacity criminal; close relationship
1671-7041(2010)06-0058-04
DF636
A*
2010-07-27
黎邦勇(1973-),男,湖南岳阳人,博士研究生,讲师;E-maillby117112@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