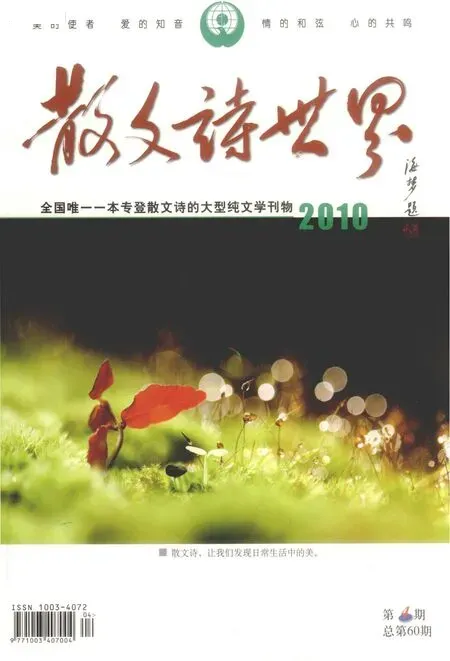浅谈中国现当代散文诗的表现特征
李标晶
散文诗在表现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象征手法的运用。象征手法对于散文诗来说,比一般诗体更为重要,也更适合。散文诗是诗,不可能像散文那样去细致地摹写生活。表现“像外之象”,对散文诗来说是第一位的东西。这是散文诗与抒情散文很重要的一个不同点。而达到“像外之象”最有效的途径是象征。
象征是属于美学范畴的宽泛概念,即通过某一特定形象或形象体系,以表现或暗示超越这一形象或形象体系的含义和观念。象征,既包含着比喻中的暗喻成分,又包孕寓言表达方式中的比附因素;但又有生发和放大。象征体所包孕的象征观念常常体现某种程度的超越性、暗示性和不确定性。散文诗人运用象征的表现方式,一般都具备了现代意识的象征的品格:象征的观念带有一定哲理性;诗情与哲理有机融合;艺术的抽象渗透于象征手法之中。
散文诗的象征表现,从与现实结合的程度和方式看,大致有三种情况:受西方象征主义文学影响的象征主义散文诗;现实主义对象征主义的吸收;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的结合。
象征主义散文诗受西方象征主义色彩影响,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表现上都效法西方现代派。有代表性的是于赓虞。在他那里,现实社会的丑恶与黑暗,被赋予了某种绝对的和普遍的性质。这种丑恶的力量,像幽灵一样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游荡,它困扰着作者,欲将其拖入阴冷黑暗的死亡墓穴,在作品中表现为荒坟、墓穴、死尸、暗夜、骷髅、地狱等具有强烈象征色彩的意象。
现实主义对象征主义的吸收,这是中国大多数现实主义作家贯用的表现方式,也是中国散文诗作家运用象征手法的主导形式。鲁迅、茅盾、瞿秋白、王统照、刘再复等作家都是如此。
现实主义对象征主义的吸收,主要体现在运用隐喻和借喻的抒情方式表达深邃的哲理内容。它舍弃象征派诗人过分注意意象的主观知觉效果而脱离客观现实的缺点,表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和参与意识。他们以象征主义为基础,实现现实性与象征性的统一。作家们试图表达自己对当时社会现实所感受到的哲理内涵时,都不同程度地在现实主义方法中掺杂进象征主义因素。这样,在现实主义作家手中,象征性散文诗就成了他们关照现实,表现生活理想和把握社会发展主流的方式和手段。如孙俍工的《红叶》,用红叶矢志追求生命的更生与永恒,象征诗人守志不移的人生价值观。茅盾《沙滩上的脚迹》,以“他”象征大革命失败后,经过苦闷彷徨、探索而终于又找到“真人的足迹”,又奋勇前进的革命者;用“夜的国”、“妖魔的堡寨”象征反动统治的黑暗和恐怖;以“光明之路”暗示反动派骗人的宣传;用“夜叉”、“人鱼”、七分像人的鬼怪,暗示各种反动人物。众多的象征物较好地表达了作者激励人们知难而进的思想和诅咒反动派白色恐怖的强烈感情。瞿秋白的《那个城》,用小孩子和那个城两个象征性形象,预示了社会发展的趋向。李广田的《马蹄》,将内心幻觉具象化,通过黑夜策马登山,马蹄撞击出金光的描写,表现执著追求光明,探索前进的心迹。阿垅《总方向》,以江河奔流、浩荡东去的雄浑气势,象征抗战洪流奔涌向前,势不可挡的历史方向。李耕《未死的树》那棵饱经严寒风雪的树是诗人自己坎坷经历和倔强不屈性格的象征。屠岸的《影子》用影子象征在风云变幻中的一种人际关系。由此可见,作家们运用的是象征主义的手法,抒发和表现的是现实的情感。
现实主义作家在散文诗创作中运用象征手法,它的渊源就不仅是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还有对我国古代象征传统的继承。《诗经》的比兴方法,实质上就是象征方法。它对我国文学影响深远。《诗经》之后的《楚辞》、张衡《四愁诗》、曹植《美女篇》《弃妇篇》《君子行》,乃至郭璞、陶渊明、李白、杜甫的诗都发扬了象征的传统。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也同样受象征的影响,《西游记》和《临川四梦》可算典型。中国古代象征与西方现代派的象征主义在本质上有很大差异;中国古代的象征强调主客观的统一,重理性,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和伦理教化作用。而西方现代派象征主义重主观,轻客观。重直觉,轻理性,常用奇诡变异的物象表现个人的情绪和对现代世界的神秘感受。很显然,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散文诗人承接了中国古代象征的传统,与现代意识相结合,创造了有象征主义内蕴又体现强烈时代精神和现实特征的散文诗。
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的结合。即在浪漫主义形象中包含意味深长的象征意蕴。这在郭沫若、徐志摩和鲁迅、彭燕郊、徐成淼等的一些散文诗中有体现。如徐成淼的《苍茫时分》,诗人融浪漫主义的想象、激情和现代主义的象征于一炉,在他的笔下,表达爱情的意象不是轻飘飘的云彩,不是轻喜剧式的和弦,而是极具象征意味的“海潮拍击岩洞”,而是“痛楚的额头偎在你的崖岸;即使“滩涂如此柔软”,却“令我惊心动魄”。
鲁迅是象征主义散文诗、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的集大成者,体现了他表现手法的丰富多样。
中国散文诗的象征,有整体性象征和局部象征两类。整体性象征即通过象征,从主要形象到次要形象,形成一个象征的体系,又可分为同一体的整体式象征和非同一体的整体式象征。同一整体式象征,是全篇借自然界某一物体含蓄而深沉地表达某种抽象的富有哲理的思想。本体和象征体之间的关系较为宽泛,对其理解也不可过于拘泥。比如茅盾的《白杨礼赞》,通篇围绕白杨树来写。白杨树是全篇的中心意象。以白杨树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军民。曾卓的《大江》主体形象是大江,从纵的方面将滚滚滔滔的长江和自己的生命历程融会;又从横的方面把自己的生命和气象万千的长江相应和,从而完成了散文诗的象征构思。耿林莽的《芦花》借芦花的形象象征中国妇女的传统性格。非同一体整体式象征是用两个或更多的象征体来反映特定时代和社会生活,如茅盾《沙滩上的脚迹》、鲁迅《秋夜》等,都是如此。
局部象征是以一景一物构成象征性意象,全篇并不构成完整的象征性环境。如茅盾《卖豆腐的哨子》中“满天的白茫茫的愁雾”,是当时作者内心的象征,也是时代的迷惘之雾。但整篇写的是听到卖豆腐的哨子后的感受。
散文诗构成象征的方式主要有切入式、虚拟式、梦幻式、点化式等几种。
切入式 截取生活某一片断或摄取某一事物的特写镜头,赋予暗示性和比喻性。如茅盾的《雷雨前》,作者抓住雷雨之前天气的种种特征加以铺陈描写,突出人的感受,以天气的特征和人的感受暗示当时的革命形势。或者对社会生活或自然景物的某些表象作细致描摹,引导读者对人生意义和事物本质作深层领悟,如我们曾提到的刘半农的《晓》对列车内外实景的切入式特写。又如杨炼的《老树》诗人将现代生活中的经验对象化为很有独特感觉的物象里。作品借眼前的一棵老树委婉地表现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冲突,表现了这种冲突中的躁动、惶惑、恐怖和灵魂的惊厥、人性的扭曲的痛苦和趋向静穆的过程。诗人依靠整体情境建构起象征性的艺术世界。
梦幻式 借梦幻将难以捉摸的心灵颤动具象化。梦幻有着自由性、随意性,它不一定是实有的,因此可以不受现实生活逻辑限制,不必去拘泥于是否有现实合理性。所以,有时梦境可以生发出现实生活难以表现的象征义。中国现代散文诗作家,善于以梦境构筑象征的艺术氛围,创造出瑰奇幽邃的象征世界。他们创造出象征主义梦幻,就是把现实生活扭曲、变形、幻化,具有荒诞性,呈现出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情境,具有超验色彩。如鲁迅《墓碣文》《影的告别》《死火》《失掉的好地狱》《狗的驳诘》等都是。另一种是浪漫主义梦幻,混合了记忆性梦境的真实感和变异性梦境的超验感。如鲁迅的《死后》《颓败线的颤动》、茅盾《严霜下的梦》、管用和的《梦》等。如管用和的《梦》:
在深秋,我作了一个梦。
我梦见自己是一棵竹笋,不知费了多大力气才慢慢地钻出了隆冬冻硬的土层。我对自己的一层壳非常珍爱——没有它,也许我就会伤残甚至夭亡啊。
然而,我就因此将它永远裹在身上以显示那出土顽强、坚定的光荣么?
第一层壳也许是令人骄傲的,它承确受过多少痛苦的磨练和赢得多少初生的欢乐呀!可是,我抛却了它。同样,我又毫无牵挂地抛却了第二层、第三层乃至以后的若干层笋壳,于是,我就在不断的舍弃中获得了自由……
我作了一个梦。当我在清晨醒来时,梦已成为昨天。我无暇去作在暴风雪的嚎叫声里或在春雨滴答的芳馨气息之中的回忆,像梦中抛却笋壳一样,毫不吝啬地丢掉我必须丢掉的昨天。
啊!我作了一个梦——从梦中解脱出来吧——然而,是梦吗?
整首诗的构思以梦境来表现,它强化了诗意的朦胧感,但结尾用一句反问:“然而,是梦吗?”这就把读者又召唤到现实中来。
虚拟式 它与梦幻式所不同的是它不像梦幻那样表现异常心理状态产生的幻象,好像是在写实,但这实和生活的本来样式不同,是虚拟的。诗人打破了生活原有的法则和样式,创造了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象征义的象征体系。如高长虹《手的预言》,诗中设置了“灵魂”和“心”与“生命”和“手”的矛盾冲突。作者让冲突双方直接对话、争论,表现出作者力图摆脱矛盾冲突的渴望和探索精神。“灵魂住在心里,生命住在手上”是虚拟的,而两方面富有哲理意味的对话,却像是两个人的交锋。茅盾《严霜下的梦》中的三个梦境,是把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加以改造,不是以生活的本来面目,而是以潜意识的梦幻形式,赋予了象征的意义。
点化式 就是诗作的象征义由作者点明。全诗一般由具体描绘和点化语组成。如严辰《鸽群》。写鸽群在天空翱翔,在地上觅食,在尘沙覆盖的路上留下足迹,像是在描摹景象,但写鸽群“在迟行的车前引领着,时而跳进路旁的荆棘丛里,去啄食残留的野红枣……”,“振奋地向上飞去”,“像是发着一种崇高的希望似的”,“它们不欢喜硝烟迷漫的战场,它们不喜欢充满了阴毒气息的恐怖地带”,这些拟人的描写,就分明具有了象征意味。最后,作者点明:“带着一份崇高的希望,鸽群扑闪着银灰的羽翅,引领我们向遥远的地方飞去,向着自由与光辉的国土飞去。……”鸽群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象征。象征义的点明使这首散文诗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时代色彩。陈文和的《鸟翅》:
鸟翅,属于蔚蓝的天空;
鸟翅,属于浩渺的海域。
在泰戈尔的《飞鸟集》里,我看见一只只洁净的鸟翅在扑腾;
在贝多芬第五交响乐里,我感到有一对对透明的鸟翅在轻扬;
在《高山下的花环》里,我看见火凤凰般的鸟翅在火焰中飞升……
人的心是一个世界,是一个蔚蓝的天空,一个浩渺的海域,多少奇异的鸟翅就在那儿翱翔……
它飞越过凡鸟不能飞越的时空的界限……
诗人通过虚化,将鸟翅化为感觉,产生朦胧、飘忽的象征意义。鸟翅象征一种思绪、一种情思、一种意识、一种精神,给人寻思的意味。
中国散文诗在表现上的另一特点是意境的创造。按照通常的说法,意境是主客观的统一。境是形与神的统一,意是情与理的统一。它们的完美结合与高度统一,可以创造出“在有限中展示无限”的境界。创造意与境谐的意境,成为中国散文诗人的一种追求。
意境的主客观因素中,情与景是最主要的因素,而中国散文诗人的作品中情与景在意境中的表现则有种种不同情况,表现出不同的特色。有情景交融,浑然一体者;有以情为主,主观色彩鲜明者;也有写景为主,寓情于景者。不论是那种情况,中国散文诗的意境的基本表现方法是虚实结合,创造像外之像,景外之景。其中第一个像和景是实的,第二个像和景是虚的,是由实景启发、引导而产生在读者的想象与联想之中的。读者看到的是作者具体的景物描写,然而他所体验到的则是作家灵感之所独辟的境界。如朱湘《江行的晨暮》。作者用诗人的想象和眼光,描绘了江南小城码头的秋暮和清晨的美好景色。朱湘没有对景物作细腻描绘,而是用精确传神的素描式勾勒。“美在任何地方,即使是古老的城外,一个轮船码头上面”。这一开篇,就为全诗定下了美的基调。作者就是要身体力行,在司空见惯的平凡事物中去寻找美,发现美。接着,诗人就层次分明、动静对照地,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和色彩鲜明的修饰,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码头画景:在暮秋的夜里,清风习习,星光灿烂,渔灯点点,人影簇簇,篷帆片片。作者把一些看似不相关的景物,运用蒙太奇的手法组接在一起,形成了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图画。连一些平时令人厌恶的东西,经诗人的点染和巧妙安排,也顿生诗情画意。如作者是这样来写小火轮的煤烟的:“在烟窗的端际,它是黑色;在船影里,淡青,米色,苍白;在斜映着的阳光里,棕黄”。色彩斑斓的煤烟点染在帆船、鸥鸟、山岭、天空的背景中,读者透过字面就会想象出一幅美妙无比的风景画。作者写清晨的景色也是美不胜收:“太阳升上了有二十度;覆碗的月亮与地平线还有四十度的距离”。“山岭披着古铜色的衣,褶痕是大有画意的”,“水汽腾上有一尺多高”。作者特别强调“清晨时候的江行是色彩的”。浅碧的天空,古铜色的山岭,闪白的鸥鸟,清阔的列树和帆船。人们由这些光影、色彩的描绘中,领悟一种美的诗意,产生一种向往光明、追求美好的情感,体会到作者通过景物描绘传达给读者的发现美、欣赏美所产生的心旷神怡的欣喜之情。这的确是一首意境优美,情思蕴藉的佳构。
散文诗的意境创造,常常是动静结合或动静对比,形成动态美与静态美的结合。如孙福熙的《红海上的一幕》。写落日景象。作者把落日时分瞬息万变的景象,极有层次地描绘出来,极富动感。作者笔下的落日是雄浑的,色彩是绚丽的:“太阳做完了竟日普照的事业,在万物送别他的时候,他还显出十分的壮丽。他披上红袍,光耀万丈。云霞布阵,换起主将一色的制服,听候号令。”雄伟、热烈是落日形象的基调,也是全诗的感情基调。接下去,作者就跌宕起伏地描绘出回落的动态情景:“太阳骤然躲入一块紫云的后面”,顿时使“海面失色,立即又转为幽暗,彩云惊惧,足不敢喘息”。但太阳捉迷藏似的却又出来了,于是“金线万条,透射云际,使人领受最后的恩惠……”。接着,作者跟随自己的背影,窥见了紫帏后那轻步而上的圆月,看到了“月与日正在船的左右”的奇观。最后,写日尽的美丽景象:“水面上的一点日影渐与太阳的圆球相接而结合,迎之而去了,太阳不想留恋,谁也不能挽留……”作者在流动中,以雄浑的笔调完成了对落日景象的描绘,产生一种动态的美。
接下去写月色,则换了一副笔墨:“天生丽质,羞见人世,他启幕轻步而上;四顾静寂,不禁迟回。海如青绒的地毯,依微风的韵调而抑扬吟咏。”“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呵,远胜珠玉。他已高升,而且已远比初出时明亮了。……凉风经过他的旁边,裙衩摇曳,而他的目光愈是清澈了。”写得轻盈,温柔,静谧,虽然也有动态的描写,但都是在渐渐地进行,红云是“渐淡而渐青”,青天是“渐淡而渐红”。
一个雄伟,一个优美,一个动,一个静,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共同构成了动态美和静态美,阳刚美和阴柔美相结合的美好意境。作者激扬的意气也就蕴含其中了。
对一些意象飘忽可感,但却可望而不可即;情景宛然在目,但主旨在可解与不可解的之间的,意在言外的作品,散文诗人有时设置“诗眼”。“诗眼”的设置,旨在揭示全诗之旨,开拓境界,使作品生色,思想感情增辉添色。如冰心《往事(七)》,描绘了大雨中的荷叶覆盖红莲的景象之后,写道:“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的天空下的荫蔽?”赞美母亲的深情点亮了全诗的意境。也有的“诗眼”设置在全诗的开头。如上面谈到的朱湘的《江行的晨暮》,开头一句:“美在任何地方,即使是古老的城外,一个轮船码头上面。”这指示了这篇作品的抒情基调和描绘的内容,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把开启诗人情感闸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