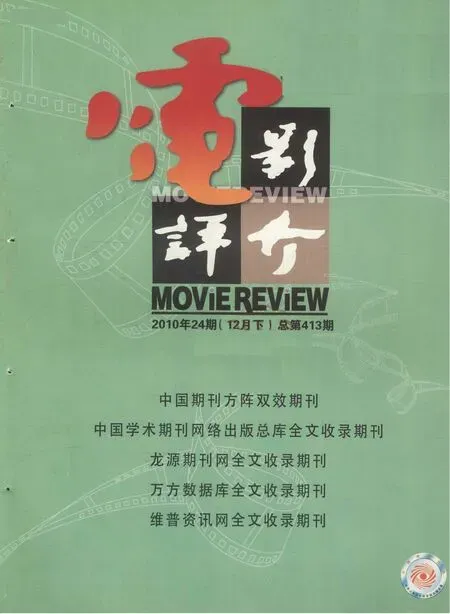红与黑——从华语获奖电影观柏林电影节
红与黑
——从华语获奖电影观柏林电影节
作为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中最为年轻的德国柏林电影节,可谓是华语电影的获奖福地。从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一举斩获金熊奖以来,谢飞、李安、王小帅、王全安也先后“擒熊”,可谓是收获颇丰。而且,从华语获奖电影中便可以清晰看出柏林电影节对于严肃题材电影的偏好,以及对于现实主义题材和小成本制作的电影的关注。
柏林电影节 华语影片 严肃题材 小成本制作
德国柏林电影节从来都不是一场商业化或文艺化的电影集结会,它自诞生之日起便束起柔软的双眸,而以其严肃的政治目光审视现实,凭借着对电影的评定揭示剥离银幕背后的残酷现实。在柏林电影节获奖的影片中,鲜有高额的投资、高调的宣传造势的身影徘徊。尤其是在当下商业大片几近席卷全球银幕的情况下,柏林电影对于小成本制作、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的亲睐,不得不说是对于新锐导演或者第三世界民族题材的电影的一大扶持。而且,华语电影在柏林电影节之中,那些屡屡取得佳绩的影片,深刻印证了柏林这座弥漫着德国人特有的严谨、深沉天性的城市,所装载包罗下的光影艺术,不可能有如戛纳电影节上那四处弥漫的小资情调,也断不能有如奥斯卡红毯上便开始闪烁的迷醉心智的商业张扬。柏林电影节,是纯粹的,它沁在世俗之中,企图用最锋利的匕首,割破现实生活厚重的皮囊,将最为真实的生活本质和人性意识,赤裸裸地摆在观众面前。
一、红:那些闪烁在柏林的华语影像
1988年,张艺谋导演凭借着电影《红高粱》,捧起了第三十八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金熊奖”,也正是凭借着《红高粱》,张艺谋“摄而优则导”,在当时成功跻身于中国先锋导演的行列。不得不承认的是,《红高粱》是张艺谋以导演身份,拍摄得深具思想内涵的一部影片,导演运用电影的造型艺术特性以及重彩的画面色彩基调,将一个原本传统的故事剧本,讲述得绘声绘色,且极具东方的神秘色彩,不仅震撼了国内观众,还大大满足了国外观影者的“猎奇”心理。颠轿、祝酒歌等有关虚构民俗的影像,不仅使得国内观众对于那段发生在偏远西部的故事产生了浓厚的观赏兴趣,更使得国外的观影者们对于这些陌生的、极具远古仪式性色彩的情节设置,大为关注。也是在《红高粱》之后,华语电影的银幕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关“民俗”与“伪民俗”的描绘,大有炫耀中国传统文化之嫌,而这些却正符合了国外观影者的某种对于异域文化的特定审美心理。中国有灿烂的历史文化积淀,以“旁观者”身份出现的外国研究者们,原本就企图在厚厚的历史卷宗中找寻出便易的符号,图解晦涩的文字叙述,将繁杂简化,于是,当最直接、最形象化的影像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必将会喜爱。尤其是当民俗文化遭遇编纂和重塑,徘徊在主流文化之外的时候,外国研究者们会更加感兴趣。
从被乌云黑压压地笼罩着的齐刷刷摇摆的高粱地,到红红火火的弥漫着酒和汗水的酿酒灶,从性格正直刚烈的九儿,到憨厚忠诚的罗汉大哥,《红高粱》在表现特定区域民俗的同时,更多浓墨重彩地描绘的是影片的主人公在特定生活环境中的生活经历,并在影片结尾处将主人公个体和小群体之间的耿直秉性,上升至保家抗敌的民族大义之上,使得影片在立意以及主题的宣讲上面,颇具厚重的历史气质。影片关注的是一群生活在边陲荒凉小镇上的底层小人物,还原他们的现实生活,不论是粗野、嬉笑,还是对“人”最原始力量的膜拜式的影像表征,都在企图用最“真”还原最“美”的往昔岁月传奇。作为对影片中唯一的女性形象的核心主人公九儿的性格特征的塑造,导演是颇费心机的。九儿,在影片中除了代表了人性中最淳朴的美之外,更多的是在代表一种女性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拯救的意识,在女性还是以一种较为弱势的姿态生存在大的社会背景中,当社会还是处在新旧观念革新的过渡时期,或者是旧观念还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这种微弱的女性意识,在通过自我救赎与自我革新之后,演变成一种愈加坚韧、有如“男人”般的刚毅生活态度,愈加显得弥足珍贵。也正是因为九儿由服从“父权”(听从父亲,被迫嫁给麻风病男人)到与男性并肩(带领着烧酒炉里的男人们为罗汉大哥祭酒),甚至在一群男人中处于领导者的身份,都在彰显着电影所传导出来的女人在绝境逢生后,自身所迸发出来的庞大的力量。
当九儿倒在血泊中,鲜红的高粱酒与她血管中炽热的血液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悲壮便油然而生。不妨将最后那个伫立在天地之间的“我爷爷”的庞大形象,形容成对于九儿的一种无限放大后的敬仰,或者对于这种觉醒于乱世的女性意识的一种严肃的坚定。而这也是《红高粱》能够在过往的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中,成为至今都为人称道的经典影片的原因。导演并没有将创作视角,单纯地放在摹写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群体的生活风貌,而是关注制作成镜像的现实背后的人物的性格转变,深刻还原和剖析着大时代背景之下的个体人的生存价值。于是,一个看似偏远神秘的传统故事,在激昂跳跃的阳光的包裹之中,完成了对人性最原始的膜拜与升华。
《红高粱》摘取柏林最高桂冠的近20年以后的2007年,在五十七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王全安导演的《图雅的婚事》又一次获得最佳影片的“金熊奖”。在这期间,华语电影的身影也不断出现在柏林电影节的最高奖项的获奖名单之中。谢飞凭借《香魂女》、徐立功(台湾)凭借《喜宴》在1993年获得第四十三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随后,李安凭借着《理智与情感》在1996年获得第四十六届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影片金熊奖。而《图雅的婚事》堪称为当年在柏林电影节竞赛片中制作成本最小的电影,它的一举成功,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柏林电影节断不像奥斯卡“金像奖”那样嫌贫爱富,它关注的是电影本身所能代表的某种深刻含义,抛却技术主义所能够提供的视觉奇观,它更执着地去坚持着关于现实本身的震撼力。于是,在柏林电影节中,很多小成本制作的影片得以生存且发扬,这也为一批批新晋导演提供了一个良好平等的交流平台。闪烁在柏林的光影故事,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中,显得纯粹了许多。
《图雅的婚事》,可以看作是继《红高粱》之后,又一次女性主义的银幕回归。《图雅的婚事》仍旧是发生在边缘城镇之中的故事,讲述的是蒙古族女性图雅企图要带着残疾的前夫再嫁的故事。影片所透露出来的有关图雅的性格信息,明显已经超越《红高粱》里面的九儿的种种。两人都是在无奈的生活之后,走向自我选择与自我拯救的道路,但是,在图雅身上,镌刻的这种女性自强意识,显得更为强烈。虽然这与两个人物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背景有关。不难看出,《图雅的婚事》,是在包裹着“寻找”主题之中升华出的、又一次对于人性的深刻思考——在个体人面临选择与被选择的时候,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与彷徨。如果说《红高粱》是一种悲壮的、充满英雄的浪漫主义情怀,那么《图雅的婚事》更多的是在传递一种纠结的心酸与悲凉的困惑的情绪。在影片的最后,在图雅的婚礼上,前夫与新婚丈夫之间的争执,以及小孩之间的打斗,将图雅逼回了一个偏僻的蒙古包中。图雅的眼泪流出了一种无可奈何,更将整部影片的颇具戏剧色彩的故事情节演绎,引领到一个狭窄的封闭空间之中,于是,之前被撒落在影片各个角落的不解与忍耐,在一瞬间汇聚,随着图雅悲恸的哭声,顷刻爆发。《图雅的婚事》,本身便在讲述一个也许不被常人所接受的故事,在影片结尾,更像是抛出另一个新的问题:图雅婚后的生活将是怎样。这也是观众们在观影过程中所自然生成的问题。对于这种偏离主流的影片,导演的人文关怀显得格外亲切,而且,对于善良的图雅来说,她所作出的这种最终的选择,已经超越了道德层面上的刻板宣讲。在社会另类的眼光聚集的图雅的婚事上,更多的是在演绎个体人在社会之中,所应勇敢担起的那份责任,有关婚姻,有关亲情,更有关人性中的璀璨美好。
二、黑:那些有关严肃的影像素描
德国人喜欢沉思和自省彷佛是与生俱来一个天性,这便也使得柏林电影节不得不严肃。柏林电影节所倡导的是追求政治性、不要商业性、看淡艺术性的电影理念,在电影节开幕之前便摈弃了许多前来参选的影片,尤其是在当今以商业电影称霸银幕的时刻,花哨的银幕投影比起沉重的主题宣扬显得更有市场销路。但是,如果全世界的电影人都卸“艺”归“商”,那么电影影像本身所存在的价值意义也会慢慢消解,最终沦为商业的直接牟利工具。
张艺谋的新片《三枪拍案惊奇》便是最直白的例子。在2010年第60届柏林电影节上,同王全安导演的《团圆》一起入围竞赛单元,后者凭借着对于海峡两岸骨肉分离后一个家庭的男女主人公重新团聚的故事,获得了当届的最佳编剧奖,而前者颗粒无收,悻悻而归。在国内上映过后便没有取得良好口碑的《三枪拍案惊奇》,却仍旧有勇气走到知名电影节上,争夺奖项,不得不承认张艺谋的自身魄力。但是,也不难揣测到张导的心理,《三枪》同当年给他带来无数荣誉的《红高粱》有着似曾相识的情节构成。《三枪》里,张导仍旧不忍割舍他对民俗的热爱,将东北二人转推至到影片当中,虽然与故事情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间隙,颇有故意摆弄之嫌。张艺谋企图想用这点民俗的东西裹住商业的内容,虽然票房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却不能再次满足国内外观众。除了显现中国民俗之外,《三枪》仍是在讲述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关落后封建的婚姻家庭问题揭示,和《红高粱》所传达的主题大相径庭。但《三枪》更像是一出有关东北“赵家班”师徒的群口小品,这使得原本严肃的主题和原本发人深思的问题,在遭遇过度戏谑化的演绎之后,更像是一场闹剧。几个当红的舞台笑星积聚在一起,演绎一个原本应该是沉重的影片,在热闹过后,注定留不下任何值得回味的东西。
这也表明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审美趣味,就是那些商业气味浓厚的影片,不会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在它面前气焰嚣张。这也是好莱坞电影鲜有出现在柏林电影节上的重要原因。当然,每个国际电影节都有各自的偏好,这也是促进全球电影事业多元发展的重要基石,只是在眼花缭乱中,柏林电影节显得更为真实而已。它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摆到观众面前,将整个社会投射浓缩到普通人身上,企图挖掘新锐视野,来关注在影像背后所蕴含的深刻主题和人性的关怀。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便是这样一部发人深思的影片。影片所讲述的故事,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时期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有几分相似,只是导演将自己的视野投射到了两个年轻的少年身上,年龄阶段的框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影片的独特性。同样是为了一辆自行车,陌生甚至陌路的少年之间先是互相争抢,后来达成了某种共识,就是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段里,两个少年分别交替使用。这也让观众不禁联想到阿巴斯的《小鞋子》中那一对苦命的兄妹,当两人只有一双鞋子的时候,为了确保都能有鞋穿,只能急速奔跑在给对方送鞋的路上。同样,在《十七岁的单车》中,两个男孩达成的这种协议,其实可以看做是对于无奈生活的一种妥协。
《十七岁的单车》是一部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影片,它聚焦的是身为底层的后代,即仍旧摆脱不了困贫束缚的新生一代,他们在少年时期,所经历的生活中的种种焦虑与不安。物质的匮乏不足以使青春的朝气泯灭,而精神的困惑却足以刺穿跳跃的阳光。剥离表面的痛苦,愈发显得鲜血淋漓,由此衍生出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也便显得更加的发人深思。于是,王小帅的《十七岁单车》在2001年获得第五十一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银熊奖。在此之后,王小帅又凭借着电影《左右》在2008年的第五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编剧银熊奖。这一回,王小帅将影像视角对准的是一对中年离婚夫妇,俩人在各自已经组建新的家庭的前提下,不得不重新发生关系,怀上新的共同的孩子,去救共同的孩子。《左右》同《图雅的婚事》一样,讲述的都是跳跃在主流故事之外的较为边缘的话题。而《左右》更多地是在一个不平常的故事之下,提醒观众:人在生活中要时刻准备着做出选择,而这又远没有像开车打转向灯那般简单。
三、结语
2010年的新年伊始,柏林电影节度过了它60岁的生日,在它的生日宴上,仍旧穿梭着话语电影的身影。王全安的《团圆》、中国香港电影《岁月神偷》、中国台湾电影《一页台北》等影片都载誉而归。其实,每一个电影节都有自己固定的欣赏趣味和偏好,这是经历了时间的磨砺,年轮的打磨慢慢形成的。从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奖的华语影片也明显可以总结出它严肃、冷峻、深沉的特点。在技术主义当道的今天,现实与模拟现实之间,在影像上并没有严格的视觉差别,这更容易迷乱观众的视野,将虚幻与现实混杂在一起,继而徜徉在缭乱目光的炫彩画面之中,脱离真实生活中所存在的种种,沉浸不畏迷失。而柏林电影节是真实且现实的,有些影像虽沉重,虽易走向极端,但不能不有所坚持。柏林电影节就像一座山峰,高耸入云端,不轻飘不空洞,带给人厚重的踏实感。柏林电影节还犹如山峰上的一棵松树,不花哨不媚俗,带给人清新的自然感,在商业弥漫的大地上空,还原一个最本真的社会全貌。
[1]高山,《国际电影节:文化输出与观念变迁》,《艺术评论》,2008年第5期。
[2]谢菁,《全球化有没有扼杀柏林?——解读第5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世界电影之窗》,2009年第3期。
[3]胡学纯、宁非,《中外电影大片之比较——从<梅兰芳>在柏林电影节颗粒无收说起》,《剧影月报》,2009年第1期。
[4]张亚璇、郝静班、严潇潇,《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和当代独立电影制作——克里斯朵夫•泰尔西特先生访谈录》 ,《艺术评论》,2010年第4期。
10.3969/j.issn.1002-6916.2010.24.002
雷萌(1989— ),女,山东聊城人,西北大学文学院2009级电影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电影学。
——以电影《图雅的婚事》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