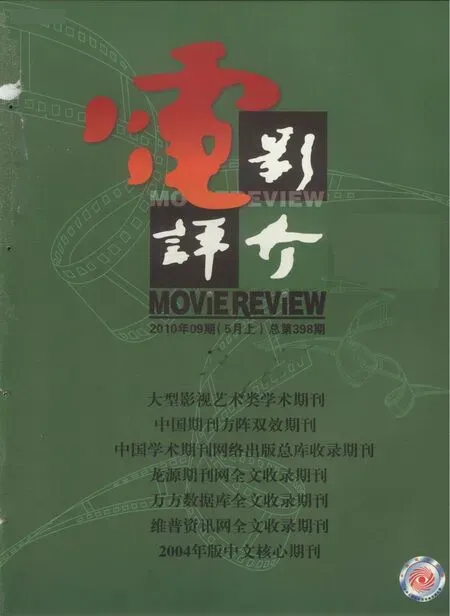贾樟柯电影的声音美学
从《小武》一直到《二十四城记》,贾樟柯都在“用满怀深情的目光凝视着被时代浪潮所改变的人生与生活,并发掘出普通群体在变迁中所呈现的饱满的生命力量”[1],都在以其对电影的个人化理解和极具风格化的声音与影像书写着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到当下几十年来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变革着的中国及中国普通人的历史。其中他对声音这一有声电影以来重要的蒙太奇要素的创造性使用渗透了他的想象和激情,传达出隐秘的意念,使他的影片别具一格。
凸现嘈杂的环境音
环境音的作用在于再现现实生活中的声音状态,使视觉形象获得强烈的现场感。它的存在打破了电影的银幕边框,从经纬两方面延展了画面,使之与生活空间紧密相连。在贾樟柯的影片中,环境音是不容忽视的叙述元素之一。他的每部影片里都充斥着“喧哗与躁动”以及各类流行文化的轮番轰炸。这种把“嘈杂”的声音独立出来的声音处理方式构成电影叙事里和影像始终平行进行的另一种叙事线索。贾樟柯正是通过这种声音美学在他影片中的每一场戏或者每一个细节中有力地强调了他构筑的这个世界中所存在的张力。《小武》中几乎保留了所有的同期声:汽车引擎声、自行车铃声、嘈杂的人声以及广播影视等所发出的声音。影片一开始便听见赵本山小品的声音;当小武伫立在录像厅门口时,里面传来《喋血双雄》的对白。这些都向我们传达着县城百姓的业余生活。而当小武乘车来到县城,广播里正播放着“关于敦促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造成严肃压抑的“严打”氛围。此处采用广播来扩大法制宣传声效,暗示了人物与大环境的冲突:法制宣传铺天盖地而小武顶风作案,广播中命令式的法规与违反秩序的小偷之间的冲突增添了电影的内在张力。而当小武回农村老家时,乡村广播里正把香港回归的讯息与乡民卖猪肉的广告并列播出,形成一种奇妙的声音蒙太奇。《站台》里亦用高音喇叭交代时间的流逝和政治语境的变迁。从文艺汇演《火车向着韶山跑》的报幕到“为刘少奇同志平反默哀”,再到“邓小平检阅三军”,重大的政治事件都作为背景声从广播中依次而出,声音构成了叙事的另一个维度。而在《任逍遥》的开头,广播中反复播放着“山西风采电脑福利彩票”和“中大奖”、“快速致富”的宣传,反映了主流媒介积极参与鼓噪拜金主义和投机心理的社会现实。其中将重大新闻与故事情节相穿插则表现了下层市民与主流政治话语的疏离。不论是北京申奥成功还是中美撞机这样的重大事件都引不起片中人物的反应,而拥挤的歌厅和简陋的野外模特表演却吸引着他们心向往之。可见随着泛政治时代的结束,普通人对政治大事件的关注程度显著下降,电视新闻也被边缘化为空洞不相关的背景音响。《世界》中贾樟柯同样运用声音元素营造空间环境。影片开场就是一片嘈杂,一个简洁的长镜头展示小桃在地下室寻找“创可贴”,然后是地上穿着鲜艳的各国服装的演员们的跳舞场面,接着镜头拉回到幽暗的地下室,底层的拥挤、喧闹一览无余。而有时候“无声”也是一种声音美学。如《三峡好人》中贾樟柯通过现实生活噪音唤起的是远景中江水、云彩等自然景观的静默,而远方的沉默又融入中国现实巨变中的混杂和喧嚣。可以说,贾樟柯电影中那些几乎出现在每个场面里的粗糙的混响音效在配合故事推进的同时都直观反映出全方位转型中的中国的当下社会文化以及我们生存的空间的喧嚣、躁动。他解释说:“我每部电影开头的时候都特别乱,就不会像人家那样很有序的……都是现实给我的压迫感,我觉得世界发展真的是太乱了”[2]“混录《小武》的时候,我要她(录音师)加入大量的街道噪音……这让她开始与我有一些分歧,因为从技术角度讲这是非常违规的作法……到我要她加入大量流行音乐的时候,我们的分歧变成了冲突。我觉得我们的分歧其实来自各自不同的生命经验……在她的经验中世界并非如此粗糙,而我一个土混混出身,心里沟沟坎坎,经验中的生命自然没那么精致”。[3]传统的后期声音处理会把环境中与叙事无关的同期声处理掉,因此已习惯于不杂有“外来”噪音的“干净”的配音的我们会因贾樟柯的电影声带上的噪音感到恼火。但他坚持大量运用各种尘世噪音来代替语言渲染环境,表现人物心理,表现当代生活中难有平静和安宁的时候。这种让我们觉得乱七八糟的从头到尾没有停止过的巨大噪音,在贾樟柯的电影里直接呈现了变化的主题……这些声音组织在一起,在某个特定的场景中表现变化,又在一个很长的声音背景中显示人的变迁。变化在这些声音中发生,一些东西消失了,或被破坏了,但声音却在持续。[4]
方言的大量运用
方言是与老百姓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然语言,是一种地域文化最外在的标记、最底层的蕴涵,沉淀着某一地域群体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人情世故等人文因素,也折射着群体成员现时的社会心态、文化观点、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地方文化的多样性。“而电影恰好是适合方言文本生产的视听传媒,通过方言区居民社会文化生活的再现,在这个公共空间中产生文化自我认同,同时也引发其他方言区的大众对自我联想性的认同”;且“在很多情况下……方言往往化约为颠覆主流文化和经典文本,标示传播者自我姿态的对抗性符号,成为负载传播者群体或个人意识形态的工具。”[5]即方言电影复现现实的原生态,以平民的视角表现普通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可引发观众对电影写实性的认同感、亲切感和信任感;而非此方言区的观众亦可通过这种视听符号的畸变、“陌生化”带来审美快感;方言电影还是草根阶层自我表述并试图掌握话语权的潜在愿望的体现。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全部使用山西方言,而《世界》也以山西方言为主,间以温州话、俄语和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其中导演将北京世界公园这个有着多重隐喻意味的人造景观作为叙事场所,讲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加速城市化进程中大批涌入城市却不是城市主人的外来打工者的故事,将普通人的生存问题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进行哲性思考,直接深入底层社会的肌理,深刻揭示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中国正处在一个意识杂陈、文化拼贴的境地。其中主角的山西方言与公园高音喇叭发出的无地域特征的强势的普通话形成鲜明对比:方言这种边缘性的语言和信息载体在这里成了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不合拍的象征,传递着贫困与落后。而太生对在工地上打工的同乡三赖很快就能用普通话交流感到十分惊讶,边缘文化竭力向主流文化靠近的努力显而易见。而以三峡工程、三线建设等宏大叙事为背景展示个体命运的《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中也是四川方言、山西方言和普通话相混杂。在贾樟柯的声音策略中,方言的运用形成了一个本地化亚文化圈,与此对照,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广播影视等传出的标准普通话则成为一种远离人物现实生活的主流社会的象征。他刻意将方言和普通话并陈来制造一种疏离的效果,凸现影片中的小人物与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的隔膜。
以流行音乐、广播影视等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文化的展示
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流行文化。而使具有时代色彩的流行文化与影片情节和人物情感发生奇妙的融合与背离是贾樟柯电影的一大特点。流行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社会意义在于它被赋予了解构一切宏大叙事并一举超越现代性的期待。依靠大众传媒,流行文化被运作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并在中国最本土地自动地被再生产。这些流行文化反映了充满活力又很粗糙的底层生存状态,表明媒介虽构造了一个世界共享的视听空间,可现实生活空间却存在天壤之别。贾樟柯的短片《小山回家》已预示了他后来影片的音效特征:“‘小山回家’……集中体现多种媒体的特征,就是要揭示王小山以及我们自己的生存状态。在越来越飞速发展的传媒面前,人类的群体被各种各样的媒体包围进而瓦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指标化、概念化,而这些指标和概念又有多少不是被传媒制定的呢?”[6]
《小武》以小偷小武在时代变迁中的失落折射出90年代迅速变动的中国的当下现实。曾与小武患难与共的哥们儿小勇由小偷转而从事更为有利可图的买卖,成为经济改革中的暴发户代表。成了阔佬忙着为自己操办婚事的小勇甚至不愿收小武这个小偷朋友送来的礼金。当小勇为小武点烟时,打火机飘出古典音乐《致爱丽丝》,而影片其它地方运用的都是通俗音乐,这似乎是一个“高贵”的生命向一个“低贱”的生命发出的远离的信号,暗示身份与地位的今非昔比以及两人差距的现实性和不可改变性。而其中充斥着的那些当年最流行的歌曲在唤起观众的回忆将其带进那个年代的同时,也艺术地表达了人物的情绪。在小武去找小勇时,歌曲《霸王别姬》就是小武的心声:“我心中你最重,悲欢共生死同……”,那时而高亢时而温柔的旋律反映了小武对儿时美好回忆的珍惜以及现在去找小勇时内心的矛盾与不平静。小武黯然离开小勇家,来到餐馆借酒消愁时飘出《心雨》忧郁的旋律,这无非是对逝去友谊的感伤与祭奠。而与歌厅小姐梅梅的一段交往是小武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梅梅唱着《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出场,唱得小武心花怒放,心甘情愿多花50块钱去跟她压马路、打电话、做头发。在梅梅做头发时,录音机里播放的《大花轿》暗示了这段感情的萌芽。在小武去看望病中的梅梅时,她为小武唱起了王菲的《天空》“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我的天空为何总是灰的脸……”,这首歌恰似梅梅生活境遇的写照,她不禁掩面而泣,为自己梦想的破灭、生活的艰辛以及看不到的未来而泣。他们在歌厅合唱《心雨》“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让我最后一次想你”,这忧郁的旋律预示着这段感情会是一个无言的结局。而节奏最强的是两人在KTV中一段MTV式的桥段,在《爱江山更爱美人》的音乐中,小武醉了,镜头切换到小武的结婚喜宴,他正爽快地与兄弟们敬酒,然而这不过是一瞬的梦,欢快的节奏与冷漠的现实构成强烈的反差。而影片中还对电视声音的权威性提出质疑:第一次是电视荧屏点歌栏目去小勇家采访并为其新婚点歌。主持人在镜头前对他作为企业家的“贡献”大加褒扬。他贩卖香烟和妇女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成为先进的企业家代表,呈现在电视(官方/主流媒体)屏幕中的形象无疑充当了社会仲裁者的角色。第二次是电视台采访“严打”时期的路人和公安局长,电视话语以维护社会治安的喉舌出现,加深观众对主流媒体权威性的认定。第三次是电视台播出小武被捕的新闻。这三组电视新闻对人物进行了道德宣判:小勇被塑造成一个受人尊敬的楷模和体面人,而小武却从电视中看到了自己被当街示众的屈辱。这种微妙的对比揭示了当下实用主义和金钱主义盛行下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面对电视作出的价值判断,观众往往会不加思考地接受,而导演此番同时构筑电影镜头与电视镜头的双重语境,对峙镜头内的虚假与真实,试图颠覆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威。
《站台》的时间横跨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时代变迁的“宏大史诗”与汾阳文工团的演员们的个体生命轨迹混杂交织。在时代大潮中他们由文工团演员沦为大棚演员漂泊演出,在漂流中他们丢失了爱情,破灭了理想,葬送了青春。这无疑是作者自己的青春祭语:“9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沉闷压抑的气氛和市场经济进程对文化的轻视和伤害,让我常常想起80年代。那正好是我由十岁到二十岁的青春期过程,也是中国社会变化巨大的十年。个人动荡的成长经验和整个国家的加速发展如此丝缠般地交织在一起,让我常有以一个时代为背景讲述个人的冲动”。[7]在影片中时代变迁的标识是大众流行文化的更迭而不是精英文化的展示。导演提供了一种个人化的对于“80年代”的“现代性”叙述,而不同于通常所理解的以“启蒙”为主题的宏大历史叙事。《站台》序场就是文艺汇演时高音喇叭的声音。对为何如此安排,贾樟柯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这么多人在此集结,听命了高音喇叭中某人的声音,只是这一幕让我幼小的心灵过早地有了超现实的感应,直到29岁时仍耿耿于怀。我不得不把它拍成电影,成了《站台》中的序场。而高音喇叭贯穿迄今为止我现有的作品,成了我此生不能放过的声音”[8]。而开场的歌舞表演《火车向着韶山跑》是典型的革命文艺,几个人排队坐在木凳上模仿穿越中国前进的火车头,滑稽的表演方式充满了集体主义的乐观。“然后慢慢开始有通俗文化……刘文正啊,邓丽君啊,张帝啊,都是那个时候的,慢慢大众文化传到汾阳这样的地方以后,你就觉得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它……不单是一个歌的问题,是一种新的生活。”[9]即到了80年代,人们开始寻找自我的意义,流行文化开始出现。最早是来自港台的流行音乐打破了革命文艺的专制,使文化出现了多元的状态,意味着中国人挣脱了集体的束缚,获得了个人的世俗生活。在《站台》里用了很多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歌,如《站台》、《在希望的田野上》、《美酒加咖啡》、《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青春啊,青春》、《是否》、《好人一生平安》等。“我们从这些老歌里获得了某种认同,好像就是认同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娱乐方式……老歌记录历史,老歌表现现实……老歌的功能已经有了从宣传到娱乐的转变,这正如文工团的体制改变了一样。”[10]其中还穿插了不少八九十年代的影视剧片断:如印度电影《流浪者》,电视《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渴望》等。可以说,《站台》是考察文革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标本。
《任逍遥》讲述了两个下岗工人子弟彬彬和小济在爱情、友情、亲情、学业的纠葛中寻求出路的故事。《任逍遥》贯穿影片始终,彬彬和女友反复吟唱这首歌,当派出所民警要求他唱一首拿手的歌时,他本能的反应就是唱《任逍遥》:“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让我苦也好,让我累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影片在彬彬在派出所里一遍遍重复的《任逍遥》的歌声中结束。“任逍遥”从字面来说是要“挣脱一切尘世的束缚,争取绝对的自由,达到无所拘泥、随心所欲遨游于天地间的境界”,然而这只可能存在于精神世界中。而强调个体的欲望感受和个性张扬的流行文化则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价值观,从而赢得了这几名小人物下意识的拥护。文化舶来品“美国大片”的情节提供了打劫银行的灵感,迪厅用来发泄精力,当代港台流行文化消解着主流话语的影响。而不断插入的主流媒体的严肃的电视新闻播报不仅交代时间线索,更传达出权利话语的舆论指向。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源构成了一个含混的意义混合体,对无业少年的精神世界共同产生着影响。但这些信息源并不负责解决生活的困境和提供一个实在的出路,因而个性的觉醒与生活的沉闷之间最终产生了冲突。这指出了流行文化包裹下的社会不能摆脱贫困和压抑的阴影,现代性与前现代的战争并未终结。[11]当被问及“在你的影片中,声音元素和影像元素看上去经常是矛盾的、对立的。你的影片里经常有收音机、电视机的意象,或者是声音……表现出古老县城里很现代的一面,现代性元素即使在落后地区也是无孔不入的……但跟我们看到的视觉形象却有着反差”时,贾樟柯说:“转型时期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地区之间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差异。在这个差异的背后又有一个很统一的东西,就是媒介提供的这个统一性。比如在最贫穷、最偏僻的地方打开电视机看到的却是来自城市的信息,最新的服装发布会、汽车广告。现实的生存和媒介化的空间之间是脱节的,这种脱节在《任逍遥》中就有比较夸张的表现。”[12]
《三峡好人》中大众流行文化的穿插也很突出。其中自诩为“小马哥”的人物的点烟动作、穿着打扮、行为方式和《上海滩》的主题歌的手机铃声等即是对周润发扮演的“小马哥”的致敬。其中还借用了80年代初传唱很广的歌《酒干倘卖无》来集中体现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追求。而韩三明的手机铃声“好人一生平安”直接涉及《三峡好人》中的“好人”。沈红在露天舞厅等丈夫时,音乐《潮湿的心》响起,抒发她落寞的情绪。韩三明碰到一个小男孩,他正扯着嗓子唱《老鼠爱大米》,而沈红碰到他时,他唱的是《两只蝴蝶》,小男孩是那么用心用情地唱着这两首当时流行的网络歌曲。片尾韩三明驻足回望,高空中一个人在废弃的两栋楼之间走钢索,伴以《望家乡》的苍凉唱腔。影片全部叙事、人物的命运和不确定的未来都凝聚在了这个场景中,表明韩三明以及追随他离开三峡前往山西煤矿“找活路”的打工者们的前途如同高空走钢索一样危险与渺茫。
有声电影的出现使电影由一种纯粹的视觉艺术变成了视听结合的新艺术,使电影能同时以人声、音乐、音响三种声音的相互交织向观众倾诉和表白。贾樟柯的影片正是通过各种杂乱的声音与画面一起共同阐述了现代人被各种声音和影像所侵扰的生活实质。他说:“我就是在这种大众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在普通民众的趣味中,我感受到了人们朴素的希望以及朴素本身所具有的悲剧力量。”[12]他的影片可谓是个人的民间的历史记忆的银幕书写。
[1]《2006年度十佳国产优秀影片新鲜出炉》,《电影艺术》,2007年第2期。
[2]张会军,薛文波主编,《银幕追求:与中国当代电影导演对话(二)》.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第171页。
[3][7][8]贾樟柯.《贾想:1996-200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98、100、85页。
[4]《〈三峡好人〉:故里、变迁与贾樟柯的现实主义》.《读书》,2007年第2期。
[5]邵滢.《声音的意义:从方言电影说起》,《当代文坛》,2005年第6期。
[6][13]贾樟柯.《我的焦点》.蒋原伦主编,《我们已经选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2、43页。
[9]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第343、368-370页。
[10]孙昌建.《我的新电影手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98-99页。
[11]伍国.《流行文化的困境:〈任逍遥〉中的后现代性与现代性解读》.《贵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2]《三峡好人》.《当代电影》,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