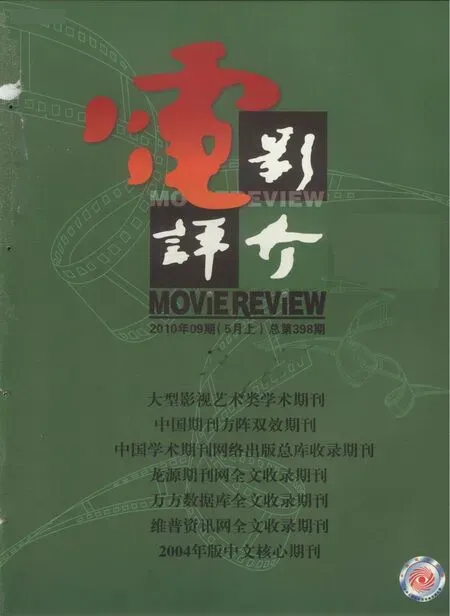一个关于网络社会媒介图景的“警世通言”——简评影片《天生杀人狂》
相信大部分看到这个片名的人,都会有些惊悚感,或许在这种惊悚感中还会夹杂着一丝不屑的意味:片名又是一个想靠耸动性吸引眼球的刻意之物。不过,笔者曾经就是被这样的耸动性所吸引而走进了电影院。后来,我才知道,《天生杀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是由美国著名导演奥利佛•斯通(Oliver Stone)执导的,1994年8月上映,并囊获了当年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委会特别奖(Special Jury Prize)。
直到今天,许多影视专业开出的值得观摩的一长串影片名单中,常常会见到这部片子的名字。我不知道专业学习影视制作的学生,在将该片作为观摩对象时的观影感受。毕竟,很多时候,当我们把一部片子作为研究对象和作为一个纯粹的消遣物时的审美接受心态是肯定有差异的。
笔者清晰地记得自己在2002年第一次接触该片时的情景。那天,影片开映时,观影厅里大概坐了30多人,等影片放到接近半个小时的时候,观影的人只剩下了4个,而这4名观众里还包含了一对窝在角落里谈恋爱压根不看屏幕的小青年。所以,那一天,这部获得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的影片真正的观众只有两名——我和我的朋友。而我俩在该片放映的前20分钟时间里,也是几度想起身离场的。
这样的市场反映,对于一部影片来讲,是否算有些失败?毫无疑问,《天生杀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不是属于大众的。至少不属于21世纪初的中国观众。当时间的指针指向当下,当大部分的国人已经习惯了互联网化的信息生存环境时,我们再回头看这部影片,将会充满唏嘘之感。尤其是2010年跨年的几件网络狂欢事件,比如“兽兽门”,这些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就像是影片《天生杀人狂》在当下的一个折射。
《天生杀人狂》94年在美国放映的时候,上座率还是很高的,但评论界争议很大,褒与贬的声音同样的响亮。而在英国,《天生杀人狂》连等级评定都没通过,但在威尼斯电影节却拿了个评委会特别奖。这种奇怪的组合,我们是否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影评来介绍它:这是一部很好的片子,这又是一部很坏的片子。
大部分观看过该片的人,都会觉得本片的影像叙事手法使人“眼花缭乱”, 看上去很累。事实上,这个也是导致当年我第一次接触该片,却在影片放映的前20分钟里几度想起身离场的原因。就视觉观感而言,在一部讲述杀人犯的片子里,充斥着大量的重金属、朋克音乐以及非常摇晃的镜头和大量拼贴的一些带有隐喻的图像、肥皂剧片段,的确不是件让眼睛以及心灵舒服的事。有人总结,该片的镜头切换在2500个以上,而一般电影的镜头切换在600至700个之间。其实就这一点而言,这部片子恰恰值得影视专业的学生观摩,这正是导演奥利佛•斯通高明的地方,这些大量且非常摇晃的镜头片段,每一个都恰如其分地为片子的叙事主题以及影片基调而服务,这可不是所有的导演都能做得好的。并且,这个影片的主题,至今来看,仍然充满了意味,其对于媒介社会的反思力度,无疑是一个关于当代媒介图景的“警世通言”。
在美国有大量的影评家在肯定该片拍摄手法、叙事手法以及该片所蕴涵的对传媒业的反思力度的同时,同样毫不客气地指出该片宣扬了“暴力美学”,对该片中的“暴力场景”予以了严酷的批评。
尽管我们不知道导演的真实想法究竟是想靠“暴力元素”博取上座率,还是是想将“暴力”作为一个叙事载体,用以载入他对传媒业的反思。但作为观赏者,我们有阐释的权力。笔者认为,《天生杀人狂》比另一部声名卓著的媒介反思影片《楚门的世界》更加冷峻和犀利。
奥利佛•斯通使用倒叙的手法,在影片一开场的时候,给观众端上了一个血腥、惊悚的大餐——在一个充满了乡村情调的小酒馆中,一对看上去很嬉皮的小青年Mickey(米奇)和Malory(梅乐莉)在这里开始了一场肆意的杀戮,而他们进行这场杀戮的原因看上去竟然是没有原因。随着影片叙事的推进,我们了解到两人的成长经历,他们事实上都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米奇从小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而梅乐莉则更可怜,直到成年后都还会受到来自父亲的性骚扰。所以从人格上讲,这两个人一直是亚健康状态,以弗洛伊德的理论来看,“童年阴影”会对人造成终身的影响,童年包括青少年期间所遭遇到的恶劣事件可能会使人心理扭曲,除非能疏解它。而米奇和梅乐莉所找寻到的疏解口就是“爱情”,两人一见钟情,两个从没享受过家庭温暖,没有享受过爱的人,靠在一起相互取暖,通过这样的一种组合找寻自己所缺失的“爱”。不过遗憾的是两人爱情的结晶竟然是“杀戮”,他们合作杀死了梅乐莉暴虐的父亲,然后开始携手逃亡,在逃亡的路上,他们一路继续杀戮,受害者共计50多名。杀戮在他们眼中,就像儿童玩游戏一样,成为了一件简单、随意而且有趣的事。
两个暴力的受害者彻底变成了暴力的施予者,成为了无可理喻的“杀人狂”。这是导演奥利佛•斯通(Oliver Stone)在影片的前二十分钟里,通过大量摇晃的镜头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充满隐喻的“杂耍蒙太奇”,告诉观众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该片叙事的一条明线。
而另一条叙事线条,在影片放映近30分钟的时候浮出了水面。这也使得该片跳出了一个单纯的暴力犯罪类型片的窠臼。影片中突然拼贴进许多新闻媒体——电视、报纸、杂志等疯狂炒作米奇和梅乐莉的镜头,在媒体的密集报道和深度追踪下,米奇与梅乐莉成为了全美闻名的新闻人物。不少青少年面对媒体镜头,竟语带崇拜地把米奇和梅乐莉的行为界定为“cool(酷)”。看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奥利佛•斯通没有辜负人们向来对他的赞誉——“最具社会反思精神”的导演。这一次,他毫不客气地撕开了媒体的皮。他告诉观众:两个“杀人狂”不过是媒体狂欢的对象,不过是媒体博取观众/读者眼球的利器。
影片中有这样一处对白:
问:“蛇,你问什么要咬我?”
蛇答:“因为我是蛇。”
我们借鉴一下:
问:“媒体,你为何要炒作?”
答:“因为我是媒体。”
是的,毫无疑问,媒体将天然的同暴力、性、犯罪、丑闻等联系在一起,正如新闻学概论里所提到的,美国堪萨斯州《阿契生市环球报》的前主编爱德华•霍的那句名言“凡是能让女人大喊一声‘哎呀,我的天哪’的东西,就是新闻。”[1],在西方新闻学里都是具有报道价值的。
就在笔者以为已经理解到影片精髓的时候,却低估了奥利佛•斯通对于媒介社会的警觉性在94年就能抵达的深度。影片的后半部分讲述了一档名叫“American Maniacs(全美狂人)”的新闻节目,该节目的主持人韦恩•盖尔为了做不一样的追踪报道,去到米奇和梅乐莉被捕后囚禁他们的监狱,他鼓噪想通过“杀人狂”博得政治支持率的监狱长以及想变得更加出名的米奇,使得一场对“杀人狂”带有灵魂追问性的现场直播在监狱里成行了。镜头前,主持人韦恩•盖尔追问得口沫四溅,看上去比“杀人狂”米奇更加狂热,他表现得崇高,但事实上他压根不关心什么道德和灵魂层面的东西。他只关心摄像机有没有记录下米奇另类、劲爆的神经质式的内心独白和犯罪语录。看到这里,实在让人唏嘘不已,因为我们知道,在现实的媒介社会中,像韦恩•盖尔这样的新闻采访者,绝不是个例。
不过,就在我们的唏嘘尚未结束的时候,奥利佛•斯通又给观众上演了一场90年代版的“越狱”。监狱暴动了,而暴动的原因竟是正在收看米奇直播访问的囚犯们被米奇狂热的话语给鼓噪的。于是米奇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劫持了主持人和摄像机,并成功救出了他的爱人梅乐莉,而整个监狱暴动的景况以及他本人的“壮举”也被摄像机如实摄录下来并直播出去了。
越狱成功后,米奇和梅乐莉用枪指向了主持人韦恩•盖尔,韦恩想求得一条生路,于是找了若干理由,他问米奇,你们杀戮后不是总要留个活口用以讲述你们的故事吗?米奇答道:“它会帮我们记录的,你的摄像机”。说完,毫不犹豫地射杀了韦恩•盖尔。
这真是个绝妙的讽刺。新闻采访者被他用尽心思追逐的报道对象绑架了,原本他沾沾自喜,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一切报道尺度和发布权都在自己手中,结果,“被掌握”和“被绑架”的反而成了自己。尤其是当新闻当事人掌握了媒介介质后,更是彻底地抛弃了报道者(记者)。看到这个结尾,我一度怀疑导演奥利佛•斯通是个媒介预言家。《天生杀人狂》就像是个关于网络社会媒介图景的预言。而这个预言,通过米奇之口说了出来。
是的,谁拥有了媒介,谁掌握了媒介制作和发布介质,他就可以记录他所想要记录的东西,并将其发布出去。
尤其是在网络时代。
在以往在互联网没有出现的年代,媒体还拥有相当的把关权。可是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当越来越多的大众已经习惯将网络作为一个媒介发布和信息接收平台,当越来越多的别有用心的人已经熟捻了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信息编码方式最能引起耸动、最能吸引网民眼球后,这一次,他们将传统媒体和记者给彻底地抛弃了。因为他们已经自己掌握了信息发布介质——互联网。“互联网”会帮助他们“搏出位”。而大量的媒体以及公众就只能沦落为“被掌握”、“被绑架”的一方。公众就像待宰的羔羊,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下一次,又会是谁,又会是怎样的劲爆事件,一夜之间像幽灵般出现在互联网上,在WWW里掀起一场场的“狂欢”。
回头梳理近期的几起网络狂欢事件,尤其是各类艳照事件,这些事件究竟是当事人在炒作,还是媒体在炒作,或是当事人与媒体合谋炒作,真相是什么,其实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合谋夺取、“绑架”了公众的关注度和眼球。
记得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他那本享誉盛名的关于讨论电视文化取向庸俗的批判性读物《娱乐至死》的开篇中,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恶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2]
所以,要小心了,小心我们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譬如,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互联网发布权限的相对自由性”。这种自由性可能正被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或是利益团体“绑架”。更可怕的是,在万维网中,还有很多人追逐和模仿他们的“秀法”,从而导致形形色色的各路网络“艳照门”层出不穷,看上去永无止境。
在互联网时代,在人人都能轻松地成为自我影像的记录者和发布者后,我们也许还需要记住:人类应该学会控制的除了技术以外,还有——道德!
注释
[1]《新闻理论教程》,何梓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2]【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