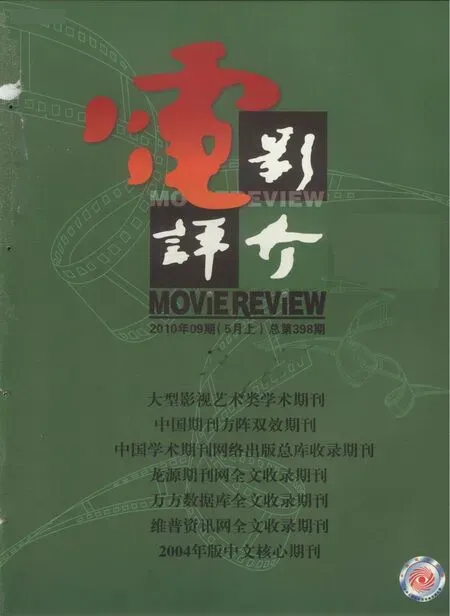从电影《革命路》看男权松动时期的女性突围
“19 世纪的工业革命把生产力功能从家庭中剥离出来, 妇女的劳动从私人领域进入了公共领域。从此性别的不平等从隐性、个人性走向了显性、社会性。”[1]乍一看这句话会觉得有点问题:女性有了参与社会劳动的机会,就有了梦寐以求的自由,还不能够如愿以偿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握生活的支配权、实现个人的自我追求? !“性别不平等的显性、社会性”从何说起?具体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电影《革命路》用一个回归家庭的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上述问题的答案,由此可以窥见男权松动时期女性解放历程中的社会现实壁垒以及女性自身存在的问题对女性发展带来的影响。
故事梗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艾普尔——一位心怀入职梦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原本希望融入社会,体现自己的个人价值。不料婚后接二连三地怀孕、做母亲,她不得解脱。由于害怕从此丧失对自我命运的把握,她利用一切机会寻找走出家门的突破口:参加业余演出,希望就此获得突围的机会,却因演出失败而未能遂意;丈夫弗兰克三十岁生日那天,艾普尔看到丈夫多年前在巴黎拍摄的相片,联想起丈夫对自己工作的抱怨和他对巴黎美景的描绘,由此产生了一个举家迁居巴黎的想法并且说服了丈夫。万事俱备之际,丈夫偶然一次在公司的信口开河竟被公司老板奉若神明,老板用加薪晋升的诱惑拢住了丈夫。丈夫心动,以艾普尔的再次怀孕为由放弃了移民巴黎的打算。艾普尔陷于绝望,自己动手人流而殒命。
男权松动时期女性自我预期与社会预期之间的矛盾带给女性的身份焦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虽然没有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女性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在职场谋得一席之地,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的。由于社会劳动赋予的独立自由,女性在相当程度上能够个性化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自由支配生活的内容,甚至能够左右家庭事务的决策。在自由的呼吸中,女性的视野得到拓展,女性的一切活动展示的是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本真形态和姿态,她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对个体存在的意义也有了社会属性:个人价值的实现必须以社会认可为驱动、以社会意义为目的,而独立地展示自我、表现自我就是人生最大的荣耀。带着这样的自我认知,女性断是不会再把目光转回家庭,把自己与传统妇女的角色捆绑在一起的。
影片中的女主人公艾普尔在没有获得任何其他可靠的谋生手段之前,她所钟爱的演艺事业就是她参与社会活动的最佳发力点。然而,无论她的个人意愿如何,男婚女嫁的人生阶段到来,自然赋予的生理秉性毫不含糊地将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的“紧箍咒”罩在她头上,她心底的自我追求与恪守传统的纠结就不可避免。难得一次业余演出机会,她指望自己能够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展现出为人认可的表演才华,由此为自己走出家门找到充足的理由,实现自己对生命意义的承诺。但是由于终日沉湎于家务,艾普尔没有时间揣摩表演、提升演技,她在丈夫面前的演出强差人意,没了入职的敲门砖,她重新踏入社会的愿望化为泡影。为此,她恨自己的不争气,却无法向丈夫明言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丈夫的劝慰更加深化了她对自己所陷困境的无奈感和绝望感。社会身份求而不得,灵魂出离的艾普尔不在状态中,走不得留不得(can’t stay, can’t leave), 陷入一种身份焦灼的状态悲哀不已。
艾普尔的经历使我们看到,女人在做母亲时,她的“生理命运”[2](西蒙娜•德•波伏娃语)就成了她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男人把女人变成母亲,男权统治就可以时间要素和下一代的牵绊---怀孕和哺育---为延展,耗磨女性的意志力,扼杀了女性生命的活力,剥夺女性做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最终阻绝女性自我发展的可能。理论起来,男人还可以振振有辞地用爱的名义堵女人的口:“你不愿意拥有和抚养我的孩子,你就不是真的爱我!”“你不爱我,呆在我的房子里干什么?! (当艾普尔说想做掉怀上的第三胎时,丈夫弗兰克如是说)”足见男权统治的冠冕堂皇、有恃无恐。处于这样的统治之下,无论女性所处的家庭环境多么优越,无论女性的丈夫对自己的妻子多么贴心,家都不过如艾普尔所说是个“陷阱”、一个生生把女性置于其中为所欲为地实施控制的“温柔陷阱”。在这个陷阱中,身体成为“性别政治角力的主要场域”[3], 弱势一方的自由不过是个画饼,强势一方的控制是绝对控制。这种绝对控制给有过独立工作体验的女性造成的压迫感和屈辱感显然要比其带给纯粹的家庭妇女的压迫感和屈辱感大得多。
再者,即便女性获得了参与社会劳动的机会,能够在外抛头露面,她还是免不了有再做母亲的可能性,那就自然回避不了相夫教子传统角色的如影随形。届时,工作与家庭都兼顾,女性所背负的责任会比全职母亲重得多。就是说无论去留与否、工作与否,女性的生理特征和社会传统都注定了女性在家庭俗务这件事上的逃无所逃,于是在社会劳动这个问题上显出的男女两性生理差别就成了女性谋求独立的第一道坎。影片中的艾普尔身处男权统治初显松动的社会,刚踏入社会便迫于“生理命运”回归传统,她的注意力还只聚焦在自我的独立自由和社会身份的重获上,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职业女性身份的双重性,也不会自觉生发平衡心态、调整自我状态的能力。艾普尔不顾一切地乞求自己的个体人格与男权统治下的女性传统角色彻底绝缘,说明她对社会现实缺乏认识,她的执拗不仅把自己逼上了自我幽闭的死胡同,还使她的婚姻生活严重缺氧。影片向我们展示的这一幕说明,女性要谋求自我解放,她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两性生理的不平等现实给她出的一道难题:“如何在自我价值的追求与传统角色的纠结中找到平衡点”?
女性突围失利暴露出的问题
从艾普尔移居巴黎的计划中我们看到的是,男权松动时期由于女性的职场经历极其有限——大多不过是男性的陪衬或者附庸(如艾普尔丈夫公司里的女性打字员,艾普尔自己去巴黎打算谋求的秘书之职),她参与社会活动的范围也大受限制,这就使她对社会的认知严重贫乏而简陋,她无法从自身的社会阅历中寻找相应的坐标点,形成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认知体系,也不可能在具体事务的处理和决断方面表现出独立性和自主性,那么在家庭的囚笼中困极之时她所依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以男人的认知和经验为基础---丈夫认为巴黎是世间最美的地方,那就去那儿了却心愿。但是,“我们所感受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它们经过解释后之物”[4]。艾普尔有所不知,巴黎的美好只是其丈夫站在游客角度阐发的感受,这种感受与真正的居家过日子的感受是两码事。再者,待她置身巴黎,她所获得的关于巴黎的切身体会未必与其丈夫相合,加上她对欧洲的秘书工作并没什么实质性的了解,她如何能够保证自己去了巴黎一切都能够顺遂心愿?!仅就这一点而言,艾普尔的天真可见一斑。
当然,仔细推敲艾普尔的移居计划,我们发现艾普尔此举的目的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所谓移居巴黎,艾普尔潜意识里寻求的是一种女主外男主内的理想生活:到了巴黎她外出工作,从此她获得自由,在具体的社会工作中找回自己被传统角色一再埋没和否定的生命意义和生命“真实感”;她成为自我的主人和家庭的主心骨,掌控一切把握大局,独立安排生活的内容。但她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男人是本能的社会动物,养家糊口是他的天职,他会向人抱怨工作的程式化和了无意趣,但他绝不会仅以兴趣和理想为出发点看待工作和生活。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优渥的待遇和晋升的空间,男性的功利心和现实本性就会让他拂去心底纯粹的理想,重振精神,披挂上阵。在这种情况下,女人经济上不独立,还要把自己的梦想“寄附”在男人身上,企望通过男人积攒的经济资源和男人做出改变来圆自己的梦,委实幼稚。
人“只有把自己作为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才能能动地驾驭物,实现人的现实价值”[5]。 艾普尔从家庭中突围回归社会的根本保证是她足以独立、自主形成对社会现实的客观认识和对自我实现途径的认知把握。不幸的是,母性、妻性在埋没艾普尔的个体人格的同时,还将她的视野禁锢在狭隘的一隅,使她长久地陷于此时此地的境况中期期艾艾,没有平静宁和的心境和心绪从容地应对家庭生活、理性处理自己与丈夫的关系,她又怎么可能跳出自我的陷阱客观地认识社会、并结合自身的状况为自我的发展做出合理的规划呢?其实,艾普尔有救,最适合艾普尔的点穴宝典就是她丈夫弗兰克工作环境中的“库存管理”信条——knowing what you’ve got, knowing what you need,& knowing what you can do without。可惜她不能意识到这一点,最终她孜孜以求的巴黎梦不过是她逃避现实的绝好借口,一个她一厢情愿地在头脑中构建的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最后,梦破魂散,就算艾普尔用自己做人流的方式终止妊娠来与命运抗争,期望以此决绝地摆脱男权强加在她身上的桎梏,也于事无补。从这一点而言,艾普尔的悲剧是其自身的幼稚和自我设限所致,看来不解决女性自我意识和认识方面的问题,女性的解放断不会从天而降。
结语
“妇女问题的特殊性, 不仅在于它集中展示了以两性关系失调形式表现出的人类社会的失衡式发展, 还在于它深刻地揭示出人-社会- 自然关系中对妇女这一半主体力量存在的忽视, 更在于其中对女性价值、女性作用与影响的抑制⑥”。从这个意义而言,女性突围走出家门,就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公然昭示天下,男女之间的关系以及男性、女性的思想意识不经历一场颠覆性革命,仅仅依靠女性走出家门这个简单的动作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是不现实的:因为没有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的理解和支持,女性的自由很容易遭到男权统治的侵蚀与消解;没有女性思想的独立和对自我意识的反省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客观认识和把握,女性自我发展的道路一定曲折不平,女性到手的自由可能被其自我的设限所葬送。另者,自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单元在男权统治的社会崛起的那一天起,如果她们只是强调个体的自主自立、只是想当然谋求与父权体系的脱钩或者反动而不能客观地从两性和谐发展的角度去认识自我、认识另一半,只会造成两性关系的冲突或者灾难,也无益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虽然艾普尔的时代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她的经历对今天的妇女解放运动而言仍有不可忽略的启迪作用。
[1][6]汪洋,王义桅.妇女问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J].《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p34-39.
[2]何晓涛.父权制道德观影响下的女性抉择困境— —剖析伍尔夫的小说《达洛卫夫人》和《到灯塔去》[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年 04期 .http://www.benkelunwen.cn/article/2009/1124/article_4901.html.
[3]朱崇仪.玛格丽特•艾特伍对女性伦理困境的呈现.http://rchss.nchu.edu.tw/chi/plane03i.
[4]弗洛伊德、阿德勒、皮亚杰等.心灵简史[C].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p32.
[5]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2005/07/15.http://www.sina.com.cn.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