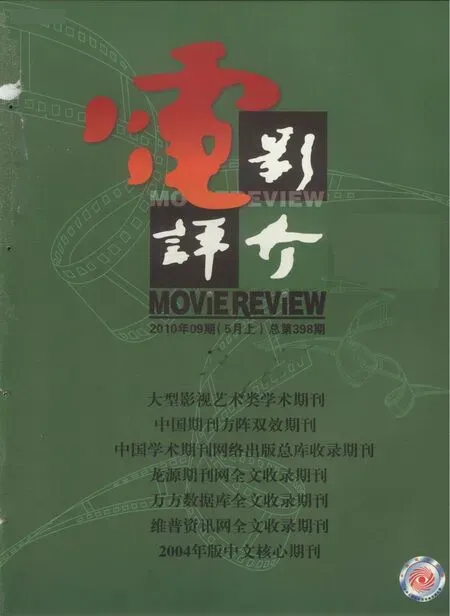浅析电影《十月围城》的修辞手法
《十月围城》自上映以来好评不断,被誉为“年度最佳华语片”,荣获了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多个奖项。作为商业电影,《十月围城》并没有一味地迎合大众,而是以一种建立在观众需求——票房价值基础上的修辞策略和“艺术”翻新来吸引和赢得市场效益的。影片除了讲述故事外还给了观众一种特别的审美感受,这与影片中的修辞格运用是分不开的。因此本文试图从影片修辞手法的形态特征、表意功能的研究和把握上,分析《十月围城》作为商业电影的成功之处,以期能为以后的电影做出些许参考。
一、长镜
电影艺术中的长镜头概念其实是一个并未严格界定的概念。对电影艺术而言,“长镜头具有美学意义,因为它在不同程度上的运用影响着(影片的)流畅、氛围和拍摄重点。”[1]
影片中沈重阳追着载有自己女儿的黄包车奔跑的段落,就非常好的运用了长镜。影片中沈重阳跟着车子一路奔跑,在跟移镜头下,影片将多个不同机位的摄影机所拍摄的画面和剪辑在一起,构成了流动且富有意蕴的画面。在这个长镜头里,除了跟移镜头外,影片还将奔跑中的人物两处面部特写镜头进行了升格处理,重点刻画了人物的面部表情。沈重阳跟着车子一路奔跑,眼里的神情错综复杂,有得知自己有一个女儿的惊诧和喜悦,也有对往昔的追悔和对当下的无奈。黄包车停下来以后,沈重阳只是眼巴巴的望着女儿却做不得声,当音乐再一次达到高潮,黄包车离去了,而沈重阳在画面里也越来越远,越来越小。长镜头段落首尾呼应,开始时沈重阳追赶黄包车和结束是黄包车的离去形成了一个颇有趣味的画面构图。这种饱含情怀的长镜辞格的运用,使得摄影机对沈重阳这个人物的“持续关照”显得非同一般。从叙事意义上,这个长镜头不仅合理的解释了一个烂赌成性只要别人给钱什么都可以做的赌棍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改变立场加入保护孙文的行列,而且,从修辞的角度来看,充分展示了人物惊诧、喜悦、追悔、无奈的种种错综复杂的情感转变、同时也为影片后半段这个普通男人深沉的父爱和牺牲做出了铺垫。
二、特写
所谓特写指的是“表现成年人肩部以上的头像或某些被摄对象细部的电影画面。”[2]当影片中的“特写”镜头以一种特定的目光聚焦和注目于人或物的细部而刻意加以审视时,“特写”实际上是作为一种修辞格而发挥作用的,从而具有了特定的修辞功能。作为辞格运用的特写必须满足两个要求,首先是“打破了原本的叙事链条,而呈现出一种刻意的关注的目光。其次是在呈现形态(时间和空间)上有明显的超长性、奇特化的观赏效果。”[3]一如米特里所说“特写镜头中的物象除了是概念和情感的瞬间符号之外,它还必然使人注意到它的感染力和与众不同之处。它能够唤起一种只有注视它的目光才能感觉到和体察到的情感性。”[4]下面我们选取几个典型意义的“特写”辞格做出分析。
影片中背负叛军罪名的将军方天所带领的戏班惨遭杀害后,金利源的老板李玉堂来寻找自己的好友李少白,却意外的发现了李少白遗失的钢笔,随后影片出现了钢笔的特写镜头,初看上去只是镜头对具体物象的刻画,可是当结合影片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这并不是简单的对具体事物的描述,而是有其深刻的暗示和喻义在里面的。是什么让这个不愿牵扯进革命的商人到最后反而变成了指挥行动的关键人物?除了一颗爱国的心,最大的催化剂便是这支钢笔。好友李少白凶多吉少白生死未卜,李玉堂悲愤难当,在好友的书桌前读着还没来得及给自己的信件,握在手中的钢笔一刻也没有放下过。日报社因为宣扬孙先生来港的消息遭到查封,悲痛和愤怒之下,李玉堂站在报社里手里拿着挚友的钢笔,激动地复述着陈少白在信件里对他说过的那些话,这个时候,“钢笔”的特写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特写了,而是承载了李少白的遗愿和一份厚重的责任的修辞功能。
特写是影像中最为常见的“辞格”修辞方式,它最能够贯彻“文本”的思想意图和潜在的情感指向。在孙文母亲的房间里,看着因为紧张和恐慌而不住颤抖的李重光,孙母紧紧的握住了他的手,这个特写镜头在影片里出现了两次。屋外腥风血雨,屋内孙母始终镇定自若,端坐不动。爱子在腥风血雨中奔走,每分钟都有性命之忧,这一别又不知何时能再见,慈母方寸间必是忧心如焚、愁肠百结,但她脸上一丝一毫也未表现出来,却只是用母亲的手掌,像握住自家孩子一般,握住了浑身颤抖的重光的双手,多么温柔而坚定的力量。从这一特写的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正是有这样雍容大义的母亲,才会教出这样勇敢有作为的领袖,才会有这许多仁人志士为其抛头颅洒热血。这看似不起眼的特写镜头“修辞”,实在是包含着精心构筑的“意义”之节点。
同样,影片中多次呈现了时钟的大特写,有孙母房间墙上的挂钟,有李玉堂手里的怀表,有桌上摆放的时钟,一切都在诉说着时间的紧迫和局势的恐慌。保护工作争分夺秒,面对屋外的残忍杀戮,革命者备受煎熬,不仅要强忍住内心的恐慌,而且还要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保护孙文。这一特写辞格不仅体现出了时间的紧迫而且还隐含了知识分子的恐慌和对新中国的希望。因此,影片中穿插的众多时钟的特写镜头所蕴含的“时间”层面上的“隐喻性”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三、递进
所谓“递进”辞格,指的是“以多个镜头的连续呈现或交叉组合方式,并常常以逐步加速的节奏,来强化某种特定的情绪或意念的修辞手法。”[5]
影片中李重光乘坐的黄包车在阶梯上滑落的段落成功地运用了“递进”辞格。这个段落与爱森斯坦《战舰波将金号》中的“敖德萨阶梯”段落颇有些神似。黄包车倒退着快速下滑,全景是无依无靠的黄包车一级一级下滑,像极了“敖德萨阶梯”里的婴儿车,镜头在阎孝国,李少白和李重光之间不断切换,阎孝国追着车子兴奋的往前跑,李少白极力阻止却力不从心,黄包车里的李重光一脸密汗惊恐无法隐藏,颠簸中手枪滑落在地,最后车子撞向石柱,侧翻在地,此时的镜头对准李重光也似轰然翻身,一切都已劫数难逃。从无法控制车子速度面临死亡的害怕和惊恐,到最后想到孙先生已经安全离开后的欣慰和释然,在这个段落里,李重光的心理过程体现得淋漓尽致。最后阎孝国追到翻倒的黄包车前,用竹竿一下、一下、又一下的插进车里,在影片的升格镜头里一切都寂静无声,只有屠杀的声音回响在观众耳边,诉说着李重光的死亡。镜头同样没有带到李重光,可是那一刻却让所有人感同身受,悲从中来。
现实空间中短短十几秒的车子下滑镜头被剪辑成了长达近三分钟的镜头分割组合段落,使时间进程在这里成为一种绵延,从而使这场追杀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悲剧性效果。这个“递进”的修辞段落通过时间上的交叉重复,空间上的分割组合、升格镜头的运用和叙事节奏上的逐步加快,成功地达到了强化意念的张力,使观众强烈地感受到了影片传达出的悲剧力量,把影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阎孝国的疯狂残忍,李少白的奋力挽救,李重光面临死亡的恐慌和释然,在这个段落里都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四、变格
“变格”修辞指的是那种“通过电影摄影(包括洗印、放映等)技术的尺度与正常规格的变化和操纵,造成影像呈现形态上的特殊变化与特殊效果的辞格运用。”[6]“变格”修辞具有明显的主观色彩,这里就影片中所运用到的慢动作镜头和定格做出分析。
仔细观看影片我们会发现,参与此次“保孙”行动的义士牺牲时影片大多都会用到“慢动作”镜头和定格手法。慢动作镜头是以“高速摄影”拍摄而以正常速度放映的“镜头画面”。影片中的“臭豆腐”王复明憨直善良,在保护行动中勇猛顽强,他高喊着“我叫王复明,我叫王复明……”而后大厦将倾将自己和敌人一起埋葬;这个段落里,影片多次运用升格镜头,王复明被敌人乱刀刺死的慢镜头让观众不忍目睹,其间所蕴含的悲情和不屈的心怀耐人咀嚼。与此类似,刘郁白的打斗段落中也多次运用了升格镜头,使整个打斗画面显得空灵而飘逸,别有一番行云流水的美感。孙家门外的台阶上,刘郁白长发飘飘,两手背负背后,从容冷静淡然无畏,可终究是寡不敌众。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斩断了阎孝国的长辫,阎孝国暴怒疯狂的砍杀刘郁白,此处的慢镜头甚至连血液飞溅的轨迹都清晰可见,更加渲染了一种触目惊心的悲壮之情。这两处慢镜头动作不仅使影片“全程追杀“的紧张节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让观众的视觉神经为下一轮的高潮到来做短暂的停歇,更重要的是这一“慢镜头”辞格饱含了编导对人物的精神和情怀的一种认同,也是人物壮烈牺牲的悲情氛围的一种营造,是一种主体意向与悲怆情怀的抒发。
“定格”修辞是对一种特定情绪、情感、氛围、意念的强调和张扬,具有触发思考的修辞效果。影片里,几乎每一个义士的牺牲都用到了定格画面,银幕上显现出他们的籍贯和生卒年。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为无名烈士做的碑铭。这些“定格”镜头的运用是颇富匠心的,不仅是对全片叙事主体的一种悲壮情怀的升华,还强化和体现了影片对每位义士的不屈精神的赞美和为革命牺牲的缅怀和纪念。这些定格镜头寄予了编导对这些义士的深切哀悼同时也给了观众无尽的思考空间。
五、偏重
所谓“偏重”辞格,指的是“影像辞格中那种具有明显的突出和强化某种修辞元素特征的修辞方式”。[7]“偏重”辞格是影像辞格中最松散、最自由的修辞手法。本文将从构图的偏重、色彩的强化、声音的突出和这三个方面对影片的偏重辞格进行解读。
首先,影片一开始,便展现了铁制楼梯的旋转画面,摄影机在楼梯底下仰视一级一级的梯阶,然后镜头慢慢旋转,只看得到一双双下楼梯的脚,影片将多个仰角旋转镜头剪辑在一起,使画面呈现出一种倾斜的不规则的状态,随后兴中会前会长杨衢云惨遭暗杀,影片开始的仰角旋转所拍摄的楼梯画面与学生们围绕着被暗杀的老师的惊慌画面叠印在一起,造成了不稳定的影像形态,隐喻这是一个不安动荡、混乱颠倒的时代,同时也为影片奠定了惶恐不安的情绪基调。通过运用镜头拍摄角度和镜头位置的特殊构图,强化了镜头画面的修辞性张力,从而有力地渲染了时局的紧张和动乱,也为接下来惊心动魄的搏杀拉开了序幕。
其次,影片在处理孙中山先生与13省代表密会的地下室时特意强化了窗子透过的光线 。影片一直是一种灰暗的色调,令人压抑,可是我们看到在孙先生踏进会议室的一刹那,万丈白光透过地下室的窗户投射进来,这是新中国的希望之光,预示着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新中国开启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影片唯一的暖色调是临战的前一天,阿四带着阿纯来到海边,温暖的阳光洒在他们的脸上美好而温馨,在我们赞叹那美好的时候,悲剧已经开始了。影片特意强化的色彩为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做出了最好的反衬和烘托。
最后,具有修辞色彩的声音的偏重在影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孙老夫人的房间里,李少白等人焦灼而恐慌,刘郁白被砍杀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镜头并没有直接展示刘郁白,而是在孙老夫人的房间里突出他的嘶喊声和刀器碰撞的声音。这些声音在李少白等人听来异常悲戚,这种对“声音有意的偏重”,引导观众在自己的想象中构造画面外的场景,从而把观众“看”的注意力转换成了“听”的注意力,而“听”却更加渲染了死亡的残忍和悲壮。
还有一种特殊的强调声音的修辞手法,是运用一种“无声”的“寂静”来达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特殊效果。“臭豆腐”、阿四、刘郁白、沈重阳、李重光在“保孙”行动中壮烈牺牲的瞬间,整个影像忽然寂然无声。正是在这种“寂静”中,我们体会到了编导对这些义士为革命牺牲的讴歌和赞美,那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民族血脉中的情怀的升华,一种顽强不屈精神的诗意观照。
结语
不得不说,作为商业电影的《十月围城》是十分成功的。影片结束时也许观众会质疑,为保护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牺牲掉这么多人是否值得?值不值得已经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了,我们只能说作为一部商业片,《十月围城》不可能深入探讨革命与牺牲的问题,片中的牺牲单纯、光明,令人震撼、感动,观众从中得到了不一样的审美感受,这样就足够了。也许有人会质疑《十月围城》的叙述模式十分老套,可是如何在老套的故事里讲出新意,这不正是电影工作者所追求的吗?
影片中编导的思想和意图通过修辞格的精心运用传达出来,使其成为了有效的“言说”和“话语”建构,从而让影片中的人物群像真实可信,血肉饱满,过目不忘,即便是在这样一个虚构的历史故事中。另一方面,影像修辞的巧妙运用还让影片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诗意和悲壮情怀,给观众带来了不俗的审美感受。这种把电影作为能够产生“价值”(包括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产品”认真看待的观念,以及对影片质量上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对电影市场的准确定位和把握是非常值得当代电影工作者所借鉴和参考的。从电影实践出发,要求电影修辞、影像“话语”,在关注电影市场的基础上追求艺术创新,也是完全必要的。最后,期待华语电影会有更好的作品出现!
[1]Frank E. Beaver:Dictionary of Film Terms.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3.pp186-187.
[2][3][5][6][7]李显杰,《电影修辞学:镜像与话语》,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96页,103页,129页,143页.
[4]让•米特里:《符号学的死胡同》,载《世界艺术与美学》,第八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