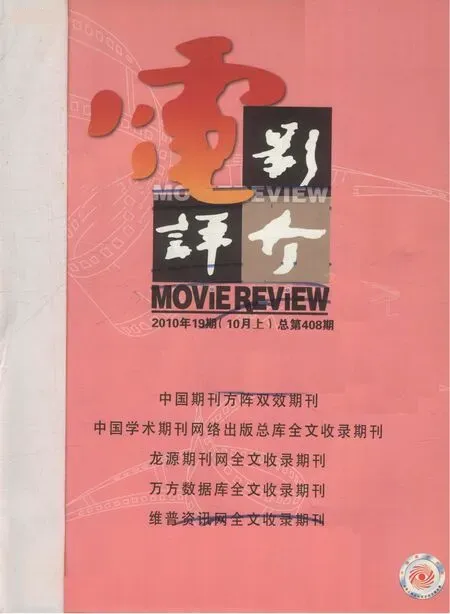从《冷斋夜话》看山谷诗法
惠洪,或作慧洪,字觉范,号寂音尊者、甘露灭,是宋代著名的诗僧,生于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卒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在宋代的诗僧中,惠洪卓绝不凡,曾被推为“宋僧之冠”[1]。惠洪与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交往密切,多诗酬唱和,尤其与江西诗派诸位诗人过从甚密。他虽然没有被吕本中列入《江西诗派宗社图》,却被方回在扩大了的江西诗派中列入,“宋苏、梅、欧、苏、王介甫、黄、陈、晁、张、僧道潜、觉范(惠洪),以至南渡吕居仁、陈去非……亦老杜之派也。”[2]
惠洪对江西诗派诗人多有推崇,其中尤以黄庭坚为最。在惠洪诗话的代表著作《冷斋夜话》中,涉及山谷者多达27条,尚且不包含《冷斋夜话》辑佚中所涉山谷者。[3]其中原因,《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冷斋夜话提要》论述颇精:“是书杂记见闻,而论诗者居十之八,论诗之中称引元祐诸人者又十之八,而黄庭坚语尤多。盖惠洪犹及识庭坚,故引以为重。”[4]惠洪与山谷多有交往,可说是同时代之人,那么通过《冷斋夜话》来了解山谷就很有必要。笔者欲借《冷斋夜话》而略窥一斑,对山谷诗法进行探讨。
一、游戏自在的意趣
山谷论诗,继承了钟嵘在《诗品序》中的观点:“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5]山谷在《道臻师画墨竹序》中云:“所遇于世,存亡得丧,亡聊不平,有动于心,必发于书;所观于物,千变万化,可喜可愕,必寓于书。”[6]诗书同旨,山谷主张诗歌应该表现诗人的性情,无论悲喜存亡得丧都可诉诸诗歌。同时他也指出“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正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7]可见山谷认为强谏、怨忿都非诗之旨,这也就是他批评东坡诗“短处在好骂”的原因了。
那么有怨忿、不平当如何呢?山谷又提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8]主张以游戏的笔墨来对抗生活中的丑恶,以调笑来对抗生活中的痛苦。而在看似游戏的笔墨中,山谷独抒机杼,创造出华妙的诗境。《冷斋夜话》卷二“韩欧范苏嗜诗”条云“韩魏公罢政判北京,作《园中行》诗:‘风定晓枝蝴蝶舞,雨匀春圃桔槹闲。’又尝以谓意趣所见,多见于嗜好。欧阳文忠喜士为天下第一,尝好诵孔北海‘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范文正公清严,而喜论兵,常好诵韦苏州诗‘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东坡友爱子由,而性嗜清境,每诵‘何时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诗曰:‘九陌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又曰:‘九衢尘土乌靴底,想见沧州白鸟双。’又曰:‘梦作白鸥去,江湖水贴天。’又作《演雅》诗曰:‘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似我闲。’”[9]山谷以白鸥自比,创造出通脱灵动,而又意趣横生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山谷的《演雅》诗就是他呻吟调笑的杰作[10],是他在“情之所不能堪”时略带心酸的微笑。
二、以俗为雅,以故为新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山谷尝与杨叔明论诗,谓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捏聚放开,在我掌握。”[11]可以说,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经过山谷、圣俞的倡导之后,几乎成了宋代的共识。周裕锴先生在《宋代诗学通论》中曾云:“‘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并非要将诗拉回学术语言或日常语言形式,而是以‘陌生化’的语词运用来强化诗的超常性质”,“它能因其非诗的常规而获得一种创造性变形的艺术效果,在陌生和困难的审美感觉中,诗歌语言找回了它的新鲜感和刺激力”。[12]
《冷斋夜话》卷四“诗言其用不言其名”条云:“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也。东坡《别子由》诗:‘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也。山谷曰:‘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又曰:‘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后汉》注云:‘常置人于险处耳。’然句中‘眼’者,世尤不能解。‘语言’者,盖其德之候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王荆公欲革历世因循之弊,以新王化,作雪诗,其略曰:‘势合便疑包地尽,功成终欲放春回。农家不验丰年瑞,只欲青天万里开。’”卷四所引的这些诗作,以事物的功能作用或形象性质来代替事物的名称,或以喻依代喻旨,或以谜面代谜底,或以具体代抽象,充分运用借代语、歇后语、熟语,而不一语道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是“以俗为雅”的典范。
另如,《冷斋夜话》卷四“诗用方言”条:“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俗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颖脱不可干之韵。老杜《八仙诗》,序李太白曰‘天子呼来不上船’,‘船’,方俗言也,所谓襟纽是也。‘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川峡路人家多供事乌蛮鬼,以临江故顿顿食黄鱼耳。俗人不解,便作养畜字读,遂使沈存中自差乌鬼为鸬鷀也。‘夜阑更秉烛,相对疑梦寐’,更互秉烛照之,恐尚是梦也。作‘更’字读,则失其意甚矣。山谷每笑之,如所谓‘一霎社公雨,数番花信风’之类是也。江左风流,久已零落,士大夫人品不高,故奇韵灭绝。东晋韵人胜士最多,皆无出谢安石之右,烟飞空翠之间,乃携娉婷登临之。与夫雪夜访山阴故人,兴尽而返;下马据胡床,作三弄而去者异矣。”方言的使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诗歌表意的能力,而且使诗歌产生了趣味,“作诗用方言,就好比在一群谦谦揖让的君子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被发左衽的狂士,这狂士反而显得超凡脱俗”[13]。山谷诗中的“一霎”,“数番”都是方言,不仅没有削弱诗歌的味道,反而为诗歌平添了别样的情趣。
三、夺胎换骨
“夺胎换骨”是对宋代诗坛影响颇大的一条诗歌理论,最早就是见于惠洪的《冷斋夜话》卷一:“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由此可见,山谷意识到了“人才”之“有限”与“诗意”之“无穷”的矛盾,希望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不易其意而造其语”的“换骨法”与“规模其意形容之”的“夺胎法”。可以说,“夺胎换骨”是宋人在唐诗艺术丰碑的压力下穷极思变的产物。[14]
文学史上历来对“夺胎换骨”的理论褒贬不一,经千年而聚讼纷纭。金代王若虚在《滹南诗话》中对山谷大加挞伐,云:“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鲁直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于前人,纵复加工,要不中贵。”“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辞达理顺,皆足以名家,何尝有以句法绳人者。鲁直开口论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处。而门徒亲党以衣钵相传,号称“法嗣”,岂诗之真理也哉?”[15]需要指出的是王若虚的指责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江西诗派末流模拟剽窃的恶习,责任不应由山谷来承担。另外,金宋两代“宗苏”与“宗黄”的差异也是产生争执的原因。虽然指责很多,却也恰可窥见“夺胎换骨”理论的巨大影响力,而宋诗也确实创造了不同于唐诗的美学风范,让千年的读者在阅读诗歌之余多了一份理性的思索,中国诗歌史上也才出现了与“唐音”相抗衡的“宋调”。
也许瑞士语言学者沃尔夫冈•凯塞尔的一段话应值得我们珍视:“当一位作家不是自己创造他作品的内容而向外面去告借,这并不是缺少独创性的标志。”[16]当唐诗的巨大山峦横亘在宋代诗人面前的时候,吸收唐诗的有益成果,使诗歌较之唐诗更加深刻,可能比另起炉灶更加切合实际,也更加有效。
四、注重炼字、炼句、炼意
惠洪在《冷斋夜话》中,大量征引了山谷的诗句以及对诗歌的评论,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山谷对诗句的苦心经营。山谷尤其注重炼字、炼句、炼意,往往有出奇制胜的效果,下面笔者举出三点论证之。
1、句中眼
《冷斋夜话》卷五“句中眼”条云:“造语之工,至于荆公、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荆公曰:‘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又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东坡《海棠》诗曰:‘祇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又曰:‘我携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山谷曰:‘此皆谓之句中眼,学者不知此妙语,韵终不胜。’”山谷不仅对句中之眼大加称颂,也在实际创作中加以运用,如“秋水粘天不自多”(《赠陈师道》)中的“粘”字,“春去不窥园,黄鹂颇三请”(《次韵张询斋中晚景》)中的“窥”字和“颇”字,都是“句中眼”的典范。
2、注重含蓄
《冷斋夜话》卷十“诗忌深刻”条云:“黄鲁直使余对句,曰:‘呵镜云遮月。’对曰:‘啼妆露着花。’鲁直罪余于诗深刻见骨,不务含蓄。余竟不晓此论,当有知之者耳。”惠洪所对之句被山谷指责不够含蓄,可见山谷作诗,含蓄是重要的审美要求。如著名的《寄黄几复》“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就是注重含蓄的佳句,诗人在诗句中注入了对友人深刻的思念之情,却不用明白的语言道出,让人去体会绵长的友情,读来令人感动不已。
3、疏离常规,独抒胸臆
山谷在《赠谢敞王博喻》中说:“文章最忌随人后。”又在《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中说道:“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求新求变就成了山谷的自觉追求。《冷斋夜话》卷四“诗比美女美丈夫”条载:“山谷作《酴醿诗》曰:‘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若出类。”面对前人都以美女比花的惯例,山谷以美丈夫比花,可谓独出己见。当然恰当与否另当别论,山谷也招致了后人不少的批评。笔者认为,这是山谷进行艺术创新的必经之路,正如梅圣俞进行题材创新时所难免付出的代价。
综上所述,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记载了许多与江西诗派,尤其是与山谷有关的诗歌和诗艺评论,保存了一些比较珍贵的材料,对我们深入了解山谷和他的诗歌主张有重要意义。同时,惠洪在《冷斋夜话》中也体现了他作为诗僧的独特审美情趣。也许正如毛晋在《冷斋夜话跋》中所说:“《冷斋夜话》虽微琐零杂,如渴汉嚼榴子,喉吻间津津如酸浆滴入,所以历世传之无穷也。”[17]
[1]吴之振《宋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08页。
[2]《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98册,集部别集类《桐江续集》卷三三,《恢大山西山小稿序》。
[3]统计数据据中华书局1988年版《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得来。
[4]《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610页。
[5]周振甫《<诗品>译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0年版,第15页。
[6][7][8]《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72册,集部别集类《山谷集》,第213页。第255页,第255页
[9]惠洪,朱弁,吴沆《冷斋诗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后文若无特殊说明,凡引《冷斋夜话》原文,均引自此书)。
[10]参看周裕锴《宋代<演雅>诗研究》,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
[11]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4页。
[12][13][14]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99页。
[15]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3页。
[16]凯赛尔《语言的艺术作品》,陈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
[17]毛晋《冷斋夜话》跋,《冷斋诗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