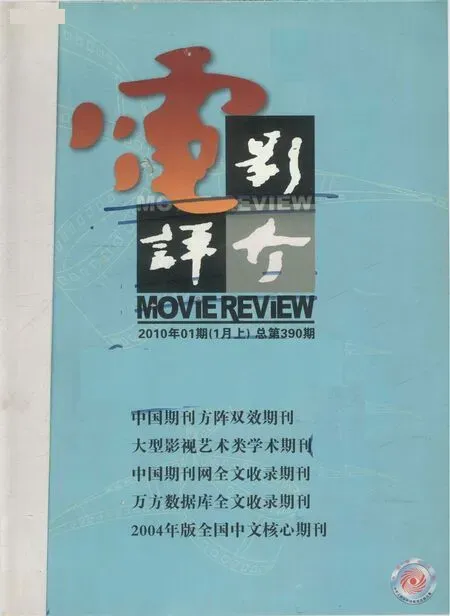审美与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电影
影视文化作为一种物质需求与精神文化的集合,体现了高雅艺术和大众通俗文化的交融。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水平的提高,这种文化与审美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为影视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传播空间,使影视文化逐渐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的主流。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成为20世纪以来流行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公开放映第一场电影至今,这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电影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特征,影视文化的产生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鲜活的、充满色彩和生机的艺术世界。在这样一个多元的、充满感性色彩和强烈的艺术化语言的审美时代,影视文化的崛起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发生着改变,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文化景象。
回顾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史,凝聚着中国电影人的思想情感和劳动创造,中国电影以其特有的题材类型和风格,在银屏上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坎坷历史、民族姿态,在逐渐成熟和发展的历史记忆中,见证和张扬着我们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气节。这100年的历史,承载着文化传承的使命,记录着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沧桑巨变。以胶片和影像为载体,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的奋斗与拼搏,民族文化的投影与记忆力求塑造一个氤氲古意却充满生机的文化中国呈现于世界。
一、以民族性为本体的中国电影
影视文化记载着一个国家的哲学思想,文化精神,价值标准以及情感方式,展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和精神风貌。正如雅思贝尔斯所说:“今天哲学不再是一小撮人特权分子的专利;因为只要个人迫切地反省,如何才能生活的最圆满,哲学就成了无数大众的切身之事。”[1]当代中国影视界无论从哲学思想还是审美层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些甚至颠覆了以往的哲学理念和审美价值,致使中国大众的审美心态趋于多元化,休闲娱乐、满足情感需求代替了理性思考。但是电影的发展应该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既要在发展中不断壮大自己,更要追根溯源保存原有的民族属性,因为传统即一种历时的精神潜流形式,融入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同时又以一种共时文化承载形式延伸到了一个社会的当代精神之中,所以,文化传统总是在历史视点和个性生命视点的结合中彰显出它的力量。[2]
中国电影的发展曲折坎坷,就像在夹缝中生存的一棵小草,艰辛却充满希望。政治基础、经济建设决定着文化的发展,中国在战乱频频、炮火连绵、社会格局混乱无序、美国好莱坞的肆意冲击下,蕴含民族意味的中国电影依然艰难的生存着。由最初的受中国观众广泛认同的以郑正秋、蔡楚生等人的影片为代表的社会、家庭、政治伦理情节剧的传统;以贵穆、吴永刚、孙瑜等导演为代表的具有鲜明东方美学风格的文人电影传统;以及以夏衍、田汉导演为代表的与中国政治具有密切联系的左翼政治电影传统和明星公司推动的以《火烧红莲寺》等影片为代表的商业娱乐电影传统,这四大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电影前半个世纪的基本格局。这一时期的电影注重东西方文化相结合,注重电影艺术形式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结合,这样将电影的商业属性、政治属性和艺术属性揉和在一起,从而为中国民族电影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如何以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智慧缔造一个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中国形象,在吸引西方电影观众的同时也可以真正博取他们在文化上的理解和认同,是中国电影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东西文化的背景不同,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与审美取向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文化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形成各具风格的生产、生活方式,同一民族也会因生活环境的变迁和文化自身的活动规律,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各异的文化形态。因此,由于民族不同,所造就的文化就更加难以磨合在一起。影视文化的民族性,就是指各民族的影视作品都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民族精神,尤其是以反映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模式为主,创造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影视文化从而体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需要。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影视作品都是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的反映与艺术创造的产物。自张艺谋1988年拍摄的《红高粱》荣获西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以来,中国电影就广为世界瞩目,他的作品中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蕴涵和民族精神的多意表达。影视作品中渗透着创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判断,融汇着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和审美追求,实现从外在民族形式的追求到内在民族气质的发掘。中国电影诞生以来,有太多展现本土的民族价值的影片,如:《火烧红莲寺》、《木兰从军》、《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十字街头》、《保卫我们的土地》、《白毛女》、《英雄儿女》、《火烧圆明园》、《芙蓉镇》、《庐山恋》、《黄土地》、《阳光灿烂的日子》等等,它们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国人民在五千年的文化熏陶下所具有的民族品质、精神与气节。这种民族特色与民族风格的产生,是由本民族的发展历史、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影视艺术的这种民族性就是让人们通过某一个国家的电影和电视,或者其他的传媒方式来直观的了解和认识这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形象感受和体验到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文化。
中国电影要将这种民族性推向世界,把这种具有民族特点的影视艺术国际化就需要注重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融合,这种融合的关键在于能否运用国际化制作方式创作出让国外观众也能读懂与理解的影视作品。尽管东西文化存在着差异,但在人类共同的根本问题上,如伦理道德、生存方式等方面上的一致,为处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民族影视艺术审美价值的实现创造了契机。另外,我们还需要创作出经得起世界性比较、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从而为各国观众所接受的影视作品,这就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持中国影视艺术的民族性。中国影视自身最大的优势,在于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影视艺术需要对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对深层古老的传统文化进行开拓和挖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结合,注重中国影视自身的美学特征,继承和借鉴中国深厚的美学思想,准确地表达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在艺术作品中渗透浓郁的民族风骨和民族神韵,这不仅可以体现中国影视文化的审美价值,也能让中国影视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民族价值。
二、中国民族电影的美学特征
影视文化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发展,已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的主流,城市化、都市化的扩展使现代人之间越来越陌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有一道无形的障碍,人们在物质追求的步伐中忽略了精神交流。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应注重道德文化的构建,影视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既成为文化交流就应承当相应的文化职能,在审美情趣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影视审美不应受制于收视率和票率房的影响,出现影视文化类型化、单一化、商业化的畸形取向,这样不仅抑制了影视文化的质量提升和多样化的繁荣发展,而且在文化传承这一重要使命中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影视文化需要根据自身的民族属性重新审视自己的审美价值体系,构建自身的美学特征。
1、影视文化传承中国古代美学思想
中国的美学思想起源于老子的道家思想,继而发展为后来的儒、道、释三足鼎立,事实上,儒道两家的美学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美学的逻辑框架,并以其儒道互补的特征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的基础,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和道家虚无消极的精神也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传统美学艺术,影视文化也不例外。无论是儒家的“仁”、“礼”还是道家的“道”都从本质特征和社会功用上制约着中国的影视文化,道德和伦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推崇的精神文化。道德和伦理是一张巨大的网,它笼罩了你对电影题材的选择,所使用的电影手法、叙事风格的倾向性,它最根本的问题是主宰了你创作之初和之外的电影观念。你的电影观念就成为一种先验的、从不被怀疑的、自我封闭的、起点与终点重合的圆圈。《九香》、《蒋筑英》、《安居》、《背起爸爸上学》、《中国月亮》、《毛泽东和他的子女们》无不在道德伦理的感召下重负述说一种道德伦理观念。[3]
然而,在当今社会发展下的影视艺术或多或少的受到商业利益的诱导,部分影视作品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更严重的会使人意志消沉,精神颓废,而这些都是由审美品位低下和强烈的拜金主义所导致的。无论社会发展的步伐有多快,作为一种文化审美,它都应该在发展中继续弘扬民族精神,继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儒、道、礼、德,以中国古代美学的哲学思想作为艺术铺垫,融入西方先进的电影理论和技术,发展属于本民族的文化瑰宝。希金森早在1867年就对人类美学文化的独立品格和理想境界作了深刻地揭示:“文化的意义在于真善美和造就完人,直到他把肉体的需要看的无足轻重,而把科学和艺术作为唯一值得追求的,有内在价值的目标,这种精神置纯艺术与功力注意的艺术之上,并未求得更高尚的精神生活而安贫乐道。” [4]
2、影视艺术重温文学经典
文学,作为人学,注重从思想观念和美学层面对人的生存状况进行关照。如果影视文化没有文学的支撑,很容易陷入单纯追求画面感觉刺激的误区,不能达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中国文学和电影从80年代开始复苏以后,并且迅速地再度携起手来,重新接轨。《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原著、编剧)、《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原著、编剧)、《牧马人》(李准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枫》(郑义原著、编剧)、《许茂和她的女儿们》(王炎根据周克芹同名小说改编)、《黄土地》(张子良编剧)、《红高粱》(莫言原著,陈剑雨、朱伟、莫言编剧)等等。中国的文学,中国的电影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生活,接近大众。歌德指出:“显示特征的艺术才是唯一的真实的艺术。只要它是从内在的,专注的,注重个性的,独立的感情出发,来对周围事物起作用,对不相干的东西毫不关心,甚至意识不到,那么不管它是出于粗犷的野蛮人之后也好,还是出于有修养的敏感的人之手也好,都是完整的、有生命的。”[5]文学作品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性,它本身具备了影视作品的基本要素,有些文学作品甚至等同于影视剧本。文学作品自身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多样性的形式,复杂的结构,为影视文化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学基础,从这一层面上分析:首先,文学作品为电影和电视提供了优秀的文本,这些文本包含了丰富多样的故事情节,为优秀的影视作品构建了伟大的灵魂框架;其次,文学与影视的情节构建技巧与叙事艺术规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复杂、多线性的叙事结构,给作品注入了鲜活的血与肉,使影视作品富有生命美感;再次,文学以语言为载体,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而这种思想性为影视作品语言的自由发挥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影视艺术丰富的艺术底蕴。
充实的故事内容、灵活多变的叙事结构、深刻脱俗的语言用字,使影视作品富有浓厚的文学气息,从而使影视文化达到了艺术的更高标准。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不能脱离文学,影视文化作为当代审美文化的主流,更不能背离文学作品的人文关怀,一部影视作品,无论创作或是欣赏,都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去审视,这是一个从感性层面深入至理性层面,再升华到审美意味的过程,也是文学为影视作品注入灵魂的需要。
但是从电影艺术的发展来看,根据影视文化重温文学经典,又可以引出一个悖论——电影需要原创性,它可以不再成寻根文学、反思文学的影像,它的选题风格可以彻底原创,同时电影本身也可以广告化、媒体化、个人化、游戏化,然而这种形式在中国电影中还是缺失的。但不管怎样,影视艺术作为一种审美形态,只有具备鲜明独特的个性特征、只有其审美价值具有鲜明生动的个性化,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价值。
3、影视审美文化的教育意义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影视艺术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以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作为影视作品内容的素材,在叙述过程中又采用象征、夸张的手法来再现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体系,使影视作品达到真实性的艺术效果。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时,应从客观的角度去审视作品中描绘的社会现实,否则,影视作品会失去指导现实人生的社会教育功能。影视艺术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的主流,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推动这种文化得以前进,更多的是影视艺术自身的社会功能——寓教于乐。观众通过对影视作品视觉艺术的欣赏和认同,获得各种生活和心理体验,在情感达到共鸣和升华的同时,得到内心情感的释放。
影视作品的创作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创作——欣赏——接受——反馈,观众欣赏和接受作品时,在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产生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又引导观众获得审美愉悦和心灵解脱,从而达到陶冶情操的教育功用。影视文化承担这样一种社会功能,应大力弘扬影视艺术的人文精神,使寓教于乐的教育意义在真善美统一的审美文化中得以体现,影视文化的美育功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因此它具有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的多重美育效果,从而对我们的人格塑造、爱心培养、人文关怀以及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都有不可轻视的作用。
三、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影视该如何体现自身的审美价值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世界电影工业已明显意味着以好莱坞为中心,美国人通过生产、发行及放映纵向一体化跨国联营的结构实施垄断。由于美国市场的重要性,在影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几乎所有国家的民族电影都希望能够跻身美国电影市场,因此,许多国家的电影都试图为了迎合美国市场不得不对本国文化进行各种商业包装和改造。这样一来,中国也面临一个如何看待文化传统,从什么视点来看待文化传统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转型对影视审美文化的影响不仅仅是正面的,它还有一定的消极作用,文化转型对传统精神的反叛就导致审美文化从过去传统的功利性向通俗娱乐性方面转变,人们也开始更多的接受以轻松娱乐方式为代表的审美文化。[6]娱乐化、感官化、消费化被日益凸显的同时,对影视文化建设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影视所蕴涵的传统价值观念开始被淡化,疏离。
中国影视文化的商业倾向受当代社会市场化的影响,中国影视走向世界也不再只是一种文化行为,更成为一种商业化行为。商品经济的最大意义在于把文化变成商品,这一转型使商品化了的审美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文化的多元性、感官性,这完全颠覆了传统审美文化的品格。商品经济时代,事实上已经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无论是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还是受商品经济挤压下的文化视野,都在发生着物质化的改变。影视文化也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在追求收视率和票房率的同时,这些受到商业限制的影片除了走高投入、大制作的商业路线外,并没有给我们的审美视野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如陈凯歌的《无极》资金投入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记录,并且动用了亚洲极为强大的名演员阵容加以商业包装,从剧本、融资、制作到营销,是中国电影真正意义上国际操作的一个范例。
中国电影自身必须进行改革,只有改革才是生存和发展的出路,中国电影所面临的危机并不一定来自好莱坞的威胁,国际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好莱坞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面对全球化,中国电影需要建立一个健康活跃、生机勃勃的电影产业机制,摆在中国电影面前的当务之急应是重新建立中国电影的评价机制,构筑中国电影发展的良性生态环境,从而积极地参与全球文化交流,在汲取西方影视文化先进水平的同时继续发扬本土文化,使民族的文化和思想价值体系在全球化范围内得以传承。
注释
[1]雅斯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北京 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3—144页.
[2]段吉方:《沉重的银屏体验——中国当下影视艺术的审美文化指向》,载《社会科学》,2001年第三期.
[3]郭小橹:《电影理论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4]朗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1991年版第33页.
[5]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01页.
[6]王德胜:《欲望的机器——当代审美文化批判视野中的大众传播现象》,载文史哲199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