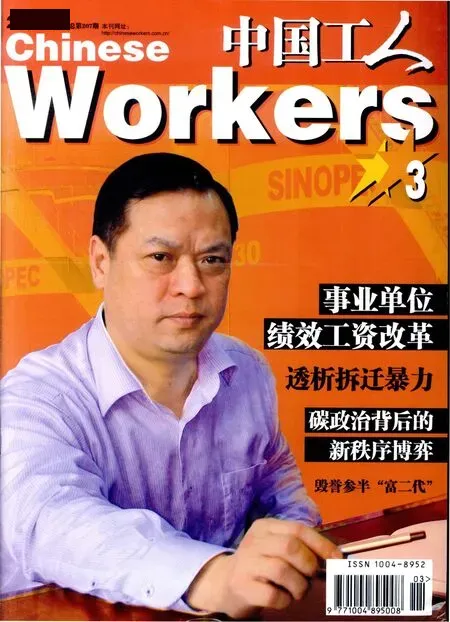冷雨
《芜湖日报》编辑 唐玉霞
冷雨
《芜湖日报》编辑 唐玉霞

听听那冷雨。它在窗外,它在窗外如同一个固执的旅人,一声接着一声,一声紧过一声,敲你的窗户,敲你的神经,敲你记忆里每一根弦。告诉它,这是间空宅,告诉它如今这里是蛛网的舞台,是蝼蚁的乐园,是蚊蚋的天堂,可是,每一滴雨都是无家可归的游魂,每一滴雨都是你前世的情人,每一滴雨都是你今生无处逃避的孽缘。在雨夜,又冷又饿的雨夜,怀抱积年的苦楚与刻骨的怨恨,伸出嶙峋手掌,要抓住那条不系之舟,抓住你的臂膀,它要过河,过往生的河。
可是,此一生,纵一苇之所如,谁能渡你?
很多年前,如果不是风湿的关节在每个下雨的日子叩响我痛神经,如果不是记忆冰冷的沿着脊梁攀缘而上,我想我一定已经忘记,我一定愿意忘记,记忆里还汪着那些刺骨寒冷的冬夜与捶心孤寂的雨夕,一间潮湿的房间,我抱着热水袋,读余光中,读李贺,读纳兰性德。读《听听那冷雨》,读《饮水词》,读他们的诗,读我生命中遇到的每一粒火以及火的面具后的每一滴雨。
在每一句诗的激情里取暖,在每一滴雨的激情里冷却。
激情是个多么好的东西,可以将千滴万滴,千千万万滴冷雨串成珠,串成璎珞,串成霞帔,串成文成章成诗,成心血的锦绣。可以将青春燃烧成一朵烟花,拼尽全力的绽放;可以将落在生命中的冰雪,还有冷雨轻易融化,流成江南泻成江湖,江南的江湖江湖的江南。
雨,冷冷的落,落在屋顶。鱼鳞瓦上弹起傅聪奏响马思聪羯鼓的悲鸣与广陵的绝唱。嵇康在最后一抹夕阳的余晖中,撕裂冷衫割断知音。然后,历史开始下雨,历史被下成了一个披发盲目的雨季。雨,冷雨,淅淅沥沥,绵绵潇潇,嘈嘈切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落在心头,落在季节的脸上,落在时间的伞上。而当,激情比青春更早的撤退,比爱情更迅速的冷却,比生命更苍凉的转身,比梦想更彻底的背叛我们,鬼雨洒空草,这冰冷的皮囊哪里经得起一阵又一阵冷雨来一层又一层得渗透,湿透,冷透。
这么多场冷雨,像又臭又长的电视剧,像又苍白又寒心的婚姻,落,无休止落在生命的这个春天。想起很多年前,流行过的一首诗:第一次放飞,就遇到下雨。雨,冷雨,总是在每一次放飞的晨曦里沉沉落下。没有被雨水沉重过的翅膀,永远不知道蓝天与太阳晴脆的滋味。可是被雨水打湿的翅膀,还有没有亲近蓝天与太阳的机会。有时候,我们比春天更快的放弃了自己。
放弃,是这个初春,不断的阴冷潮湿里不断浮现出的念头吧?
冷雨敲窗。敲在时间的键盘上,敲在生命的乐章里。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凄凉。
真的。也许是雨水的原因,也许是温度的原因,也许只是一次季节性感冒。令人消沉。据说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精神病患者。在《非诚勿扰》里,冯远征对葛优说: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是的,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个同性恋,据说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同性恋者。就是说你的身体里都有这颗种子,无非是有的种子生命力旺盛,有的种子先天性羸弱,但是再羸弱的种子如果温度太合适水分太合适氧气太合适,都是可能发芽的。终朝浸淫在冷雨的料峭里,大概是抑郁最合适的温床。
商略黄昏雨,可是这雨终朝不息,如同愁肠百结千结万劫不复。听听那冷雨。林妹妹写道:冷雨敲窗被未温。真的是又冷又湿的被?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这个孱弱的抑郁症患者哪里能够扛得起一个又一个愁煞人的雨乱灯昏,人飘零。听听那冷雨,李贺说,南山一何碧,鬼雨撒空草。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帝胄的黄昏,早衰的心灵,早熟的思想,又湿又重,压向他纤细支离病骨,压得他即使呕出心血,目光也不能穿过雨云上的天空喘口气来。半世浮萍随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也许那凄冷的细雨只要再下一日,就足以埋葬我。纳兰容若说,他的薄得一触就碎的灵魂甚至连一缕春风也不能承受,更不要说冷雨,连日的冷雨。
可是我们不是李贺不是纳兰不是林妹妹,我们的生命,我们强韧的枝条,在冷雨中爆出青芽。听听那冷雨,我们一起听听那冷雨。当雨水把莽莽大地,染成秧青色;当雨水把浮动的红尘,洗成黑白默片。一半是湿黏黏的苔藓一半是滂沱的流年。明日惊蛰,接着清明,接着谷雨,雨季来了,雨季过去,雨季不再来,但是,日子,密密麻麻的日子,是一场更大更持久的豪雨,冲刷着生命中的尘埃,和尘埃般的生命。
所有该被清洗的。
栏目主持:胡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