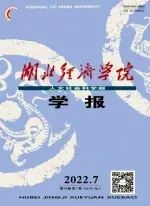人类认知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色彩语码
王学森
(福建工程学院 外语系,福建 福州 350108)
人类认知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色彩语码
王学森
(福建工程学院 外语系,福建 福州 350108)
色彩语码是国际上认知科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对于人类认知的普遍性具有相当重要的解释作用。本文通过对色彩语码的进化论进行阐述,介绍了色彩语码进化论如何有力地从根本上否定了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决定论,指出了人类语言发展在认知发展过程中具有普遍的共性,为现代语言学、翻译学和跨文化交际等领域的发展做出来重大贡献。
认知;色彩语码;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色彩语码是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色彩语码认知研究是目前国际认知科学上的前沿课题。色彩语码是对色彩现实即色谱进行切分和命名的结果。色谱是一个连续体,各种色彩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每一种语言中的色彩语码都代表了对色谱的一种切分和命名方法。如何看待这种切分和命名的性质,这与如何认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密切相关。由于这一原因,长期来色彩语码认知研究一直是有关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往往能为语言认知理论提供重要证据。(张金生,2004)而近代以来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就是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直延伸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出现。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被探究和假设的一个永恒的主题。限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取海德、洪堡特、萨丕尔和沃尔夫这几个学者的经典学说来展示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史的历程。
一、近代的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研究:海德、洪堡特
(一)海德的研究
海德(G.Herder)是18世纪时的德国哲学家,他的论文《论语言的起源》(Abhandlung u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获得了1769年普鲁士研究院颁发的奖金,该奖金是为了奖励能回答语言是如何演变而来的论文作者。海德认为,语言与思维是不可分割的,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内容和形式。语言和思维起源相同,发展一样,它们共同经历了不断成熟的阶段。他强调民族语言的个性,强调语言和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学和民族团结的密切联系。他的这种看法同当时欧洲民族国家逐个形成以及民族主义开始盛行有密切的关系。
(二)洪堡特的研究
19世纪是历史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空前发展的时代,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些杰出的语言学家。洪堡特就是其中影响极大的一个。洪堡特(Wihelm von Humboldt)曾任普鲁士的疏密顾问,周游过列国,通数种语言,甚至对美国印第安人的语言也有所了解。
洪堡特继承了海德的观点,认为各种语言的特性是其民族的特有财产。洪堡特认为同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思维是不可分割的,他还进一步发展了海德的观点,认为“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洪堡特认为语言不同,其内在形式也不一样,对相同的感觉经验整理的结果也就不同。感觉和思维只有通过语言才能确定,才能变成有形的东西,才能交流和传播。思维和语言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词是一个个的名称或者标签,同时又表示着特定的东西,使这种东西在思维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概念。只要讲出一个词,就等于决定了表达思维过程的整个语言,所以语言的不同会引起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解释的不同。在一定意义上说,讲不同的语言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具有不同的思维体系(刘润清,2002)。洪堡特的这种语言决定思维的观点直接影响了美国的语言学家萨丕尔 (Edward Sapir)和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从而产生了影响极大同时也是争议不断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
二、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有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争论随着岁月的前进也在进行,随着语言学的研究阵地从欧洲转到美国,有关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研究也在北美异军突起。美国学者博厄斯(Franz Boas)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对印第安人的土著语言进行描写。博厄斯没有留下很有影响力的理论,但是他的基本观点和描写语言的方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萨丕尔(Edward Sapir)就继承了老师博厄斯的传统,采用调查的方式描述和研究印第安人的语言,并且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调查。他在《语言学作为科学的地位》一文中写道:“人并不是独自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也不是像平常理解的那样独自生活在社会之中,而是受着已经成为社会交际工具的那种语言的支配。事实上,所谓的客观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建筑在社团的语言习惯上。没有任何两种语言十分相似,可以认为它们表达同样的社会现实。”萨丕尔的观点就是人类的一切观点都受语言形式的支配。
沃尔夫把萨丕尔的观点进一步论证和发展。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是语言学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的研究影响极大,但却不是专业的研究学者,终生从事保险公司的防火检察官。而恰恰是防火检查工作让他相信语言对世界观的影响。他注意到人们在靠近贴着“满油桶”标签的东西时比较谨慎,靠近“空油桶”时则不太注意。事实上,空油桶里面有爆炸性气体残留,比满油桶更危险。人们对空这个词的注意反而引起来更多的火灾。正是出于兴趣和爱好,沃尔夫加入到语言研究中去。他主要研究了美国的印第安人霍皮人的语言——霍皮语(Hopi)。沃尔夫认为语法已经成为人类的背景现象或背景知识。所谓背景现象就是人们意识不到的东西,只有例外情况发生时,我们才会意识到该背景现象的存在。他对语言研究对比后发现,语言的结构直接影响到人对世界的观察;由于语言结构的不同,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截然不同。例如霍皮语中没有时间、速度、物质等概念。因此一个欧洲人和一个霍皮人谈论物理就很困难。
自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问世以来,许多语言学家就开始进行调查和实验,探讨萨丕尔和沃尔夫提出的语言决定思维和世界观的观点是否合理。长期以来,这个问题都是莫衷一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色彩语码的研究中的进化发现才最终证明了人类语言发展和其他认知一样是具有普遍性的。
三、色彩语码进化理论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问世以来,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据理力争阐述自己的观点。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双方却谁也不能拿出过硬的证据来驳倒对方,例如本文所举的霍皮人的语言的例子,似乎就能证明欧洲人和霍皮人由于所用语言的差异决定了其世界观的根本性差异。20世纪50~60年代,人类学家发现各种语言中的颜色词是不同的,这成为颜色切分任意性的证据,支持了沃尔夫的不同的语言对现实的语言进行不同切分的语言相对论。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破解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时机成熟了。两位美国心理学家柏林(Brent Berlin)和凯伊(Paul Kay)携手合作,发表了半个世纪来色彩语码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基本色彩词语:普遍性与进化论研究》。通过实证研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98种语言的基本色彩语码系统,揭示出不同语言在色彩辨析与语码匹配之间的许多有趣现象。其中最主要的发现有三点(杨永林,2003):11个基本颜色词语构成了自然语言色彩语码系统中最基本的部分,可视为一种普遍性原则;这11个基本颜色词语按照严格有序的进化过程,出现在不同语言的色彩语码系统中;各种语言中基本色彩词汇的数量,取决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处于不同进化阶段的色彩语码系统,其色彩词汇数量的多寡,也不尽相同。
他们不仅发现了基本颜色范畴,而且发现了某一颜色范畴中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颜色(most typical example),发现人们是根据这些定位参照点系统(system of reference points),即焦点色(focal colors)对颜色连续体进行切分和范畴化的。这些被伯林和凯伊称为“foci”(或focal colors)的定位参考点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们在不同的语言中是基本相同的。(赵艳芳,2001)
这个发现颠覆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理论,如果按照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观点,不同的语言颜色词也完全不同。然而柏林和凯伊的发现却是不同的语言的颜色词有其共性,只是随着进化的历程而先后出现。这11种语言的进化过程是直线性的,顺序非常严格,分为6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黑、白两种颜色,第二阶段是黑、白、红3种颜色,第三阶段是黑、白、红、绿、黄5种颜色,第四阶段是黑、白、红、绿、黄、蓝 6种颜色,第五阶段是黑、白、红、绿、黄、蓝、褐7种颜色,第六阶段是黑、白、红、绿、黄、蓝、褐、紫、粉、橙、灰 11 种颜色。人类的颜色认知是具有普遍性和共性的,而不是因语言不同而存在本质差别。
以达尼语(Dani)为例,此种语言只有两个基本的色彩词汇,modla代表光明的,白色的;mili则表示黑暗的,阴沉的和黑色的。讲达尼语的人要是想说黑色和白色以外的颜色可怎么办呢?实际上,达尼语用modla代表所有暖色调的颜色词,比如红色、黄色等等,并用mili来指代所有冷色调的颜色词,比如绿色、蓝色等等。因此,modla vs mili的对比绝对不仅仅是黑色和白色两种颜色的概念。这说明达尼语的部族还处在人类颜色基本词汇演化的第一阶段,随着历史的前进其颜色词会按照严格的顺序逐渐增加。
19世纪以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自然语言的色彩词语系统体现出语言相对件特征和语义。赞成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欧洲“文明化”社会和其他“未开化”社会之间在色彩感知和色彩表达上存在极大差异。这一派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未开化”社会古语群体中基本色彩词的数量远少于欧洲“文明化”社会诸语言,而基本色彩词汇的多寡又恰恰反映出语言系统的概括能力和抽象水平。这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的种族优越主义的表述。 萨丕尔-沃尔夫以及之前海德和洪堡特的语言决定世界观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收到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用欧洲语言和世界观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程度不一的不同语系的语言。前面说过霍皮语没有时间、速度和物质的概念。可是并不能因此说霍皮人世界观就是低等的,如果当他们需要这些概念时一定会以其特定的方式表达出来,如同达尼语两个基本颜色词并未影响人们表达其他颜色的概念一样。
通过基本的颜色词汇的发展和演变的严格规律反衬出人类语言和认知进化的特点,粉碎了欧洲中心论的种族优越论,说明人类语言具有相当的普遍性(Linguistic universality)。
四、色彩语码进化理论的影响
柏林和凯伊的基本颜色词进化规律理论有力地挑战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指出了人类语言发展是认知进化过程中的共性过程。人类的世界观不是收到语言枷锁束缚,人类及其世界观不是语言的奴隶,说明人类语言和认知具有共性,其意义很大。它粉碎了欧美种族优越主义的观点,表明世界上的语言没有高贵和落后之分,也表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如果按照萨丕尔-沃尔夫的假说,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世界观,那么两种语言就无法实现互译。同时也对不同语言间的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既然语言具有共性,那么讲不同语言的人就可以学会另外的一种语言,这对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和外语学习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承认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和共性,也有利于不同语言和民族间的交流和沟通,从而促进了跨文化交际的发展。
五、结语
色彩语码是认知科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柏林和凯伊的基本颜色词进化规律的发现推翻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语言决定世界观的观点。这不仅对语言学、语言教学、翻译和跨文化交际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使人类的认知科学研究迈进了一大步,意义深远,值得后人总结和发展。
[1]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2]杨永林.色彩语码研究一百年[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1):40-46.
[3]张金生.我国色彩语码认知研究的一次突破——评杨永林教授的两本书[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9):395-397.
[4]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