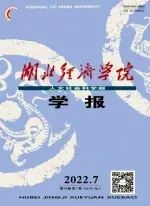痛楚的分裂亦是成全
——细读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李 群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痛楚的分裂亦是成全
——细读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李 群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方方的《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讲述了一个知识女性自我分裂的人生悲剧。主人公黄苏子白天是白领丽人,夜晚则化身妓女,造成其命运的正是来自男性社会的种种规范。黄苏子以变态性的分裂表示了对男性道德规范的抗议和报复,显示了自我意识的觉醒,有自我成全的意义。但这种自我成全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主人公自我的迷失。
自我分裂;自我意识;男性道德规范
在当代文坛的小说创作领域,方方的名字并不陌生,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文坛涌现一股新写实小说创作热潮,湖北作家方方被视为该流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方方的写作逐渐表现出对女性题材的关注,佳作频出。其中,1999年的《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应该算是得到较多关注的一篇,这篇小说也曾以《风中黄叶》为名发表。
正如小说曾有的这两个题目一样,“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以一种颇似谶语的表述传达出一份悲凉的意味,“风中黄叶”则直观地“描述出一幅秋风萧瑟、黄叶飘零的画面,小说讲述的是一名当代知识女性的人生悲剧。主人公黄苏子出生在1966年的秋天,父亲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为了自保,将原来想好的颇有诗意的名字“苏子”改为吹捧伟人的“实践”,直到文革结束,才将其改回“黄苏子”。为此,在文革中曾担惊受怕的父亲特别厌恶这个女儿,除了因其不是“想象中的儿子”这个理由以外,更因为她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自己曾有过的卑琐和怯懦,故而对她百般挑剔。黄苏子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亲情关爱的家庭里,除了兄姐的欺负、母亲对兄姐的偏袒以外,就是父亲严厉、刻板的管教和挖苦。中学一个男同学的追求引出父亲失态的怒骂,因这失态使得黄苏子陷入被同学嘲笑、戏弄的境地。在这个环境下成长的黄苏子,形成了孤僻、冷漠的性格。考上大学后,在一群明朗快乐的女同学中,寡言少语、性格阴郁的她让身边的男同学们敬而远之,并得到一个“僵尸佳丽”的绰号。从此,她再无盼望男生追求的欲念,积存在内心的压抑和愤怒转化为收集脏话的怪癖。大学毕业后的黄苏子意外地分到了不错的机关,新单位的同事并不知道她的绰号,她也逐渐习惯了机关的生活。本来她也有机会正常地恋爱、结婚,可是最初相处的对象竟然和当年给她起外号的武姓同学认识,恋爱落了空,“僵尸佳丽”的绰号再次和她相伴,甚至因为这个原因,她被公司总经理的老婆认为是最合适做经理秘书的,因为她让男人没有任何欲望。所有这些再次激起她内心的愤怒,更多下流奇绝的脏话在她心里汹涌澎湃,但她依然压抑着自己的欲望和愤怒,用沉默来面对一切,直到她邂逅了曾经追求过她的中学同学许红兵。许红兵对黄苏子表现出了旧情难忘的眷恋和温柔,并维持着绅士般的尊重和风度,这些都是黄苏子从没经历过的,让她以为自己遭遇了真正的爱情。最终当许红兵在琵琶坊粗暴地与等待柔情蜜意的黄苏子发生了性关系并暴露出他是玩弄报复黄苏子的真面目的时,黄苏子在极度的震惊中彻底爆发,内心深处被爱情业已掩埋了的脏话仿佛定向爆破一样喷泻而出,眼泪也在痛骂之后决堤。对真情的彻底绝望毁灭了原来那个靠沉默来压抑内心欲望和愤怒的黄苏子,没有多久,黄苏子多了一个身份:夜晚琵琶坊的妓女“虞兮”。最后,一个发现她化身秘密的捡垃圾的老头在敲诈未遂后杀死了她。
这个故事讲述起来颇为沉重,黄苏子的压抑、分裂、死亡都让人有种说不出的愤懑和伤痛。从她的父亲,到大学同学、单位同事,以及许红兵,每个人都在黄苏子的悲剧上加了一把力,正是这一点一点的力合起来造成了最后黄苏子的变态和分裂。小说中所体现出的性别对抗的色彩较为明显,所有的男性在黄苏子的成长历程中都扮演了丑恶的、阴险的角色。其实这也是作者借主人公的遭遇对父权或者说是男权社会文化规范表示了决绝的对抗。从“黄实践”到“僵尸佳丽”,其实都是被这种父系社会的文化规范出来的对象。如果说是众人合力杀掉了黄苏子的话,她的父亲是第一个凶手。为了在政治风潮中自保,他将中意的名字“苏子”改为“实践”,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后来为了显示自己的苦难史而不顾女儿自尊当众宣布改回“苏子”的名字,更为了维护自己儒士雅人的形象而失态辱骂女儿的追求者,以及羞辱女儿没有文学才能并自作主张将她调到理科班,这些对苏子缺乏尊重和关爱的管教不但没有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反而为女儿的成长制造了太多的难堪与羞辱。黄苏子的父亲企图在自己的威严和想当然中制造一个淑女,并且这种制造不过是为了显示家庭良好的教养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却没料到这种粗暴的羞辱教育只导致了女儿压抑、阴郁性格的形成。父亲羞辱女儿时的语气“并不激烈,仿佛还有些漫不经心,但黄苏子却觉得字字如针扎耳,扎得她感觉自己的耳朵流出了鲜血。鲜血流到她的肩膀,又顺着手臂一直滴到她的指尖。她的手指夹筷子,于是血又沿着筷子流进了碗里,以致饭都被染红了。”[1]P314方方用形象的语言把父亲对黄苏子的伤害直观地呈现出来,字字触目惊心。之后,黄苏子在大学里渴望异性追求的热情又被“僵尸佳丽”的绰号浇灭,带有侮辱性的绰号让她以更冷漠的姿态来维持骄傲的自尊。但多年的克制终归需要一个发泄,骂脏话这个癖好的养成似乎在挑战着父亲和他人对女性的认知,有着优雅气质、沉默外表的她内心堆积了如山的脏话,这种反差也让她获得了一种兴奋的快感。随着“僵尸佳丽”这一绰号在新单位的流传,黄苏子对新生活的希望也随之破灭,感情几乎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偏偏这时许红兵又出现在她面前。一直都在渴望着尊重、真诚的黄苏子为当年自己的唐突向许红兵诚恳道歉,但这份真诚以及对爱情的渴望换来的却是欺骗、玩弄和报复。
从父亲、同学、同事,再到许红兵,黄苏子身边的每一个男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猜测、想象、安排她。父亲希望女儿是一个优雅、纯洁的淑女,以配得上自己的所谓上层家庭;同学希望她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女孩,以便男生们的追求;同事则希望她是一个会撒娇发嗲的女人,这样才是大家的意淫对象。在许红兵之前,黄苏子虽然厌恶包括父亲在内的身边人的安排与规范,但她选择了压抑与忍顺的态度对待这种规训,虽然并未满足身边人的期望,但也并未表现出正面的反抗。许红兵的出现触动了黄苏子内心最深处的真情。他就如同一把钥匙,开放了黄苏子的真性情,但这个人的背叛与欺骗也让她释放出来压抑已久的积怨。或许“虞兮”就是黄苏子最愤激也最畅快的内心表达。她以这种变态性的分裂表示了自己最强烈的抗议:以妓女、荡妇的身份嘲弄来自父系社会的约束,从而得到自我满足。这种变态性的分裂是一步步地被身边的男性们逼迫造成的,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单位,从同学到“情人”,随着每一次环境的改变,黄苏子一次次地试图逃离这些人对她的控制与想象,但每一次逃离都宣告失败,而每一次失败又都在黄苏子最后的选择上加重了一个砝码。
对于黄苏子最后做妓女的选择,有的研究者指出这反映了黄苏子性的压抑和变态,是她的愿欲没有得到正常宣泄的结果。[2]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更愿意把黄苏子的这种选择理解成她对男性道德规范的挑战和报复,而不是对自己生理欲望的宣泄。在为自己的妓女身份起一个名字的时候,黄苏子想到了“虞兮虞兮奈若何”这句诗,她喜欢这种“不知拿你怎么办才好”的感觉,于是给自己起了“虞兮”这个名字。这其实很明显地表现了苏子内心的渴望,她不愿意做一个人人都可以拿她怎么办的驯顺者,父亲用自己对女性的规范来管教她,同学用他们对女性的期望来审视她,同事用他们对女性的欲望来戏弄她,许红兵更用自己的安排来设计她。大家似乎都有一个对女性、对黄苏子要求的模子,他们用这个模子和黄苏子比来比去,在发现黄苏子的不合适后或打击、或嘲笑、或侮辱,从中获得满足和优越感。黄苏子是不甘于此的。她让自己变成一个众人无法想象的对象,在对自我的这种设计中获得操纵的愉悦。尤其是面对许红兵的欺骗,她迅速地把许红兵想象中的淑女、贞女的形象变为粗俗的泼妇、廉价的暗娼,似乎不是许红兵设计了她,而是她设计了许红兵。在这样的倒错中黄苏子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许红兵的成就感,从而也降低了自己的挫败感。黄苏子不愿做一个被人想象的人,或许她在一开始并未有做妓女的愿望,但被激发起的抗争心使她带着一种报复的心态行事,以颠覆他人的想象来成全自己。从这一点来看,黄苏子可谓是一个“在压抑中反叛,乃至于疯狂,勇敢地反抗父权制的女斗士形象”。[5]P224这种变态式的分裂虽然痛楚,但焉能不说其中也有自我成全的意味?
姜广平在《“阅读也是需要训练的”——与方方对话》中曾经谈到:“《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有一种好女人却想作贱自己的意念。她们是不是被自己压垮的呢?或者说,这些好女人其实需要释放。譬如黄苏子,内心积压了太多的肮脏情结,它需要有一个奔放的出口。”[3]P237这种意见恐怕代表了很多人对黄苏子后来变化的看法,认为黄苏子最后沦为最低贱、最没有廉耻的暗娼是一种堕落。固然,黄苏子的这种分裂人生是不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变态的,而且她的死去更是让人扼腕叹息,但把白领丽人黄苏子说成是“好女人”,把做妓女说成是作践自己的观点我并不认同。这里所谓的“好”和“作践”其实还是代表了男性视角的意见,他们要求女性端庄、优雅、纯洁,倘若她再因为受骗而痛不欲生、凄凄惨惨戚戚的话,男性更可以获得一种拯救者的优越与从容。而妓女,这个“直接象征着性欲,以风流、妖艳、下贱、恬不知耻和自甘堕落等等作为外在表现特征”[4]P154的特殊身份,是与男性对女性道德约束的规范大相径庭的。黄苏子看透了这一点,她故意地让男性推崇和贬斥的两个极端形象统一在一起,从而获得了颠覆的快乐。分裂的人生也许是痛苦的,但黄苏子的分裂反而让她获得快乐。
邱运华在《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中提到:“在女性主义批评看来,人类的进步和男性的文明是建立在对于女性的压抑之上,父权制正是通过对女性的压抑并隐匿这种压抑而得以维系,妇女的成长史则是女性在被压抑和反压抑中追寻自我意识和主体存在的历史。”[5]P224方方的《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正可以看成是对这一说法的极好诠释。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的要求,黄苏子也不例外。但是一直以来她都在实现着(或者说遵循着)别人——尤其是男人——对她的要求,而她的自我意识则被这种种要求所压制,这样的生活压抑而痛苦;变身后的“虞兮”则大为不同,黄苏子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了,在这个崭新而又陌生的身份掩盖下,她无所顾忌,体验着颠覆自我的兴奋和快乐。这种变态性的分裂是黄苏子在对男性彻底失望后对男权规范的最大嘲讽,也正是在这种嘲讽中让她获得了自我的满足。她迷恋变身游戏的原因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生理欲望的满足,而是白天和夜晚两种身份、两种生活带来的巨大反差,以及这种反差所带来的心理超脱。但可悲之处在于,这样的生活实际上是分裂的,黄苏子在嘲讽男性的同时也迷失了自我。虽然她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自我意识的觉醒:终于不再做一个别人——尤其是男人——想象中的人,可是变身以后是否就是真正地实现了自己呢?尤其是后来在一个无聊的敲诈中丧命,更凸显了人生的孤独与悲凉。黄苏子的人生悲剧反映出她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对男性世界的绝望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只是,这觉醒的代价未免太过沉重。
综观方方的女性小说,我们发现她对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较为深入的表现,黄苏子只是这众多身处困境的女性中的一员,但她的人生经历却形象地诠释了西蒙·波伏娃的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这形成在黄苏子的记忆中就是一个被“腌制”的过程,“腌制”这一词语形象地传达出一个健康的、饱满的生命如何被一双双粗暴的手搓揉、折磨,盐分杀进去,水分被析出来,而不可逆转的结果又使过程尤其有锥心的痛楚。小说的另一个题目《风中黄叶》描绘出了一幅秋风萧瑟、黄叶飘零的凄清画面,但黄叶为何飘零呢?随风飘逝的黄叶是黄苏子不能左右的命运,但结局是一样的,分裂的生命在开始已经结束。
(注:本文系河南省信阳师范学院青年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0907)
[1]方方,王安忆,池莉.情之殇[Z].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2]余莉萍.畸形的文化心理,畸形的人生现象——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黄苏子的形象透视[J].景德镇高专学报,2002,(1):42-43.
[3]姜广平.经过与穿越——与当代著名作家对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5]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