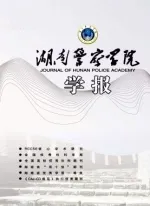能动司法哲学观的解读
王保建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240)
能动司法哲学观的解读
王保建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240)
司法能动主义首先是从美国兴起的一场司法运动。在历史上司法能动主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含义。在美国历史上就司法克制还是司法能动的争论非常激烈,而司法姿态也是在这两种审判哲学之间呈现出“来回摆动”的情形。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这种争论也渗透到我国的司法界和理论界。目前我国提出能动司法的审判哲学,这与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存在交集,同时也有区别。对此,我们应该予以辩证地看待。
司法能动主义;能动司法;调解;正义
一、司法能动主义的历史与含义
司法能动主义首先是从美国兴起的一场司法运动,在美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正如美国学者john Patrick Hagan所说,没有一个词能够完全容纳“司法能动主义”这个术语的广泛内涵,也因此而引发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论。首先有必要对司法能动主义的起源与内涵做一番梳理。
(一)司法能动主义的起源
司法能动的思想比“司法能动主义”这个术语出现要早得多。早在20世纪之前,法学家们就提出了法官造法的观念。但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术语的并非法律人士,而是一个叫做Arthur Schlesinger的非法律人士在《财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Arthur Schlesinger描述了当时最高法院的九大法官,并把他们分为司法积极主义派,司法克制主义派。他将布莱克、道格拉斯、墨菲定位是司法能动主义者,将法兰克福、杰克逊、伯顿定位为司法克制主义者。Arthur Schlesinger对司法积极主义者作了如下描述:1.他们认为法官的判决应该促进社会福利,法官应该利用司法权能达到他们自己认为对社会有利的效果;2.司法积极主义者认为法律与政治是不可分的,法院不可能脱离政治,让法官用他们的政治权力去达到对社会有益的目的。政治关切是司法决定的核心;3.司法积极主义者认为司法决定是结果导向的,但结果向来不是事先注定的,所以对于法官要解释的法律词语就像一个空的容器一样,法官可以随意放进任何东西。接着Arthur Schlesinger表述了司法克制主义的观点,即司法克制主义者否认法律用语是“空的容器”,法律没有确定的含义。相反他们认为法律用语有确定的含义,背离这个含义不管对哪个群体有益都是不适当的,他们认为法律不是政治,司法应该遵循立法机关的意志。Schlesinger在文中将“司法能动主义”这个术语引入了公众的视野之中,但是他并没有给司法能动主义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如果Schlesinger让人们认识了司法能动主义这个术语,那么McWhinney则推动这个术语或为了理论界的主流。McWhinney是一名出庭律师,也是多伦多大学的法学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大辩论》中,McWhinney认为不能将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进行简单的两分,而应该将它们看作一个统一体的两面。在司法领域第一次使用此术语的是法官Joseph C.Hutcheson,Jr,同样,他也没有给司法能动主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二)司法能动主义的含义
尽管司法能动主义没有一个被学者普遍接受的统一概念,但是由于杰出学者和法院案例的影响,在学术界和最高法院的意见中,它具有了5个核心的概念[1]。
1.对其他领域的在宪法上有争议行为的否定。这种定义的司法能动主义是指:由于宪法语言的模糊性,法官禁止政府官员或机构选择一些宪法上没有明确禁止的政策。这个定义主要依靠说话者对宪法的理解,即在一个给定的领域中甚至是宪法未规定的领域中,宪法是否明确地禁止了某些政策选择。这个定义的主观性特点意味着对这个定义的讨论演化为对宪法含义的争论。这引起了一个古老的争论:如何可以最好的解释宪法和确定司法审查的范围。
2.忽视先例。此种定义必须注意两个区分:一是垂直先例和水平先例的区分。不遵守垂直先例是司法能动主义,这点没有异议。关于不遵守水平先例是否构成司法能动主义在司法界存在分歧,不过,法官和学者们一般认为忽视水平先例也是司法能动主义。二是宪法先例、制定法先例和普通法先例的区分。这里效力最弱的是宪法先例,一般较少遵从,效力最强的是制定法先例。法院一旦解释一部制定法,此解释就成为了制定法的一部分,因此,否决先前的解释无异于从事了专属于立法机构的立法工作。
3.法官造法。当法官立法时,他们被成为是司法能动主义者。比如,沃伦法院就是司法能动主义的范例。
4.不适当地使用解释方法。在这里司法能动主义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是不同的法官用不同的解释方法解释法律;二是法官关于解释方法的选择上无异议,但是在具体案件中如何利用这些解释方法存在分歧。
5.结果导向的判决。这种司法能动主义有两个条件:一是法官具有裁决的隐蔽的动机;二是作出的决定偏离了正确的“基线”。但是这种司法能动主义很难被觉察,因为一来这种具有主观性的隐蔽的动机很难被证明;二来很难确定一个没有争议的正确的“基线”。
二、能动司法
2009年以来,中国法院点击率最高的一个词想必就是“能动司法”。经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倡导,这个略带学术味道的词语已成当前各级法院奉行的司法理念。那么中国的能动司法的含义指什么?它与起源于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又有哪些区别联系?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理解我国的能动司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能动司法的含义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大法官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一文中提到:人民法院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必须切实转变就案办案、机械司法的观念,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保障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必须切实转变被动服务、消极司法的观念,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提高政策执行力,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确定工作重点,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审判工作中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必须切实转变重裁判、轻调解的观念,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充分运用综合协调的手段,采取教育、协商、疏导、救助等多种办法,努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确保审判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积极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司法服务。[2]
2010年5月5日在江苏盐城召开的“人民法院能动司法论坛”上王胜俊法官再次强调: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的基本规律出发推进能动司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应当是服务型司法、主动型司法和高效型司法…要从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要求出发推进能动司法。人民法院要善于根据具体案件,从司法理念、法律价值、法律原则、政策导向等多角度出发,准确适用法律,力争达到最佳办案效果;要善于按照“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要求,努力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目标。[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能动司法是在3种意义上被使用的:
1.在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上。如王院长在“人民法院能动司法论坛”上强调的人民法院要善于根据具体案件,从司法理念、法律价值、法律原则、政策导向等多角度出发,准确适用法律、力争达到最佳办案效果。[3]这说明法官在进行判案或法律解释时不要一味地拘泥于法律文本,要防止因片面追求程序正义而“机械司法”。[4]
2.在纠纷解决的途径上。如必须切实转变重裁判、轻调解的观念,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充分运用综合协调的手段,采取教育、协商、疏导、救助等多种办法,努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确保审判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积极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司法服务。[4]
3.在法院的功能上。这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点。王院长主张必须转变被动服务、消极司法的观念,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应当是服务型司法、主动型司法和高效型司法。必须积极主动地开张调查研究,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善于从司法活动中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及时完善司法政策;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未雨绸缪,超前谋划,提前应对,努力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水平。[4]
(二)我国能动司法和司法能动主义的联系
在本文第一部分中,笔者提到起源于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有5个核心概念。本文第二部分,笔者总结了我国能动司法的三个层面,那么我国的能动司法和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有和联系与区别呢?
1.司法能动主义的第一个核心概念,即违宪审查层面上,我国不存在这种能动司法。因为美国司法能动主义的违宪审查权的前提是最高法院运用其享有的最终宪法解释权推翻议会通过的法律,而我国的宪法解释权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法院不具有宪法解释权自然也就没有违宪审查权。
2.忽视先例。我国并非是一个判例法国家,没有遵循先例的传统,因此我国也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司法能动主义。
3.以结果为导向的判决。正如Keenan D.Kmiec教授在《THE ORIGIN AND CURRENT MEANINGS OF"JUDICIAL ACTIVISM》一文中所说,这种司法能动主义很难觉察,因为法官这种具有主观性的隐蔽动机很难被证明。[4]或许只有法官自己才知道是否在司法能动。但是,笔者认为法官虽然受过专业的训练,具有专业的知识以及受到职业道德的限制,但法官不是神,尤其是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法官在判案过程中受到非法律因素的影响在所难免,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判决在我国法官判案的过程之中也是不可避免的。
4.在法律解释层面以及法官造法层面上。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我国已经在实行司法能动主义的司法哲学。理由有如下两点:第一,我国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实质上是一种造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综合治理重要内容的司法建议的数量经历了高峰期和剧降的阶段。与此相应,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的工作则长盛不衰。司法建议对于相对者无约束力,但司法解释一旦作出即成为法律的一部分而具有法律效力。它具有澄清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的作用,“是填补法律漏洞,弥补法律缺陷的基本方法”[5],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直接的“法官造法”。[6]第二,案例指导制度的强化。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刊载的案例最具权威性。正如《公报》编辑所述,最高人民法院以公报的形式公布案例,已经不是就事论事,它创设了法官判案的一些规则,弥补了成文法的不足。[7]公报案例对各级人民法院待决案件的裁判起着导向作用。[8]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具有“法律”性质的判决也是可见一斑。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9年第1期案例所确立的雇工合同中“工伤概不负责”条款无效之原则,具有弥补法律漏洞的作用。由此可见,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已非个案指导,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指导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类似判例的作用。
5.我国的能动司法和司法能动主义的另一个不同点是我国能动司法的后两个意义上的,即纠纷解决方式和法院的功能方面。这两方面在后文中笔者将详细阐述。
三、对我国能动司法的评价
目前,能动司法已经成为了我国法院的司法哲学。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的能动司法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那么,对于我国的能动司法能否适应我国的发展要求,三种意义上的能动司法是否都是我国实务界的应然选择?我们对此应该予以怎样的评价?在下文中笔者将分别予以阐述。
(一)在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上的能动司法。此种意义上能动司法的选择是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之间的选择。这也是笔者所赞同的。在论述之前,首先要强调一点:不要将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完全的割裂开来。这两种司法理念的关键区别并非性质上的,而是“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限制的程度问题”。[9]“如果将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作为两个极端,那么在每个这类问题上,所有的宪法评论家都可以被放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位置上。但要在每一个问题上站在一个极端,在另一个问题上站在另一个极端,这倒也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法官可能对立法的最初意图持怀疑态度而有对先例情有独钟,反之亦然”。[9]美国著名法社会学家庞德也指出:可以据法司法,也可以不据法司法。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都可以发现这两种司法形式的因素。法律的历史表明人们始终是在推崇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坚持严苛详尽的规则之间来回摆动。[10]在坚持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可以论证目前我国需要这第一种意义上的能动司法的合理性。
1.从理论的角度
第一,法具有滞后性。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提到了造法失败的8种情况,进而提出法律内在道德的8项要求,其中有一项是:法律在时间之流中的连续性。[11]这一项的意思是法律要保持稳定性,不可朝令夕改,让人们莫衷一是。但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却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这里就产生一对矛盾,即法律的稳定性要求与实践的多变性之间的矛盾。法律从制定出来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落后于时代。这时若仍然坚持司法克制主义将导致社会的法律道德共识与严格依法审判之间产生冲突,如美国的布朗诉教育委会案。因此,此时需要能动司法来消除这种由法律的滞后性所带来的法律规定与道德共识之间产生的断层,从而达到最好的社会效果,实现社会正义。
第二,法具有不完善性。这里有三点含义,一是法律存在漏洞;二是法律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三是即使在法律的核心概念也存在解释的必要。这里说法律有漏洞是指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毕竟,立法者也是人不是神,他们不可能洞察到未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法律漏洞的出现在所难免,此时法院不可能因为法律没有规定而拒绝受理,而应该根据司法理念、法律价值、法律原则等创设相应的规则审理案件。正如苏力教授所言,“在法律没有规定的地方,一个理想的法官可能根据习惯的做法以及有关的政策性规定或原则以及多年的司法经验作出实质理性的判决,补充那些空白”。[12]其次,法律语言具有不确定性。正如哈特所说,在所有的经验领域,不只是规则的领域,都存在着一般语言所能提供的指引上的限度,这是语言所固有的。[13]也就是说任何词语都包含核心含义和边缘含义,法律语言也不例外。例如一条规则规定:公园禁止车辆通行。那么这里的车辆包含公交车(核心含义)自然没有争议,但是否包括儿童玩具车(边缘含义)呢,这就需要法官进行解释,而法官解释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造法的过程。再次,即使是在法律的核心概念也存在解释的必要。这种情况的存在是因为立法者不可能将法律调整的所有情况都考虑在内。再以上述公园禁止车辆通行的规定为例,假如现在是一辆救护车要从公园通行,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救助车里的伤者。如果此时法官还是“依法”判决则很难为社会的道德共识所接受。正是因为法律具有这些不完善性而为法官的能动司法提供了客观、合理的空间。
第三,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对于上述两点法律的弱点,反对者可能会说法律存在漏洞或者不完善性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机关的立法予以调整,无需能动司法。不可否认立法机关是民选机关,最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因此交由立法机关解决无可厚非。但是,立法工作绝非易事,需要繁琐的程序,往往要经过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倘若凡是遇到法律漏洞的情况就交由立法机关立法,那么即使最后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是不正义的,因为迟到的正义即非正义。
第四,能动司法有利于实现个案正义。法律思维里有重要一条就是形式合理性优先于实质合理性。但是,形式合理性本身也是具有局限性的,“因为如同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规则的一般性并不是说每一种个别的情况都能够被预测或做适当的规定,于是形式上的正义在个别的案件中就可能丧失”。[14]更何况,当实质正义被过分扭曲之后,必须进行区别对待,这才能使法院的判决和社会的道德共识相一致,才能产生更好的社会效果,才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这都需要法官的能动司法,需要法官根据社会民情的发展,根据社会道德共识的现状,根据司法理念和法律原则对法律含义进行“活”的解释,给法律用语贴上时代的标签。
2.从实践的角度。我国的司法改革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11年,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法制日益正式化和程序化,法律队伍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然而正是在这种大好局面的前提下,我国近年来社会矛盾不减反增,涉法和涉诉上访人数急剧上升①2008年,我国各级法院受理和审结的案件超过了1000万件,2009年上半年案件总量同比增长8.25%。,案件执行难等情况屡见不鲜。针对这些情况只有从社会层面才能看出我国司法改革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国目前司法改革取得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只是法治“硬件”上的进步,而在“软件”上并没有跟上。目前我国仍有大约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些地区大多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他们更加注重实质正义的实现,这与司法更加注重程序正义的实现存在断层。要弥补这种断层,要弱化民众因实质正义无法实现而产生的失望则必须依靠法官的能动司法。
(二)在纠纷解决方式上的能动司法
这种意义的能动司法是指法院要突破单一的纠纷解决模式,切实转变重裁判、轻调解的观念,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充分运用综合协调的手段,采取教育、协商、疏导、救助等多种办法,努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确保审判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也就是目前所大力倡导的大调解。大调解大概的意思是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整合和联动。大调解注重的是综合利用我国解决纠纷的各种资源,追求的是矛盾的解决,案结事了。大调解与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也存在差异。比如在调解过程中法官是以司法者的身份出现,积极主动地解决纠纷,这与西方法官以非司法者的身份进行的调解是不同的。笔者认为这种意义上的能动司法适应了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值得推广和实践的。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的国情和发展现状。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其传统的人文精神中缺乏法治基因。虽然我国在立法和法律制度建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民众的法治理念、法律精神和法律信仰方面并没有获得同步的发展,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这点尤其明显。而目前我国的农村人口仍然占全国人口的50%以上,在这些地区还保有熟人社会的特点,这种熟人关系在纠纷解决之后还要继续维系下去。也就是说在民众的法律素养和严格依法司法之间还存在严重的断层。在这样的环境中,相对于更适合于陌生人社会的法院判决,调解更有利于矛盾的解决,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正如日本著名法学家棚濑孝雄曾说过,审判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纠纷的解决。[15]卢埃琳也强调,解决争端是法院最为重要的职能并始终为其他功能的实现创造条件。[16]此外,由于各地区法治建设的不平衡,贫富差距的拉大,能动司法比消极的克制主义从社会的道德共识来看也更公平,能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试想一个流浪汉和一个百万富翁对薄公堂,他们无论是在学识,还是在财力方面(富翁可以雇到更好的律师)都存在较大的差距,此时若坚持消极克制的司法理念则是在表面公平的遮掩下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能动司法更适合我们的道德和法律共识。因此,调解是我国特有的纠纷解决模式,它适应了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在借鉴西方法律经验的同时不可盲目的一味照搬照用,而必须考虑到我国的发展现状,必须回应我国的现实问题,体现中国特色。正如美国法学家霍姆斯所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三)在法院的功能上的能动司法
这种意义上的能动司法,正如前文所述,它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应当是服务型司法、主动型司法和高效型司法。必须积极主动地开张调查研究,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它要求法院以积极的态势,介入到纠纷解决的前沿。笔者认为这种能动司法必须慎行。
我国的司法改革的目标就是要确立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确保司法公正。要达到这个目标,法院必须坚守法律底线,严格奉行不告不理的原则,不能超出司法裁判的功能范围,送法上门。此种能动司法存在以下问题:
1.因先入为主而使得结果不公正。众所周知,司法是被动的,行政是主动的。行政管理要求到第一线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但司法则是在纠纷出现后,由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出面解决,它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并非是第一道防线。如果凡是遇到纠纷,都由司法机关第一个冲上火线,则其可能深陷其中,先入为主,从而“当局者迷”,不利于最后结果的公正,继而引起上诉上访的数量上升,产生法院终审不终的现象,严重损害法院的权威。再者,如果法院按照政府的模式来做,就可能演变成一个政府单位,使得人们以为法院只是政府的一个行政机构,从而产生对法院的不信任。因此,法院必须中立,超脱,切不可送法上门。
2.引起法院职能的混乱。司法的主要职能是解决纠纷,但司法并非万能,有很多事是司法不该管,不能管也管不了的事。如极力主张司法能动的安徽合肥中院院长许建提到了法院终审不终的问题,判决没有权威,涉诉信访不断;现实中有很多把司法机关当成一个党委机关或政府部门的现象,甚至法院还要担负起文明城市建设、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等行政任务。这不仅会引起司法行政不分,大大损害法院的权威和形象,而且会因为法院由于在社会公共决策等方面知识和信息的缺乏而好心办坏事。
3.主动型司法无法回避由此所带来的司法成本问题。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应当是服务型司法、主动型司法和高效型司法。必须积极主动地开张调查研究,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它要求法院以积极的态势,介入到纠纷解决的前沿,这种形式的能动司法必然增加司法成本,而司法成本、司法负担上的膨胀或许会侵蚀司法效益,从而脱离了司法所追求的原初目标效果,与此种意义的能动司法目的产生悖论性结果。
耶林说过,“文化教养的最可靠的特征是判决的非冲动性以及自制性。”[17]因此,被动性是司法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司法中立性尤其是对相关利益冲突无涉的前提。没有了被动性,司法达致公正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对于目前提倡的第三种意义上的能动司法几近可以说是“对司法本质属性和自身运行规律的重新评估”。[18]如果说此种意义的能动司法是为了直接回应社会现实,那么当社会局势、经济环境的要求发生变化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我国司法的属性也要开始重新构建。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式的司法理念可能短期内会取得一定效果,但是从长远看来不利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因此,这种主动型的能动司法必须慎行。
四、对我国能动司法的一点建议
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倡导,能动司法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法院的司法理念。但是在提倡能动司法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在大调解的时候更应如此。在进行能动司法的同时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调解并非万能
任何一种制度的有效性都是有边界的,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有些司法审判不能解决的问题,调解同样也不能解决。另外,对于有些案件调解的结果未必比审判结果更好。此外,还有一些纠纷是调解不适宜解决的。因此,必须对调解适用的普遍性有一个冷静的估计。若对所有的案件一律强行调解,甚至在明显不适宜调解的案件中也调解,就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也会降低人们对司法的满意度,同样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和社会的稳定。
(二)注意审判与调解的平衡
我国存在几千年的人治历史,官本位思想严重。任何调整都有一面倒的可能,如果分寸掌握不当,善良的追求也会演变成盲目的实践。对于目前我国提倡的大调解尤其要注意这一点。要保持审判与调解的平衡,防止一种制度压倒另一种制度。实践证明这种忧虑并非杞人忧天,有些地方法院在执行这一司法理念时甚至要求法官做到“零判决”。这必然会使法官在受理案件时违背“调解自愿”原则而强行调解,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味地追求调解的另一个不利之处在于它不利于法官钻研法律知识,提高司法业务素质,不利于培养优秀的审判法官。另外,在我国这一矛盾高发期,新型纠纷层出不穷,如果过分强调调解,很可能丧失一些经典案例在同类纠纷解决中的指导价值。而案例指导制度无论对我国法治的发展还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的司法制度仍然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受到经济,政治,道德等一些因素的影响。但是,一国司法的模式必须回应本国的现实问题,不可以照搬照用他国的司法经验。此外,随着本国经济、政治、社会力量、道德的发展,其司法模式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称呼、概括中国司法的特点也许并不重要,只是人们对相关的利弊必须头脑清楚,形成共识,也就可以了。[19]
[1]KeenanD.Kmiec.THEORIGINANDCURRENTMEANINGS OF JUDICIAL ACTIVISM,California Law Review 2004.
[2]王胜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J].求是,2009,(4).
[3]王晓雁.王胜俊要求把握司法规律坚持能动司法[DB/OL].http://www.legaldaily.com.cn/leader/content/2010-05/06/content_2134078.htm?node=20950.
[4]王胜俊.高举旗帜与时俱进努力开创人民法院工作新局面[J].中国审判,2008,(7):6.
[5]江必新.司法解释与司法公正[N].法制日报,2003-05-08.
[6]季卫东.最高人民法院的角色及其演化[J].清华法学,(7).
[7]马群祯.说说公报和公报案例的推荐与写作[J].三明审判论坛,2003,(增刊):8.
[8]董皞.司法解释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52.
[9][美]克里斯托弗·沃尔夫.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M].黄金荣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
[10][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48.
[11][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12]苏力.送法下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6.
[13]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126.
[14][英]劳埃德.法律的理念[M].台北:台湾联合出版公司,1984.113.
[15]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16]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潘大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7][德]鲁道夫·冯·耶林.罗马私法中的过错要素[M].柯伟才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15.
[18]能动司法是司法运行规律的本质所在[N].人民法院报,2009-09-01.
[19]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J].中国法学 2010,(1).
Abstract:Judicial activism at first is a judicial campaign sprung up in America.There is no unity of meanings in history.There is an intense argument between judicial restraint and judicial activism in American history,and judicature is also oscillating between the two trial philosophie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legal construction,the controversy began to permeate the judicial circle and theoretical circle in our country.At present,our country put forward the trial philosophy of active judicature,which has intersection with the western judicial activism as well as difference.Therefore,we should treat it dialectically.
Key words:judicial activism;active judicature;mediation;justice
(责任编辑:左小绚)
Interpretation of Active Judicature Philosophy
WANG Bao-jian
(Law Schoo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200240)
D915.14
A
1008-7575(2010)06-0104-06
2010-10-16
王保建(1983- ),男,江苏徐州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