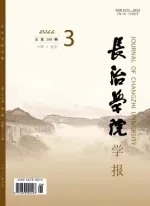ADR制度在中国乡土社会的构建
李中杰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ADR制度在中国乡土社会的构建
李中杰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了“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农村依然具有浓浓的乡土性。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的失语给了ADR制度一个展示其优越性的机会。文章通过对乡土社会特点的分析,发现了ADR制度与之契合之处,在论证乡土社会构建ADR制度可能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构建想法。
乡土社会;ADR;熟人社会
自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写就《乡土中国》一书以来,“乡土社会”这个语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费孝通先生在这本书中以社会学的方法透视了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阐明了其“乡土性”的突出特点,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乡土社会的清晰画卷。60多年过去了,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农村依然具有浓浓的乡土性,究其原因主要有:第一,当前严格的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农村社会仍缺乏流动性,这就使得农村社会具有很强的血源性、地缘性;第二,乡土社会赖以存在的社会意识和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第三,以家庭生产为主的农业经济和对土地的依赖决定了我国农村社会仍有着稳定的内部结构。在乡土社会中,乡规民约被大量用于解决农村内部的争端矛盾,国家法则被束之高阁。当前基层法院的调解客观上导致了调审不分的局面,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为此,笔者以为在乡土社会中建立健全ADR解决机制,将调解功能从法院中剥离出来,赋予专门的机构,才能在保证法律统一适用的同时又兼顾到乡规民约,在保证纠纷解决合乎人情的同时又不悖法理,在保证国家法贯彻实施的同时又能尊重民间的自治性。
一、ADR的相关理论
ADR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中文含义为“替代纠纷解决方式”。这个概念发源于美国,一般用来统称法院以外的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但是在ADR的具体认识上,学界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形成统一的观点。
首先我们来看看作为ADR起源地美国对ADR的认识。美国1998年《ADR》法对ADR所下的定义是:“代替性纠纷解决方法包括任何主审法官宣判以外的程序和方法,在这种程序中,通过诸如早期中立评估、调解、小型审判和仲裁等方式,中立第三方在论争中参与协助解决纠纷。”而美国法律信息网“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指南(Introduction to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则指出:“ADR是一系列多样化的纠纷解决程序的统称。ADR程序的共同之处在于‘代替’这一概念。每一种ADR程序都是对法院判决的一种代替。”[1]学者Henry J.Brown认为,ADR系指任何作为诉讼替代性措施的程序,它通常涉及一个中立和独立的第三人的介入和帮助,ADR包括仲裁。但除非有第三人介入,谈判本身不是ADR;只有在谈判失败时,ADR才开始启动。[2]以上是国外对ADR的理解,我们再来看看我国学者对ADR概念的不同表述。如范愉认为ADR是“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在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称谓”;宋冰认为ADR指不经过正式审判程序而解决纠纷的“供当事人任意选择用来避免正式对抗性诉讼的办法”。[3]
从上述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ADR实际上只是对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法的一个总称。尽管ADR方法众多,但不同的ADR方法之间仍然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第一,意思自治:这是ADR的首要特征,也是ADR吸引人的魅力所在,这一特征契合私法的理念,使其在市民社会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二,灵活性:ADR不但可使当事人自由地设计程序,甚至可以跳出法律的规定,增设法律之外的救济,以实现个体之特殊要求。
第三,谈判结构:通过谈判达成和解是ADR的基本目标。
第四,以利益为中心:与民事诉讼以当事人的权利为导向不同,ADR主要以当事人的利益作为纠纷解决的焦点。
第五,降低交易成本:较之冗长繁琐的诉讼,ADR具有节约时间金钱的优势。
二、乡土社会的特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把中国广大农村基层社会概称为“乡土社会”,认为乡土社会的特点是“富于地方性”,即“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4]在乡土社会,人们彼此之间都是熟人,信用的确立不必依靠对契约的重视。他们追求“无讼”,公共秩序的维持无需仰赖国家的法律而仅仅依靠“对传统的服膺”,即所谓的“礼治”。他说:“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国家权力维护的原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护,维护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5]
从费孝通先生对乡土社会的描述中,我们至少可以概括出乡土社会以下一些基本特点:
(一)乡土社会是一个稳定、流动较少的社会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农业总是农村生活的物质基础。农业与商业、工业的重要区别在于农业发展所依赖的生产要素——土地是不能流动的,而且农业的收成也需要时间的等待。如果频繁的迁徙势必要重新开荒垦地、修渠播种。这样带来的结果只能是劳力伤财、得不偿失。同时农作物“春耕秋收”的特点也要求人们要稳定,不能时常迁移。由于农业这种需要稳定的特征,在乡土社会里,农民们祖祖辈辈只能像植物一样把自己的根扎在自己耕作的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千百年来在这方寸之地上繁衍生息。农民被束缚在了土地上,安土重迁的观念也随之产生,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稳定、流动较少的社会。
(二)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石头丢入水中,在水面上形成了一圈又一圈的波纹,被波纹所推及就产生了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互相联系起来,构成了以人为中心及其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一张关系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为了实际上的功利性,突破了血缘,将非亲属也纳入自己的交往圈子,学界将这样的社会称为“熟人社会”。熟人社会讲究的是什么?是面子,是关系。只有给足了对方面子,才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彼此都会给对方面子。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人们都尽量维持好相互间的关系。谁都不能保证没准有一天要有求于人,就算没有这样一天也不意味着关系不需要维系。一旦得罪了什么人,平日里总难免要碰面,那可能就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了。总之,熟人社会讲究“和为贵”,息事宁人是一种双方都乐于接受的处事方式。
(三)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
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在儒家看来,“礼”是人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它决定人的本质。“礼”是划分、确定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和衡量人的一切行为的根本准则和尺度,从亲疏、上下、尊卑关系到仁义道德,从治军治国到供奉鬼神,都离不开“礼”。“礼”的主旨是规范人伦关系,具体来说是规范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在社会中人们必须绝对服从于礼,礼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法律只不过是对礼的具体化和补充,所谓“礼为本,法为用,礼主内,法治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是典型的礼俗社会,礼治而非法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6]
三、乡土社会中ADR建构的基石——乡规民约
(一)从乡土社会的特点看乡规民约
如前所述,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样一个“阡陌相通,鸡犬相闻”的世界里,“同村人之间交往频繁、联系密切,势必产生某种团体意识,即所谓社区认同感,形成特定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农民之间以‘互惠’为基础的民间习惯规则由此而生,民间习惯规则有助于农民获取信息,交流思想,沟通感情,加深了解,融洽关系,在这些磨合的过程中自然内生出一套指导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心照不宣’的规矩”[7]。这规矩就是乡规民约,它代替了法律的功能,充当着法律的作用。一旦村民们发生冲突与纠纷,往往请社区中声望较高的长老、族长出面,以家族和乡邻关系为基础的人情、礼俗和乡规民约进行调解和缓和。
(二)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乡规民约
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对“正式约束”(正式制度)、“非正式约束”(非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的内涵做了系统阐述。他认为正式约束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行为法则,它们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再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共同约束、规范人们的相互行为。非正式约束则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渐近演化的文化的一部分。它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非正式约束比正式约束的约束空间要大得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们的交往关系主要通过非正式约束规则来维持其秩序与稳定。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可以蕴含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知道乡规民约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卢梭曾经说过非正式制度“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8]那么为什么说非正式制度能“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呢?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考虑这是由于一种路径依赖效应。路径依赖是戴维在一篇讨论技术选择及演化路径的论文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技术由于偶然的因素被选定时,随后的技术选择便被锁定在一定的开发路径上,而这条路径未必是最佳路径。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指的是当制度创新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因此经历了千年沉淀的乡规民约才能如此根深蒂固。
四、乡土社会中的ADR构建的可能性分析
(一)良好的思想基础——乡土社会中的厌诉观念
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曾经说过:“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在法官前面去。”[9]正如达维德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向来奉行“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无讼”是儒家对社会秩序的一种理想,孔子就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10]这种理想渗透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并逐步形成了“乡治调解”、“宗族调解”、“邻里亲朋调解”等息讼制度。乡土社会在“礼治”的环境下浸淫千年,儒家反复强调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向外的权力而在身内的良心。所以“礼治”要求人们注重修身、注重克己。而注重修身、克己的一个重要外在表现就是息事宁人以维持邻里间的和睦和谐。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各种人情充斥于人际关系间。就连古代衙门的横匾上也常写着“天理,国法,人情”,这说明连审狱断案都不能不顾人情。因此,一旦与人打起官司,不仅意味着自身教养不够,没有做到“修身克己”,而且还被视为置人情于不顾,绝情绝义了。有一则故事很能说明中国传统中官民对诉讼的态度:
在明朝时,松江太守赵豫,每逢受理案件,总要劝告当事人回家冷静想一想,实在忍受不了,第二天再来起诉。他们认为,“民之有讼,往往处于不得已而告官,官之听讼,也往往是不得已而后准,皆非乐于有事者”。[11]
(二)满足对特殊正义的需求
什么是正义?千百年来,多少人都曾为此绞尽脑汁,然而直到现在人们对此仍莫衷一是。尽管不能对正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仍可以在本文的语境下对普遍正义和特殊正义做一个大体的区分。所谓普遍正义是由国家所维护的,建立在现代契约社会关系基础上的正义观念。“以契约为基础的正义观念是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这种观念认为一个社会要想保持良好的秩序,相互必须订立一定的契约以避开早期社会混乱无序的状态,这种正义观反映到法律上就是一种现代法学意义上的普遍正义,而国家法就是维护这样一种依据事实,通过法律程序来作出审判的普遍正义。”[12]而乡土社会中的特殊正义观是“一种以伦理为本位的观念,这种正义是指‘义’要依‘情’而定,合乎情的就是义,反之就是不义。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秩序的维持靠的是一种传统习俗,合乎礼俗的就被看成是正义,反之就是非正义”。[13]
国家法的普遍适用性导致其无法满足乡土社会的特殊需求。同一类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往往因为地域的不同而导致解决方式的不同:有的地方可能要求上门赔礼道歉,有的地方则要求敬酒赔罪。国家法显然没有办法做到如此细致多样的规定。正是由于国家法正义的普遍性和乡土社会正义的特殊性的矛盾,导致了国家法在乡土社会中的失语。这时ADR就有了用武之地,它灵活多样的特点正好契合了乡土社会对正义的特殊需求。
(三)满足农民对效率的追求
在我国,大部分农民在其权益受到侵犯时,往往忍气吞声,很少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这与国家法好不好关系不大,主要是由农村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是由于他们的经济条件和文化状况所决定的。根据肖卫东先生做的一项调查,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3750元;综合成本在3420-5720元。[14]
与国家法相比,运用ADR来解决纠纷,时间短、效率高。ADR机制可免除不少繁琐的手续,避免了像诉讼那样花费过长的时间和大量的金钱。同时它可以随时进行,不会耽误农业生产活动。
五、ADR制度构建之我见
(一)取消法院调解,设置独立的ADR机构
我国的调解模式分为法院调解和法院外调解。法院外调解又分为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民间调解。当前我国法院调解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调解与审判在主体上的竞合和程序上的混同。简而言之就是调审不分。日本学者高见泽磨先生认为“中国解决纠纷的特征不在民间调解的优势,而在于官方诉讼过程的调停性运用”,指出了我国“调审不分”的现状。审判主体上的竞合主要是指:在诉讼调解中扮演调解者的法官,虽说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但他与一般调解者不同之处是他的身份具有潜在的强制力量。这种调解者已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调解者,而是与审判者具有实质的联系,判决权与主持调解权融为一体。法官在同一诉讼结构中的双重身份,决定了法官在调审结合的模式中要想真正把握自己的身份是相当困难的。此外,在程序上,许多法官仍然普遍存在将调解视为法院的职权和与审判并行的结案方式而非当事人自治解决纠纷的传统司法理念,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诱促调、以骗促调的现象仍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抑制。更有甚者,一些法院给审判人员下达强制性的调解率指标,这其实早已使调解偏离了其应有的轨道。[15]因此我以为为了实现调审分离而设立独立的ADR机构是必要的。
(二)将ADR机构设置于法院之内
虽然为了实现调审分离,笔者主张取消法院调解而设立独立的ADR机构。不过笔者以为ADR机构设置于法院之内比较合适。首先,将ADR机构设置于法院之内有利于增强其严肃性,有利于当事人更好地履行调解后确定的义务。我们知道调解场合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既可以在田间地头也可以在当事人家中。这虽然带来了些许便利,却会让人感到严肃性不够。而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象征着国家权力在地方的延伸,充满了威严感,有利于当事人严肃对待调解,尊重调解的结果;其次,将ADR机构设置于法院内有利于ADR程序和诉讼程序的快速对接。调解并不是总能成功的,如果双方分歧过大最后将不得不对簿公堂。将ADR机构设置于法院内就能方便当事人迅速上诉,节约时间。更为重要的是法院可以快速了解ADR机构调解时所掌握的基本情况,这将有助于纠纷的高效解决。
(三)对ADR人员进行法律培训
从事ADR的人员一般应该在当地比较有名望,能够服众。“名望”是日积月累而成的。没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名望的人的。而阅历、经验往往和年龄成正比,也就是说名望越大的人年龄往往也越大。从我国现实来看,这部分人群的法律知识有所欠缺。因此,对他们进行简单的法律培训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通过培训,才能让他们在处理纠纷时把国法、人情结合起来,从而避免出现“曲法伸理”的现象,维护好社会主义法治。
[1]刘晓红.构建中国本土化ADR制度的思考[J].河北法学2007,(2):36-40.
[2]齐树洁.民事司法改革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3]刘晓红.构建中国本土化ADR制度的思考[J].河北法学2007,(2):36-40.
[4][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7][9][11][12][13][14] 田有成. 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8][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论语.颜渊》
[15]刘晓红.构建中国本土化ADR制度的思考[J].河北法学2007,(2):36-40.
On Establishing ADR System in Rural China
LI Zhong-jie
(School of Law,Xiamen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361005)
The concept of'Rural China'was proposed by Mr.Fei Xiaotong in the earlier 1940s.Rural China has been undergone a dramatical change in the past 60 years,nevertheless,it is undeniable that strong rustic character still maintains in countryside of China nowadays.The system of ADR has a chance to display its great superiority due to the malfunction of legislations and regulations.This thesis makes an attempt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nd adaptability of ADR system and Rural China by analysis of Rual China's typical characteristic,and further presents concrete proposals for ADR system establishment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ADR System in Rural China.
rural society;ADR;acquaintance society
D92
A
1673-2014(2010)06-0001-04
2010—10—25
李中杰(1984—),女,山西晋城人,硕士,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ADR研究。
(责任编辑 卫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