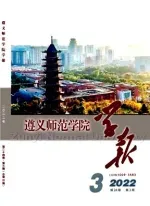建国前萨特在中国的译介述评
刘大涛
(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贵州遵义563002)
建国前萨特在中国的译介述评
刘大涛
(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贵州遵义563002)
文章介绍了建国前萨特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在这一时期,肩负着救亡和启蒙重任的国内文学界人士在译介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思想时,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态度,将他视为自己的同路人;在世界两大阵营形成之初,有人开始从阶级论立场出发,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萨特;译介;救亡;启蒙;批判
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近代开始担负起艰巨的反帝救亡重任。魏源、冯桂芬等中国第一代现代思想家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得出结论,那就是中国的技术落后于西方,只要学到西方的先进技术,就可以制服西方,于是主动翻译西方的有关实用方面的书籍,成为中国启蒙的先驱人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与西方为争取个人的自由、权利的启蒙运动不一样的地方是:中国最初的启蒙就和救亡交织在一起,都是为了国富民强。此后,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对国民的思想启蒙日益受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紧跟其后的五四政治救亡运动与新文化启蒙运动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这就是李泽厚所说的“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时期:“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李泽厚的这一概括非常准确地抓住了中国当时的启蒙和救亡的关系。他接着指出:“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在随后的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然后是十年内战、抗日战争中,好几代知识青年甘愿放弃自己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救亡的革命洪流中贡献出自己,“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1]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说法,由于针对的是投身于革命事业中的知识青年而言的,无疑是正确的,不少人对他的质疑显然是对他的一种误解。在事实上,当时很多在大后方的学者面对时局,在同时做救亡宣传和思想启蒙的工作。
我国最早对萨特的译介,始于1940年,在《艺风》第3期上,发表了无名氏翻译的萨特于1937年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墙》的选译文,取名为《三个被处死的人》,在仅仅相隔几年时间内,艾芜和戴望舒又全文翻译了该作品。何以我国的翻译者最初都选择萨特的《墙》进行重复翻译呢?这在翻译史上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这是因为萨特这篇小说是以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三个被俘的抵抗者临刑前的种种表现,而此时适逢中国反法西斯战争时期,于是被视为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加以引进。《墙》经过选译者的处理,小说中的“我”成了一个为了保护革命的同志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
艾芜的译文发表在《文阵新辑》的1944年第3期上,在编后记中,编者介绍说:“在这选辑里收了六篇小说:四篇创作,两篇翻译。它们所反映的事件,虽然时地各不相同,然而都与今日的反法西斯战争有关一点,却是共同的。”并将之定名为《纵横前后法》。戴望舒的译文和译者附记一并刊载在《文艺春秋》的1947年第3期上。在附记里,戴望舒给萨特定位为“在法国沦陷时期,他是一位有力的‘抵抗’作家”,并指出《墙》“虽然是他的较早的作品,但却已经深深地渗透着他后来提倡的‘生存主义’的思想了”。用译作来配合国情,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在文学译介实践中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尤其是笼罩在国难的阴影之中的国人无不自觉遵守并强化这一趋向,使其成为主导意识。三位译者之所以都选择翻译萨特的《墙》,无疑是把萨特看作是为民族“生存”而“抵抗”的作家,《墙》就是作者抵抗法西斯之作。
由于《墙》取材于西班牙内战,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反抗法西斯而被俘的抵抗者,一直以来,有人仍然认为它是一部写实作品。“《墙》则基本上是一个社会写实性的小说集,其中五篇小说都是以社会现实、世态人性为描写对象,不像《恶心》那样充满了人物的哲理性的感受与思考”。《墙》中“主人公的自我选择的意向显然是很明确的,他所作出的自我选择也是完全正确的,具有革命性与道德感,他宁可自己被枪毙也不供出一个革命者的藏身之处”。[2]如果我们从萨特的人生经历来看,《墙》其实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在文学上的生动表现,而所谓的西班牙战争只不过是这篇小说的背景而已,有两点理由可以说明:其一,《墙》的写作在前,萨特介入政治在后。《墙》于1937年7月发表在《新法兰西评论》上,而萨特介入政治始于1941年加入一个叫“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知识分子抗战组织[3];其二,作品中的“我”(伊比埃塔)没有革命者应有的为国捐躯的崇高理想,有的只是选择一旦停止,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的清醒认识,伊比埃塔选择死亡与西班牙革命无关。这是一堵什么样的“墙”?我们只有返回到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观念“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上去分析,才能把握“墙”的真正意蕴所在。萨特认为,人与物最大的不同在于,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人在不断的选择和行动中超越自己的本质,获得自由;但是选择又必须不带任何目的,否则选择就会受到本质的限制,使人丧失自由,因为像“‘友情’、‘温柔’、‘关爱’、‘使命’、‘人道主义’等都可以成为人的本质,成为对人的限制。”[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伊比埃塔为了防止自己的选择落入“本质”所设置的陷阱,他宁死不屈,选择死亡并不是为了西班牙革命,而是为了“选择”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选择的自由。借助于小说《墙》,萨特想要阐明的是,作为有意识、会思考的人,你不可能做到像“墙”(物)那样成为一个物件,即使你想钻进“墙”里去,“墙”也会竭力抗拒你,因为“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这民族存亡之际,全国人民重新联合起来,投入了这场反侵越战争中。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后方纷纷创办刊物,撰写抗战文章,为前线的战士鼓舞士气。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们又开始介绍和翻译各国文艺界同仁在抗战期间新的创作倾向。在抗战期间,在译介国外文学及思潮方面,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时与潮社”。秉承“报道时代潮流,沟通中西文化”为宗旨的“时与潮社”于1938年在汉口应运而生,创办《时与潮半月刊》,主要介绍各国有关时局、战争以及政治的言论和文章,同年迁至重庆,并且增办《时与潮副刊》。1943年初,“时与潮社”又创办一个大型月刊《时与潮文艺》,聘请当时的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语系教授孙晋三任主编。由于中法两民族在当时具有相似的经历,中国文学界在欧美诸国中更多关注着法国文坛在抵抗法西斯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影响,在国内曾掀起了一个介绍法国文学的小高潮,其中徐仲年和盛澄华的功绩更为突出。在《时与潮文艺》中,徐仲年先后发表过《四十年来的法国文学》(上下篇)、《纳粹铁蹄下的法国文学》、《法国文学主潮》和《巴黎解放后的法国文学》;作为纪德研究专家的盛澄华分两期发表了《试论纪德》,不过,两位当时法国文学的研究专家在文章中都没有提及萨特,这可能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与抗战文学相距甚远的缘故。
此外,主编孙晋三撰写了四期《照火楼月记》,分别对英、美、法、苏等国家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文艺状况作了较系统和全面的评价,“这为当时中国大后方文艺界和读者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了解世界的窗口,为后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外国文学保存了珍贵的史料。”[5]在为《时与潮文艺》1945年第1期撰写的《照火楼月记》之一,孙晋三较全面地介绍了法国文艺界反法西斯斗争的现状,对法国文人在国土全部沦陷后“在铁蹄下勇敢的反抗和光荣的成就,这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赞许有加,以此证明曾流行于国内的“文艺伤国”的言论不过是邪说:法国的文艺在“武断者眼中可以是颓伤、玄妙、或纤柔脆弱”,但“面对着黑暗的势力,它并没有屈膝或萎谢,反而开出更鲜妍的花朵;在需要坚强的时候,它真的显出了坚强。”[6]
由于战争的爆发,以及莫名其妙地就成了俘虏的经历使萨特存在主义的自由观开始发生重大改变,由早期的抽象自由转变为中期的处境自由。萨特认为,自由及其实现与人的境况相关,人的完全自由是在面对各种境况不断地自由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承担全部责任,由此,“自由选择”和“承担责任”是一体两面的。在实践中,萨特选择了更能表现这种自由观的戏剧体裁以取代早期的小说体裁,他于德国占领期间的1941年创作的《苍蝇》就是其中一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哲理剧,它“既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文学表达式,是哲学家萨特以文学为武器参加现实斗争的一个范例,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表征”。[7]戏剧主人公俄瑞斯忒斯由最初悬浮在空中的空虚的自由到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行动后果的处境自由的蜕变也正是萨特思想发生变化的最好见证,不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和精神上谈论自由的萨特,“想从一个处境自由的人着手,他不满足于想象中的自由,而不惜采取特殊的行动来获得自由,哪怕这个行动是极其残酷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行动才能使他获得他自己的最终自由。”[8]当巴黎沦陷后,贝当傀儡政府为了苟且偷安,叫嚣“抗战必亡”,要求全国人民对德国法西斯表示忏悔时,萨特则通过塑造俄瑞斯忒斯这一抗拒上帝的形象,号召人民为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而起来反抗,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孙晋三看到了萨特的《苍蝇》一剧的现实意义,并根据我国当时的国情,将之加以转换性地阐释,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在文学译介中所采取的为我所用的精神。
随着抗战的结束,孙晋三对萨特存在主义的分析由救亡转到了启蒙方面,他于1947年又撰写了《所谓存在主义——国外文化评述》一文,专门介绍了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的要义。在此文中,孙晋三首先对萨特(即文中的沙特瑞)的存在主义思想追根溯源,指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祖师爷是基尔刻迦德(Soren Kierkegaard),之后又传到了德国。其次他分析了欧美知识界所掀起的一股存在主义浪潮的原因:由于萨特把存在主义从纯哲学领域移到文学作品中时,适逢二战期间,它所包含的悲观绝望的一面迎合了沦陷后的巴黎市民的情绪,尤其是巴黎的知识分子趋之若鹜,于是,存在主义很快成为一种时尚,因此,“若数今天世界文坛上第一红人,就得推沙特瑞”,“存在主义已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那存在主义的价值何在?孙晋三将之概括为“以人生为中心的,不拘泥于抽象的玄理的思考,或道德伦理的价值,而直接去讨论‘人’这个问题,和为‘人生’求解释”,并对之进一步补充说明,“他们认为,人存在着,并没有什么固定或命定的性格,却只是一束可能性,要看他自己怎样安排,他可以向各种不同的方向发展。……非到盖棺论定,不能断言。所以,存在主义里有一条原理:‘存在(existence)早于本质(essence)’。”然后,他又对萨特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和“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这两大原理分别加以论述,指出存在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自由问题”,但“一定要选择了,见之于行动,并向一个自己决定的目标在前进,人才能说是自由的”;可是人的“自由选择”并无价值标准可循,需要人自己来选定,因此,“人生永是充满着恐惧焦虑和忧惧的,有的是一种绝望的情绪和勉强生存的感觉。但是,他也不是没有救的。他有了抉择,有了目标,便可以有所成就。只是,世上太多的人害怕自由,往往逃避人的责任(自由),而昏昏冥冥地放弃了真正做人的机会。”萨特的剧本“此路不通”中的三个人由于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只能在痛苦中煎熬。他最后总结道:“存在主义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也自有其作用。”[9]孙晋三秉承新文化运动开创的以“人的文学”和“为人生的文学”的启蒙现代性精神,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把握,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到位和准确的。
在1947至1948这两年间,除孙晋三外,还有吴达元、盛澄华、罗大冈和陈石湘等人也都从启蒙角度著文介绍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及哲学。吴达元在《大公报》“名著评介”栏目中介绍加缪的新作《外人》(现译为《局外人》)时提及萨特。在介绍这一作品之前,他对法国新近出现的“存在派”进行了概括,指出萨特、波伏娃和加缪是“存在派”在文学界的主要作家,“他们同时是哲学家,小说作家和戏剧作家,他们不但把哲学思想写成哲学书,还把他们的思想表现在小说和戏剧创作里,因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生哲学,小说和戏剧是最适合于表现人生的文艺作品。”同时,吴达元也看到了“生存派”所提倡的人性不同于传统上人性的善恶之分,并提醒我们不能妄加对错的评价,而只能说“生存派的人性主义不是普通的人性主义”[10]。他的理解是很准确的,可惜他没有对这种差别作进一步分析,因为萨特的存在主义正是从人性的不确定性中来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盛澄华在《新法兰西杂志与法国现代文学》一文的最后一节“结语与展望”中介绍了萨特:“哲学家、小说家、戏剧家,兼批评家的沙尔德由于他所创导的‘存在主义’已成为今日法国文坛上第一个受人注目的人物。”并对萨特的哲学著作《生命与虚无》(即《存在与虚无》)作了介绍:“它认为生命本身是荒谬,但生命可以藉人为的力量而具有意义,因此‘存在主义’虽以哲学性的否定作出发,却主张藉人间共同的合作以谋世界的改进。”对这一文坛上的新星,盛澄华提醒人们说:“我们处在‘两世界’这一端的人们姑且拭目以待吧!”[11]要人们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
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罗大冈发表了《两次大战间的法国文学》一文,其中介绍了战后在英美人士中引起轰动效应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并表明自己的兴趣:“存在主义即使没有解答全人类出路问题的野心,至少在思想上,道德上,都似乎希望有新的贡献。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新事实。可惜因为是这次大战后才热闹起来的,故已不在本文范围内。”[12]后来他在《大公报》上连续两期发表了《存在主义札记》长文,为了帮助大家对战后在法国盛行的存在主义文学的理解,他“掀动了哲学的酱缸盖”。他首先指出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是“对于人,先有存在,后有本质”,来反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因此传统哲学所谓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对它都没用,“它什么‘唯’都不是,什么‘唯’都不要。因为所谓‘唯’(L’Absolu)就是本质在先之意。存在主义反对本质在先。”然后对存在主义的各主要术语逐一加以解释,如“存在”、“抉择”、“自由”、“投效”(即“介入”)、“焦虑”等。在介绍存在主义的“自由”时,借用萨特的小说《理智之年》(今译为《不惑之年》)的主人公达尼(即马蒂厄)的话:“我愿意完全由我自己来左右我自己”,但是,“自由,这种特权并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并不是人人都配享受。我们周围的人,大多数为群众所左右,为因袭的势力所牵制,为畏怯与怠惰所误。”最后他指出,存在主义者承认人生的荒诞和不合理,但他们“怀焦虑的心,积极入世”,自由抉择即投效,所以,“存在主义之所谓自由,本身包含着浓重的悲剧意味。可是你倒不必冷笑或蔑视存在主义的‘可怜’的自由。”因为“能明白清楚地决定自己的态度,用反宾为主的战略,把握着自己的命运者,是存在主义的三味。”[13]在很多人把存在主义所描述的“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视为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而加以批判时,罗大冈则透过这一描述看到了它的积极意义,这是非常难得的。
为了使中国读者对存在主义有一个更具体的认识,罗大冈计划比较具体地介绍存在主义文学作品到中国来。如果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他希望继续翻译萨特的其他作品,《恭敬的妓女》就是他的问路之石。为“简捷易晓起见”,他将之易名为《义妓》。译作当时并未见刊,但他于1948年4月为这部译作写的序言,经过6个月的等待,终于刊载在天津《益世报》上。从当时发表的“译序”,我们可以明白译者的立场和动机。在译者序言中,为了避免大家把《义妓》理解成是萨特对美国种族歧视政策的批判,罗大冈反复提醒读者,萨特写这部独幕剧,并不是要替“有色人种”打抱不平,“万一有粗心的读者,自作聪明,以为萨特在作反美的宣传,以为《义妓》的主旨在于冷嘲北美洲某大国的伪善与自私,那就未免冤枉作者,曲解文学作品。”与作者一样,自己“介绍《义妓》的用意,绝对不是对美国有所针砭”。那他的用意何在?从他对《义妓》的点评可以看出:
《义妓》是一个含破坏性的文艺作品,正和《墙》里边的几个短篇,正和长篇《恶心》一样。对于抉发人生的愚蠢可悯、卑鄙秽亵的丑态,换句话说,就是人的本来面目,《义妓》的作者可以说是肆无忌惮。……那黑人明明没有犯罪,可是他见了白绅士们就发抖。白人说他犯罪,他连声辩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他觉得自己仿佛真的犯了罪一样。为什么这样心虚,这样卑怯?可不就因自己皮肤黑!这种奴隶根性,是弱者之所以为弱者的重大原因之一。不但黑人,就是那妓女,虽然身为白人,见了绅士们(统治阶级的代表人),也觉得心虚。黑人不敢对绅士们开枪,白种的娼妓,她也不敢。存在主义者说人在因袭势力支配下,倘不自己猛省,终无翻身的一日。至于统治者对付奴才们,气焰不能不盛,否则人吃人的“文明”不能支持下去。[14]
从上面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罗大冈翻译萨特的作品,是为了对弱者的奴隶根性的批判。这正是“五四”时期的鲁迅对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批判的续编,目的都是为了疗救。
如果说罗大冈把存在主义介绍给国人是从反面否定人的旧形象的话,那么,陈石湘的《法国唯在主义运动的哲学背景》一文则是从正面肯定人的新形象。文章从萨特的名言“存在先于质性”(即“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出发,在批判传统哲学的决定论和本质观念,甚至是尼采的超人论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把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抬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陈石湘首先指出,“二十世纪两次无人性的机械化战争”使沉浸于“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迷梦中的人类惊醒过来。“知识分子为了新价值的追求和建立,独立的负起冲锋的责任”,于是进行了一场唯在主义运动,对现时代进行批判。鉴于中国现代哲学心物二元论上唯物和唯心的简单划分,陈石湘将“L’Existentialisme”译为“唯在主义”,以作对照,因为唯在主义“所自期许的和向来一切的哲学传统反对着”。向来一切哲学“承认超乎个人存在的一个外在的普遍大规律,作为世界的本源,人生的依归”;但唯在主义要“否认一切外在规律的对人生的现实性和价值,而只要把人,具体的个人,从生到死一般个人所能经验的存在,作为一切现实的出发点。把个体从普遍中解放出来——不但如此,而正要由个人对普遍的矛盾的自觉,创造人生的新价值。”接着介绍法国唯在主义的重要领袖萨特是“曾因反纳粹被捕入狱,在战争期间一直作着地下工作,而在战后成了法国文艺,思想,甚至社会运动中,一个最受现代知识界注意的人物。”由此指出唯在主义的中心思想就是萨特所提出的“人的‘存在先于质性’”,并从无神论出发,反对宗教和一切向来的哲学,因为它们“总暗示着宇宙间自有必然性,人生下来应该是怎么样,应该完成什么目的,早已定下了。因而多暗示着人的存在和割纸刀没有什么不同,‘质性先于存在’因而像割纸刀一样,人也是另外一个大东西的工具:像东方哲学所谓天地的刍狗,或黑尔德(Herder)所谓历史巨轮上的蚂蚁。”在陈石湘看来,同是激烈的无神论者,但唯在主义的无神论比尼采和马克斯(即马克思)更为彻底:尼采的超人论,“捧出少数‘优秀’人种,代替上帝地位宰制世界”;马克斯的辩证唯物论,“承认外在的必然性,和以全体规律授权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法则来消灭个人”;而唯在主义所强调的是“现代个人对自己存在中生命的敏锐自觉。以个人从生到死一段只有自己主观能把握和经验的存在作出发点,以这非神力所假、非由任何命定法则或固有外在原理所铺排的个人自觉的存在作基础,由自己自由创造生命的意义”。陈石湘之所以产生如此过激的观点,不过是为了强调引出萨特的“自我选择学说”。他指出:“在你这样自由自主的每一步行动中,你把自己造成什么,你都自己负着责任,而且你这样不但实现你自己,并且,因为没有上帝,你的每一自由行动,都在创造着人的新形象。”为了避免人们对萨特的自由观发生误解,陈石湘进一步对它加以解释:“唯在主义所强调的个体主观与自由意志,绝不是个人主义的放荡自由了,或像尼采的‘自我’那样抹杀多数的别人。相反的,萨特却显示着由于个人自由意志出发,对生命意义的创作与选择,同时具有非常积极的普遍伦理。……个人的自由意志,只要是真实的出于你的自身存在意义的自觉,则虽然你的行动限于你自己,但同时你就创造了人的新形象。”虽然尼采和马克斯宣告“上帝已经死了!”,但是被他们“迎进来的新主不是人,而是少数‘优秀’的超人,或经济决定论中消灭个体的集体人”。在二十世纪“人是否已经死了?”的质疑声中,“萨特和他所代表的唯在主义者,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反映着现代人极度的苦楚,而挣扎着发出一声强硬的呼喊:人没有死,只要每人的‘我’复活起来!”[15]陈石湘以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参照系,对萨特的个体主体性思想给予高度评价,而对被淹没在集体中的个人的批判,这无疑是秉承了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想。
此外,这一时期还翻译了不少国外学者论及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的作品。有肯定的,有批判的,不一而足。老作家冯沅君翻译了Dumont Wilden创作的《新法国的文学》一文,刊载在《妇女文化》上。Wilden从萨特新近创办的《近代》杂志的一篇宣言出发,充分肯定了萨特提出的不同于法国近代文学传统的文学观,即文人要介入社会、为社会负责,同时又能保持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在萨特看来,从一个世纪以来,不管是“为艺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写实主义者,还是自然主义者,他们都抱着对社会极端冷漠的态度,“对于他们的作品的道德与知识的影响或道德的破产不负责”,并且“无不自安于不负责任”,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一篇文学作品,有其用处是其堕落;最纯粹的文学与时代无关,甚或超出其上。”Wilden指出,“这是种根深蒂固的成见”,以致发展到今天,正如萨特所描述的,“如今一些事已达到这步田地:人们看到那些因为以文字事德人而受责被罚的作家从痛苦的惊讶中出现”,“唉,什么,他们说,写作的东西也要牵涉到?”在社会矛盾日渐加深的现时代,“文人不再有这种权:将些他不知道将来落到肥地或瘠土上开结些什么有毒的花与果的种子播向四方而轻蔑的退回到他的书斋,离开他的世界和国家。”应该像萨特所提倡的社会文学一样,“文人,果真象文人,须完成一种社会的职务。”在作家为社会负有全部责任时,又不能以牺牲“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为代价,而自由是在自我选择和行动中实现的,“用同一的运动去选择他自己的命运,一切人的命运及他所应贡献于人类的价值是自由的。”[16]身为作家的冯沅君把这篇文章翻译过来,其用意应该很清楚,就是作家既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同时也要保持自己自由选择和行动的权利。
孙源也翻译了一篇取名为《新法国的文学》的文章,不过作者是法国的安德兰罗素。作为战后法国文学批评家、影响很大的斐加洛报文艺副刊主编的作者,面对当时法国文坛的萧条景象和“以抗敌及革命的主张的剧烈深浅来判定‘硬派’或‘软派’”的批评界,他非常渴望产生一种文学新学派来扭转这种衰败的局面,可是,“今日似乎尚难见到一种什么文学新学派的产生”,让他兴奋的是,出现了“以若望保禄萨尔达尔为中心的一个哲学新学派,并且对青年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人已提出警告了”,“人们担心萨氏的著作《存在及虚无》的道理所包含的失望及虚无主义,会在大家的心灵上播下种子”,因此有不少杂志,尤其是天主教的刊物已经对这个哲学开火了。在文章最后,作者说道:“会不会发生一个浪潮对付这湍急的激流呢?或者在这个法国面临危机的时期,这最明显的文化运动也许只是过渡性质,等候别的许多东西来恢复原来的本位,那只有等着将来用事实来说明了。”[17]正如作者所企盼的,随后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发表,在欧美文化界引发了一场存在主义浪潮。
以研究纪德而知名的盛澄华所译纪德的《意想访问之二》和《文坛追忆与当前问题》,也有纪德对法国存在主义的评论。纪德认为,文学作品思想的贫乏与否,与它是否“描写堕落的生活和下流的场所”无关,在这一点上,他对萨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请看沙特尔(Sartre)吧,他以奇特的才具来描写卑贱的事物,但他从来不使人感到贫乏。”[18]纪德在分析当前出现的问题时指出,遭受战争浩劫的部分青年人,由于对未来缺乏信心,接受了今日最时髦的“存在主义派”所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绝无意义而荒诞的世界中”的思想。他鼓励青年人:“这全仗人自己,而我们必须以人作出发。这个世界,这个荒诞的世界可以成为不荒诞,这全仗你们。世界是要看你们自己去造成的”。[19]萨特认为,世界是荒诞的,无意义的,但人能通过自己的自由选择和行动创造意义。从这一点看来,纪德和萨特的思想多么相似!
二战结束后,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美苏结成的战时同盟已不复存在,从战时合作走向冷战。两个大国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以遏制对方,各自通过对其他国家的扶植,形成了两极对峙的局面。为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苏联在文化方面也开始大力批判美国及其同盟国的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同样,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对苏联文学的译介工作。由苏联学者D·查斯拉夫斯基创作,梁香翻译的《法国的“僵尸”——关于法国的存在主义文学》一文,可称得上是这一文化气候变化的晴雨表。
文章从列宁和高尔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出发,分别从“《摩登时代》的‘死亡’文学”、“法国‘僵尸’的家谱”和“法国‘僵尸’的新主子”三个部分来展开对“反动”和“腐朽”的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猛烈批判。作者指出:“在战前法国的一切输出品中,在战后变得最活跃的是巴黎仕女时装式样的输出。”以至《Illustration》杂志不无兴奋地写道:“让那些迷人的时装的需求在国外增长起来。到那时候,我们国内就可以繁荣了。我们法国的勤恳的蚂蚁也需要过过蚱蜢的生活。”这被这位苏联学者讥讽为蚱蜢哲学。在作者看来,与《Illustration》杂志一样,萨特及其学派不过是“《existencialisme》(‘存在主义’,或‘苟安主义’)的文学作品”的工场,生产“时髦的诗歌,时髦的小说,时髦的哲学。”因此,萨特创办的杂志《Le Temps modernes》“最精确应该译做《时髦时代》或《摩登时代》。”在这棵“苟安主义的系谱树中含有着极端反动的中世纪神学的意味。被萨尔特奉为他最近的导师的丹麦的神秘学者萧朗·寇格高(1813—1855)和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由于寇格高(即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生的基本要素是“对无法了解和无法认识的生活的恐怖”;同样,海德格认为是“临死前的苦恼”,查斯拉夫斯基由此推导出,萨特“否认人类与人民的生活中的任何意义”,而奉行的是“个人的利益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受原则。”在这苟安主义的指导下,“有几个追随萨尔特的作家所写的人物是荒淫无度的表现者唐璜。有几个人特别注意虚荣和庸碌生活的题材,自杀和死亡的题材。伪装的悲观主义结合着公开的犬儒主义。”接着在第二部分,作者进一步指出,法国的“僵尸”不过是萨特发掘出了早已过时的反动的流亡白俄“哲学家”塞斯托夫和白尔佳叶夫,作为自己的同道,然后,“萨尔特及其学生们穿着这些陈旧的外衣招摇撞骗。”萨特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的副标题为《现象学的本体论》,查斯拉夫斯基把它形象化地称作“破烂的靴子”。他说道,曾被高尔基讽刺为“僵尸”的诗人叶夫斯基格尼·斯梅尔佳西金从事病态的色情文学的创作,与其同类的“存在主义的诗歌小说也都充满着这种粗俗的春画似的色情”。在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这位苏联学者将法国“僵尸”的基本要素概括为“思想上的尸奸”,并且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为了“向民主和向马克思主义斗争”的政治需要,保护着萨特。为了政治需要,在抵抗运动的营垒中敛积了不少民主资本的萨特在《存在主义与人文主义》一文中“企图将哲学上的虚无主义去和民主主义的句子相联结起来”,“实际上是在哲学的呓语的掩护之下进攻唯物论和科学,进攻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作者认为,萨特到美国演讲存在主义,就是想“贩卖自己的思想和以之来谋发迹”,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他们,对于富豪的美国资产阶级是非常需要的。”[20]由此,法国的“僵尸”又找到了新主子。
萨特在40年代主张文学介入政治,并且身体力行,以知名作家的身份参与了大量的反法西斯的事件。为何在法西斯战争刚结束,在苏联学者眼中突然变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呢?原来在苏联和美国在争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刚拉开序幕时,萨特在自己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唯物主义与革命》一文,批判了斯大林的唯物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接着又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提出“不要去当共产党的看家狗”,要求在“苏联和英美集团之间保持中立的政策”。[21]作为一个文人,萨特不愿加入任何党派,总是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参加反对法西斯斗争以及以任何理由践踏人的尊严和自由的行为的事业,可是,在那特殊的年代里,他的学说却往往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这是他有生之年都没有明白的事情。
[1]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第3卷·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19,36.
[2]柳鸣九.萨特早期作品两种[J].外国文学研究,1992,(03):7.
[3]柳鸣九.萨特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10, 412.
[4]李克.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揭示——对萨特《墙》的解读[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6):95.
[5]苏光文.大后方文学论稿[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431.
[6]孙晋三.照火楼月记(之一)[J].时与潮文艺,1945,5(01):26.
[7]刘莘.《苍蝇》与萨特中期思想[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1):54.
[8](法)萨特.萨特文集(第6卷)[M].沈志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34.
[9]孙晋三.所谓存在主义——国外文化评述[J].文讯,1947,7(06):319.
[10]吴达元.名著评介《外人》[N].大公报·星期文艺(第21期), 1947-6-20.
[11]盛澄华.新法兰西杂志与法国现代文学[J].文艺复兴,1947, 3(03):249.
[12]罗大冈.两次大战间的法国文学[J].文学杂志,1947,2(05):36.
[13]罗大冈.存在主义札记[N].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2-8.2-17.
[14]罗大冈.《义妓》译序[N].益世报·文学周刊,1948-10-25.
[15]陈石湘.法国唯在主义运动的哲学背景[J].文学杂志,1948, 3(01):27.
[16](法)Dumont Wilden.新法国的文学[J].冯沅君译.妇女文化,1947,2(01):30.
[17](法)安德兰罗素.新法国的文学[J].孙源译.文萃,1945,(05):20.
[18](法)纪德.意想访问之二[N].盛澄华译.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2-1.
[19]纪德.文坛追忆与当前问题[J].盛澄华译.文艺复兴,1947,4(01):63.
[20]查斯拉夫斯基.法国的“僵尸”——关于法国的存在主义文学[J].梁香译.时代,1947,(18):22.
[21]徐崇温.萨特及其存在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3.
(责任编辑:魏登云)
On the Translation of Sartre’s Works in China before 1949
LIU Da-tao
(Chinese Department,Zunyi Normal College,Zunyi 563002,China)
In this article,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translation of Sartre’s works in China before 1949.During this period, with the attitude of let-me-take-it-down in translation of Sartre’s thought,personages in China from literary circles shouldering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enlightenment viewed Sartre as their soul mates;nonetheless, Sartre was taken to severe task for his wrong class stand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two Camps in the world.
Sartre;translation;salvation;enlightenment;criticism
I106.4
A
1009-3583(2010)-03-0024-07
2010-02-15
刘大涛,男,湖南麻阳人,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四川大学文艺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