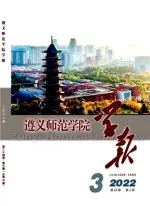花间词的道教题材及其文化意蕴
林洁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花间词中包含着诸多道教文化和仙人传说的语汇、意象、人物及典故,如洞房、玉楼、玉郎、青鸟、舞凤、仙郎、天仙、仙景、仙客、仙乡、仙冠、真仙、巫山、十二晚峰、高唐、云雨、阳台、巫峡、瑶台、刘郎、阮郎、桃花洞、桃源深洞、吹箫侣、萧郎、秦楼、凤楼、鸾回凤翥、凤箫、乘鸾、鹊桥、七夕、玉蟾、嫦娥、银汉、瑶池、湘妃、霞帔、五云双鹤、醮坛、丹灶、三清、步虚坛、降节霓旌、蓬莱、紫微、墉城等。其中,有些是与词中所表现的仙道文化方面的内容题材有关,有些则是一般性的泛化引用。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考察。
一、道教神话与仙人传说
据笔者统计,花间词中的仙道文化内容题材主要表现为对道教神话传说以及仙人意象的摄入。其中,巫山、刘阮入天台、箫史、姮娥、织女、湘妃较有代表性。以下词作以李一氓校《花间集校》[1]为据,或通篇本于道教神话以述情事,或有句、有意象与之有涉,这里杂收统采,以期有个全面的印象。
1.巫山
宋玉《高唐赋》: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人附会,为之塑像立庙,号为朝云。后称男女幽会为巫山、云雨、高唐、阳台,皆本于此。花间词内容涉及巫山神话的有:韦庄《归国谣》(其三)、《清平乐》(其三)、《望远行》、《何传》(其三),薛昭蕴《浣溪沙》(其六),牛峤《菩萨蛮》(其四),张泌《浣溪沙》(其三),毛文锡《赞浦子》、《巫山一段云》(其一),牛希济《临江仙》(其一),和凝《河满子》(其二),孙光宪《河传》(其一)、《菩萨蛮》(其一)、《临江仙》(其二)、《更漏子》(其一)、《何满子》,魏承班《诉衷情》(其四),阎选《虞美人》(其一)、《临江仙》,毛熙震《浣溪沙》(其二)、《临江仙》、《南歌子》(其二)、《菩萨蛮》(其一),李珣《浣溪沙》(其三)、《巫山一段云》、《河传》(其一),共二十九首。
这些有关道教巫山神话的花间词往往语义双关,借用巫山、云雨、楚云等语汇含蓄地流露出文人对爱情的渴望,或用“正是柳夭桃媚,那堪朝雨暮云”(毛文锡《赞浦子》)、“偷期锦浪荷深处,一梦云兼雨”(阎选《虞美人》其一)、“椒房兰洞,云雨降神仙”(毛熙震《临江仙》其一)、“云雨态,蕙兰心,此情江海深”(孙光宪《更漏子》其一)表达男女幽会的柔情蜜意,或用“睡觉绿鬓风乱,画屏云雨散”(韦庄《归国遥》其三)、“暗想为云女,应怜传粉郎”(毛熙震《南歌子》其二)、“燕双鸾耦不胜情,只愁明发,将逐楚云行”(孙光宪《临江仙》其二)展现女子的深闺恋情,或用“玉鞭魂断烟霞路,莺莺语,一望巫山雨”(韦庄《河传》其三)、“目断巫山云雨,空教残梦依依”(和凝《河满子》其二)、“早为不逢巫峡梦,那堪虚度锦江春”(李珣《浣溪沙》其三)表述男子的相思愁情。
2.刘阮入天台
据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载:东汉永平间,浙江剡县人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采药,迷不得返。忽于溪边遇二女子,资质妙绝,并邀至家中成亲,遂留居半年。后二人怀乡思归,二女乃指示还路,送其回家。既归,见邑屋全异,亲旧零落,无复相识,其子孙已历七世。道教神话传说刘阮入天台所用的语汇意象通常为:刘郎、阮郎、桃花洞、天仙等,内容多就题发挥,述说天台神女怀想刘阮的春愁,如“来洞口,望烟分。刘阮不归春日曛”(韦庄《天仙子》其五)、“刘郎去,阮郎行,惆怅恨难平”(毛文锡《诉衷情》其一)、“桃花洞。瑶台梦。一片春愁谁与共”(和凝《天仙子》其一)、“洞口春愁飞簌簌。阮郎何事不归来”(和凝《天仙子》其二),或以“刘郎此日别天仙,登绮席,泪珠滴,十二晚峰高历历”(皇甫松《天仙子》其一)、“千万里,错相倚,懊恼天仙应有以”(皇甫松《天仙子》其二)写刘郎别天仙本事,或借“唯有阮郎春尽,不归家”(温庭筠《思帝乡》)、“不为远山凝翠黛,只应含恨向斜阳”(薛昭蕴《浣溪沙》其八)抒发女子的春日恋情,也有借刘阮艳遇故事写男女情人从相会到欢合的情事,如“曾如刘郎访仙踪,深洞客,此时逢”(顾夐《甘州子》其三)。花间词内容涉及刘阮入天台神话传说的有十八首:温庭筠《思帝乡》,皇甫松《天仙子》,韦庄《天仙子》(其五),薛昭蕴《浣溪沙》(其八),张泌《浣溪沙》(其三)、毛文锡《诉衷情》(其一),和凝《天仙子》,顾夐《甘州子》(其三),阎选《浣溪沙》。另外,温庭筠《女冠子》(其二)、薛昭蕴《女冠子》(其三)、牛峤《女冠子》(其三)、张泌《女冠子》、顾夐《虞美人》(其六)、鹿虔扆《女冠子》(其一)、李珣《女冠子》(其二)七首词有句或意象涉及刘阮入天台传说,其内容表现女冠的思凡情怀。
3.萧史
传说中的仙人。汉刘向《列仙传》记春秋秦穆公时有萧史,善吹箫,作凤鸣,穆公女弄玉好之,穆公以女妻之。遂教弄玉作凤鸣,引凤凰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一旦乘凤仙去。后人以“萧郎”、“吹箫伴”、“吹箫侣”代指女子意中人;以“凤楼”、“秦楼”代指思妇的住所。花间词内容涉及箫史的共五首:薛昭蕴“东风吹断紫箫声”(《小重山》其一)、“玉箫无复理霓裳”(《小重山》其二)写宫女的愁怨;牛希济“魏阙宫城秦树凋。玉楼独上无聊。含情不语自吹箫”(《临江仙》其三)咏写箫史弄玉的爱情故事,同时表达出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孙光宪“勿以吹箫伴,不同群”(《女冠子》其二)、毛熙震“应共吹箫侣,暗相寻”(《女冠子》其一)则咏写女道士。
4.姮娥
姮娥亦作嫦娥。《淮南子·览冥》:“后羿请得不死药于西王母,其妻姮娥窃食之,以奔月宫,是谓蟾蜍。”李商隐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诗句抒发主人公长夜不眠,孤独寂寞的心境。花间词涉及姮娥传说的有:韦庄《谒金门》(其一)、《天仙子》(其二),张泌《浣溪沙》(其一),毛文锡《临江仙》,顾夐《浣溪沙》(其八),孙光宪《更漏子》(其一),鹿虔扆《女冠子》(其二),阎选《浣溪沙》,共八首。其内容主要用“嫦娥”、“蟾彩”、“玉蟾”、“银蟾”等语汇象征月光,以烘染离情,表达主人公相思的苦楚和独处的凄冷。如“天上嫦娥人不识。寄书何处觅”(韦庄《谒金门》其二)、“蟾彩霜华夜不分。天外鸿声枕上闻”(韦庄《天仙子》其三)、“花满驿亭香露细,杜鹃声断玉蟾低”(张泌《浣溪沙》其一)、“露白蟾明又到秋。佳期幽会两悠悠”(顾夐《浣溪沙》其八)、“扃绣户,下珠帘。满庭喷玉蟾”(孙光宪《更漏子》其一)、“嫦娥终是月中人”(阎选《浣溪沙》)。另外,毛文锡《临江仙》:“银蟾影挂潇湘”凭吊湘妃,鹿虔扆《女冠子》(其二):“玉珮摇蟾影”则吟咏女道士。
5.织女
《荆楚岁时记》:“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天锦云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其一年一度相会。”花间词涉及织女的有六首,多用“鹊桥”、“银河”、“银汉”来隐喻女子闺中独处的寂寞情怀,如“宫树暗,鹊桥横。玉签初报明”(温庭筠《更漏子》其四)、“锦字书封了,银河雁过迟”(牛峤《女冠子》其四)、“银汉是红墙,一带遥相隔”(毛文锡《醉花间》其二)、“银汉云晴玉漏长。蛩声悄画堂”(魏承班《诉衷情》其三)、“深秋寒夜银河静,月明深夜中庭”(尹鹗《临江仙》其二),或是词人得意地诉说自己与心上女子幽会的场面“鹊桥初就咽银河。今夜仙郎自姓和”(和凝《柳枝》其三),也有就题咏写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七夕年年信不违。银河清浅白云微”(毛文锡《浣溪沙》其二)。
6.湘妃
据《墉城集仙录》记载,湘妃为舜之妃,长称娥皇,次称女英。相传舜南巡时死于苍梧之野,二妃在山下求舜不获,望九峰而泣,疑舜在其上,故号九嶷山。湘妃精诚感通,得仙而去,时人以为沉于湘江,立祠祀娥皇为湘君,女英为湘夫人。花间词咏湘妃词共五首,其中“翠竹暗留珠泪怨,闲调宝瑟碧波中”(张泌《临江仙》)、“灵娥鼓瑟韵清商。朱弦凄切,云散碧天长”(毛文锡《临江仙》)、“风流皆道胜人间”(牛希济《临江仙》其四)抒写主人公游黄陵庙凭吊湘妃,有感于湘妃为舜而死的忠贞不渝之情,“江上草芊芊。春晚湘妃庙前。……独倚朱栏情不极。魂断终朝相忆”(孙光宪《河渎神》其二)则由湘妃庙所见而直抒主人公怀人之情。牛希济《临江仙》(其七)则合咏湘妃与罗浮仙子。
另外,花间词中咏道教女仙的还有和凝《柳枝》(其一)、牛希济《临江仙》(其五)两首咏洛神,牛希济《临江仙》(其一)、阎选《临江仙》其二)两首咏巫山神女,牛希济《临江仙》(其二)咏谢真人,牛希济《临江仙》(其三)咏弄玉,牛希济《临江仙》(其六)咏汉皋神女。因词作数量较少,故不在此赘述。
以上花间词思刘盼阮、怀仙咏真的题材,正是晚唐五代文人落寞消沉的心理写照。他们一面歌酒狂欢,一面又无法掩饰狂欢背后的失落与哀愁。于是借踪迹难觅的神女仙姬传达出了理想的失落与无奈,借思刘盼阮的俗世仙真的声色之欲传达出无望等待中的焦虑情怀。[2]可见,花间词也不像人们成见中的那样一味只是香艳,而是“往往在其表面所写的相思怨别之情以外,还同时蕴含有大时代之世变的一种忧惧与哀伤之感”[3],而道教文化意象作为一种载体,既体现出花间词镂玉雕琼的整体美学风格,又表达出晚唐五代文人在末世中艰难生存的困惑与无奈。
二、女冠
唐代是女冠最盛的一代,由于君主崇道,上至公主嫔妃,下至宫女以及各类民间女子大量涌入道观,其中容貌姣好又能文善艺者吸引了不少文士前来道观与之结交。李冰若《栩庄漫记》说:“唐自武后度女尼始,女冠甚众,其中不乏艳迹,如鱼玄机辈,多与文士往来,故唐人诗词咏女冠者类以情事入辞。”[4]因此,文人与女道士交往成为唐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这样一方面,一些女道士的遭遇、经历得到他们的同情,其技艺、才情得到他们的赞赏;另一方面,在交往中也会产生一定的感情,甚至是爱情。[5]花间词中以道教女冠为描写对象的有温庭筠《女冠子》,薛昭蕴《女冠子》,牛峤《女冠子》(其三、其四),张泌《女冠子》,顾夐《虞美人》(其六),鹿虔扆《女冠子》,毛熙震《女冠子》,李珣《女冠子》,孙光宪《女冠子》,共十五首。女冠词常常通过女道士艳冶的容貌、妖娆的情态来揭示其思凡情欲,“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前。寄语青娥伴,早求仙”(温庭筠《女冠子》其一),或是借女仙故事传达世俗的情爱愿望,“对花情脉脉,望月步徐徐。刘阮今何处,绝来书”(李珣《女冠子》其二)、“翠鬟冠玉叶,霓袖捧瑶琴。应共吹箫侣,暗相寻”(毛熙震《女冠子》其一),也有通过描写女冠服饰、道观环境以及斋醮仪式来咏写女道士求仙情形,“雾卷黄罗帔,云雕白玉冠”(薛昭蕴《女冠子》其一)、“步虚坛上。降节霓旌相向。引真仙”(鹿虔扆《女冠子》其二)、“蕊珠宫,苔点分圆碧,桃花践破红”(孙光宪《女冠子》其一)。花间词人在与女冠的交往中得到了心灵的安慰,同时也在其词作中表达出对女冠同病相怜的沦落之感。而女冠艳冶的服饰及其宫观环境满足了花间词人在人间寻求“仙界”的虚幻心理,女冠的艳丽容貌及其风流心性又满足了他们在“仙界”享受人间欢娱的世俗情欲。因此,花间词中女冠作为一个重要题材,传达出晚唐五代文人及时享乐的欲望与寻找心灵安慰的双重心理需求。
三、“仙”字意象
陈寅恪先生《读莺莺传》一文在阐述《莺莺传》的别名“会真记”的含义时说:“唐代‘仙’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娼妓者”。[6]由此可知,唐代诗文中的仙女常常指代现实生活中装扮妖艳的女子、风流女道士或者是妓女。在风习开放的唐代,狎妓成为风流,官员可以养乐伎,艺伎又常常被自命高雅的文人称呼为“真”或“仙”。仙妓合流,是唐代诗文中新出现的文学现象。[7]花间词中也多处出现“仙”字意象,如仙子、仙容、仙景、仙客、仙郎、仙家、仙乡、仙踪、仙坛、天仙、神仙等。《花间集》含“仙”字意象的词有二十余首,其中泛化引用“仙”字意象以借仙述艳的词作有韦庄《喜迁莺》、和凝《柳枝》(其二、其三),张泌《浣溪沙》(其十),毛文锡《恋情深》(其二),孙光宪《浣溪沙》(其九)、《生查子》(其二)、《风流子》(其二),共八首。如“莺已迁,龙已化,一夜满城车马。家家楼上簇神仙,争看鹤冲天”(韦庄《喜迁莺》)写文人进士及第后的快乐与逍遥,“醉来咬损新花子,拽住仙郎尽放娇”(和凝《柳枝》其二)写幽会时女子在情郎面前撒娇的情态,“小市东门欲雪天。众中依约见神仙”(张泌《浣溪沙》其十)、“谁家绣毂动香尘,隐映神仙客”(孙光宪《生查子》其二)、“楼倚长衢欲暮。瞥见神仙伴侣”(孙光宪《风流子》其二)写男子的艳遇,“乌帽斜欹倒佩鱼。静街偷步访仙居”(孙光宪《浣溪沙》其九)写男子娼门寻欢,“玉殿春浓花烂漫。簇神仙伴”(毛文锡《恋情深》其二)则写后妃与皇帝的恋情。对道教“仙”字意象的泛化引用使花间词的世俗艳情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是艳情词与道教结合以后产生的效果。
另外,在花间词中,还有一些与道教有关的语汇意象出现频率较高,如洞房、玉楼、玉郎、青鸟等,对这些道教语汇的泛化引用,同样也使花间词带上了一定的仙道韵味。
总之,花间词的题材内容呈现出浓郁的道教文化特征,有其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究其原因,主要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从词本身的文体特点来看,“词为艳科”的特性与道教生存享乐的宗旨相契合,成为晚唐五代士大夫文人宣泄末世情感的精神寄托。道教是以生为乐的,生存和享乐是道教的根本目的,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情爱的追求,而词最大的一个功能则是“缘情”。王国维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8][清]查礼说“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宛形容之。”[9]所谓“诗之不能言”、“诗不能道者”,主要就是指那种窈深幽约的男女情爱,可见词与男女艳情的密切关系。因此,词所具有的“香艳味”决定其“好写女性生活和女性之美而带来的一种特殊的审美新感受”[10],而且它所描写的形象多是现实生活中的歌妓和舞女,这些女性形象以“美色与爱情”为其突显特质,这就奠定了词“艳”的基调。“词为艳科”的特性,使得道教更容易渗透其中。道教追求修性延命,道家主张摆脱社会礼仪的束缚,“写意”、“畅神”、“汪洋自恣以适己”[11]。道家和道教的这种乐生理念符合了没落的晚唐五代士大夫文人的精神需要。由于时运衰颓,士大夫文人失去了往日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功名的客观社会条件,因此他们需要某种精神寄托来延续自己的理想和生命。而晚唐五代“礼教松弛,享乐淫逸之风盛行,狎妓冶游,成为时尚”,士大夫文人将道教生存与享乐的人生理念作为全身避害的良方,他们将对现实生活中科举和仕途上缺少出路的失望“寄情于闺阁”,甚至“转而从男女性爱方面寻找补偿和慰藉”[12]。所以,晚唐五代词就挣脱了正统文化向来禁锢自由情志、压抑正常人性的不合理性,表现了对个人幸福的高度关注以及对于“享受人生”的空前热情。[13]于是,沉溺于“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牛峤《菩萨蛮》其七),“歌满耳,酒盈罇。前非不要论”(顾夐《更漏子》),“年少。年少。行乐直须及早”(冯延巳《三台令》其一)的精神享受中成为晚唐五代士大夫文人共同的心里需求和人生体验。
(二)从唐五代崇道风气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来看,借仙述艳是诗文创作中的普遍现象,而充满道教语汇意象的花间词可以说是晚唐五代西蜀地域文化色彩与道教及时行乐思想相融合的结晶。晚唐五代巴蜀偏安一隅,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达,自然条件良好,西蜀“君臣务以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14],形成了追求声色之好的社会习俗。这种崇尚享乐奢靡的社会风气,也孕育了《花间集》镂玉雕琼、裁花剪叶的侧艳之辞。再加上晚唐五代西蜀崇道之风炽烈,于是偏安心态与及时行乐的思想相伴而生,这种享受人生的激情在花间词人的作品中则表现为仙道与艳情的结合。在唐五代,艳情仙化是诗词、传奇创作中的普遍现象。如唐代曹唐的大、小游仙诗,用刘阮遇仙的神人恋爱故事来比拟俗世男女相恋的凄幽情怀,元稹《会真诗》以游仙为诗境来铺垫作者自己的艳遇经历,白居易《长恨歌》用方士招魂的情节来铺叙天上人间的刻骨相思,还有李商隐与女冠相恋所写的《无题》、《碧城》、《圣女祠》等等。在诗中,士人与女冠之恋、士人与妓女之恋、俗世中的男女之恋以及帝王后妃之恋都被置于仙境来表现,使得艳情被仙化了。与此同时,唐代的传奇小说中,文人们更是有意识地敷衍仙凡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甚至文人的狎妓生活也借游仙的方式加以表现。[15]如张鹜《游仙窟》、李朝威《柳毅传》、李景亮《李章武传》、牛僧孺《玄怪录》、薛用弱《集异记》等都有叙写人仙恋爱的故事内容。尤其是张鹜的《游仙窟》,写作者奉使河源,中途投宿所谓的仙窟,受到十娘、五嫂的盛情款待,即以游仙的方式展现文人的狎妓生活。道教的媚俗与唐代文人的浪漫正好相符,在词中也有比较鲜明的体现,因此借仙述艳也是唐五代词惯用的方式。唐五代词中《巫山一段云》、《女冠子》、《天仙子》、《临江仙》、《洞仙歌》、《忆仙姿》、《阳台梦》、《甘州子》、《醉妆词》、《河渎神》等词牌源于道教本事,而内容涉及道教艳情者则更为广泛。因此,唐五代文人把有关的道教典故和语汇意象,如十洲、蓬莱、墉城、高唐、云雨、巫峡、桃花洞、刘阮、姮娥、秦楼、吹箫侣、瑶台、霞帔、霓袖、羽衣、醮坛、三清等等,随心所欲地引入艳情词作中,仿佛信手拈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这些道教意象已经成为文人随身携带以备写诗作文所需的“随身卷子”,“一到需要点缀或夸饰的时候,这些意象词汇便涌上心来,写入诗中”[16]。在崇道之风最为炽烈的西蜀,花间词人更是能娴熟地驾驭这些道教意象,往往将艳情与求仙融为一体。如“乌帽斜欹倒佩鱼。静街偷步访仙居”(孙光宪《浣溪沙》其九),“鹊桥初就咽银河。今夜仙郎自姓和”(和凝《柳枝》其三),“曾如刘阮访仙踪”(顾夐《甘州子》其三)等等。在这些词里,风流文人以“仙郎”自喻,以“仙女”指代妓女,把妓院称作“仙乡”、“玉楼”,而其娼门寻欢的行为则被美化成为“访仙”或如刘阮“遇仙”,这就满足了他们在人间体验仙境的虚妄追求。由此可见,花间词人正是利用了借仙述艳这一范式,在仙道艳情词中大胆地表示男女情爱,宣泄他们的情感体验,同时也隐曲地反映了其求仙觅艳的心理。
综上所述,花间词的题材内容呈现出如此明显的道教文化特征,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唐五代时期道教文化对词的影响和渗透。
[1] 李一氓.花间集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95.
[2] 尚丽新.道教与唐五代仙道艳情词[J].山西大学学报,2000,(1):22.
[3] 叶嘉莹.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词家对此种特质之反思与世变之关系[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1).
[4] 李冰若.花间集评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83.
[5] 孙昌武.诗苑仙踪——诗歌与神仙信仰[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330.
[6]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07.
[7] 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79.
[8] 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81.
[9] 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1481.
[10] 杨海明.唐宋词美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58.
[11] 史双元.宋词与佛道思想[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28.
[12]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13.
[13] 杨海明.略论晚唐五代词对正统文化的背离和修补[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3).
[14]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805.
[15] 高文利.唐五代文人词的仙道意蕴[J].绥化师专学报,2000,(2):28.
[16] 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