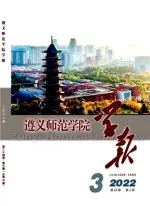欧洲政治认同与社会历史条件
伍京京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5)
(School of the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一、关于认同
要分析“欧洲政治认同”,首先需界定“认同”一词的涵义。“认同”一词的起源可追溯至拉丁文idem(即“相同”,the same),其字面意义与认可、同化相近[1]。而汉语中的“认同”一词,通常是在英文的identification和identity两词的联合意义上来使用的。identification是指人类从自身出发经过与他者的参照比较最终关照自身的认知过程和方式,而identity作为认知结果形成的是一种自我定义和A与非A的结构[2]。英国学者戴维·莫利在《认同的空间》里,分析了认同的概念,认为认同涉及到排斥和差异,是“差异构成了认同”。[3]而中国学者王海兵进一步指出“当代的认同”是指“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它围绕着各种差异轴(譬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展开,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是一个力量的向度,人们通过彼此间的力量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我身份进行识别。”[4]简单地说,认同是一种归属心理,一种对共同体的忠诚感,一种对“我们”与“他们”的识别。而这种“识别”会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同,产生出多种形式:如“民族国家认同”、“地区认同”、“阶级认同”、“宗教认同”、“种族认同”、“性别认同”等等。这些认同虽然可以共存于人的认同体系之中,但这并不表明它们之间总是各司其职、相安无事。相反的,认同之间产生激烈竞争是常有的事,因为人们对共同体的忠诚度有时是很难割裂开来的。近代以来,人们对民族、民族国家的认同在诸多认同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最终成为了一种世界范围内的主体认同。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并最终使“认同”一词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领域。
对认同问题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别:
(一)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认同问题。这主要是从哲学的形而上学的高度考察“认同”这个概念本身。譬如约翰·洛克在《人类理智论》的1964年版本中增加的关于人格认同的章节[5],德里克·帕菲特的“人格认同理论”,昔德尼·舒梅科尔(Sydney Shoemaker)的专著《自我知识和自我认同》,以及中国学者王成兵的专著《当代认同危机的人学解读》。而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有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该书认为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其成员通过“自我和身体的内在参照系统”来建构自我认同,以此实现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化[6]。而哈贝马斯则从皮亚杰的个体发生学意义出发,强调人的系统(社会化的人)和社会系统在结构上的共生性;强调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形态、集体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的一致性[7]。这些研究都力图从发生学上阐释“认同”——这一复杂的精神现象,并往往带有普遍性意义。
(二)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认同问题。从宽泛的意义上说,“认同”本身即可大致归入文化领域。但从更为精确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文化认同特指历史性的、习俗范畴的认同行为。其认同的内容包括共同或具有承继性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等。
(三)从政治的角度研究认同问题。这主要是指民众对政治共同体所表达的态度。具体来说,主要指行为主义和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如果说第一类研究着重探讨认同行为本身,那后两类研究则是在说明认同的来源,或者说是认同的对象。如果从政治角度出发,以政治认同为目的,逻辑上,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但后者还应包括更多的内容。
二、欧洲政治认同的社会历史条件
研究“欧洲认同”的重大意义更多地应体现在政治认同领域——人类在形成了坚固的民族国家认同之后,是否有可能从范围、对象和内容上对其进行重大突破?欧洲有其一定的文化认同,且主流看法认为欧洲共同的思想、习俗、道德规范起源催生了当代的欧洲认同[8],使政治认同成为可能。但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的政治认同并非一个完成的概念,而是一个正在建构的概念。这一建构是否能够完成并非是模糊的文化认同能够决定的。因此,本文将把对欧洲“政治认同”从哲学、文化的角度下降到社会历史条件的角度加以考察,并就其完成建构的可能性提出疑问。人类历史上各种政治认同的形成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关。这里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前者决定了共同体可能形成的范围,即认同可能的界限。譬如,当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经济以国家为单位发展,即“每个国家都把自己视为一个整体,积极推行重商政策”[9]时,欧洲各民族国家认同的边界就基本确定了。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某种政治认同被统治阶层人为地加强,而最终优于其他各认同成为主体认同。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民族国家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凭借其政治资源,通过国旗、国歌、对历史的重新诠释、对他者的强调等等手段来强化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保证其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二)技术条件,即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毫无疑问,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水平限制着人类认同的范围。将他人定义为“他者”或“非我类”的先决条件是意识到他人的存在。这里的一个典型事例是,早在18世纪,北美洲就已建立了自己的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但与之相比,西属美洲的居民却并未考虑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泛西属美洲的民族主义也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则是“18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和科技发展的一般水平,以及西班牙资本主义与科技相对于其帝国管辖范围而言的‘地方的’落后性”,[10]这使得西属美洲各组成部分之间相对隔绝并最终影响西属美洲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范围。而此时的北美洲,由于地域范围较小(此时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地区),各殖民地间联系较为密切,得以形成现代民族认同并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另外,技术条件还涉及文化传播的条件。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只能通过手抄本的方式使圣经在少数的主教、神甫之间流传,拉丁语从此被渲染成一种神圣的语言,为神圣的宗教认同提供了条件。而当资本印刷业兴起之后,在路德的带领下,用方言写成的圣经遍布整个欧洲,方言地位上升、拉丁语遂即衰落,紧随其后的,是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逐渐超越了对宗教的认同。
(三)新闻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公共空间的参与情况。这一条件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深刻,也更为复杂地影响着人类政治认同的形成。社会的政治生活,是人的社会属性的直接体现。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11]而如果按照亚氏目的论的逻辑理解,则可得出政治生活的本质属性是一种公共生活的启示。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公共生活的特征是,“在那里出现的每一件事都是每一个人能见能闻的。”[12]即是说,只有在同一公共空间活动的人才有可能将彼此视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这意味着人们“共时性”地参与某一共同事务并会同样受其影响(当然程度会有所不同)从而视彼此为“命运共同体”。然而,随着新闻媒介(最早是报纸,后来是电视、网络)的出现,这种公共空间呈现出一种“拟态”存在,这使得人们即使不在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的实体中活动交流,也可以通过新闻媒介对某一共同事务产生“共时性”关注进而形成“想象的共同体”,并由此产生认同。政治认同是各种历史社会条件偶合的产物,而并不具有目的论的必然性。其形式、内容、范围以及程度都高度依赖于它诞生和发展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简单地说,对政治认同的认识应该是历史主义的。在2005年,欧洲宪法草案先后在法国、荷兰被否决,在英国、爱尔兰、波兰等国被无限期搁置。于是,人们开始发现欧洲政治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并随即认识到了这种缺失的后果。正如前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指出的“不考虑这种认同(欧洲政治认同),不努力确定欧洲人应该对他们自己有什么样的认识,能够重新统一欧洲吗?坦率地说,我认为那样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个使命被证明是具有冒险性和困难重重的。”[13]然而,对欧洲政治认同的构建并不是“努力确定”那么简单,它涉及到当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诚然,欧洲古老大陆的文明、历史与传统赋予了欧洲政治认同以可能性,但并非必然性。
三、结论
如果我们用上文提出的几个社会历史条件来考察欧洲政治认同,将得到以下一些结论:首先,就经济条件而言,二战以后,欧洲在经济方面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战后重建。到了上世纪70年代,欧洲又面临如何应对全球化的难题。不过,其解决问题的基本手段是一致的,即通过区域内的合作来尽量减少恶性竞争,合理调配资源,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从1950年《舒曼计划》中提出建立欧洲煤钢联营开始,到2002年1月1日欧元面世,欧洲的区域经济逐步发展到经贸联盟的水平并已相当成熟。从这层意义上说,构建欧洲政治认同的经济条件是相当优越的。但是,如上文所言,经济条件只确定了认同可能的界限。而事实上,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如果要动员大众真心实意地从政治上支持这一充满风险的联盟大业,单单依靠经济利益的动机是远远不够的。”[14]且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一条件的作用就更加模糊了。
而在政治条件方面,情况更加复杂。当前的世界仍是民族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欧洲也不例外。但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欧洲大陆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使欧洲人在世界范围内最先意识到了民族主义的危险性。所以,如果说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人民民族主义情绪的激励的话,那在欧洲,情况会有所不同。不难发现,上世纪欧洲的政治家们,尤其是德法两国的领导人,都非常注意对民族主义情绪的规避,并全力以赴地构建理想中的欧洲联盟。在此,我并不想赘述这些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鼓舞人心的讲话。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领导人对欧洲政治认同的强化与对欧盟——这一功能性机构的构建相比是明显滞后的。以《舒曼计划》为代表的功能主义手段,“令人信服地证明,可以通过哪些手段来把经济上获得福利、社会的普遍满意和使和平得到长期保证相互联系起来”。[15]故功能主义的思想,起到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决定历史方向”的作用,“导致对某些利益的确定并把一些行为称之为‘合理的’及‘可行的’路径。其结果便是对于军火制造及重新建设最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建立一种专家所设计的合作。其他的行为选择尽管同样存在,例如通过达成统一的宪法而建立联邦式的统一欧洲,但是它们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作为政治上的主导观念去影响决策者们。”[15]所以,从一开始,欧洲的领导人们便没有把对欧洲政治认同的构建提到实质性的地位,而欧洲的民众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所持态度与其说是基于一种对欧洲的政治认同,不如说是一种“宽容共识”。[16]这说明,欧洲的政治认同从来没有被系统而精心地强化过——就像民族国家所惯常做的那样。它只作为欧洲人诸多认同中的一种,甚至还不如业已发展成熟的“阶层认同”、“地区认同”。
欧洲政治认同的形成过程正好与电视新闻媒体迅速发展壮大、并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也最特殊的公共空间的过程相一致,而后者对政治认同的影响是巨大的。不过,更重要的也许是其加快了理性多元化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新闻媒介造成的是一种“拟态的存在”,“它确实制造了一种‘卷入’(involvement),产生了一种归属感,但无论如何,这不是真正的政治参与”[16]。即它会使人们产生“在那里”或“一同参与”的错觉。这就可能使得人们去关注那些在他们影响范围外的事务(比如英国人可以通过BBC的报道全程关注法国大选)。于是,人们就这些事务形成自己的意见,但由于超出了决策范围,故他们的意见无法被纳入体制之内,而是成为社会多元理性的一种被保留下来。另外,受众在接受媒体信息时必需同时接受一些除事实外的“副产品”:这包括报道背后的商业利益、政治斗争、以及最重要的——该媒体本身所坚持的价值判断。这就使受众在接受事实的同时认识到了多种理性的可能。而上述两点在政治领域的反映是在使政治决策过程一定程度公开化的同时,向民众传达其他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们对该问题的不同意见。民众们通过自己的判断形成观点,再通过公共生活交流进行整合重组,使共同体内形成几股主流意见,再经由媒体报道进行强化。而新闻媒体的这种作用强化了韦伯所谓的现代性的西方价值领域分裂的事实。于是,社会理性多元化发展起来。这里提到的“理性多元化”是作为一种民主政治的结果而存在的。指它们之间的共存,及民众对其进行自由选择的可能。正如罗尔斯清醒地意识到的,“自由理念的确立带来了现代社会的多元化,特别是社会文化、价值、信仰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不单是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的基本条件,而且是西方民主社会的一个永久性特征……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里,人们有权利和理由选择和信奉自己认为合理的学说或观念,并以此制定自己的生活谋划。”[17]如果把欧洲看作一个整体,理性多元化已成为一种大众的社会取向,而并非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精英之间意见的歧出。这一事实意味着人们有充分的自由和可能选择各种政治认同——民族国家的认同、欧洲的认同、阶层的认同、地区的认同等等。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理性多元化的现实意义首先并不是造成一个多元认同,而是作为一个现实社会条件,直接地影响着欧洲政治认同的构建过程。换句话说,理性多元的事实使得尚在构成中的欧洲政治认同过早地失去了必要性。在这一事实下,人们并不必然要选择欧洲政治认同。甚至,欧洲政治认同从来没有像对民族国家的认同那样具备一种权威的、主导的意义。正在形成中的欧洲政治认同只能作为欧洲人诸多“备选认同”中的一个。这显然极不利于其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以至于斯坦利霍夫曼在1964年的《欧洲认同危机》中断言“今天的欧洲没有清晰的认同和轮廓,除了一个工业化进程和一个经济一体化进程外,今天的欧洲没有方向和目的感。”斯坦利霍夫曼在1994年的《欧洲认同危机的修订》中仍然坚持了这一观点[18]。
所以,公共空间的多元理性是欧洲政治认同构建过程中的最大障碍。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多元理性作为民主政治的结果,将会进一步充分发展。于是,我不得不说,从现有社会历史条件来看,欧洲政治认同的构建远没有一种普遍意义的必然性,更不用说对民族国家认同构成威胁的可能性了。
虽然,欧洲政治认同的构建缺乏一种必然性,但这并不过多涉及欧盟合法性被削弱的问题。因为欧盟并不是为了诸如“欧洲统一”这样的政治目的而建立的。正如上文提到的,它的建立带有功能主义的色彩,并有着极为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方式——如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建立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引入联盟公民身份,发展司法和国内事务的紧密合作等等。所以,正如在欧盟宪法草案先后被法国、荷兰否决后,巴罗佐所言“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将不会拥有一部宪法,这是显而易见……我们应在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方面继续努力,而不是无休止地就体制问题进行讨论。政治决断和领导能力比体制更重要”。所以欧洲政治认同层面的问题并不会过多地影响具体层面的事务。而后者才是欧盟整合最坚实的基础。
[1] 贾英健.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74.
[2] 王昱.论当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兼评欧盟的文化政策及意向[J].国际政治研究,2000,(4).
[3] [英]戴维·莫利.认同的空间一一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M].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61.
[4] 王成兵.对当代认同概念的一种理解[J].学习与探索,2004,(6).
[5] [美]J·佩里.人格认同和人格概念[J].韩震译.世界哲学,2004,(6).
[6]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47-253.
[7]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
[8] [意]梅吉奥尼.欧洲统一,贤哲之梦[M].陈宝顺,沈亦缘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9]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43.
[10]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2.
[1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7.
[12] HannahArendt.TheHumanCondition.GardenCity[M].NY:Doubleday,1959.45.
[13] Jacques Delors.“Europe:The Continent of Doubt”,Aspenia,(Fall 2000.37.)转引自李明明.试析欧洲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J].欧洲研究,2005.37.
[14]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M].曹卫东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284.
[15] [德]贝娅特·科勒,托马斯·康策尔曼,米歇勒·克诺特.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M].顾俊礼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8.
[16] [日]猪口孝,[英]爱德华·纽曼,[美]约翰·基恩.变动中的民主[M].林猛等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224.
[17] [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574.
[18] Stanley Hoffmann:“Europe’s Identity Crisis”,Dedahis 93(Fall 19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