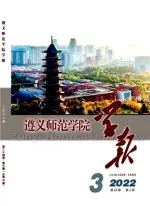唐代诗人的“独”精神及其在诗歌中的体现
黎文丽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陕西咸阳712000)
唐代诗人是一个人格意识比较突出的群体,在他们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诗人思想及创作的影响。唐代诗人秉承了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并且对此有了更深的体悟,这种体悟表现在诗歌中就是出现大量“独”意象的诗句。这些诗句所传达出的精神、所塑造的傲岸孤独的形象,正是唐代诗人不断追求自我完善的真实写照。唐代诗人在儒道文化的交融中汲取养分,修身养性,既体会了“独”之人格独立的治世追求,品尝过“独”中黯然伤神的苦闷,又在调适自我中发现了“独”之超脱。
一
唐代诗人都有崇高积极的人生追求,注重人格意识的高扬。唐代繁荣的经济和文化,相对太平的社会政治,形成一种积极向上、自由开放的时代精神。唐代诗人与唐以前诗人相比,个性意识要强烈得多。他们不仅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且还有着十分清醒的自我形象的塑造。他们自觉承担应尽的时代和历史使命,他们将唐以前诗人的人生理想现实化,以实践的姿态迎接社会和人生,所以他们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我”,也不是一个远离于人世的“我”,而是一个带着安民济世之志奋力拼搏的“我”。[1]在这种时代风气影响下,“独”精神主要体现在唐代诗人独有的人生追求和积极的治世理想,以及对于社会的忧患感。
诗文中的“独”字出现较早,体现了人们对于这一含有独特意义文字的认识和欣赏。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独”字的涵义渐渐丰富起来,也具有了特殊的精神意义,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对此都有自己的理解和阐述。“独”主要表现为儒家之社会理性的“独”和道家之自然理性的“独”。儒家重视人的道德,以道德完善作为人格追求的主要目标。儒家所构想的理想人格从现实社会出发,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担负治国平天下的历史重任。《大学》里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而治国平天下这一使命的实现要以“内圣”为核心,故而儒家之“独”重在修身和自我完善,在调节自我与社会政治之关系,因此有“慎独”、“独善”之要求。儒家主张通过自我修养、自我觉悟,使人的善良本性得以发现和复归,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在道德品性上趋于完善,以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故《礼记·礼器》有“君子慎其独也。”《礼记·儒行》“儒有特立而独行。”孟子也提出:“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修身”是“平天下”的基本前提,“平天下”是“修身”的一种现实追求,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要以完善的内在品格作为保证。儒家学说为天下的士人君子树立了人生理想和价值观,也成为唐代诗人们塑造完善自我和经国治世的永恒追求。与儒家不同的是,道家崇尚人的自然本性,其理想人格是“道法自然”。道家也重视“独”的观念,道家之“独”重在养性,在追求自我与宇宙之和谐,故有“斋心”、“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之追求。庄子认为心与道相即,自然“稠适而上遂”。由这种稠适而上遂,自己的精神投入于无限之中,从一切形器界的拘限里得到大自由、大解放,这便是“无所待”的“独”的境界。“独”的境界即是“天”的境界,所以便“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便“上与造物者游”。[2]庄子的“斋心”与儒家的慎独虽然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就二者是指内心的精神状态而言,则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建立在他们对“独”的共同理解之上。故此,唐代诗人继承了古代思想家的优良传统,坚持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作为理想追求的保证。他们由此而发现了一个独立自足的道德天地,“独”也因此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既体现了士人独有的经世报国之志,又体现了他们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唐代诗人们在耳濡目染中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是大多数诗人共同的人生目标。同时,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是一个高扬理想和积极奋进的时代。故而,他们追求的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将济世安民作为自己的责任,以积极的参与态度去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如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李白的“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都体现出他们对人生理想的认识,对士人操守的坚持,也表现出洋溢的政治热情和凌云壮志。孟浩然也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入仕愿望。白居易早年也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如“此君节操独凌寒,冰雪丛中更耐看”(白居易《题李次云窗竹》)表现其远大的志向。
出于对国家安危和时代风气的考虑,诗人们还表达了自己对时代和社会的忧思之情。唐代诗人自小受着儒家思想的熏陶,深怀济世报国的大志,信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同时,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忧患精神也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思想里,积淀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渗透到文化的各个方面。《易系辞传》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种忧患意识,是对自己肩负的道德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深沉思考。唐代诗人继承了儒家的优良传统,大都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感,对于时代和社会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初唐诗人陈子昂胸怀治国救天下的理想,有着卓越的政治才华。他发出“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陈子昂《感遇》)的感慨,更写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千古绝唱。陈子昂的这种忧患意识,洋溢着一腔浩然正气,所思所忧充满着深深的悲怆之感。诗人杜甫深深地感受着时代苦难和时局艰难,“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描绘出社会的动荡不安与广大人民的辛酸痛苦。正是这些艰难苦恨,才使他头上的白发愈来愈多,而自己又衰年多病,独自登台,自然是悲从中来。这“悲”字是诗人感时伤怀思想的直接流露,也是诗人忧国忧民感情的充分体现。储光羲《五古·效古二首》中的“翰林有客卿,独负苍生忧”也表达了诗人对社会和民生之忧。杜牧《题敬爱寺楼》“独登还独下,谁会我悠悠”融身世之感于社会苦难中,诉说着诗人对时局的担忧之情。
二
唐代诗人有着积极入世的想法和要求,他们对政治理想的歌颂,对人生崇高目标的向往,要远远胜过其他时代的诗人。作为时代和社会的精英,他们意识到自身在历史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充满了时代自豪感和强烈的进取心态。然而,诗人的理想总是被无情的现实所击败,他们在不断追求的过程中饱尝了失落之苦,这种苦闷凝成一团难以释怀的郁结之气,体现在诗歌中,就形成一种惆怅苦闷的“独”情结。这种苦闷又因为诗人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人生境遇,而具有不同的表现内涵。
唐代诗人们有着豪情壮志,但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理想的热情被无情地摧垮。李白生活在以政治清明、重视贤才而著称的历史时期,他希望能像鲁仲连、谢安等人那样,当国家陷于危亡之时,能大显身手挽救时局,而一旦完成使命则可以功成身退,从此退隐江湖,飘然而去。当得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时,李白以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时机到来了。然而,李白“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思想在当时的环境中无法得到实现,这使怀抱着积极用世之心的李白感到极度苦闷。卓然独立的李白,此时深深感到行路的艰难,他在难言的苦闷中吟唱“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李白《月下独酌》),在壮志难酬的失意中“窥觞照欢颜,独笑还自倾”(李白《九日》),在孤立无援的处境里哀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行路难》)。这是胸怀大志而被统治者弃之不用的悲愤之情。故而,李白的“独”中充满了壮志难酬的孤愤之意。
杜甫自比稷契,有治世的决心和能力,他到长安的目的是想通过科举考试获取一定的政治地位,施展政治抱负。天宝六年(747)曾应试“制举”,天宝十年(751)向皇帝献赋,但均无结果。杜甫的愿望不断落空,生活也急转直下,常为衣食所困。虽然他做过拾遗,却成为朝廷政治勾心斗角的牺牲品;到白头为郎时,已是有心无力。杜甫生活在大唐盛世,但这一盛世并没有给诗人提供展示其才能和实现其志向的舞台,更多的是诗人所体会的政治不得志以及生活在困苦中的悲哀。杜甫的大志是开天一代文儒的共同志向,而杜甫仕途的坎坷也典型地反映了文儒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固有的矛盾。[3]诗人在痛苦之时也不断反思,这其实是他所追求的道德理想和人的生命本真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悲剧。杜甫满腔报国之志却难酬壮志,只能感叹“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杜甫《独立》)。他深深地感受着时代苦难和时局艰难,“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为国家的未来和民众的苦难深切担忧。他以推己及人的人生体验表达出悲天悯人的情怀,反映民生之疾苦、志士之艰难。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高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旅夜书怀》“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更是刻画了一位独立寒江、忧国忧民、执着坚毅的志士形象。“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梦李白二首》)是对李白命运的不平之鸣,其实这也是诗圣杜甫自身的确切写照。[4]因此,杜甫的“独”体现出诗人对于国家和民众的深沉的忧思之情。
李商隐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有着强烈的经世观念。但因为身出寒门,虽然有济世之志却在政治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想在政治舞台上一展才华,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却误入党争的漩涡,长期受到排挤和打压。他的一生都在奋力挣扎,却难以实现胸中的理想和抱负。李商隐坎坷复杂的人生经历使他的诗中处处弥漫着漂泊无依、孤独凄凉的伤感,即便是面对阳春金秋之时,有的也只是怅然春恨。诗人《滞雨》中“滞雨长安夜,残灯独客愁”流露出孤独寂寥的愁绪。“李径独来数,愁情相与悬”(李商隐《李花》)、“独夜三更月,空庭一树花”(李商隐《寒食行次冷泉驿》)在言与不言之间点染愁绪,欲言又止,欲止又言,给人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鸟啼花落人何在?竹死桐枯凤不来”(崔珏《哭李商隐》)高度概括了李商隐坎坷世途、怀才不遇的一生。因而,李商隐的“独”体现出诗人在重重压力下所弹奏的伤感无奈之音。
三
儒家学说为人们树立了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观,鼓励人们去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胸怀大志的唐代诗人们,又总是不可避免地感受到理想破灭的痛苦。在饱尝失落之苦,历尽人间沧桑之后,道家思想成为抚慰诗人精神痛苦的一剂良药。诗人们开始转向自我的内心世界,在淡泊明志中体味到超脱的妙境。体现在诗歌中,“独”精神表现为一种历尽艰辛后的超脱与旷达之境。
儒道两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犹如鸟之双翼,能起到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作用。儒家主张积极进取,但在进取中有退让,不走极端,这是中庸之道所要求的;道家提供了另一种人生哲学,提倡自然、清静、无为,崇尚“不争之德”,但并非一味退让,而是要在无为中进行反思,要以退让取得进取。在儒道互补的人生模式中,士人在顺境中多以儒家为指导,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在困境和逆境中则多以道家为调适,超然通达,静观待时。儒道两家对待人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儒道互补构成一种完整的、艺术的人生观,它视人生为一种变速的曲折运动,使得人们能刚柔相济,出处有道,进退自如,心态上和行为上都具有良好的分寸感和平衡感。[5]儒家和道家各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人生的真谛。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即便是理想无法实现,也可以退而自适。庄子认为可以通过“坐忘”、“斋心”来悟道以回复性灵的本明。由悟而明,由明而悟,进入一个无分别、无对待的世界。顺应自然,不滞于物,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唐代诗人在其人生实践中常常遇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当诗人们的热情在现实中遇到挫折时,会感到无尽的愁苦、愤懑。此时,“穷则独善其身”的观念就为诗人提供了另一种精神需求。人生的失意悲愁是难免的,故道家的淡泊明志、清静无为在一定程度上慰藉着诗人们满是伤痛的心灵,支撑着失意诗人的精神世界。在现实生活中,诗人们逐渐将儒道思想融会贯通起来,采取灵活的生活态度,使自己能够摆脱现实烦恼、获得内心的平静和适意,并将这种情感更多地形诸歌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然自得、忘情山水便成为诗人们的精神寄托和人生向往。王绩《黄颊山》有“无人堪作伴,岁晚独悠哉”描画出诗人隐于故乡黄颊山的悠闲生活。卢照邻《春晚山庄率题二首》“田家无四邻,独坐一园春”也表达出悠然于山水的意味。钱起《同严逸人东溪泛舟》“朝霁收云物,垂纶独清旷”流露出诗人的旷达态度。当诗人们告别出仕的梦想后,闲适恬淡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点点滴滴的快乐与悠闲,他们忘却了世间的纷扰,投入到自然的怀抱之中,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超脱。
孟浩然和盛唐时代的许多诗人一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孟浩然《抒怀贻京邑故人》)。他有过济世报国的宏图,也有一展身手的理想。孟浩然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愿意曲意逢迎、随波逐流,但入仕的渴望与受挫的痛楚时时困扰着他的心灵。此时,道家“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理念为孟浩然所接受,道家旷达散淡的追求符合孟浩然耿介不随性格和清白高尚情操的要求。求仕屡屡受挫的事实使孟浩然看清了统治者的真实面目,他便愤然抛却了入仕之念想,为自己寻求到了精神上的超脱之道。孟浩然在《自洛之越》中表明了自己的想法:“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在盛唐人眼里,孟浩然是“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赠孟浩然》)的超脱形象,他追求并沉浸于那种与自然同为一体的生命体验,这使他的诗歌充满着清新淡远的韵味。“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孟浩然《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勾勒出人与自然之间互相依托的情趣,细致入微地传达出日暮山间听泉时的感受,韵味悠长。诗人怡悦而安详地观赏,领略这山色之美,体验着心灵的超然和愉悦。
诗人王维更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走出了一条仕隐两相得的道路。青年时代的王维是很向往功名的,但官场的失意和挫折使王维心中的禅意日益浓厚,乐静好隐的人生情趣便强化了淡泊人格,他广交道友,徜徉山水,参悟禅理,无往不适。王维在《与魏居士书》表明他对于隐的态度:“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在他看来,只要身心相离,任心之所适,就可以平衡仕宦和心性超越的矛盾。王维最终协调了名利与自由的矛盾,“独善”从禅学思想出发具有了另外的解释与行为方式,仕即仕,隐即隐,仕非仕,隐非隐,从而达到对人生的大彻大悟。王维《终南别业》“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表露诗人自甘寂寞的山水情怀;《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构思精巧而不露人工雕琢的痕迹,具有空灵而自然的意境美。在清幽的山水中,只有一片空灵的寂静;《归辋川作》“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表现了随缘任运、闲适自在的境界;《早秋山中作》“寂寞柴门人不到,空林独与白云期”抒发了自己乐隐好静的生活理想,体现了气和容众,心静如空的“无我”境界,使他的诗歌创作体现出禅意和禅趣。
儒家学说重视理想人格的塑造,把道德培养看作是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这种主张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一直是有志之士的精神力量。道家学说以超越的态度观察人生与社会,为人们提供涵泳人生、观照内心的精神需求。儒道学说共同建构着诗人们的精神世界。唐代诗人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实践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要求,因此上说,唐诗中不断抒写的“独”精神体现了诗人们对理想和人生价值的体悟和追求;当理想的热情被无情地摧垮后,“独”精神体现了诗人们失意的苦闷;在寻求自我的过程中,诗人转向内心世界,“独”精神体现了诗人在淡泊明志中找到了超脱的方法。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唐代诗歌独特的内容和风格,更丰富和深化了诗歌主题。
[1] 霍松林,傅绍良.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0.
[2]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8-79.
[3] 葛晓音.杜甫的孤独感及其艺术提炼[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6(1):94-98.
[4] 莫砺锋,童强.杜甫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317.[5]白奚.孔老异路与儒道互补[J].南京大学学报,2000,37(5):9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