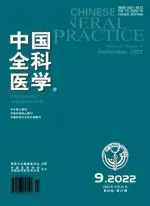基于脑动脉硬化量化评分系统构建脑卒中预警模型的基本思路
康庆云,宋 治,郑 文,贺国华,薛 俐
1 脑动脉硬化量化评分系统对脑卒中预警的意义
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病死率及致残率均较高,它与心脏病、恶性肿瘤构成人类的三大致死病因。我国每年因本病支出人民币近 200亿元,给国家和众多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1]。如果能对脑卒中在未来时间里的发生进行个体或群体的预测或预报,评估患脑卒中的危险度,筛检出高危人群,并将他们作为特别干预对象进行重点干预预防,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那么对于避免或推迟脑卒中的发生有重大意义。这也符合我国卫生部对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的主导思想——针对发病率和病死率高的疾病,筛选高危人群进行重点预防。然而,如何对脑卒中发病做出准确的预测,是脑血管病预防研究领域里一个难点问题。此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卒中预测和高危人群识别(脑卒中预警)曾进行过许多有益的尝试与探索[2],形成了多个脑卒中的预警模型。如卢启秀等[3]对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颈动脉硬化斑块预测缺血性脑卒中的效能进行了评价,形成了颈动脉斑块检测预警模型;韦贵珠等[4]利用综合指标法对394例中老年人的脑卒中预测结果进行了报道,形成了以血液流变学检测构建的脑卒中预警模型;曹奕丰等[5]根据队列基线的危险因素调查和脑血管血流动力学指标 (CVHI)检测结果,建立了 CVHI脑卒中预测模型。此外,国内伍期专等[6]提出了溶血磷脂酸 (LPA)在缺血性脑卒中的预警作用。陈新军等[7]提出溶血磷脂酸和氧化低密度脂蛋白 (Ox-LDL)可作为脑卒中早期预警的可靠指标。国外学者 Moons等[8]对男性队列人群基线调查资料与随访结果进行了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病史、体检、血脂、纤维蛋白原和心电图等是脑卒中的独立预测因子。但目前仍无一种预测模型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通过对上述各类模型分析发现,上述预测模型的构建主要基于卒中事件中的某一指标。众所周知,医学事件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有其必然性,但偶然性也同样在发病中扮演重要角色,显然以上预测模型难以反映事物的全貌,因而其预测结果将大打折扣。
因此,针对上述不足,将系统论理论运用于脑卒中预警系统的构建,我们提出“点线面体”系统预测观[9]。如果将脑卒中发病预测问题视为一个 “体”问题,那么完整的 “体”预测应该建立在由“点 ” 及 “线 ”, 由 “线 ” 及 “面 ”,再由 “面 ”及 “体 ” 3个层次组成 (类似树状结构,称之 “预测树”)的预测体系基础之上。基于公认的医学模型,脑卒中发病预测的 “体”问题,应从 “生物面”、 “心理面” 与 “社会面” 3个面上建立预测体系。而 “面”预测问题实质上为其上的各 “线”预测问题,后者再由各 “点”预测问题组成。由此可见,“点”预测乃至 “线”预测可谓之方法,都以 “体”预测为最终目的。
脑动脉硬化是各种危险因素长期作用于脑血管导致血管结构改变的客观体现,对脑动脉硬化进行量化评分,建立科学的脑动脉硬化评分体系,虽然只能视为一个“线预测”问题,但脑动脉硬化作为脑卒中发病的生物学基础 (结构线)是核心问题,因而,基于该结构线构建的预测系统,可望获得重要的预测信息,如能较好地结合脑血管储备能力 (功能线)预测,可望建立较完整的预测模型。
2 脑动脉硬化量化的评定方法
基于脑部供血动脉解剖学特点,按供血动脉直径的大小,大致上可将脑供血动脉分为 3个等级,即大口径动脉 (4.0~8.0 mm)、中等口径动脉 (2.0~4.0 mm)与小口径动脉 (<2.0 mm)。依据解剖学资料,内径在 4.0~8.0 mm的大口径动脉包括颈总动脉 (CCA)、颈内动脉 (ICA)、双侧椎动脉和基底动脉。内径为 2.0~4.0 mm的动脉包括大脑中动脉、大脑前动脉和大脑后动脉等。而内径<2.0 mm的动脉很多,如眼底视网膜动脉 (内径 1.0 mm左右)、脉络膜前动脉及大脑中、大脑前和大脑后的各二级以上分支等。因而通过检测上述 3种口径的脑部供血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参数,可望在“结构线”的水平上实现脑卒中发病预测系统的构建。
2.1 大口径脑动脉粥样硬化的量化评定方法 国外学者 Sutton等[10]应用多普勒超声法对颈动脉等大口径动脉进行检测,依据检测结果获得斑块指数和 ICA/CCA血流速度比值这两个参数,并把其分别作为评价颈动脉硬化范围及颈动脉硬化病变程度的指数。国外学者 Handa等[11-12]用斑块积分及动脉管腔狭窄百分比两个指标来衡量颈动脉硬化的程度。颈动脉狭窄的评价是脑动脉硬化量化评定的热点,目前常用的计算大口径脑动脉狭窄程度的方法有 4种[12-13],分别是北美症状性颈动脉内膜切除试验法 (NASCET)、欧洲颈动脉外科试验法 (ECST)、颈总动脉法(CC)和颈动脉狭窄指数法 (CSI),其中 CSI是测量颈动脉狭窄最可靠的方法。依据计算的结果,将狭窄程度 <50%划为轻度狭窄,狭窄程度 50%~70%划为中度狭窄,狭窄程度 71%~90%划为重度狭窄,狭窄程度为 100%者视为闭塞[14]。同时,内中膜厚度、斑块性质等亦是评定动脉硬化的指标[10,15]。上述结果表明应用多普勒超声法可为等级评价大口径脑供血动脉提供重要的信息。
2.2 中等口径脑动脉硬化的量化评定方法 磁共振血管造影 (MRA),CT血管成像 (CTA)及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是评估颅内中等口径血管的良好手段。依据此类检查结果,可为中等大小口径的脑供血动脉提供重要的评价方法。虽然 DSA被视为血管评价的金标准,但因其系有创性检查,难于广泛使用,因而,MRA与 CTA可望成为评价颅内中等大小口径供血动脉的重要方法。
同时,经颅多普勒 (TCD)通过对颅内中等口径动脉血流速度、搏动指数及阻力指数等指标的无创检测,间接地反映颅内中等口径动脉的功能状态,从而成为评价脑动脉硬化的理想工具。Baumgartner等[16]把:(1)狭窄处彩色血流显像呈异常色彩,即有混叠现象;(2)色彩异常部位收缩期最大流速大于正常值 2个标准差以上;(3)色彩异常中心部位 Vs高于狭窄前后部位 30 cm/s以上;(4)多普勒信号显示湍流征象,如频窗充填等,作为诊断大脑中动脉 (MCA)狭窄的 TCD诊断标准。北京宣武医院把 MCA狭窄分为3级:(1)轻度狭窄:60岁以上,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 120~150 cm/s;60岁以下,140~170 cm/s;(2)中度狭窄: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 171~200 cm/s;(3)重度狭窄: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 >200 cm/s[17]。
此外,Mori等[18]于 1998年将颅内动脉硬化性狭窄分为 3型:A型病变长度 <5 mm,向心性或适度偏心性狭窄;B型病变长度 5~10 mm,严重偏心性狭窄,或时间短于 3个月的闭塞;C型病变长度>10 mm,严重成角病变伴有近端路径明显迂曲,或闭塞时间大于 3个月。Jiang等[19]于 2004年提出了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 (IAS)的部位 (Location)、形态学 (Morphology)、路径 (Access)分型,即 LMA分型。不过,此两种分型更常用于拟行介入手术患者的术前风险评估。
总之,无论是应用 MRA、CTA、DSA,还是 TCD,均能获得评价内径在 2~4 mm的中等大小动脉的相关参数,从而为构建预测系统提供重要的信息。
2.3 小口径脑动脉硬化的量化评定方法
3~4级以上的颅内各分支动脉及视网膜动脉,其内径在 2 mm以下。用于显示颅内分支动脉的检查手段有 MRA、CTA和 DSA。但前二者对 2 mm以下动脉显影不佳,难以作为评价动脉结构变化的工具。DSA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工具。
另外,视网膜动脉可以作为小口径颅内供血动脉的代表。早在 1953年就建立了根据高血压患者的视网膜小动脉痉挛和视网膜小动脉硬化程度分度的 Scheie氏分类法。该分类法把视网膜动脉硬化分为4度:1度,视网膜小动脉变窄的程度轻微,临床上常不易看出,即使患者高血压较重,如预先不知患者有高血压,也常因小动脉狭窄程度轻微而漏诊;2度,狭窄现象明显,由于血管痉挛关系,出现局限性管径粗细不等;3度,视网膜小动脉狭窄及管径粗细不等现象显著,视网膜出现出血和 (或)渗出,其中渗出物是诊断的要点,出血的分布与视网膜静脉血栓不同,呈散在性分布;4度,除 3度变化外,又增加了视盘水肿。该方法至今仍不失为指导临床评价脑动脉硬化的重要参数。
2.4 国人脑动脉硬化量化评分表的制订
拟收集目标人群相关资料,基于上述对脑动脉硬化量化评定方法的阐述,确立评价指标条目,通过对 3种不同大小口径的脑动脉的各个评价指标进行等级评定(半定量),并依据等级评定给予赋值评分,形成目标人群脑动脉粥样硬化量化初始评分,同时应用相关的统计学方法,对指标的赋值评分进行修改,最终形成科学的脑动脉硬化的量化评分体系。从而实现科学的脑动脉粥样硬化量化评分,并把其作为结构线上反映脑血管病变程度的指标。
3 脑卒中预警模型的构建
3.1 脑动脉硬化级别的 Ordinal Regression预测模型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拟收集脑供血动脉处于不同状态的 3组大样本人群,即以 “20岁以下无心肝肾疾病的人群”代表无动脉硬化的群体 (A群体)、以 “初诊的高血压病人群”代表轻度动脉硬化的群体 (B群体)、以 “高血压病已患脑卒中人群”代表中至重度动脉硬化的群体 (C群体),依据上述脑动脉硬化量化评分体系,通过完成规定的检测项目并评分,把评分值纳入 Ordinal Regression回归模型行回归分析,建立 “量化评分与脑动脉硬化级别的回归方程”,同时应用相应的统计学方法评价上述硬化级别的科学性,并对上述硬化级别的划分进行必要的修订。
3.2 预测脑卒中发病概率的 Logsitic模型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同上。通过收集脑供血动脉处于不同状态的 3组大样本人群,把评分值纳入 Logsitic回归模型做回归分析,通过 “B”与 “C”之间的回归分析,建立 “量化评分与脑动脉粥样硬化并继发脑卒中的回归数学方程”,可预测已患脑动脉粥样硬化者将患脑卒中风险的概率,同时应用相应的统计学方法评价该预测模型的科学性。
4 展望
以 “点线体面”系统预测观为指导,收集目标人群的相关信息,构建脑动脉硬化量化评分及脑动脉硬化量化评分预警卒中模型的数据库,从而建立脑卒中发病的预测模型,为筛检出脑卒中发病高危人群、明确高危级别及制定不同高危级别人群的预防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1 李金国,白波 .线栓法制备大鼠局灶性脑缺血模型的研究 [J].泰山医学院学报,2008,29(4):308-312.
2 郭吉平,黄久仪 .缺血性脑卒中的预警研究进展 [J].中国全科医学,2005,8(13):1104-1106.
3 卢启秀,刘厚林 .颈动脉粥样斑块显示与中风预报 [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2,9(2):98-100.
4 韦贵珠,郑军 .中风预测 394例分析 [J].中国蛇志杂志,1995,7(3):16-18.
5 曹奕丰,王桂清,黄久仪,等 .脑血管血液动力学参数脑卒中预测模型的建立 [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3,24(9):798-800.
6 伍期专 .溶血磷脂酸在心脑血管疾病诊断及病因学中的作用 [J].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2003,5(2):77-79.
7 陈新军,龚爱平,荣良群 .脑卒中患者的溶血磷酯酸与氧化低密度脂蛋白测定 [J].心脑血管病防治,2007,7(3):148-150.
8 Moons KG,Bots ML,Salonen JT,et al.Prediction of stroke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Europe(EUROSTRKE):is there a role for fibrinogen and electrocardiography[J].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2002,56(Supple 1):130-136.
9 宋治,郑文,谷绍娟,等 .构建脑卒中发病定性预测系统的理论与方法 [J].中国全科医学,2008,11(4A):619-622.
10 Sutton Kc,Wolfson SK J,Thomp son T,et al.Measurement variability in duplex scan assessement of carotid atherosclerosis[J].Stroke,1992,23:215-220.
11 Handa N,Matsumoto M,Maeda H,et al.Ultrasonic evaluation of early carotid atherosclerosis[J].Stroke,1990;21:1567-1572.
12 Handa N,Matsumoto M,Maeda H,et al.Ischemic stroke events and carotid atherosclerosis.Results of the Osaka follow-up study for ultrasonographic assessment of carotid atherosclerosis(the OSACA study) [J].Stroke,1995,26:1781-1786.
13 武剑,王拥军.颈动脉粥样硬化的评价[J].国外医学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分册,1997,24(2):62-65.
14 秦正良,陈心岭 .颈动脉粥样硬化与脑梗死的相关性研究 [J].临床荟萃,2007,22(9):641-642.
15 Medina G,Casaos D.Increased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thickness may be associated with stroke in primary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J].Ann Rheum Dis,2003,62:607-610.
16 Baumgartner RW,Mattle HP,Asilid R.Transcranial colorcoded duplex sonography 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methods applications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J].Journal of Clinical Ultrasound,1995,23(2):89-111.
17 华扬 .实用颈动脉与颅脑血管超声诊断学[J].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55-65.
18 Mori T,Fukuoka M,Kazita K,et al.Follow-up study after intracranial 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cerebral balloon angiop lasty[J].AJNR,1998,19:1525-1533.
19 Jiang WJ,Wang YJ,Du B,et al.Stenting of symptomatic MI stenosis of middle cerebral artery:an initial experience of 40 patients[J].Stroke,2004,35:1375-1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