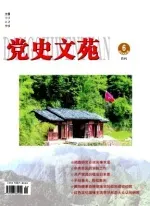邓小平新型党际关系原则形成的条件分析
徐东辉
(安徽工程科技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加了若干重大的党际交往活动,尤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间进行的意识形态论战中,他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那个时代中共与外国政党尤其是与苏共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通过对党际交往实践经验的正确总结和新形势的准确分析判断,又提出了构建国家间各类型政党新型关系的指导原则①,使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国家间政党交往的新局面。
一、主观认识与国内外大趋势的客观现实相统一的要求
邓小平新型党际关系原则的形成,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主观上对时代主题这一客观大势的重新认识和对我国国情的全面分析,离不开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并对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1.确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自俄国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一直被认为是时代的主题。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共未改变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从北方虎视眈眈直接威胁我国安全;而美国直接插手越南战争,直逼我国南大门;苏美还在全球展开争夺,互有攻守,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因此,中共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迫在眉捷,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发展趋势有了重大变化。美苏在全球范围的争霸引起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同声谴责,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政治独立后,开始把目光由转向经济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目标。1977年到1979年的三年是我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的三年,与美国的正式建交标志着我国与西方各国关系的根本改善;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联系使我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巩固。这些成果“奠定了我国外交上的新格局,使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了比较好的国际条件,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也扩大了阵容”[1](247)。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经过冷静分析,改变了以往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1](416),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对外政策的纲领,一心一意搞建设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
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确认,使中国共产党把改革开放的对内政策与捍卫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的对外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也使中国共产党与外国众多的各类型政党有了共同语言,为中共与这些政党建立正式的党际联系提供了条件。
2.实行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曾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了与苏联结盟防范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政策,1960年以后,中苏同盟名存实亡,两国间矛盾加剧。20世纪70年代,为抵制苏联对我国安全的现实威胁,中共开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并执行了一条联美抗苏的策略。这些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弊端也十分明显。不仅使我们的对外政策受到苏美的牵制,不利于我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执行,影响了与一些国家的关系,而且使我国的内政也分别受到苏、美霸权主义的干涉,妄想我们吞下违反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从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明确放弃以往那种结盟政策。正如邓小平所讲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高举反霸旗帜,谁搞霸权就反对谁,“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2](57)。 我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与谁结盟,都会使当时美苏的战略平衡失去重心。中国共产党完全按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来判断对错,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目的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保障我国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促进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与发展。
我国实行真正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使世界和平有了更大的保障,也让中国共产党可以灵活地与外国各类政党进行交往。
3.确定了对外全面开放的基本国策。新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宣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然而,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国门基本上是关闭的。原因是,以美国首的西方主要国家一直对华采取了经济上封锁、政治上敌视、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主客观条件上,我国都不具备与之往来的条件;20世纪60年代,苏联及东欧国家因意识形态争论而与我中断来往,我国失去了与世界交流的主要渠道。再加上当时战争的阴影时时笼罩在我国的头上,这使我国加重了对外的戒备,关起门来搞建设成为当时国家安全的一件大事。
尽管我们在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封闭起来搞建设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我们要赶超世界经济强国,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打开国门,扩大交流与合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果断地确定了对外全面开放的基本国策。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工作的目标也相应地做出调整,通过党际关系,学习外国政党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的有益执政经验,加强与外国各阶层人士的联络,巩固国家间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基础,努力维护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中共与不同类型政党正常交往的客观需要
自1977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活动越来越频繁,对象多、范围广、程度深、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已成为新时期中共对外工作的特点,许多国家的不同意识形态的执政党或在野党纷纷与中共重建、恢复或建立了正常的党际关系。
1.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恢复或重建党际关系。1977年八九月间,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应邀访问我国,邓小平以老战士的身份与铁托举行了会谈。两党领导人本着“不算旧帐向前看”的精神,不再纠缠以往两党历史上争论是非,达成了谅解,做出了恢复两党关系的重要决策,打开了中南两党关系的新局面。这在国际共运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0年,中国共产党先后与意大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国内派)恢复或建立了党际关系。1982年与法国共产党也恢复了关系,与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也逐渐开始解冻。
在新的大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克服以往各国共产党处理相互间关系的严重缺陷,反对党与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既反对外国党对自己指手画脚,又反对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别人,干涉别国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倾向。正如邓小平所讲的,对外国党内部的事“不赞成是一回事,指手画脚又是一回事,这是个原则问题”[3](864)。因此,中共需要提出构建对外新型党际关系的指导原则。
2.与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建立党际关系。过去,中共基本上只同各国共产党发生联系,尽管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政党和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如英国工党等有些来往,但没有建立正式的党际关系,也没有明确与此类政党交往的指导原则。197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已认识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那种用意识形态来划分阵营的做法已不合时代潮流。中共尽管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不同,但在维护世界和平,争取社会进步,加强各国人民的友谊,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缓和热点地区紧张局势,推动南北对话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等方面有许多相似点和共同点。因此,发展和加强与他们交往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重要任务,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这也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的要求。1977年底,中共中央批准了中联部和外交部《关于黑非洲等地区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求与我建立关系问题的请示》,突破了只同共产党联系的传统做法,开始了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政党的友好往来。1981年2月,以密特朗为第一书记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团访华,中共本着完全平等、求同存异的原则与法国社会党建立了正式的党际联系。在此期间,邓小平在回答法国记者提问时说:“就我们来说,所有法国的政治力量我们都愿意接触。”[4]中国共产党与法国社会党的交往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兴趣和积极评价,引发了此类政党与中共建立联系、发展友谊的热潮。1981年4月,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代表团访华;1984年5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访华,他们均与中共建立了正式的党际关系。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处理与这些政党的关系,使之为维护和发展国家关系服务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成为中共发展对外党际关系的重要工作思路和价值取向。
三、新时代条件下构建新型党际关系模式的需要
所谓模式,一般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俄国十月革命后,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列宁创建了共产国际,国际内形成了一种国家间党际关系模式——“中心模式”或“大家庭模式”。即共产国际是领导中心,各国党是共产国际支部,必须接受领导中心的指导。无形中列宁创建的苏共获得了与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位,苏联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这种国家间政党关系模式,且不说苏共与东欧国家党关系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仅从中共与苏共(共产国际)的关系上就确实有深刻的教训值得记取。
1.“领导中心”和“领导党”的弊端。共产国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中心,而苏联共产党,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共产国际内居于“领导党”的地位。共产国际和苏共在指导中国革命中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所暴露的问题也是鲜明的。“领导中心”和“领导党”的过多干预不利于中共党的领导集体的成熟,影响了党内团结。邓小平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2](309)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共年轻,经验少,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低;另一方面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干预不无关系。由于共产国际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当国际的领导机构将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际相结合,未能准确掌握具体情况而发出指示,用具体布置代替原则指导时,这样的“领导中心”就成了干涉各国党内部事务的中心。各国党难以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实践,无法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的革命策略,相反却鼓励了党内教条主义的流行。如向忠发作为中共历史上最不称职的一位总书记,他的当选是当时共产国际和苏共“唯成分论”的结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直接造成了党内斗争的严重扩大和斗争手段的错误,伤害了大批优秀的党员干部,给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犯的“左”倾错误与抗战初期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照搬法共“人民阵线”的经验,不顾国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推行右倾投降主义政策均是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他本人直到1941年还坚持错误观点,“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5](200)
2.以“以苏共为首”的教训。“以苏共为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二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以美国为首,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两极政治格局。苏共和欧洲其他八国工人党共产党还在1947年建立了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变相恢复了1943年解散的共产国际的组织模式,形成了以苏共为首的共产党国际组织。
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不仅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的敌视,而且还面临着苏共的猜疑。由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曾屡次抵制来自苏共的干扰,在中国革命的若干重要关头,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所以“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是真正的革命”。[6](122)正在此时,苏南矛盾激化,于是“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6](120)
为了争取苏联和其他进步国家的支持,打破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威胁和封锁,以利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因素和当时现实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共提出了“以苏共为首”的观点。中共对苏共的态度是真诚的,因为中共认为:“‘为首’和‘中心’不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不是父子党的关系,要强调相互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帮助和支援。”[7](29)“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不但符合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和全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8]然而,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共都未能改正“老子党”的错误做法,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共,对中国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引发了两党之间严重的意识形态争论和两国关系的破裂。1964年11月7日发生的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②使中共判断苏共领导“仍在搞颠覆兄弟党那一套”。由此可见,以某国党为首的做法,特别是当这个党不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的时候,在实践中只会重蹈“领导中心”或“领导党”的复辙。
事实说明,“中心模式”或“以某国党为首的大家庭模式”造成了国家间党际关系的不平等,伤害了民族感情,必然导致国家关系严重受损。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心模式”或“大家庭模式”存在的基础已消失,中共以经济建设为全部工作的中心,与各国各类政党相互交往需要崭新的模式,这应该是无中心的、以平等为基础的、以经济交流和执政经验交流为中心,交往内容丰富多彩的、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促进国家之间求同存异,加深友谊的政党交往模式。
四、结束语:新型党际关系价值理念的显现
邓小平新型党际关系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理论在新时期的重大突破与创新。在该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广交朋友,既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也为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发展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各国之间的合作,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更重要的是,透过原则和在原则指导下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不再把党际交往看成是一项重要的策略行动,而是在构建国家间新型党际关系过程中向世界展示了始终追求“自主、平等、友谊与和平”的价值理念。○
注 释:
①1980年5月,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邓小平阐述的原则概括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新型党际关系四原则。
②1964年11月,周恩来率中共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在11月7日的苏联政府国宴上,苏共中央委员、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对周恩来和贺龙说:“不要让任何鬼来扰乱我们的关系。”“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他的挑衅,当场遭到周恩来、贺龙的严厉驳斥。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新华社.邓小平副主席会见法国记者就当前国内外若干重大问题作了回答[N].人民日报,1981-02-13(1).
[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吴冷西.忆毛主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8]《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N]人民日报.1956-12-29(1).
[9]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