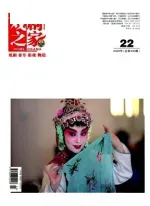探析萨满音乐的构成要素
□王黎平
探析萨满音乐的构成要素
□王黎平
满族萨满音乐在文化传承上保持着的这种相对的一贯性和稳定性,一方面是与满族悠久的历史和坚实的文化根本密切相关,另方面是由萨满音乐的独特存在方式、表现功能、传播途径以及音乐结构形态所决定的。
满族萨满音乐的构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音乐表现工具
在萨满的观念中,对于在跳神活动中应用最广泛的神鼓和腰铃,并不具有乐器的含义,而只是人们所说的神器、法器或礼器。按照现代乐器分类方法,神鼓和腰铃则分别归属于膜鸣乐器和体鸣乐器。此外萨满经常使用的神器还有抬鼓、晃铃、扎板、神镜、哈马刀等,其中,有的神器按照发声机制、形制以及使用功能严格地划分,很难划入乐器类。
从一些乐器的形制和制作材料上看,以及通过一些满族民间传说中的记载,可以判断,神鼓的历史最为久远,而腰铃、晃铃等一些金属制乐器,最早也只能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人类掌握冶炼技术之后。能够看出,萨满使用的乐器基本是以体鸣乐器和膜鸣乐器为主。这些乐器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一代又一代萨满文化交流传入北方的一些弦鸣乐器、气鸣乐器,尽管音色多变、技巧丰富,但已很难再进入萨满的祭祀仪式以至观念当中了。
二、音乐表现形态
如果从音乐形态学的角度剖析现存的满族萨满音乐,它所具有的人类早期音乐特征是极其明显的。神歌的音域一般较窄,旋律平直,多以同度、二度、三度、四度音程构成。有的神歌甚至只用了两三个音,如被认为是满族民间“原生腔”的神歌《念杆子调》,只用了宫、商、徵三个音,全曲通篇几乎完全是在调式主音宫音上进行的。从满语研究的角度,这种近乎于念白的旋律特征,被认为是“受满语语音谐合规律”所制约(满语无四声)。按照旋律生成、演化的规律,这种缺少小二度、大小六七度及增减变化音程的旋律形态,正是音乐欠发达的标志。
笔者认为,造成神歌旋律缺少变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神鼓在萨满祭祀活动中的意象作用,而使节奏(鼓点)占居主导地位,这也是人类原始音乐构成特征之一,由此,对于萨满音乐的研究,尤应重视节奏的形态和作用。从目前探知的一些具有规律的节奏原型,如老三点、老五点、快五点、正七点、花七点等节奏型来看,其组合运动形式完全是以满族语言的“音节规律”和人体的律动周期规律作为发展基础的,其中也蕴含着满族在长期的生活、劳动中形成的独特的心理素质和审美趋向。
三、音乐表演形式
与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的原始音乐存在方式,表演形式相类似,满族萨满音乐的表演形式也带有一种综合性艺术表演的特点。所不同的是,由于萨满的艺术表演一直贯穿于整个祭祀活动当中,大量神辞融于其中,从而形成“歌、舞、乐、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表演形式。匈牙利学者迪欧塞吉曾作过形象地概括:“萨满是一个演员、一个舞蹈家、一个歌手和一个整体管弦乐队。”其中就包括了词、舞、歌、乐四个方面的表演技能。
在萨满看来,神器有一定的暗示作用,从各种器具奏出的音响中,可判断是什么神降临。此外,神器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一些萨满的神鼓鼓面上常绘有云、鸟、虎、蛇、海涛、树、日、月等自然景象和动物图案,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宇宙世界。在萨满观念中,“鼓代表云涛,灵魂坐神鼓飞天入地,所以萨满神鼓一敲,即台翔天飞舞。”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流域,曾传流一部满族先世女真时期的著名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其中有一段描述乌布西奔因神授而成为盛名再世的大萨满的内容:
“轰勿(晃铃)响了,腰铃响了,神鼓响了,众萨满焚香,叩拜东海,只见从江心水上走来了一鸣惊人的哑女。她用海豚皮做了一面椭圆鸭蛋鼓,敲起疾点像万马奔驰……神鼓轻轻飘起,像鹅毛飞上天际。在众族人头上盘旋一周,忽悠悠落在乌林毕拉河面之上……‘我为乌布逊部落安宁而来人世,你们就叫我乌布西奔萨满吧!’从此,东海响彻新的征号——乌布西奔萨满大名历世传流”。乌布西奔相传是当时女真部落中一位“神威无敌、盛名盖世”的大萨满。
萨满的神器在充当各种角色的同时,也发挥着重要的娱乐作用,一些萨满在挥弄神器时的出色技能表演和着意创造出的娱乐氛围,也使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而且,“无论是从技艺还是从完全为表演娱乐的意义上看,音乐都是可以培养而且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一种个人创造技艺;通过音乐,人们可以互相交流或分享情感和生活经验”。
以上对于满族萨满原始音乐形态特征的客观分析,以及对于萨满音乐观的认识,有助于我们从萨满本体文化上去判断其价值,否则,容易造成音乐价值观方面的错位,尤其是当研究主体与客体在音乐概念方面,表现出巨大的理论认识差距时。
本文为黑龙江省艺术规划项目成果之一。(编号RY10B023)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 王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