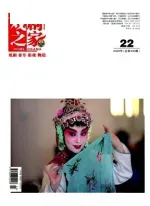淮海戏
——我执着无悔的追求
□赵 娜
淮海戏
——我执着无悔的追求
□赵 娜
淮海戏,是中国江苏苏北地区的一个地方剧种,这一带的方言俗称“海阔腔”,而淮海戏正是用这种方言的演唱形式感动着这一带的观众。
记得在小的时候,每年夏天大伙儿一块乘凉的时候,总会有人唱上几段,我的母亲也是其中之一,虽然他们的唱腔称不上有多艺术,但我还是被那朴素的语言和优美的旋律所吸引。也许是天赐良缘,1995年,江苏省淮海剧团招生,当时我正好是应届毕业生,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毫不犹豫地就报考了,并且在家人的支持和自身的努力下,终于如愿以偿踏入了淮海戏这个艺术殿堂的大门。
随着戏曲艺术生活的逐年深化,淮海戏所特有的品格、风姿、韵味又使我从情感上滋生起一股追逐淮海戏艺术的强烈欲望。正是这种欲望,使我和它已经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已经不再满足于对它的模仿了,而更倾心于对这门艺术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在唱腔上,对于我们地方戏而言,可能更注重于唱腔的表现,但是,想要把它唱好、唱活、唱出韵味来,不是仅凭一副好嗓子或者有“一点就通”的悟性就可以的,而是要有文化的积累和表现技巧,要有对本剧种传统戏曲音乐规律和美学精神的深层领悟才行。作为一名戏曲演员,要想在舞台上滚爬出个样子来,我深深意识到该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因此我苦苦琢磨传统,体验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去悟出一条革新、进取、开放的道路。本着这一理想,我认为在演唱时要把握它的风格与技巧还有气息的运用,然后才能谈到它的韵味,以及如何给人新意。
首先要提高演唱技巧,加强音乐感,锻炼表现能力,使观众能够得到艺术的享受,受到剧中人物情绪的感染。演唱时能够和观众交流,主要靠真实的情感。在演唱时尽量避免矫揉造作,避免在演唱时尖着嗓子喊叫以致后来嗓音嘶哑的那种不科学发声方法。练习演唱时尽量松弛,声音通顺舒畅饱满,咬字清楚,四声纯正,行腔干净,咬清字再拖腔,注意防止音裹字的现象。做到字正腔圆,唱快板字不乱,唱慢板情不断;低音纯厚饱满,高音足但不喊,拉腔不散,花腔灵活润甜;追求唱情,不追求唱形。还有,我觉得一个演员贵在有自知之明,一定要抓住自己嗓音的特点,不要好高骛远,人没有全材,每个人的嗓音条件都不同,不能说什么行当、什么音调、什么剧种都能唱,一个演员对自己的声带要有正确的认识。我过去因为唱法不科学发音方法不对头,声带也出过毛病,这也是从失败中得来的教训。
其次要说的就是气息了,气息是歌唱的动力,歌唱气息运动对声音的音色、音量、音准都有非常重要的制约作用。声音的高低、强弱,音质的好坏,歌唱时的感情的表达,声音的把握都与气息的运用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能正确地运用气息,就可以使声音洪亮、持久且富有穿透力,能够表达演唱的内涵,增加艺术感染力。我觉得气息是决定你演唱是否成功的源头,我们的老师一直教导我们,声未动,气先行。演绎一段优美的唱腔,哪怕你投入的情感再多,再认真,但是气不够了也是枉然,我学戏时老师常说:“小肚子用劲”,就是运用丹田,唱什么也得用上丹田气。西洋唱法,民族唱法,都要用上丹田气才能唱得丰满,呼吸要匀称,丹田气如果用不上,唱的气力就不足,共鸣也就不会好。
所谓韵味、新意,说到底也就是要体现出“味儿”,通过创腔,润腔,充分展示出剧种音乐的特色,因为任何一种地方剧都是要受制于它的地域文化环境和地域传统文化的熏陶,如果淮海戏丧失了它那地域文化环境和地域传统、还有豪放色彩的巨大内力,也就脱离了群众的审美情趣,断然地否定了我们剧种本身。因此我认为“韵味”就是剧种音乐生命力的核心,“韵味”就是剧种音乐特色的精华。比如,淮海戏《皮秀英四告》,《三拜堂》等,它的传统唱腔百听不厌,句句入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呢?就是因为它运用了地方语言的特色,再加上淮海戏的常规曲牌《好风光》、《二泛子》等,让观众听了觉得通俗易懂,也领略了其中的韵味,其中贯穿着浓烈的地方风韵。
所谓唱出新意,我深深地体会到要切忌“千人一面”、“千角一腔”,而要像调味品那样的功能,不断给人以新鲜、味美的快感,之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不同的时代总有不同时代的情势,而戏曲生命的延续有正式通过形态的渐变来体现它的本质特点,如果停留在一个腔调上唱他个千遍、万遍、十载、二十载,那还有什么艺术感染力呢?
在《失子惊疯》一剧中我扮演胡氏一角,为了衬托“胡氏失去儿子”后的那种疯态,我在原有的唱腔上,适当加了一些花腔和哭腔,用这种唱法来体现剧中人失去儿子后内心的害怕、紧张、无助、失魂落魄,一直到疯疯癫癫的状态,给人以一种心灵的震撼,较好地托起剧中人内心所蓄藏着的情感色彩,也给观众以一种韵味浓郁、独具风格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
新时代在激励着我们,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在呼唤着我们,淮海戏的发展也在等待着我们,为肩负起新时代的重任,我将把我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上,淮海戏是我的唯一、也是我执着而无悔的追求!
责任编辑 王庆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