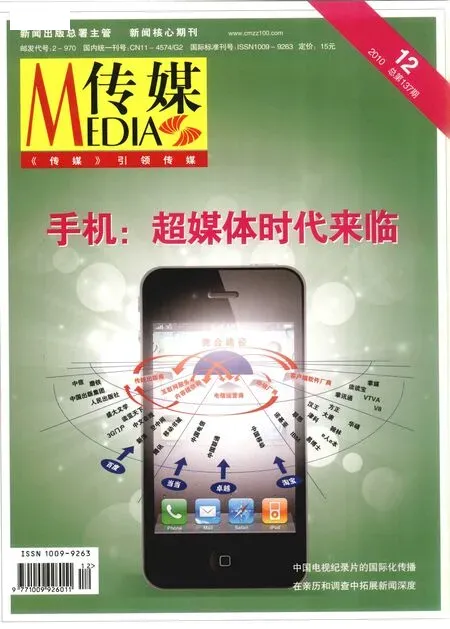媒体考核应着眼于人的建设
文/冯秋红
新闻媒体现行的考核方法,最普遍的是打分制。这种方法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生活类报纸的崛起。由于当时的信息传递手段的局限,获取信息成为媒体最紧急的任务。打分制提醒记者多抓信息多写稿。打分制的实行促进了媒体信息量的提高。
随后,大量的报纸拷贝这种考核方法,甚至连一些严肃的大报都不例外。时至今日,打分制根深蒂固,成为各家报纸考核编辑记者最基本的手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阅读兴趣的变化,这样的考核方法在当下却越来越捉襟见肘,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编辑记者创造力的发挥以及自我提升。
量大为王,“王”却未必最优秀
所谓打分制,就是对每条稿件都给出一定的分值,比如,头条是9分,头条下面的二条是5分,其余小稿是3分,简讯是1分。1分相当于10元,这样,编辑记者一个月的所得就由分数换算成奖金。这种方法能够提高编辑记者多抓稿、多写稿的积极性。同时,它简单易操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生活类报纸遍地开花之际,信息的短缺和匮乏是各家媒体面对的问题。大家愁的是信息,追逐的是发稿量。打分制提醒编辑记者量大为王,见报越多,收入越丰厚。所以,打分制的实行,有利于解决报纸信息短缺的问题。
以当年《扬子晚报》为例。开创于1986年的这张报纸从成立之初,就对信息表现出如饥似渴的需求,报纸上所有的稿件都堪称短、频、快。也正因此,当年它创造了一纸风行、在南京独霸江湖的神话。
但在今日,任何一家报纸的核心竞争力却不取决于发稿量,因为它永远也比不上网络的海量存储。不过,我们的纸媒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考核体系也没有太大变化。
打分制沿用至今,近20年来几乎没有变化。媒体已经习惯了在这样的评估体系下生存。多采稿,就多拿钱。如成都某报:30篇以下,每篇5分;31至40篇,每篇10分;41至45篇,每篇20分;46至50篇,每篇50分。每分折合多少钱是一定的。写得越多,奖金就越高,最终鼓励的,仍然是发稿量。
量大为王,然而“王”却未必是报社最优秀、最需要的。目前的现状是,报社里得分最高的,往往不是最优秀的。很多上了报纸的,可能是垃圾信息或者无益于报纸美誉度的无用信息。由于报纸“天生注定”的滞后性,网络上的新鲜信息只有第二天才能在报纸上出现。搁置了一天的信息,其价值大打折扣,也无益于报纸的美誉度和竞争力。在信息泛滥的形势下,打分制显然已经与报纸的实际需求格格不入。报纸现在最需要的,主要是两类,一是独家信息,二是成体系的信息。而打分制,对这两类稿件的鼓励作用相当有限。反倒是很多雷同的信息在各家报纸上遍地开花,导致媒体的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
打分制助推编辑记者的浮泛之风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由于打分制的着眼点在于量,而不在质,使媒体形成一系列不好的风气。其中比较严重的,就是编辑记者的浮泛之风。在这种考核体系下,谁都不愿意冒较大的风险,去琢磨一篇有质量的稿件。所有的人都会以尽量少的投入、尽量少的风险,去获得尽量高的产出,进而导致了各类低层次稿件的盛行。
邮箱稿件上版。由公关公司发往媒体的邮箱稿、红包稿,稍加改头换面,就堂而皇之署上记者的大名,有的甚至只字不改,直接扔给报社编辑。记者一样可以拿到分。
捕风捉影稿件有市场。出去采访的时候耳边听到一句话,或者电话里听某位经纪人说到一句什么,立即就可以敷衍成一个大稿。这种道听途说而来的“一句话”大稿在目前的生活类报纸上并不鲜见。有意思的是,随后记者还可以接着写主人公辟谣、经纪人辟谣、主角的朋友辟谣等诸多稿件。这类记者堪称低投入高产出的典范。明星走光、某个表情、某个动作甚至放个屁,均可以成为记者兴奋的焦点。这种以无聊当有趣的稿件,在娱乐新闻中竟然非常有市场。
这种浮泛之风,与读者对新闻媒体的要求相去何等之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新闻媒体从事新闻报道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也是新闻报道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法宝。但目前,很多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恐怕连“三贴近”是什么都搞不清。低层次稿件的盛行背后,是低层次媒体人的不思进取。
打分制催生报纸的同质化竞争
可能是一种惯性思维吧,报社的管理者也常常陷入对信息需求的恐慌。最常见的一句批评语就是“这条信息我们漏掉了”。没有人问一声,为什么不能漏稿?别人有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如果各家报纸报道的都是一样的信息,那么有必要存在那么多的报纸吗?
由于各家报纸追逐的都是信息类的低端产品,而这类产品的市场资源就这么大,导致报纸的同质化竞争倾向日趋严重。往往一件事情出来,各家媒体的报道如出一辙,就像事前商量好一样,谈不上独家,更成不了体系。报纸与报纸之间,没有多少风格可言。看一张报纸,就等于看了全城的报纸。在媒体,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样一句话:“各家都差不多”。
应该说,由于现在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采撷独家信息变得非常艰难。但在信息的解读上,却可以各有各的不同。然而,在今天,没有多少编辑记者愿意沉下心来耐心地编写这样的稿子。因为报社并不鼓励这样的独家解读,在奖惩机制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因为报社的打分制,鼓励的就是短、频、快的信息。大家都是追求短期收获,没有深入采访,也没有深入思考,所有的人都像蜜蜂一样,嗡嗡嘤嘤,为挣分奔忙。打分制下的编辑记者,常常自嘲“新闻民工”——每日辛苦奔忙,只为挣分吃饭,根本没有时间沉淀自己、提升自己。在这种制度下,产生不了有大智慧、大情怀的大记者。
媒体考核应以人的建设为着眼点
为体现公平,各家负责考核的部门常常强调一句话:对稿不对人。本人以为,这样貌似公允的话,恰恰是一种错误的说法。任何制度的建设,最后都应该着眼于人的建设。只有人的素质普遍提升,才能带动一张报纸的建设。只考核稿件不考核人,恰恰是一张报纸无法有后续发展的软肋所在。因为,这种考核体系下,可能是人云亦云,出尔反尔,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思想上很不成样子,编辑记者只知道拼命扒稿拿分。

制度的建设对任何一家媒体也是至关重要的。而考核制度,则为重中之重,因为它会直接影响人努力的方向。未来的报纸,如果想在竞争中胜出,就必须着眼于人的建设,在一种良好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打造一批思想成熟、作风扎实、能独立判断的记者编辑队伍。而这支队伍的建设,则有赖于新的评价体系的建立。也就是说,考核方法应由针对单篇稿件的考核过渡到对人的考核。那么,怎么样才是对人的考核呢?
我们不妨来看看名记者的成才之路。如果没有深入农村实地的采访,穆青不可能写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样有警世意义的作品。在大跃进浮夸风的时代氛围中,敢于说灾难,敢于说真话,这需要非凡的勇气。这部作品,让人看到记者的智慧、道义感、独到的思想,看到一名真正的记者。然而,这样的记者,他的年产量可能一年不过两三篇;但也就是这两三篇,甚至是一篇稿件,却奠定了其在新闻史上的地位。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样的记者,如何在打分制下生存下来?
所以,对于这样的优秀从业人员,报业应有留住人才的激励措施。由对单篇稿件的打分变为以半年或一年为单位的考核,由对量的考核过渡到对质的考核。
那么,怎样通过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考核机制来进行“以人为本”的考核呢?不妨来看看“他山之石”。据悉,很多国外媒体人士对于我国新闻绩效考核的做法很惊奇,尤其是打分的做法。
美国的报社一般不规定记者固定的发稿定额,也不用发稿量来衡量记者是否称职,记者只是负责自己分工的领域。在《纽约时报》,一周发稿两篇是很正常的。编辑记者的收入是固定的,平均水平在3万美元左右。英国报业的市场化程度很高,但也并不为记者打分。比如《考文垂晚电讯报》的考评,每半年才举行一次。考评的重点主要放在如何提高工作,怎样设定目标以及未来要如何做。新加坡报业控股设立了专门的报酬委员会,由5名成员组成,决定员工的酬劳、工资和高级员工的升迁,并根据公司业绩,决定员工的变动。以上这些考核办法,对我们的报业考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