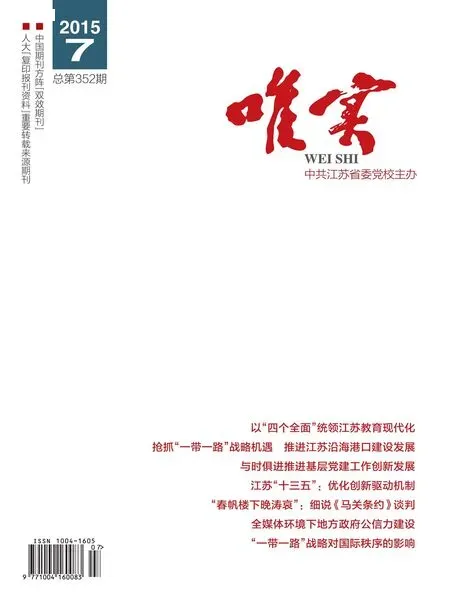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浅析
冯建辉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北京 100091)
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浅析
冯建辉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北京 100091)
在《后现代的状况》中,美国学者戴维·哈维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转向灵活积累体制这一经济趋势,从而建构起独特的时空压缩理论。在这一诠释话语系统中,哈维注意到,对时空压缩的体验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变迁和积累体制转型之间的中介环节。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时空压缩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以下简称哈维)以人文地理学的学术背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继承和发挥,并在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指引下,对晚期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系比利时学者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1972年以德文出版)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对晚期资本主义也多有发明。哈维承接了曼德尔和詹明信等人的思想,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使用“late tw entieth-century capitalism”来表述这一概念〕的政治经济变化和文化观念冲突进行反思,从而提出了“灵活积累”、“时空压缩”等独特概念。系统诠释“时空压缩”是哈维《后现代的状况》一书的重要理论贡献,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
《后现代的状况》写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学术界对后现代的流行看法是:现代主义以理性规划的刻板模式破坏了人们所居住的城市环境,而后现代主义尊重城市的自然发展和建筑风格的多样性。这一观点成为哈维对后现代主义展开文化批判的言说场域。
1.城市柔软—个性可塑—后现代的涌现
哈维先从乔纳森·拉邦的《柔软的城市》(1974年)切入考察后现代主义的涌现。哈维指出,在拉邦所描述的城市中,“一切等级感甚或价值的同质化在其中都处于消解的过程中”[1]9。通过刻画外表的柔顺性,拉邦凸显人类个性的可塑性。这一做法表明,上个世纪70年代前后以来,西方社会都市生活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不少学者将这种变化冠之以“后现代”的称号,用以表达对现代主义的某种反抗。“分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普遍的或‘总体化的’话语(为了使用受偏爱的词语)的强烈不信任,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标志”[1]15。对“元叙事”的拒绝成为后现代主义共同的主张,但是在哈维看来,意识到都市生活的重大转变是必要的,但这些变化是否值得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仍需进一步探讨。更为重要的是,理解“后现代主义”内涵的前提条件是要弄清楚“现代主义”的确切含义。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维曾参加过《资本论》阅读小组,深受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方法的影响。马克思对斯密等人的学说很是尊敬,但这并不能阻止马克思把他的概念同斯密等人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例如,在分析“交换”形式时,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斯密的错误在于“把‘成品同货币或其他商品交换’和‘成品同劳动交换’相提并论”[2]。承继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哈维意识到,挖掘后现代的意蕴离不开对“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概念内涵的比较分析,于是,哈维的视线从“后现代”倒推至“现代”。
2.流变—现代性规划—后现代
为了考察现代性,哈维引用波德莱尔的名言:“现代性就是短暂、流变、偶然事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17的确,现代生活的表象特征就是短暂性和流变性。如何在时间和空间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找寻永恒?启蒙运动思想家开出了“现代性规划”的药方。
作为一种世俗运动,启蒙运动把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通过流变和分裂实现理性的现代规划,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启蒙精神。哈维认为,一战前的现代主义与其说是新的生产条件(工厂生产、交通运输、大众消费)的诱因,不如说是对前者的后应;现代主义不但提供了考察生产条件变化的方法,更提供了适应或改善这些变化的行动方案。现代主义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强加给我们不少前所未有的体验:其一,人从主观依赖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更多的个人自由;其二,在获取自由的同时,我们也感觉到自己“对空间和时间的感受方面也受到了一种严格的控制”[1]39。
哈维进而以1945年为界对现代主义进行了区分,以此凸显后现代主义和权力中心的融洽。换言之,现代主义美学已经被吸收到官方的和体制的意识形态中去,而这种状况为后现代的出现提供了前提环境。因此,与之相对应,各种反文化的主张开始出现,并与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官僚理性压迫性的特质形成鲜明对比。用哈维的话说,“1960年代的各种反文化与反现代主义的运动才突然活跃起来”[1]56。
3.感受性转移—时间性崩溃—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在梳理现代主义发展历程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哈维引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情感结构”(the structure of feeling)的一种深刻转变[1]58。哈维从建筑规划、小说创作、哲学转向等方面对后现代的感受性“转移”作了描述。不过,透过这种表层的“转移”,哈维看到了背后的“观念混乱”:后现代主义是代表和现代主义的彻底决裂,还是“只不过是在现代主义内部反叛某种形式的‘盛期的现代主义’”[1]60?是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的某种彻底重建,还是只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3]?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哈维援引哈桑(1985年)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纲要性差异的表格,以更加直观和生动的形式凸显二者的差异。在哈维看来,后现代主义不像现代主义那样透过流变追求永恒,相反,却只是在“分裂和混乱的变化潮流中游泳,甚至颠簸,似乎那就是存在的一切”[1]58。因此,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元语言、元叙事或元理论进行猛烈的批判。后现代主义把体验变成了一系列纯粹的和无关联的“现在”,从而导致事物在时间上的秩序的崩溃。时间维度的崩溃和对片刻的关注使得后现代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紧密联系。
哈维用历史的视线对现代主义进行了勾勒,又用文学的语言为后现代主义进行画像。哈维的言说逻辑表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是一种对某种形式的“盛期的现代主义”的反叛,它属于文化层面的转移,而非整个经济社会秩序层面的跃迁。值得注意的是,关注后现代主义的画像不是哈维的目的,挖掘后现代主义的日常生活根源才是他真正的目的。于是,在“情感结构的深刻转移”的表象背后,考察其内在的机理就逻辑地摆在哈维面前。
二、文化变迁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之维
哈维是“马克思主义在地理学中发展的主要始作俑者之一”[4],基于人文地理学的素养,哈维强调,空间维度对于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诸如空间、位置、时间、环境这些地理学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解世界的核心,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5]。因此,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角观之,历时性的文化变迁背后存在着共时性的经济体制根源。
1.剧变—不变—积累体制转变
如前所述,不少学者在后现代问题上更多的是强调后现代主义的革命性,突出其在社会生活方面引起的巨大变化,哈维对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点就放在这样的认识上。哈维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生活在许多方面确实发生很大变化,但更应该看到的是人们依然生活“在一个为了获利的生产仍然是经济生活的基本组织原则的社会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继续在历史的地理的发展中作为一种不变的塑造力量在起着作用”[1]161。
基于这样的判断,哈维以“调节学派”所推崇的“积累体制”为理论武器,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研究。哈维试图说明的是:从1945年到1973年,资本主义的战后繁荣业已建构起一种社会“轮廓”(configurations)[6]:即由一系列劳动控制的实践、技术上的组合、消费习惯和政治经济力量所形成的结构(哈维以“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作为这种社会结构的核心)[1]164。但1973年后这种体制被打破,一种新的更加灵活的积累体制出现并日益成熟,它以更加灵活的劳动过程和市场、地理上的流动性和消费实践中的各种迅速变化为特征(哈维将其称之为“灵活积累体制”)。哈维强调,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向灵活积累体制的转变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特征。
2.从“刻板”到“灵活”
福特主义萌芽于1914年,其标志是福特以组织和技术上的创新推进大规模生产的实现。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福特主义才最终作为制度被推广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阻碍福特主义传播的两大障碍是20世纪上半期的阶级关系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方式。哈维指出:“国家权力适当的结合和运用的问题,只是在1945年之后才得到解决。这就把福特主义带向了成熟,成了羽翼丰满的和与众不同的积累体制。就这样,它接着形成了战后长期繁荣的基础,这一繁荣直到1973年都完全没有受到触动。”[1]172
为具体考察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哈维提出了“三维权力结构”分析框架。在哈维看来,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之所以发挥作用,主要靠三种力量: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权力、持自由主义的企业力量、有组织的劳动力。从1945年到1973年,这三种力量虽然屡有较量,但总体而言在斗争中呈现牢固均衡的状态,这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持续的繁荣。但是,作为硬币的另一面,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在1965到1973年期间也日益暴露出自身的问题。“这些困难可以用一个词语来很好地概括:刻板”[1]187。哈维同样是从生产体系、劳动力市场和国家计划三个层面描述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刻板性”。
1973年的衰退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社会也随之出现种种波动,这些波动和不确定性呼唤着一种全新的积累体制的出现。于是,与福特主义的“刻板”相对立,“灵活积累”体制呼之欲出。在哈维看来,“灵活积累”体制首先表现为与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劳动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哈维在提出“灵活积累”这一新概念之后,紧接着就基于自己的人文地理学素养提出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时空压缩”[1]192。通过哈维的表述,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从“后现代的文化变迁”到“积累体制转变”再到“时空体验方式变化”之间的逻辑理路。
3.灵活积累—价值观转变—时空体验
“三维权力结构”分析框架凸显的是国家权力、工业企业和劳动力三者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基于此,哈维强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变必然会引起工业结构的变化。“在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之下所追求的规模经济,已经遭遇到日益增加的小批量廉价制造各种商品的生产力的抗衡。区域经济已经压倒了规模经济”[1]200-201。显然,小批量生产可以规避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刻板性,以其特有的灵活性满足更大范围的瞬息多变的市场需求。
灵活积累体制投射到消费领域也会引发相应的转变,它要求企业“更加密切地关注快速变化着的时尚”,学会并善于运用“调动一切引诱需求的技巧”[1]201。这种对时尚的关注和对需求的引诱本身就暗含了一种文化观念的转变。
通过对灵活积累体制的分析,哈维最终把灵活积累体制的出现和价值观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灵活积累体制凸显的是资本的灵活流动,它“突出了现代生活的新颖、转瞬即逝、短暂、变动不居和偶然意外,而不是在福特主义之下牢固树立来的更为稳固的价值观”[1]220。于是,20世纪50、60年代那种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集体规范和价值观,向着更加具有竞争性得多的个人主义转变,它是一种渗透了很多生活方式的企业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1]219。很明显,在哈维的眼中,对于生产方式转变而言,观念改变不是原因,而是结果。这样的判断既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方法的继承,也是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深刻剖析的结果。
在哈维看来,1973年以来资本主义至少在外表方面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这种外表上的变化“是否预示了一种新的积累体制的诞生,是否能够为下一代人遏制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或者说它们是否预示了一系列暂时的补救,从而构成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结构中隆隆作响的危机的过渡时刻”[1]239?这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哈维注意到,西方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使金融的重要性在资本主义结构中进一步凸显。“这意味着形成独立自主的货币和金融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比从前要大得多,哪怕这种金融体制能更好地把风险扩散到更加广泛的方面”[1]211。为此,我们尤其应重视信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哈维指出,如果说灵活积累体制能给资本主义带来中期稳定性的话,那么,这种中期稳定性就存在于“时间上和空间上修复的新的循环领域与各种形式”[1]248之内。因此,变化着的时间和空间体验构成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实践转变的基础。
三、“时空压缩”与后现代主义
1.时空自证性—时空压缩
以往,人们往往将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时间、空间相挂钩,由此而获得一种可靠的“我们在世界上”的感觉,这种观念的前提预设使时间和空间具有自证性和客观性。上个世纪70年代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在哲学上受到质疑。哈维提出以“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 ression)[6]240这一概念来诠释社会物质实践巨变语境下的时空属性,以挑战传统的时空观念。
哈维强调,时空压缩这一术语“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我使用‘压缩’这个词语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我们崩溃了”[1]300。换言之,时空压缩表征的是这样一个实然的过程: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方式实现了革命性转变,先前所认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品质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缩小的深刻体悟,它导致“世界进入我们视线、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的根本性改变。时空压缩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现存就是全部”,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地球村的出现。因此,哈维强调,对时空压缩的体验将引起来自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等领域的不同反响和回应。
2.西方世界“时空观”的历史演变
哈维注重考查的是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意义。他指认,在中世纪的欧洲,外部空间经常被概念化为由某种外在权威所控制的神秘宇宙,另外,日常生活也因缺少变化而让人产生时间不朽的观念;文艺复兴后,环球航行使人认识到了一个有限的、可知的地球。应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时空观革命为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规划奠定了基础。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借用“文艺复兴的空间和时间概念,并把它们推向力求建造一个新的、更加民主的、更加健康的和更加富裕的社会的极限”[1]312。然而,哈维同时强调,启蒙思想家的失误在于把某些理想化的空间和时间概念当作真实情况,使人们不得不面临着体验的自由被局限于理性化结构的危险。
在哈维看来,1846-1847年西方的经济危机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在时间与空间意义方面发生重大调整:“1848年之后,进步的时间的意义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产生了疑问。”“它变得更容易产生某种循环的时间的意义。”[1]319上述转变造成一种表达的危机:“文学和艺术都不可避免国际主义、共时性、不稳定的短暂性的问题,不可能避免金融体制及其货币或商品基础之间的主导价值尺度内部的紧张关系。”[1]328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应当被视为是在空间和时间体验中对一种危机的回应。
单纯地梳理西方的时空观并非哈维研究的重点,关于时空的观念史梳理只是考察西方文化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转变的一个必要环节。因此,哈维更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对空间和时间的利用及其意义是如何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转变的?探讨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的是对时代特征有一个基本的判析。对此,哈维提出:“最近这20年我们一直在经历一个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它对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了一种使人迷惑的和破坏性的影响。”[1]355后现代主义正是伴随着这种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而出现的对“某些混乱的政治、文化和哲学运动的强烈同情”[1]355。在哈维看来,灵活积累体制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加速”来实现的。在“加速”所产生的众多社会影响中,哈维将视线聚焦于“那些对后现代的思维、感受和行为方式具有特殊影响的后果之上”[1]357。生产的加速使得社会开始强调一种易变性和短暂性。短暂性不仅意味着“时间维度的粉碎”,也涵括了商品和服务通过空间而实现的迅速流动,并由此带来“空间障碍的崩溃”。这一切使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种比先前更为普遍的表达危机。为阐述这一表达危机,哈维首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形象的刻画:“全世界一切不同的空间都在一夜之间集中为电视屏幕上的各种形象的拼贴。”[1]378这种现实反映到文艺创作中表现为后现代小说中分裂的空间性战胜叙述的连贯性,反映到政治事件中表现为特殊的地区利益群体开始在政治层面出现分裂。
3.后现代语境下“时空压缩”的理论应对
哈维坚信马克思学说的生命力和解释力,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这种从伦理学向美学的转向并不新鲜,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所提出的“元叙事”方法依然对其具有解释效力。
如何应对时空压缩带来的消极体验?哈维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存在如下四种方式:第一,退缩到沉默中去,屈从于外在的压力;第二,忽略世界的复杂性,以各个修辞学命题展开空洞的“口号革命”;第三,努力在政治生活与知识生活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位,由此,它抛弃了宏大叙事,却真正孕育出有限行动的可能性。其益处在于试图超越电视屏幕,寻找其他可能的世界形象,弊端在于它很容易滑向地方观念、流于短视。第四,“试图通过建构一种能够反映并希望支配它们的语言和意象而骑上时空压缩的老虎”[1]435。
在上述反应中,哈维更为关注的是一种激进的思想是如何出现的。他对新左派的努力持总体肯定的态度,认为它“以全新的面貌将自己视为一种文化的和政治经济的实力,推动着后现代主义所从事的那种向着美学的转折”[1]439。哈维同时强调,新左派看到了各种新的社会运动,却流露出对工人阶级的不信任,由此带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不过,危机之中蕴含着生机,哈维认为,“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质问”[1]440具有积极意义,它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领域。在他看来,他所提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辩证的探究方法,它“并不是对总体真理的一种陈述,而是与历史和地理真理达成协议的一种努力”[1]441。
作为左翼学者,哈维的学术研究在西方世界具有强烈的实践旨归。他把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历史地理状况,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证明西方经济政策的反光镜已经碎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主动发起一场叙事反对形象、伦理学反对美学、规划“形成”而不是规划“存在”的反攻。这样的尝试固然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某种偏离,但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深入批判及其对全球化语境下“时空压缩”的独到把握却对当代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具有启发意义。□
[1]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8.
[3]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三联书店,1997:420.
[4]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71.
[5]胡大平.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升级及其理论意义[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5).
[6]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M]. Oxford:Blackwell,1990:124.
责任编辑:戴群英
B151
A
1004-1605(2010)07-0033-05
冯建辉(1981-),男,山西临汾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2008级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