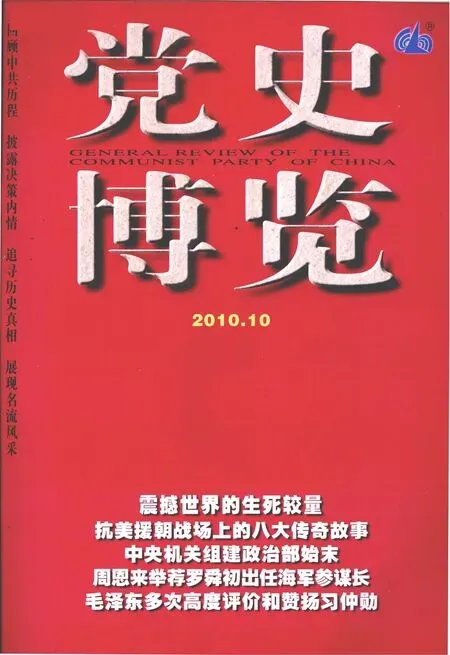中共南方局与重庆的抗战话剧
○ 张正霞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从1938年6月开始,聚集在武汉的政府机关陆续西撤,重庆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中心,聚集了全国重要机构和各界名人。仅就戏剧界而言,这里聚集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华剧艺社等10多个戏剧团体,聚集了中国最多的话剧人才,包括郭沫若、曹禺、陈白尘、老舍、田汉等著名剧作家,张瑞芳、黎莉莉等著名电影演员,涌现了曹禺的《北京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宋之的的《雾重庆》、郭沫若的《屈原》等众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话剧,为抗战戏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的文艺方针,积极领导重庆的抗战文艺,使重庆的话剧艺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时期成为话剧史上的黄金时期。
“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北京人》可能就被打倒了。”
抗战时期,著名作家曹禺来到重庆江安的国立剧专任教。江安是个距离重庆200多公里的偏僻小城,但中共江安县委却十分重视国立剧专。当得知曹禺将来江安国立剧专任教,县委责成江安戏剧协社组织欢迎大会。大会上演出了曹禺的话剧《原野》,这使初来乍到的曹禺异常惊喜。随后,中共江安县委代理书记张安国邀请曹禺到他家居住。张家府第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四合院,院内清池假山、楼台亭榭,院外树木葱茏,环境清幽。张安国为了使曹禺有个良好的写作环境,特意将大门楼上的一间阳光充足、清静的房间腾出来,让给曹禺居住。
1940年秋,曹禺经过长时间的思索、积累,写出了著名的话剧《北京人》。《北京人》具有戏剧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曹禺诅咒封建主义的没落、资本主义的腐朽,渴望新生命的力作,是曹禺创作艺术日臻成熟的代表作。1941年夏,曹禺将剧本《北京人》送给著名导演张骏祥,请他排演。张骏祥请张瑞芳担任主角,联络国立剧专的学生江村、耿震、沈扬、赵韫如、刘厚生、吕恩、张家浩、蒋廷藩、李恩杰等,聚集在中央青年剧社认真地排练起来。10月24日,话剧《北京人》在重庆抗建礼堂首次公演。导演张骏祥。演员张瑞芳饰愫方,江村饰曾文清,沈扬饰曾皓,赵韫如饰曾思懿,耿震饰江泰,邓宛生饰袁圆,傅慧珍饰陈奶妈,蒋韵笙饰曾文彩,张雁饰袁任敢。这出戏公演之后,轰动了重庆,接连演了三四十场。
《新华日报》最早于1941年12月13日刊登了柳亚子的 《〈北京人〉礼赞》一文。茅盾在阅读了剧本之后,写了一篇颇有见地的简短剧评。他认为:创作《北京人》,“作者又回到从来一贯的作风。这是可喜的”。他还说:“曾皓、曾文清、江泰等这一群人物,写得非常出色,每人的思想意识情感,都刻写得非常细腻,非常鲜明。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物。无疑问的,这是作者极大的成功。”


时隔两个月,《北京人》再度公演,再次轰动重庆,受到观众的热捧。但与此同时,各种批评也纷至沓来。国民党文化官僚张道藩抓住《北京人》中出现北京猿人的身影做文章,批评剧本脱离抗战现实。左翼文艺家劭荃麟、杨晦也批评曹禺在写出了《蜕变》后,又去描写抗战前的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又倒退回去了。左翼作家胡风批评《北京人》说:“作者所写的那个封建家庭 (封建社会),看来错综复杂,但其实是过于孤立了一点,因而那些人物看来须眉毕肖,但其实是单纯化了一点。……至于当时应有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政治浪潮,在这里没有起一点影响。”
《北京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作者指导思想模糊,不应该回到原始社会去,应该旗帜鲜明地喊出来。面对此情况,周恩来立即安排《新华日报》的记者去了解戏剧界各方面人士的意见,让徐冰组织南方局的同志去看戏,自己也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一遍又一遍地观看演出,然后组织讨论。他综合大家的意见,肯定《北京人》是一个好剧,并责成张颖执笔,徐冰修改,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署名茜萍的评论文章《关于〈北京人〉》。文章说:“《北京人》写封建家庭的没落,老姑娘在死气沉沉中出走,这样的故事,说明封建社会必然没落,老少两代走向光明,走向解放区,歌颂光明,是我们抗日所追求的,怎么与抗战无关呢?!”针对有人批评《北京人》是抗战八股式的剧本,文章还着重肯定了《北京人》的社会意义:“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的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它对《北京人》的肯定,使曹禺很快摆脱了困境。
周恩来与曹禺是天津南开学校校友,他们时常有书信往来。《北京人》第二轮公演后,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给曹禺,以学友的身份同曹禺谈论抗战的形势和前途,谈论戏剧。他说他很喜欢《北京人》,印象很好,并邀曹禺到曾家岩50号来做客。不久,曹禺来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对封建大家庭崩溃的描写,说剧中人物性格鲜明,是一部积极的反封建的力作。同时,他也对曹禺在《北京人》中对原始人类的憧憬,发表了意见。周恩来说:“外面对剧中这种表现有批评,我以为这是作者一种想象的表现,不必苛求。”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你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了。这一处是否要修改,请你考虑。如果改起来有困难就不要勉强。”
周恩来从政治的视角提出了意见,但并没有强求曹禺修改。多年以后,曹禺谈到此事,真诚地说:“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北京人》可能就被打倒了。”
“郭先生的剧一定要搞好。石凌鹤带头将剧排出来,大家协助。”
郭沫若是我国著名学术大家,早年主要从事历史研究和新诗创作。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妻抛雏,从日本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时期,国民党恢复已撤销的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郭沫若担任管文化宣传的第三厅厅长。周恩来和郭沫若共同领导起抗日的文艺队伍。
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郭沫若悲愤地说:“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到愤怒。”于是,满怀着强烈的愤怒,郭沫若奋笔疾书,将自己积累了20多年的历史材料写成了话剧《棠棣之花》。《棠棣之花》剧名取自《诗经·小雅·棠棣》的诗句。棠棣俗称郁李,落叶灌木,春开花,夏结果,古人常用棠棣之花来比喻兄弟亲情。《棠棣之花》叙述的是战国时期的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的故事,借以寓古喻今。重庆话剧界人士听说郭沫若写了剧本,都争着一睹为快。著名导演陈鲤庭、马彦祥、应云卫、史东山看过剧本后,都默默地将剧本退了回来。他们说:“《棠棣之花》全剧诗意馥郁,缺少戏剧冲突,无法导演。”
周恩来一向赞赏郭沫若的才华,更珍视郭沫若所创作的历史剧的政治价值。因此,他对郭沫若的创作倍加关怀和支持。当他得知实情后,决定在中共党员中想办法。石凌鹤是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职业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人员,兼抗敌演剧第八队政治指导员、孩子剧团教导主任。他是国统区话剧界的能人,既能编剧,又能导演。于是,周恩来找来石凌鹤,语重心长地说:“郭先生的剧一定要搞好。石凌鹤带头将剧排出来,大家协助。”石凌鹤接受了任务,号召党员参加排练,并聘请孩子剧团的著名演员孙坚白、颜良昆等人参加演出。在排演前,周恩来多次与郭沫若商谈修改剧本。在戏剧界同人的努力下,剧终于排练完毕。在一次彩排时,周恩来和郭沫若来到抗建礼堂观看。郭沫若见剧中人物聂政拿着一枝桃花送给村姑,嫌桃花太少,就找来一大束桃花,让聂政送给村姑。导演石凌鹤和周恩来都认为这不符合表演艺术,但郭沫若坚持要这样,大家只好同意。饰演村姑的演员张瑞芳接过郭沫若的一大束桃花,却发愁没有地方放,只好放到水缸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棠棣之花》顺利上演,观众反映良好。郭沫若尝到了创作剧本的甜头,剧兴大发,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写出了《屈原》、《孔雀胆》、《虎符》、《高渐离》、《南冠草》等历史剧。这是他历史剧题材创作的高峰期,也是中国新文学历史剧的黄金时期。郭沫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是分不开的。
大力支持 《风雪夜归人》的演出,抵制国民党“禁止公演”的做法
《风雪夜归人》是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于1942年创作的一部反封建的爱情悲剧。该剧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靠走私鸦片起家的法院院长苏弘基的四小妾玉春与京剧名旦魏莲生相知相爱,两人欲私奔,结果被苏弘基的仆从王新贵告发。苏弘基一气之下,把玉春送给朋友、天南盐运使徐辅成做使唤女奴。这样,魏莲生与玉春私奔未遂,魏莲生被驱逐出城。20年后,魏莲生回到城里,到苏宅寻找玉春,最后惨死于狂风暴雪中的海棠树下。
《风雪夜归人》讲述的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剧情也比较单纯,许多导演看过剧本都认为不便于排戏。唯中华剧艺社的导演贺孟斧独具慧眼,认为剧本的内容好,单纯的情节为导演和演员提供了再创作的空间。于是,贺孟斧挑选基本功扎实、表演准确细腻的演员路曦饰演女主角玉春,“话剧皇帝”项堃饰演魏莲生,应云为、刘郁民、阳华、李纬等参加演出。该剧于1943年初被排成五幕话剧,于1月9日在《新华日报》第三版左下方刊登首演广告,2月19日在重庆抗建礼堂演出。导演贺孟斧高超的舞台表现处理手法,演员的精彩表演,使首次公演就轰动山城,观众为其进步的内容和感人的艺术魅力所倾倒。周恩来也非常喜欢这部戏,多次悄悄地坐在观众席上观看演出。
公演演到第13天,蒋介石行营办公厅主任钱大钧带着姨太太来看戏,看了一半,竟拂袖而去。第二天,国民党就下令“禁止公演”,诬蔑这部戏“诲盗诲淫”。
面对国民党的无理阻挠,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积极组织反击。周恩来团结重庆的10多家报纸,并特别指示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和民营的《新民报》,全力支持和肯定《风雪夜归人》的积极意义。1943年2月26日,《新华日报》副刊发表了朱柟《关于〈风雪夜归人〉》的评论:“在血与火的抗战年代,《风雪夜归人》这么很简单的故事,如一首抒情的诗,给了我很多温暖和激动。因为我在这里面,找到了很多熟识的面孔,熟识的姿态,熟识的口吻。他们都靠得我们这么近,似乎一伸手便可以触摸得到的,所以他们的命运,他们所受的一切哀乐,令我不由自主地像关心一个好朋友那么关心他们。 ”3月15日,《新华日报》副刊又登载了著名剧评家章罂的《评〈风雪夜归人〉》、梁华的 《愤怒的雪花——〈风雪夜归人〉书后》、华君的《观〈风雪夜归人〉后零感》、白夏的《风雪夜归人中的演员与导演》。《新华日报》用整版的篇幅来介绍和评论 《风雪夜归人》,大力支持这个剧目,抵制了国民党的攻击。
当然,在积极肯定 《风雪夜归人》时,对于玉春命运的处理,也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章罂就主张把表现玉春结局的尾声全部拿掉。但是,吴祖光认为:“这个戏的序幕与尾声是同一时间发生在室内与室外的戏,拿掉尾声,序幕也不要了,《风雪夜归人》的名字也就不存在了。”
周恩来也认为剧本尾声不太符合女主人公的性格。他对作者吴祖光说:“你写了一部与抗战大时代无直接联系的作品,但反帝与反封建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女主人公玉春是一个聪明的、有头脑的、有智慧的女子,其结局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她不应该做这样的妥协。”
1946年元旦,吴祖光由重庆乘飞机去上海,担任上海《新民晚报》副刊编辑。行前一天,他向周恩来辞行。周恩来与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多次谈到对《风雪夜归人》的看法,并告诉吴祖光,自1943年 《风雪夜归人》在重庆上演后,他曾将剧本带到延安,向延安文艺界介绍该剧。周恩来动情地说:“《风雪夜归人》虽然剧本题材内容与现实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针对国统区反动统治的具体情况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1957年,吴祖光到孙维世家做客,孙维世问他:“你知道总理在重庆看过几次《风雪夜归人》吗?”吴祖光回答说:“我不知道,大概总有两三次吧……”孙维世说:“总理告诉我说,他一共看了七次。”孙维世的话深深触动了吴祖光。
20世纪80年代,吴祖光终于领悟到周恩来关于《风雪夜归人》尾声的指示精神,遂将尾声作了修改:20年后的冬天,苏弘基与阔别多年的朋友徐辅成再见,徐辅成责怪苏弘基:“20年前,你送给我玉春这个大活人,我至今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她送给我?自从她进了我家门,一句话也不说。”吴祖光把玉春变成了“哑巴”,用这样的表现方法来写玉春的反抗,完成了玉春性格的统一。修改后的尾声得到戏剧界的好评,但遗憾的是,周恩来已经不在人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