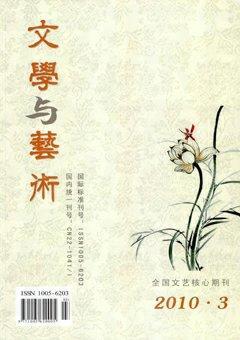浅谈《老人与海》中存在句的文化差异
李厥云
【摘要】汉语强调人的主体意识,是一种按照逻辑事理顺序铺排而成的语义型语言,而英语则讲究以动词为核心来构词造句,是一种深受语法规则制约的形态性语言。本文依据英汉语思维习惯的不同对存在句的生成结构进行了对比,发现英汉语存在句的语表结构、谓语动词、存在主体的语义特征和话语功能等诸多方面均有相似之处,但在语序、存在主题、存在动词和被动形式的有无等方面亦有较大得差异,因此,从东西方文化思维与习惯角度审视英汉存在句的差异以及形成因素就具有了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实际用途。
【关键词】存在句;存在主体;语义;文化差异
1. 引言
存在句表示某处存在着(单纯存在,以某种状态存在或以某种方式存在)某人或某物,它不但要表达“存在”的语义,还要受到语法结构的制约,即“处所词语+存在动词+名词或名词性词语”的固定范式,只包含存在语义但不符合存在句式的句子不被认为是存在句,不能只因为某种句式含有“存在”的意义就归人存在句的范围。存在句表示某处存在着(单独存在,以某种状态或方式存在)某人或某物。它由已知的环境说到未知的实在,以未知的实在为语义表达重心,从而实现了旬末信息核心的原则。(杜瑞银 1982) 从语义上讲,表示某个地方(已知)有什么(未知),以确认人或物的存在,一般包含三个组成部分,即:处所词语A+动词或动词性词语B+名词或名词性词组C构成。汉语可以说是SVO式语言,由动词充当谓语是一种常见的、典型的句法现象,但是也存在着由名词性成分充当谓语的名词谓语句。因此,对存在句的分析我们以存在语为视点,将存在句按其功能分为静态存在句和动态存在句两种类型。
存在句有独立的表意功能,非叙述行为,也非评论话题,只是确认某物的存在与否。各类存在句的表达功能是等同的,都是表示一种状态的存在,即:某处所存在着事物。汉语的语法是集语法、语用、语义和修辞于一身的,要“以大观小,从篇章看句子”,而且汉语用词模糊,时态语态句法难以程式化。英语以动词为中心,建立起了明晰的句法系统,体现了西方哲学的分析性和抽象性。本文从《老人与海》中的存在句出发,深刻揭示英汉语句法结构的深层特征,系统分析其语法、语义和语用功能,对进一步认识英汉语句法的特点具有积极意义。
2. 存在句的语意特征
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英语是形态型语言。汉语有语法,但没有英语那样显露的形式,而是隐含在内部的。他不是通过形态来表达成分间的关系,而是通过语义本身来体现的。宋玉柱(1992)认为,存在句都具有结构方面的固定模式:空间词语(A段)+动词(B段)+名词性词语(C段),指某个地方(已知)有什么(未知),确认某人或物的存在。英语有严格的形式结构,比如名词的数,动词的时,主谓之间的一致关系等。而汉语只要符合事理逻辑,无需时态和语态的限制,有极大随意性。因此,我们应以功能为主,形式为辅的标准来进行分类,如申小龙言,“句读本体,逻辑铺排,意尽为界”。 (下转第44页)
2.1 存在主体的语义功能
英语存在句中,存在主体处于末端语义中心的位置,具有非确定的特指性,符合语用学的“句末焦点原则”原则,而主体名词前可用不定冠词,零冠词,数词和其他非确定意义的限定词修饰。许多情况下英语的核心词在前,较长的修饰语放在后面, 承载主要信息的主句放在前面,表示限定条件的次要信息放在后面。汉语的时间顺序与其语序往往一致,修饰关系上一般都是核心词放在后面,修饰语放在前面,叙述顺序上往往是先讲发生了什么事情,再对此事发表看法。申小龙认为,汉语存在句“由已知的环境说到未知的实在,以未知的实在为语义表达重心,从而实现了句末信息核心的原则。” 比如,
“In it there was a bed, a table, one chair, and a place on the dirt floor to cook with charcoal.”
“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泥地上一处用木炭烧饭的地方。”
汉语存在句的结构形式是“处所词语+存在词语+存在主体”,句首的处所词语是汉语存在句独特的结构特征,并从中还可看出主体非确定的特指性。但是,英语中存在句的典型结构形式是:there +V+存在主体+方位词语。比如:
“On the brown walls of the flattened, overlapping leaves of the sturdy fibered guano there was a picture in color of the Sacred Heart of Jesus and another of the Virgin of Cobre.”
“在用纤维结实的“海鸟粪”展平了叠盖而成的褐色墙壁上,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另一幅科布莱圣母图。”
夸克等人认为,在there 存在句中,there 只是具有语符或语音形式而无语义内容的“假位成分”,总是出现在语法主语的位置上。而章振邦指出,若地点状语前移,便可省略引导词there,可变换为:方位词语+v+存在主体。比如,
“In the house stood an old man.”
从这一层面来看,英汉存在句在语表结构上极为相似,存在句也大量使用格式“方位词语+there+V+存在主体”,而且there也经常省略。
2.2 存在句的谓语结构
存在句中大部分句子表达的是静态的语义,但是也有一些表达的是动态的语义的存在句,这主要由表动态的“着”字句充当。汉语存在句有静态句和动态句两类,两者的区别取决于动词的情况。静态存在句的动词有“有”、 “是”和“零动词”等,表示一种静态的存在。而动态存在句中包括动词+“着”、动词+趋势补语等,表示某种运动方式的存在或延续。英语存在句中常见的是there be结构,相当于汉语存在句中的“有”字句和“是”字句,除了be动词外,还有一些不及物动词,相当于汉语中“着”字句、“了”字句、“零动词句”和一部分动态存在句。比如,
“In this river lived many kinds of beautiful fish.”
“河内生活着各种漂亮的鱼类。”
第一类动词相当于汉语静态存在句的“有”、“是”、零动词等,由于“有”字句在汉语存在句中比例最大,表达最简易,一般采用“有”字句表示静态的存在。例如,
“There are three things that are brothers: the fish and my two hands.”
“有三样东西是兄弟:那条鱼和我的两只手。”
英语存在句中,存在主体特指实义主语,而动词都是不及物动词,名词与前面的存在动词是主谓之间的关系。如,
“In the tree perched many beautiful birds.”
在此句中,“birds”是“perched”的主语,对应的翻译为,“树上栖息着许多漂亮的鸟。”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存在主体都具有施事性特征。
但是在汉语存在句中,许多句子后面的名词并非施事主体,而是以主动形式表达一种被动的意义。如,
“地上铺上了厚厚的雪。”
“The field was covered by snow.”
但是,上句并非存在句,因为英语存在句动词必须是非及物动词,而不及物动词是没有被动形式的。
2.3 存在句的句法结构
存在句是以表达事物的客观存在为主要的语义功能,这一点英汉语是相通的。英汉语存在句都以介绍、引入语境信息为主要功能,起着开篇引题、承上启下的作用。汉语存现句通常由(处所)、地点名词作为主题成分,即处所、地点词语都是确指的,这些处所和地点往往是受话人(接收者)能够在现实生活或精神世界中找到的。英语存在句的典型结构为“there + be/v + 存在主体+方位词语”。而there只是“英语存在句型的一个特殊的信号”,“英语there存在句具有可辨性极强的句法结构标志语,在标志语there的统领下,构句部件的前后移位只体现语义侧重点的不同,而并不影响句式的辨认。” (金积令,1996)
汉语主要以词序为语法手段,词序的变更通常意味着句式的转变。汉语存在句中,前段的处所词语是一个句子的主题,称之“处所主题”。它是句子构造的支撑点,后面的存在语是述题,是信息的核心和语义的中心。主题确立表述的出发点和表述的框架后,述题将对主题进行叙述、描写、解释或评议,预告说话表述的起点,并确立了连接后续述题的框架结构。而英语存在句的“存在主体和方位词语”是句子的结构中心和语义中心,他们通常趋于句子的末端,而没有汉语存在句中所谓的主题和述题。比如,
“There was no stringiness in it, and he knew that it would bring the highest price.”
“一点筋也没有,他知道在市场上能卖最高的价钱。”
句中存在主体(no stringiness) 和方位词语(in it) 连在一起,没有主题和述题之分,以动词形式统摄句子的结构。而汉语是注重主题的语义型语言,各成分间的组合往往借助事理逻辑而非语法结构,这与形态型语言的英语是相对的。
3. 结语
英汉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是形成各自对应语言形态特征差异的能动根源。英美人注重个性、客观性、分析性、逻辑性的思维习惯客观上要求英语语言以形统神,在表述逻辑关系时必然依赖连接词,语言结构严谨;汉民族重综合整体性、感悟性的思维习惯客观上要求汉语语言以内容统摄形态,语言简洁而灵活,汉语读者有这种心理预期,那么存在句的译文应当在可能的情况下适当调整语序,把一个语句的语义重心往句子的后部移动。可见,人们的思维模式偏向对语言表现手法起着一种支配、统摄作用。因此,了解中英思维模式的差异,对研究两种语言的句式的差异及其各自的本质特征至关重要。思维模式分析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不但有利于我们了解不同语言的结构特征,还有利于我们尽量避免汉语文化思维在英语学习中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Culicover,P.W. (1982) Syntax(Second Edition)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吴福祥 《汉语体标记“了、着”为什么不能强制性使用》,见《当代语言学》,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