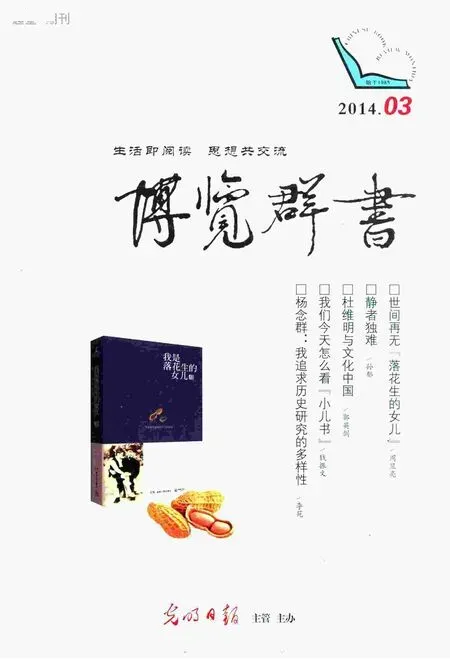整理梁漱溟先生晚年口述的感受
○逄 飞
我没有见过梁漱溟先生。最早见到这个名字,大概在初中二三年级。有一期《读者文摘》上登了许多人生隽语,其中有几条下面的作者写着“梁漱溟”三个字。后来我考入哲学系,可以专门有时间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努力思考人的生命和天地宇宙的事情,也接触到了更多思想家的名字,对某些著作也仔细读过。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在长春一个小店里看到梁漱溟先生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也许因为算是曾经谋过面吧,就买了一本。但其实主要是为了“纪念”自己若干年前的“少年心思”,故尔没翻两页,就在书架上一直放着,直到在北京读研并毕业。
后来,在2000年底,我开始要做“一耽学堂”。开始时只是个简单的愿望,好像是自己那时候突然生起一股很强烈的关心,希望这个世界好,希望为它的好贡献自己的努力,希望人世间春日花开秋日结实。这个希望就好像是一轮光,照耀到我们的每一个足迹——学堂就这样一天天地长大。
记得是2002年的冬天,学堂在北大电教做一次讲座,题目是“我的父亲梁漱溟”,主讲人是梁先生的长子梁培宽老师,讲座大受欢迎,约有四五百人。那次讲座以后,和梁培宽老师有了更多的交往。我们都住在承泽园,相距很近,经常可以见面。梁老师很关心学堂的日常生活和办公条件,不断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于是,大概在2003年底,我们开始协助他整理梁漱溟先生的谈话录音。
这个工作首先是把30盘录音磁带转成电子格式(做成“C D”和压缩盘),这方面的工作因为李家振先生和高忆陵老师的无私帮助使得我们没有花一分钱而且顺利、快捷地完成。2004年的春天,我们开始正式做录音转文字的工作。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坐下来听一个人说话、听他的声音,再由自己“写出”他的感受和故事,循着彼此同一的节奏和语气,同时保持一个见面的距离,这对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该是多么难于把握的一件艰深的事情啊!有的朋友说,这事简单嘛,找人分工,大家一人一张碟;也有人说,花钱雇佣好了,又快又省事。总之,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技术活儿!这是多么令人感到痛心的想法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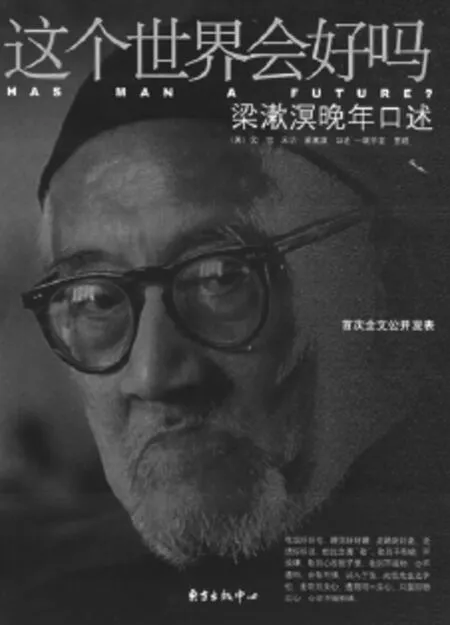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一耽学堂整理,东方出版社,2006年1月,35.00元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见面”的机会。我常想,我们活着,看到、听到或碰触到这世界的一件东西,可能是一棵树、一个文件、一句话,它们都记录了生命的历史,它的信息正要借着“看、听和碰触”向我们敞开。我们“见面”的机会全在这里边;如果没有见过面,我们又会见到什么呢?我就是抱着这样虔敬的心开始工作的。这个状态简直是耳入口出、心到神知!在整理工作之前,我不断地准备,要求自己小心翼翼;在整理工作的进行中,我也不断地在持续或者停顿中调整状态。所以,这个工作弄得很长。
现在,工作已经结束好一段时间了,好多人都已经看到了成书,并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可我一直在避免回忆或者怀想。因为,我觉得它还在我的心里,准备的过程还要继续,尽管很微弱。而且,我以为,这个过程并没有太多人需求,不会有谁想关心。要不是梁培宽老师提到《博览群书》可能会给予刊登这样一篇文章的机会,我根本不会想到提笔。
在这本书形成的过程中,特别有一位朋友徐君,有极专注和负责任的精神,过半的录音由徐君转成初步的文字,她有一种相当纯粹平坦的潜质。蔡陆,中国人民大学即将毕业的女孩子,聪慧而充满热心,2004年6月刚刚做完眼部的手术,就已开始在家里工作,非常值得赞赏和表扬。张来周、张佳也为文字的整理付出不少努力。而我所做的,就是不断地反复地倾听、体会和校正,这个过程约有两年。
梁漱溟先生那清澈有力的声音,仿佛未曾淡远的味道,从耳畔至于心海,我似乎有一些看见……
梁先生曾经在回忆里讲过:
——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地看见……
可以说,我对梁先生也有一些望见,远远地如在雾中……
我凭着这依稀的望见,谈谈个人几点具体的收获。这也就是梁先生对今天、对21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几点启迪。当然,这是仅仅就我做一耽学堂几年来的经历体验所能感觉的有限体会。
首先,回到简单事实。谈21世纪民族复兴和文化建设,实质是讲生命的建设——讲族群生命和个体生命的养成。这一方面必须要从事实谈起,抛开现象的纷纭和学理的复杂,从情绪和名相上的贪婪和虚荣回归到最基本、最简单的事实。这样的事实是什么呢?是生命的事实!是生命的人格!
中国的文化是讲求实用的文化,它有实际的“用处”——只有讲求生命才能够出境界,只有讲求人格才有力量。只有在境界上,才可活跃生息,只有有力量,才能作用功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梁先生时时刻刻都注重于此!日中所见,心中所信,平等平等,实见实信!他对于生命一事,庄重严肃,始终不忘怀;他的思索、茹素、去北大教课、讲唯识、写《吾曹不出当如苍生何》、往山东、搞农村乡建、抗日国是、访问延安、创民盟、山城勉仁、冒险出港、政协发言、著《人心与人生》等等……一一的都在这悠久长远之中。
他注重忏悔自新,省求觉悟;在人格的修养上,培养真正的力量!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立足生命立场上的觉照、生活本位上的陶冶。这等人物光辉伟大,今日少有而又至为需要,我等真有心学者当生凛凛景仰之情。
其次,要有一种相信。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处在剧烈的变动中,从民生舆情到个人遭际,都充满了怀疑、彷徨、愤懑的各种力量与声音,每个人都很难过上稳定安静的生活,因为旧有的被颠覆,新生的尚未建成,正是混乱无望飘摇无定的时候。而梁先生一生经历种种,却自有一副骨格,一种耐性。这是源于他的“信”,大信——对人、对己、对民族、对文化……相信中国会好,相信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会好。这一个“信”字,不以势易,不以时变。
他曾说:
这个(“五四”时代有很多人是盲目的崇拜西洋的一切)也是一个自然之势吧。事情发展到今天,自然如此。这个不足怪,也不必责备。实际上,可以说是动摇不了根本。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可怕,没有关系。……事实要发展,发展总是好的,我认为发展总是好的。
有信之人常行不易之志,他总有一种岿然和超脱的气质——梁先生的话就今日文化现状听来亦是铿铿有劲节:
我看没有什么威胁……近来尽管有点对旧的风俗习惯有些个破坏,但是前途并不悲观……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所以我刚好不悲观……中国文化原来是起于家庭,老话嘛就是孝悌……就是“孝悌慈和”……我这么推想,到了社会主义,恐怕就要大家都来讲究孝悌慈和,推讲敬老啦、抚幼啦、兄弟和好啦……这个我就谓之“中国文化复兴”。
最后,应当清醒而努力地生活。一切的态度都在致力于真实的生活,最为务实地、实事求是地实践。对于社会大众的生活和对于他们的教化导向,梁先生客观平实,从未悬帜高蹈,脱离社会整体氛围。
对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陈焕章搞儒教和他们搞儒教的方法,他明确反对;关于佛教,在那一个国家危亡社会不堪的时代,对于个人的兴趣或者修行的需要,他不遗余力为其成全,但从不认为这个就是解决民族社会问题的方案。观看今天的现实,我们该从中有多少的借鉴啊!要使一个人清醒,恐怕要做最艰难的努力。梁先生对自己是做到了的,而我们呢?今日的中国已在努力前进,为着那将来的民族复兴,为着那待成的教化文治,不正是需要大家有这样清醒实际的努力吗?没有清醒,努力就不过是建立在情绪激动之上;没有努力,清醒者也终究只是一旁观看客而已。
先生一生未见懈惰慢怠,在基层在一线,与百姓一起,风雨寒暑,山南地北,真正实践众生的情怀——为民请命,为国忘躯,精勤日夜,身语遍行!朝话有似清音弦歌,途迹有似辉阳和煦,今天的学者和志愿者恐怕都和先生有莫大的差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