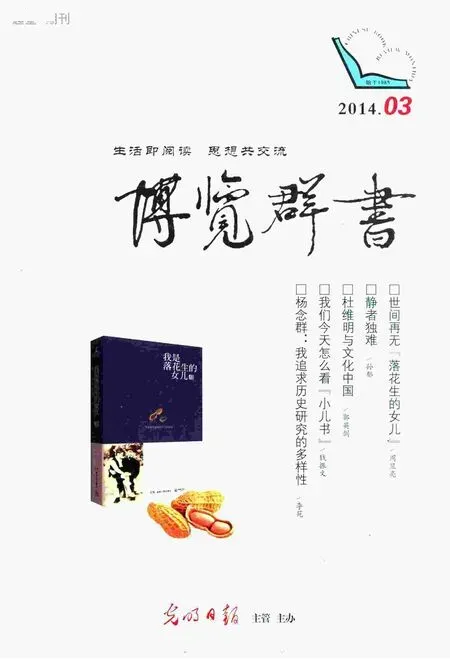严谨扎实的实证功夫
○陈梧桐

《故宫问学》,章宏伟著,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9月,36.00元
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成立起,就重视学术研究,并渐形成重实证、不空发议论,文献与文物并重的实事求是学风,涌现出一批在明清史和宫廷文化研究、文物保护和鉴定等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章宏伟自调入紫禁城出版社任职以来,工作之余狠抓学术研究。在故宫学术氛围的耳濡目染之下,他也走上重实证而不尚空谈的治学路径,养成严谨扎实的实证学风。他推出的论著《故宫问学》,即充分体现了其治学的这种鲜明特色。
《故宫问学》一书,汇集了章先生近年研究明清故宫学术特别是出版事业的一批论文。细加研读之后,它给我留下了三个特别深刻的印象。
一是史料丰富。章先生深知:“历史研究,只有详尽地占有史料,对史料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否则,就连一般的研究也无从着手。”(P 213)他不像时下的某些学人,从网上或别人的论著中扒下几条史料,就急于著书立说,而是学习史学前辈那种“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广披博览,沙里淘金,深入发掘有关的史料。除一般史学研究常用的官修实录、政书、正史和方志之外,他还特别注重档案、文集、野史笔记、碑刻谱牒以及文物遗迹的搜寻,力求找到第一手资料,接近历史的原貌。由于这种几近“竭泽而渔”的广泛搜集和深入发掘,书中的每一篇文章,史料都非常丰富而翔实。如《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价值》一文,除大量征引这部卷帙浩繁的《嘉兴藏》,还征引50多种有关的史籍。《明代工部尚书雷礼生平考略》一文,也征引了50多种史籍。即使是篇幅最短的《袁了凡生卒年考》一文,仅仅是考证袁了凡生卒年这样一个问题,征引的史籍也达20多种。正是由于作者掌握了大量史料,书中的论述皆“言必有据”,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不空发议论,不主观臆测,显得厚重而扎实。
二是考证严谨。章先生也深知:“研究历史,史料不足,会得不出结论或得出片面的结论;史料不正确,会导致结论的谬误。”(P 213)他不仅重视史料的搜集发掘,更重视史事的审查考证,力求做到史实的准确无误。章先生没有轻信每一部史籍和每一条史料,也不盲从某些流行的成说,而是勤于思考,敏于求证。他的求证,除了使用史学界常用的几种方法之外,还继承故宫老一辈学者的传统,经常运用王国维首倡的二重证据法,将文物(实物)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进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导出新的结论。例如《嘉兴藏》的雕版地点,故宫老专家杨玉良先生曾提出在五台山时期有妙德庵与妙喜庵两处之说。但章先生根据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每卷经文之后的施刻愿文,编列出五台山时期的刻藏事由及地点,却只见到妙德庵一个雕版地点而没有妙喜庵。于是,他又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将长达12000多卷的《嘉兴藏》从头到尾翻阅了四遍,并对施刻愿文逐一重新过录,还是没有找到妙喜庵雕版的文字记载。后来,经过反复思考琢磨,发现只有正藏第101函第4册《大智度论》卷50第22页的施刻愿文,将妙德庵的“德”字刻成异体字的“直”字,他由此推断杨先生可能是将“直”字误认做“喜”字,将妙德庵错成了妙喜庵。经过一番艰苦的求证,他最终得出了五台山时期只有妙德庵一个雕版地点的结论。又如满文《大藏经》,由于该书没有书名页,卷端、修书职衔、目录之前也不署书名,它的正式名称叫什么,学术界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章先生查阅故宫博物院藏的满文《大藏经》,发现卷首有篇乾隆帝撰写的序文《乾隆御制清文翻译全藏经序》,后来又在阿桂等修纂的《八旬万寿盛典》卷14找到这样的文字记载:“乾隆五十五年,命以《清文翻译全藏经》成,皇上亲制序文申训。”据此内外证,他推断这部满文藏经的书名应为《清文翻译全藏经》,而按照清代内府刻书的惯例,书名之前还应加上“钦定”、“御制”或“御译”二字,查检该藏的目录,边款又恰有“御译大藏经目录”的字样,进而判定该书的全称应为《御译清文翻译全藏经》。这种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并以文物与文献记载互相比对的考证,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扎实牢靠,令人信服的。
三是创见迭出。由于作者勤于搜求,严于考证,这本书的论文绝少时下某些论著常见的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和一大堆新名词的堆砌,而多有自己新颖独到的见解。如《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研究》一文,即提出在刊刻《全唐诗》之前并不存在扬州诗局这个机构,扬州诗局的经费也不是来自两淮“盐羡”的观点,推翻了某些长期流行的成说。又如《明代观政进士制度》一文,指出进士观政制度与有明一代的科考相始终,而非只存在于洪武年间;观政进士的责任是观政而非行政,是“试事”而非直接任职,也不是职前培训;观政进士不算正式官员,但已取得做官的资格,可以奏议政事,享有朝廷颁给的出身禄米,并按官员的标准穿戴青袍角带;观政的时间长短不一,而非仅止三个月的期限。这些论述,也都纠正了前人的错讹之说。再如《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价值》一文,除订正五台山时期的雕版地点之外,还就《嘉兴藏》首函的许多问题,以及《方册藏》的最早首创者、募刻前期的实际主持者、刊刻之初的规模规划,选择五台山为刻藏地点之原因、五台山刻藏的现存经卷、刻工,《方册藏》正式刊刻前的刻经等都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类似的创新之见,书中随处可见,多不胜举。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章先生严谨扎实的实证功夫和求真求实的优良学风。在学术空气十分浮躁、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充斥的当今社会,这种学风尤显难能可贵,值得大加赞扬和提倡。
当然,智者千虑也难免会有一失。就具体史事的论述而言,书中的个别论点尚可进一步斟酌。如第1页的脚注①,作者重申他此前提出的一个论点,认为叶德辉先生将我国古代的刻书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个系统的观点不够妥当,因为私刻和坊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而主张根据出版的投资主体和经营性质,划分为政府出版、私人出版和民间出版三大系统。但我认为,既然将政府出版单独划为一个系统,与之相对应的就都是非政府出版系统,实际上不论是私人出版或民间出版,也确实都属于非政府出版系统,而政府出版也还可以细分为中央政府出版和地方政府出版两个子系统。因此,似可考虑将我国古代的刻书划分为政府(官方)出版和非政府(非官方)出版两大系统,然后在两大系统之下,再细分其子系统,如在政府出版系统之下分列中央官府出版和地方官府出版两个子系统,非政府出版系统之下分列私人出版和民间出版两个子系统。这样的分类,或许更为周全严密。再就全书总体而论,作者的微观研究成就突出,宏观研究则相对薄弱,从而影响到论述的深度和力度。历史研究的任务,不仅在于弄清每一件具体史实的原貌,更重要的是要揭示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忽视微观研究的宏观研究,只能是空中楼阁,无法真正提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忽视宏观研究的微观研究,又只能是盲人摸象,同样难以提示历史演进的奥秘。宏观研究必须以微观研究为基础,微观研究必须以宏观研究为指导和归宿,两者应该并重,不可偏废。如果作者能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宏观研究,定将更上层楼,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