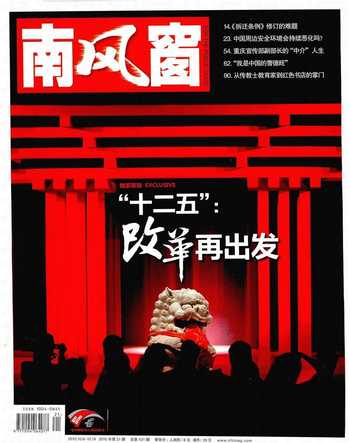那一代人的上山下乡
章剑锋

会议本来是开不成的。但是张志尧找到了张永乐,事情马上发生了转机。
张永乐是新疆公共关系协会的秘书长,她把新疆一批知青出身的头面人物请出来,帮助谋划。万般承诺,一次得到官方允许和支持的知青集会最终在石河子落地。
“每个来的人,都是带有期望的。”张永乐说,“谁不希望来参与忆往昔看今朝?”
老知青
9月14日,会前两天,在乌鲁木齐一家五星酒店内,张志尧和张永乐一同出席一个小范围的洗尘晚宴,宴会主角是来自香港的几位商界人士,他们都是早年的大陆知青出身,后漂流到港,打拼成功。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时间相谈甚欢,张志尧兴致高涨,不由得倒起苦水来。
他曾在新疆一些地方性研究机构任职。1960年代,由上海下放到新疆,大半辈子埋没在塞外荒蛮之中。落实政策的时候,却不是衣锦还乡,回到上海,面对只有20来平方米的房子,儿子要结婚,一家子难以安居,两个家长不得不放弃拥挤的大都市,重返6000里外的阿勒泰居住。他们这些知青出身的人,在上海是找不到归属的。那里的人,多半不把他们视同为上海人,他们早已被打上了“新疆人”的标签。
张志尧已经退休,妻子又没有工作。为了在公开场合能够显得体面一点,或者说是为了能风风光光地开这个会,他身上那套西服都是借来的。
对自己的处境满腹愤懑的张志尧,越说越来气,他们从前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离开属于自己的那两分地,要投身世界大展拳脚。如今回来了,发现那两分地还是那两分地,一切都没有大变过。这样一番情绪,被他毫无顾忌地脱口说出來,但是很意外地,这并没有博得大家的响应。在座的知青同仁们,眼看面前有一颗火苗正在闪现,他们立刻群起而扑灭之。
“你要是这样,我们是不答应的。你要把每个人的发言稿打印出来事先给我看过,我才能确定参不参加。”商人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不要发出和政府不同的声音,不要提诉求,我们要把这个会开成一个快乐的会,圆满的会,交朋友的会。”
数番正告之下,张志尧这颗火星,终于被摁了下去。
“你算什么啊?你不过就是多有几个钱而已啊,”事后他不无悻悻地说,“我说的是很中性的话,‘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参加这个会。我想你这个老板怎么……”
张志尧是被敲打下了,但另一些人又冒出来了,会议当天的发言中,有人喊出“多思善疑”的口号。
“我们在那段特殊的时代被耽误,这个运动对每个参与的知青本身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我们知青和共和国一样,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
当天吃晚饭的时候,知青中间起了摩擦。香港的知青代表突然拽住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邓贤发飙,“你说我们都没有理想,就你有理想。你不能代表我们知青,你无法代表我们……”
邓贤于1971年跑到云南当知青,后来以写作知青题材而闻名。他在公开场合里回顾了自己的知青生活,内容琐碎,不愠不火。香港的知青代表显然是找错了对象。大庭广众的,这一下把性情温和的邓贤搞得下不来台,脸色很不好看。
“我什么时候说我代表知青了,?我只代表我自己。我的所有讲话只代表我自己。我连我老婆都不能代表,法律上我们是独立的主体,我怎么可能代表大家?”
两个争执得面红耳赤的人最终被大家劝解平息了。那个因故离开座位,事实上是香港商人真正要发飙的知青回到座位后,得知此事,立刻握着邓贤的手安慰道,“你代我受过了,你为我受委屈了。”
这个从前有着同一颗闪闪红心、同一种坚定路径的群体,在分崩离析若干年代后,重新坐在一起,他们中间,却出现了某种再也不能交汇到一处的裂变。
香港商人因其旗帜鲜明的立场而被一些知青私底下称作“红色资本家”,他们在内地拥有产业,属于“水陆两栖”,对于会上那些自作主张的言谈显得格外警惕和不满。有知青私下商议与他们公开呛声,但是被有识之士制止了,“我们要求民主,就要允许人家讲话,我们首先不要表现粗暴”。
第二天一早,香港知青代表们就气鼓鼓地退出了会议。
“今天他们还和我提这个事情,”张志尧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说各自社会背景不同,命运不同,对某些问题存在认同差异。”
向日葵
被时代从主流序列中抛出来后,知青们的寂寥大约无人可知。这些人,不惜血本从全国各地奔赴石河子,还是那样一种知青风格——有人带去一堆咸菜,逐桌分发给大家食用,有人带去自酿的白酒,请大家挨个儿品尝。一位热衷收集红色题材影片的上海知青,千里迢迢扛去旧式放映机,只为让大家在几部老电影所带来的语境下重温当年那段激情燃烧过的岁月。
受此启示,也曾是放映员的张永乐决心帮助这位知青收集一些旧电影,她还提议知青们集体行动起来,建立一些博物馆。“历史总会被提及的,不可能把这一段跳过去。现在大家不说,但总有一天大家会对它进行研究。不管历史怎么评价,在我们都还活着的时候把这段历史记下来,先把真实的东西,留给后人。如果要成立新疆博物馆的话,我会把这边的事儿先干起来。”这些差不多是爷爷、奶奶级的人物,坐在一起是又唱又跳。他们如今已经回归到生活的常态,在历史的震荡中,渐渐找回了30年前那个一度迷失的“我”。但是那段裹挟着他们的纯真年华的岁月,竟是如此难以吞咽,以致临到暮年还要进行一轮接一轮的反刍。
“我和我老婆都是上海知青,在北京定居30多年了。特别奇怪,我们有个毛病,北京要是十天半月不下雨,我们肯定就会嘀咕:这不下雨庄稼怎么办?或者雨多了,我们又会嘀咕,雨太大了。北京这个地方,雨多点少点根本不影响整个国民经济,也不影响市民的生活,更不会影响我和我老婆的生活。但我们一定会犯嘀咕。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色,和国家命运、民族命运、老百姓命运紧紧勾联在一起。任何情况下,我们心里总有三个字:老百姓。”知名作家陆天明说,“2000万人上山下乡,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怎么样让一代年轻人也具备那样的素质和情怀?”
不错。这的确是从他们口中喊出来的。他们期望自己那一代人身上曾有过的舍身忘我风格可以得到发掘与弘扬,以便对当前矛盾激化、物欲横流的社会起一点激浊扬清的作用。
这当然只是一种愿望。若想使之实现,前提是必须让人们能够记住他们这一代人存在过。即便是流星划过天幕,常常也会有痕迹去证明它们曾经绚烂绽放。人还活着,就已经面临行将被遗忘的尴尬,这样一种共同忧虑促使知青们振臂而起,想趁着有生之年给人们留下一点历史遗产。
陆天明有过两次下乡经历,第一次是去安徽插队,结果身体搞垮了,吐血,不得不返回上海;第二次北上新疆,为此是
哭着喊着要把上海户口注销。孩子们要跑到火焰山脚下当农民,对于很多父母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就算是跪在孩子面前,也挽不回他们那颗铁石一般的心。对于现在的年轻一代来说,这根本就是无法理解的。之前有两位记者去采访陆天明,一位本科毕业,一位是研究生,他们问陆,当年为什么会有知青?这让陆天明一时哑然,心情无比沉重。
“聚会的时候,我们慷慨激昂,热泪盈眶,风采不减当年,我们唱着当年的歌,喊着当年的豪言壮语,一散会,我们白发苍苍,融入到大马路上的人流车流中间,谁还认识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是了。”陆天明不无凄凉地说,“在我们这个年龄,说句伤心的话,是聚一次少一次。”
陆天明的话,让张永乐不无触动。当年她也是以一个少不更事的城市高干娇小姐身份卷入上山下乡大军的。梦醒了,真正是时移世易,沧海桑田。世事就像被放置在一架永难平衡的跷跷板上,不是在这一端。就是滑向另一端。
“我们那个年代,还是理想放飞的年代,是一个有信仰的年代。大家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现在是哪儿最轻松最挣钱我就到哪里去。理想就是挣钱。大家还有没有特别心疼老百姓,心系国家命运?未来怎么样,还有多少人来考虑这个事兒?”
一场没有风云的际会,将那段被冷却和尘封的时光轻轻掀起一角。曾经单纯的人们,现在心情有那么一点复杂。
在去瞻仰知青故迹的路上,一位电视制片人请求大家假若遇到向日葵田的时候可以稍稍驻足停留,以便能够补拍一些镜头。高原郊野上,秋意已浓。田地里生起了烧荒的烟火,玉米地和葡萄林不时擦肩而过。这一群人,终究无法找见那片没有收割的向日葵。
新问题
正式的招待宴会上,地方政府几位主要官员莅临探望,并即席发表了祝酒词。领导们于言辞之间肯定知青群体当年单枪匹马投身当地建设,只求付出不要索取的无私精神。
“他妈的,现在外面来石河子淘金打工的人,比如某省的人,一来不是一个,是拖家带口一大帮人。”
有人向领导提问,怎么看待知青们当年的贡献。官员答道,他们给我们这里带来了发展,带来了服装文化、家具文化和餐饮文化,他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讲话的官员才走开,一位知青就说,“这位领导的话我不能赞同。知青们难道只给这里带来了吃喝玩乐?这种说法,不是浅薄就是蓄意浅薄,知青们到这里来,既有负面的意义又有正面的意义,负面的是对地方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正面的是付出了大半生。”
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试图对自己的灵魂坐标进行重新定位,这种轻浅而官样的评价,根本就不能够进入他们的满意指数评价系统。
中国当年的知青队伍总规模达到1700万人。事实是,回首那样一段挥之不去的历史,他们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分化。
“我不主张赔偿,为什么?因为不现实。我们国家面临着好多好多社会问题,财力有限,要求把这笔旧账还掉,很不现实。我主张这个问题一般在法理上谈一谈,学理上谈一谈,实际上是不应该的。”湖南知青艺术团的负责人郭晓鸣说,“你要赔偿,有时候于事无补,而且还会起反作用。”很多时候,金钱追偿并不具有足以愈合伤口的效用,它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性甚至是仪式性的安慰。在这一点上,那些走出阴影的人看得更为明白。
“补偿那也就是一种经济上的,还能把你的18岁要回来?不可能的。补偿也是有限的,他能给你补偿100万么?这么多知青。如果就三两块,能帮助你改变什么?”张永乐说,“我觉得那是消极的心态。对待那一段青春岁月,积极总比消极好。要把积极的东西放大,把消极的东西缩小。你在里面找消极的,你就消极下去,但你找积极的,它说不定能推动你朝自己的方向走。”
张永乐属于从消极当中找积极的那一部分知青。1971年,在新疆乌拉斯台农场吃尽苦头后,她有幸被红旗军工厂招去做了广播员。
多年后,厂子已经倒闭了,一帮老同事想要寻求补偿,商量着让张永乐牵头联名。她没有答应。
“提出诉求也不过分,是合理的,正当的,你完全有理由实现你的愿望,但我绝不,我绝不会加入到你的行列里去,也去争取。”张永乐说,“我认为这个路,我自己就可以走出来,我自己就可以创造我的未来,我不需要靠谁来联名支持我扶我一把。我们得感恩生活啊,感恩你的阅历啊,哪怕它什么也没有给过你,但它至少给过你苦难,苦难让你坚韧不拔。”
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专门的知青关爱基金会,这是由一些曾经的知青发起和掌管的,比如设于北京的中国光华知青关爱基金会,他们就在全国一些省份相继设立了工作站,以便对那些弱势知青提供某种物力以及机会性帮扶。在石河子集会间隙。也有人提出进一步深化知青关爱工作,以致细微到了期望可以通过这些机构得到哪怕一包有折扣的廉价奶粉。
“埋头苦干,自强不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这是知青最宝贵的财富,”郭晓鸣说,“一定要让它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