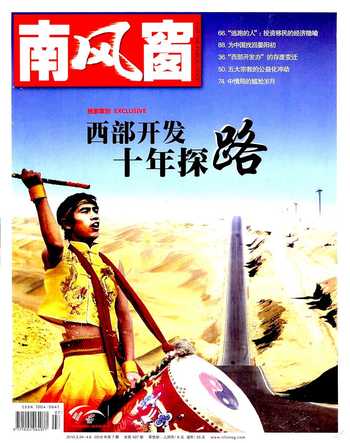批评政府,旧瓶新酒
赵 义

全国人大十一届三次全会高票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最大的亮点之一是明确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报告一面世,这一提法就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评述。而在公民借由网络发泄对于政府施政的不满情绪,却被以诽谤名义遭到调查屡次发生的情况下,新闻媒体更是借着“两会”期间这股东风“为民请命”。比如,“两会”期间,湖北省十堰市负责人就网上发帖者陈永刚被拘一案作出回应,并称提前释放发帖者说明公安部门已经意识到处理不妥。
《京华时报》记者录音笔事件发生后,新华网新华时评发表评论:创造条件让人民安全地批评监督政府。这篇评论广为传播,引起极大共鸣。
评论特别指出,当前屡屡发生官员打击报复批评者,一方面是“皇权思想”作祟,一挨群众批评就受不了,不觉得群众有权批评,反觉得群众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另一方面是对违纪违法官员的处置很轻,赔偿也由国家掏腰包。
对于“安全”的广泛共鸣,说明现在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不仅面临着诸多制度障碍,更越来越多地要冒着遭受被批评和监督对象打击报复的风险。本来,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是执政党一直坚持的执政理念。最有名的就是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窑洞对”提出的:已经找到了跳出王朝兴衰更替周期律的道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为什么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条件仍不如人意?《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行政监察法、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对公器私用打击报复批评者的官员进行行政处罚。对于被批评和监督的具体对象来说,如果实际政治生活中,因为打击报复而遭到惩罚的概率较小,自然容易“目无国法党纪”。但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需要最高层大力推动,则说明一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三个“善”
首先就是新闻媒体的双重性。一方面,在官员看来,新闻媒体是要讲政治的,服从大局的。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特征。而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尤其是转型社会,和其它力量相比(比如社会性组织),媒体是反映和凝聚民意的主要渠道之一。诸多引言获罪的不幸事件,现在主要还是依靠媒体的广泛报道和集中施加压力,正义才得到伸张。因此,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首先就要看如何对待新闻媒体。
这和民意代表里的双重性是一样的。人们对于那些永远举手拥护的民意代表多有怨言,但这些民意代表自身却有一套行事逻辑:顾全大局,领导并不比民意代表傻,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必须拥护领导的决定。而在另外一些民意代表身上,则主动“挑刺”。
比如,在有突发事件或恶性事件发生时,双重性下存在不同的选择。所谓顾大局,本来多是解疑释惑,总结经验教训,在“碎步”中不断积累进步。但相关官员往往多注重应急,那么所谓顾大局就是尽快平息事态,这本是对的,实际上变成了尽快让事件消弭,甚至不容忍公开讨论。
而互联网即时传播的特征更是刺激了官员的极端反应。正如人民网人民在线总编辑祝华新所说,在“跨省抓捕”事件之后,又出现了“跨省删帖”的现象。他认为,从“跨省抓捕”到“跨省删帖”,瓦解的是中央对意识形态的统一有序管理,藐视的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影响中央借助舆论制约地方坐大和贪官污吏的努力。两个“跨省”,是公权力恶性扩张的标志。从动用警力到动用意识形态控制力,表明官官相护,特殊利益集团深度勾结保护不良官员,其对民主法治的破坏更为严重,对执政党合法性造成严重损害。
2010年伊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充分发挥媒体凝聚力量、推动工作的积极作用。
这三个“善”,可以说很有针对性,实际上提出了意识形态管理的新要求。而第一位的就是善待媒体。从此次全国“两会”一些地方大员的表态来看,至少在口头上善待媒体是有共识的,对于负面报道和舆论监督的关系的认识进了一步。比如对于所谓负面报道,有地方大员就提出:“舆论监督不能叫负面报道,而应是正面报道。”有的提出:“官员应该以感恩之心,去对待老百姓,以惶恐之心去面对舆论。”此次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李肇星更明确说:“一个没有舆论透明的社会,人民的权利、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文明建设,都不可能做得很好。”
善管媒体,针对的是新闻媒体行业的一些弊病而言的,比如失实和数据不真等,绝非是指为了捂盖子而禁言。一事件成为公共事件,一问题成为公共议题,从原则上讲人人都有发言评论的权利。现在人民批评和监督的渠道有限(准确地说,是渠道众多,但作用发挥得不充分、不到位),传统的信访制度已经让行政体系和信访者本人不堪重负(“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竟然建议立法惩罚信访中骚扰领导的行为),如果“跨省删帖”的处理方式普遍化,那么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条件将更显逼仄。社会矛盾和社会情绪找不到出口,积累起来,将会导致真正的“广场政治”,类似于瓮安事件那样。此次“两会”,比较集中反映了不同新闻观的差别。
官民共同主导公共议程
现实中抗拒批评和监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社会的重大变化,即公民社会开始成形,政府已经不能完全主导公共议程。很多官员之所以从内心到行为都排斥新闻媒体对一些公共事件的追根究底,是因为还不能适应这个重大变化。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和属地化的发包式的行政治理模式,带来了官员的思维和行为惯性:公共议题和公共程序也是由我设计和主导的。
在抗拒批评和监督的时候,很多官员的口头禅是“干扰了中心工作”,这是上述思维的典型表现。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和社会利益的分化,政府完全主导公共议程已经不可能。虽然执政党和政府的学习能力很强,能够不断根据变化的形势提出不同的政策,但突发事件发生,或者某一社会问题的曝光,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决定了政府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面对“突然”出现的公共议题。这不是靠控制就可以避免的,关键是政府要习惯于官民共同主导公共议程。
当这种情况出现后,政府过去已经习惯的处理方式可能就会引起反弹,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在这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认识落差较大,各地政府的想法和做法也不尽一致。有的地方开放一些,在应对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和平抗议和诉求方面转变很快,避免了矛盾的激化;而有的地方封闭一些,不愿意作适当的改变。
正是在官民共同主导公共议程的过程中,人们见证了社会的进步。中国近些年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政策调整,其间就不完全是政府主导公共议程的结果,也包含了媒体、社会组织等力量长久的“批评和监督”。可以说,只要政府愿意与社会共同主导公共议程,官员愿意与民众一起设定公共议题,接受批评和监督就顺理成章,围绕网络媒体的“围剿”和“反围剿”的恶性循环就可以停下来。
今天中央政府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其旧瓶中的新酒就是官民共同主导公共议程。而对于突发性的“焦点事件”,事实证明,处理得好,都是缘于政府认真对待了“焦点事件”背后的公共议题。纯粹纠缠于“焦点事件”,则会走进死胡同。
从此次“两会”来看,这方面只是走出了一小步,还需要艰苦探索。比如上海钓鱼事件背后是有奖举报制度,但有獎举报制度和问责个人是什么关系?是制度的错,就可以不追究个体了吗?又比如网上发帖者陈永刚被拘一案,也不能只是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了不妥”,案件背后涉及的政绩工程问题怎么办?
从这个意义上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真正难的地方在于政府和官员放弃完全垄断公共议题的心态。我们也无法排除部分官员或者囿于利益,或者囿于艰难,不甘心放弃这种垄断地位,“创造”出新的抗拒批评和监督的办法。但我们更相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