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中国
邓晓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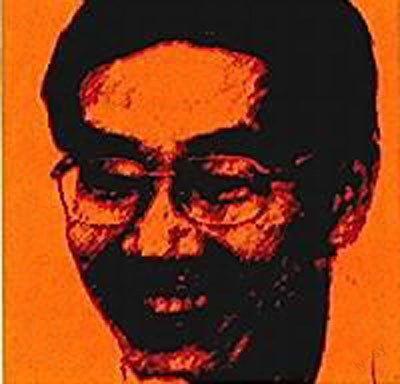
近年来,“山寨”一词颇为流行,其含义似乎也无所不包。举凡一切模仿、假冒、跟风、复制、借代的事或物,均可冠之以“山寨”或“山寨版”。从山寨手机、山寨软件、山寨红歌、山寨春晚、山寨《红楼梦》、山寨鸟巢到山寨诺贝尔奖,往往带有嘲弄或自嘲的成分,假装欺骗,实为恶搞。我们甚至可以将它看作一种中国式的幽默,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一看就懂,并且兴致勃勃地跟着起哄,情不自禁地加入这场“狂欢”之中。不过,山寨的前提是,有可供山寨的样本和原型,然后人们纷纷在这一原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加以变形、扭曲甚至解构,于是皆大欢喜:这些神圣庄严的偶像原来不过如此!这其实暴露出了山寨作者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贫乏,他们除了亵渎和贬损已经存在的典范之外,自己并没有能力建立起新的典范来,反而透露了对旧的典范的某种艳羡和嫉妒。
说到底,这种山寨心态并不是21世纪中国社会的新生事物,而是在我们古老的文化心理传统中有深厚的根源。在先秦时代,孔子所深恶痛绝的“八佾舞于庭”的现象,就是一种山寨现象。秦统一中国不久,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那口号就是最早的山寨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来的历代王朝更替,都不过是山寨版的转正,而转不了正的,就成为粱山泊的小朝廷——我怀疑这才是“山寨”一词的真正来源。最后一个山寨皇帝应该是袁世凯,他虽然具备了正式皇帝的一切威仪,却仍然不被全国人民所承认,原因是这时已从西方引进了新的原型,帝国模式已被民国模式即共和国模式所取代。然而,吊诡的是,就连共和国模式在中国也一开始就呈现出山寨特色,从北洋军阀到蒋民政权,国家体制尽管套入了西方总统制和两院制的构架,但在旁观者看来,都颇像一场场闹剧。
1949年以来,我们模仿苏联老大哥,最初似乎还是诚心诚意的。但不久就发现,这一模式本身就带有山寨性质,与其做山寨的山寨版,不如另立山寨。要说另立山寨的底气,我们比苏联还要足得多,想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都是山寨出身吗?只不过当今时代,要仿效古代帝王转正为天下人主,做“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谈何容易!于是只好满足于“文革”的意淫。“文革”之所以发动得起来,盖因中国当时遍地都是山寨心态的干柴,打倒走资派,造反派夺权,新的革委会成立,除了民间自发的反抗意识之外,“彼可取而代之”的山寨豪情也在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以山寨意识所煽动起来的这种山寨心态,最终当然是无功而返。“上海人民公社”只是“巴黎公社”的山寨版,而山寨林立则导致全国武斗,每个寨子都坚称自己才是正版,结果是最山寨的一伙造反派遭到镇压,红卫兵小将则“求仁得仁”,真正被赶到了山寨。到了“由大乱达到大治”时,人们终于发现,这场运动本来就是一场恶搞,哪里有什么“正版”?
经过了“文革”的中国人,开始有了山寨心态的自觉。80年代理想主义短暂的“春天”只不过是最后的验证,随后就进入了“玩主”的时代,玩文学、玩深沉、玩刺激、玩时髦、玩股票、玩爱情……目前的山寨文化也是玩出来的,人们在对山寨产品不满的同时,又有一种满不在乎或难得糊涂的境界。这世道嘛,你哄我我哄你,何必那么较真。就算是毒奶粉假酒害死了人,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古稀之数,所谓“太平盛世”也不过如此。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是什么?就是沉沦啊!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山寨中国。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说法,正版是从来没有的,所谓正版的作用仅仅在于引发山寨版,给山寨一个借口;万物都处于“延异”的“痕迹”之中,一切原型都是“替补”,一切所指都是另一个所指的能指。中国人一听,对啊!我们2000年前就已经后现代了,这还不足以提高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吗?总有一天,西方世界也会像我们一样,意识到所有的原型(例如普世价值)都是狗屁,山寨才是一切!那时我们就成了世界山寨的寨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