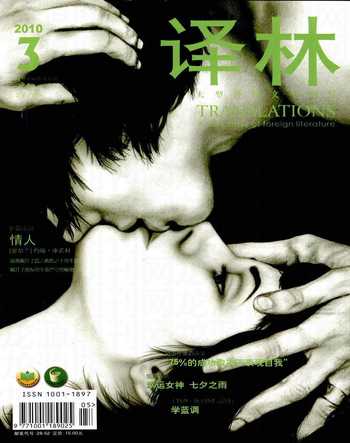学蓝调
卡特琳•施密特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筹办的第五届中德文学翻译大赛正进行中,作为此次大赛的协办媒体,本期刊登了德国作家卡特琳•施密特的短篇小说《学蓝调》和长篇小说《你不会死》的节译。5月19日,卡特琳•施密特将与毕飞宇一起,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翻译比赛颁奖仪式,朗诵各自的作品,并进行公开对谈。
——编者
卡特琳•施密特1958年生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图林根州哥达市,曾从事心理咨询师、编辑和社会学者等工作。现居柏林。发表《有天使的河景》等诗集和《则巴赫的黑猫》等长篇小说,荣获众多德国文学奖项。
2002年夏,施密特突发脑溢血。当时她挣扎着爬到丈夫身边说:“我要死了。”丈夫回答:“你不会死。”
这话她记住了,七年后成了她的新书书名。凭借长篇小说《你不会死》,她击败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荣获该年度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德国图书奖。书中,女主人公脑溢血后昏迷,接受了开颅手术,醒来后发现生活成了彻头彻尾的挑战:瘫痪、失忆,最严重的是以语言为生的她现在连说一个完整的句子都有困难。在找回失去的世界的道路上,她看到了一个陌生的自己。她找到了以往生活中的断层和压抑的激情。当发现与悉心护理自己的丈夫的婚姻其实濒临破裂时,她感到脚下的大地倾斜了。这是一部特别的成长小说。图书奖评委在颁奖辞中说:“小说时而简练、时而嘲讽、时而怪异地描述了病人的内心世界,讲述了她的家庭婚姻以及一段匪夷所思的爱情故事。由她的记忆片段凑成的世界里有没落的民主德国和两德统一后的岁月,一段从死亡边缘挣扎回来的个人故事由此被柔和而巧妙地置于历史政治转折时期的大环境中。”
那是一个苦夏。或许“苦”字通常被用来描写冬天,可在那一年,苦的是夏天。那种苦彻底击败了阿尔乔姆、孩子们和我,最后弄得我们像疲惫的战士一样,在秋天的门口徘徊,盼着解脱。阿尔乔姆那年五月刚开始在柏林市中区热电厂担任数学专家,休假自然遥遥无期。双胞胎才一岁半,正蹒跚学步,本该老是牵着,可我只有两只手,实在没法子,只好在院子里的梨树近旁安了个学步围栏,把她俩搁在里头。我在围栏和我妈之间跌来撞去,从早奔到晚,两头忙着喂饭换尿片。我妈当时大我一倍,七十二。我有时候还指给她看,太阳怎么躲在梨树叶子里头跟自个儿捉迷藏,希望她看了能打起精神来,可对我那两个女孩儿,我就只好指望她们俩互相忙活了。顺便说一下,我给她俩起了个小名叫娥儿,她俩的大名里都有个写法像“娥”的音节,不过念起来并不像,一个叫克萝尔,一个叫菲妮克丝。晚上,阿尔乔姆回到家,疲惫不堪的我把两个娥儿交到他手里。阿尔乔姆是那种好爸爸型的人。他偶尔也跟两个女孩儿说俄语,看看她们的反应。有时候她们简直像在跟他说一种混合语,一半儿一半儿的。每逢这时候,我妈就仿佛清醒过来,她教过俄语,她的脸上阵阵放光。我备了一架相机,打算最后一次给她拍张脸上放光的照片,可惜这光转瞬即逝,我根本来不及按快门。累死人的日子。
“宝贝儿,明天吃的桃子蛋糕你烤好了吗?”那天晚上,阿尔乔姆问我,口气格外随便,言外之意,要是我没来得及做,他就自己动手。可这种随便激怒了我,我以问代答:“你今天买土豆和厕纸了吗?”他一跃而起,把两个女孩儿抱在腰间,跑到走廊里,他进屋的时候把提包和买的东西随手扔在那儿了。当然,一样不落。有四层的厕纸,有硬土豆。我从冰箱里取出桃子蛋糕,放在他面前。我妈在沙发椅上睡着了,不时哼上一声。一个娥儿哭起来,另一个莫名其妙地欢呼。阿尔乔姆似乎很欣赏这种模范之家的样子,虽然他一言未发,但他咧开的嘴巴表明了这一点。做蛋糕底是我的拿手活,再铺上浸在甜酸奶里的桃片,整个儿冰一冰,最后浇上黄色的糖衣。阿尔乔姆心满意足地送孩子们上床。我呢,应付我妈就够忙的,每晚送她上床,她总要闹腾一番。
她睡着了,我冲了很久的澡。冲澡时我没想阿尔乔姆。我平常就很少想他。尽管他用丰厚的收入加上对双胞胎的关爱撑起了我的生活,但不知怎的,我对此视而不见,我在家务活的旋涡里团团乱转,根本看不到陆地。洗完澡,我散着湿漉漉的头发,站在镜子前面,看自己涂深色口红和睫毛膏。我看起来就像我妈从前的样子。这时我突然想起来,她以前很爱跳舞。她周末常跟我爸去舞协,估计她爱跳舞甚至超过了爱我爸。这时我又突然想到阿尔乔姆,我觉得,要是不跳舞,我就没法睡到他身边去。九月的晚上很暖和,让头发在街上自然吹干还不要紧。我套上牛仔裤,披上一件70年代风格的印花长袍,拣了双最轻便的鞋,拎起五彩斑斓的小坤包,轻手轻脚地关上门。
夜的黑暗正推开最后一线亮光。我住了脚,惊奇地发现,九月夜晚的气味很重。我迷迷糊糊,一步一步挪到埃尔利希路,上了有轨电车。就两三站。哈瓦那酒吧。我把头探进门里。就在三年前,我还把每个多余的夜晚都送进这家酒吧,还送上我多余的钱。现在,我在眼前年轻的顾客里头一个熟人都看不到,估计这些年轻人跟我当年一样,还在上大学,单身或者正在找伴儿。我头一回清晰地感到自己正在变老。我不知所措地缩回头,上楼踏进轻轨,车开了。我对面坐了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长头发。他在看一本英文书,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我包里正好有德文版,我拿出来打开,那人一抬头,看到我的书,笑了。他要在雅诺维茨桥下车,他询问地看我一眼,我便跟着他下了车。两本书已经放回各自的包里。他拉起我的手。话是没什么要说的,我们俩都沉默不语。我们沿着布吕肯路往南走,一直走到克罗伊茨贝格。我感到一丝凉意,拽着他进了一家酒馆。我们喝啤酒、吃粗肠。最后我扯扯他的袖子,酒馆免不了喧哗,不过还不影响我们跳舞。我们找了个桌子的空当,摇摆起来,自顾自的却又紧紧相连,我们搂成一团,闭上眼睛,有节奏地晃悠着对方,店主看到我们跳舞,把音乐开响了。是凯蒂•玛露的《学蓝调》Learnin The Blues,20世纪50年代美国流行情歌,最后一句歌词是“你感到心碎,你在学蓝调”,“blue”也有悲伤忧郁之意。,天知道这家酒馆怎么会有这首曲子。一曲终了,店主按下“关”键,我们睁开眼睛,才发现其他客人正盯着我们看,最后面还有个人拍起手来。我们买了单,回到街上,要分手却不那么容易。我们俩之间似乎有什么未了,不是有账没清,不过其实也差不多,我们撒不开对方的手。我感觉到,我得跟他睡了才回得了家。他的脊背绷得就像阿尔乔姆拉满的弯弓。我们在一幢楼房的门厅里合二为一,那是一场顺畅而有力的较量。一个醉归的女人进门时,灯亮了起来,这时我的牛仔裤已经拉回到腰上。我觉得他的背肌在紧窄的T恤衫下放松地嬉戏。我亲亲他的额头。他从地上捡起提包走了,我选了相反的方向。
回到家已是次日两点。我又冲了个长澡,用宝宝油洗净睫毛膏和口红,上床躺在阿尔乔姆身边。他把左大腿搁在我的肚子上,满足地清清嗓子。早上起来,我从夹模里取出桃子蛋糕切开,最后在外面套上一个蛋糕圈以防损坏,我很得意自己想到了这招。阿尔乔姆喝了我煮的咖啡。他亲亲我的额头,就像我昨夜亲那个小伙子一样。我很享受自己知道一件阿尔乔姆不知道的事情。我祝他跟同事们过个美好的生日,送他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作礼物,德文版。他把书放进包里,插在文件当中,走进房间再看了两个女孩儿一眼,就走了。下了楼,他把蛋糕放在副驾驶位子上。这时两个娥儿有了动静。我又有活儿干了,天天如此。
我妈通常比两个女孩儿早醒很多,我总算得空去看她的时候,发现她已经死了。我们的家庭医生海尔曼博士认为她死于心力衰竭。殡仪馆的员工把我妈装进一个灰塑料袋里,拉上拉链,抬下楼去。我当时想,我昨夜还在镜子里看到过她的。我不想哭。打电话给阿尔乔姆吧,他今天过生日,我觉得不合适。我跑进院子的围栏里,跪下来跟孩子们玩,才觉得安全了。我想睡上一会儿,可是女孩儿们不停地用玩具娃娃、塑料汽车和小沙桶干扰我。后来我从草丛里捡了两只既漂亮又新鲜、裂了口的梨子,去厨房削好给克萝尔和菲妮克丝吃。我妈生前老爱坐在梨树下的小凳子上出神,现在她死了,熟透的梨子我吃着不香。
晚上,我和阿尔乔姆分吃了两块剩下的蛋糕。他紧紧搂住我。我们谈了我妈的事。她葬礼那天,她原来学校还在的员工来了,十三位老师,都老了,还有阿尔乔姆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们的老家是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我妈生前说过,死后要个木十字架,估计后来是他爸在十字架上加钉了两条横杆,现在我妈坟上竖的十字架成了东正教的了。幸好一直没人发现这一点。至少没人向我问起过。
我妈死后依然占着那张小凳子,我没法坐在上头歇脚或是看书,后来我发现,双胞胎踉踉跄跄走出屋子到院子里去时,老是盯住那张空着的凳子看,我知道了,她们也看见我妈坐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