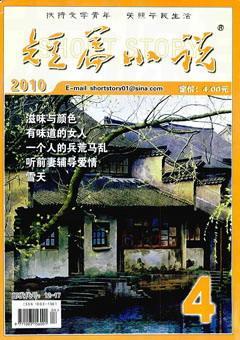盐路往事
戢建华
我对盐最初也是最深刻的记忆来自山爷的一次谣传,现在看来简直就是恶作剧。山爷不知听谁说盐要涨价,于是一下子买回来一百多斤屯着,够吃好几年。并且很不小心地散布了这个内部小道消息。于是人们纷纷效仿,一时间区供销社门前人满为患,盐供不应求。后来没买到盐的人受气氛渲染更是加深了盐马上要涨价的恐惧,供销社的同志的辟谣也更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此后很长时间供销社不得不对盐采取限购措施。而此后的五六年里山爷所担心的情况都没有出现,盐依然维持着一毛二的价格没有变。山爷及那伙屯盐的人那次发疯的举动也成了笑谈,在人们都吃着散酥酥白花花的盐的时候,山爷那伙精明人还在吃着发黄的盐疙瘩,放到锅里还要拿锅铲拍半天。后来我终于理解了山爷的那次举动。他们那辈人都是被盐吓怕了的。
山爷家的条件在生产队里算是好的,一来他是生产队里的粮食保管,二来他女人年轻时多少攒了些家底儿,这后者是人们私下议论的。夏天的晚上,人们吃过饭都搬着椅子聚集到山爷家的院子里,或在地上下成三棋卵子棋,或拉家常拍古今儿,热闹场面仅次于大队部里放电影。在人们都提心吊胆用电的时候,山爷家院子里都安了电灯,而且每晚都亮着,直到人们散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山爷家的院子是用石灰渣硬化过的,每晚都会燃起一堆蒿草驱蚊,我们几个孩子就围着山爷听他讲杨家将岳家将,有时也讲自己年轻时当盐背子的事。我那时已上了几年学,识得文字。有一次我把从书上看来的一个关于盐的笑话讲给山爷听,说是一家人吃饭,没有菜,就在房梁上吊了一小包盐,规定吃一口饭看一眼盐。老大吃了一口饭看了两眼,老二立即向父亲举报,父亲说成死他。但是山爷听后并没有笑,反而说这不是笑话,这是真事儿,只是那小盐包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舌头舔的,吃一口饭舔一下盐包,知道盐包是用什么做的吗,就是纱布包着盐坨。山爷也不止一次给我们讲起他年轻时背盐的往事,一讲到盐就表情肃穆。我笑他,盐是你的神啊。山爷说,是前半辈子的命。
山爷年轻时是辗转在南山里的盐背子。南山是对鄂西北房县往南直到川鄂边境的大巴山区的统称。自古以来就深邃歧杂人烟稀少,而这其中却隐藏着一条经神农架官封、高坪、红举、板仓、大九湖到川东巫溪大宁厂绵延千里的古盐道,山爷当年就是身背竹篓手持打杵行走在这条盐道上的盐背子之一。山爷说盐背子出门是不带钱的,凡事都以盐作交换,到民国后期,盐比钱还硬通。出门也只需一个背篓一根打杵一张家织布上桐油的雨盖,外加若干苞谷面干粮,干粮去的时候就沿路寄放在客栈,委托店老板代以蒸熟记下名字,以便返回时充饥。那盐六十斤一包,力气好的汉子能背上两三包就算了不起。
盐背子大多都受雇于盐行掌柜,也有零散农民自个儿当盐背子,背着黄豆、苞谷、木耳去换盐,回来再几家平分的,一般出行都是数十人结伴,以防野兽伤害山匪劫道或气候突变等不测因素。话说盐背子中有两个是叔侄俩,为叔的不知道什么名字了,是个年愈五十的老光棍儿,也是在这条盐道上跋涉了几十年的老盐背子,当侄的三十啷当岁,小名儿叫骡子,也是实在找不到别的生路才人的盐背子行,在这条路上还是走头一趟。骡子年轻血气方刚,背三包盐却不常打杵,一路止只是顾盼着奇山异水石龛古寨。路过鸾英寨,骡子打了一杵,仰头远远地望了一番山上的石寨墙历经千年却依然雄浑如初。史载戢鸾英在此筑寨落草计伏薛刚后二人成婚,并在九道梁、大九湖一带屯兵拥护庐陵王李显反周复唐,不知道鸾英寨扼古盐道而筑是否也干过杀人越货的营生。骡子记得不久前看到路边的一棵大树上刻着九条命在此几个大字,听叔讲是山匪劫了九个盐背子的货,又把那九人绑在树上活活冻死,那地方也因而得名九条命。吓得骡子逢走到山隘阴暗处就寒毛直竖。正思量着,忽闻“呦——嗬嗬”一声长啸,前方树林里就蹦出六七个拿大刀长矛的汉子,个个脸抹锅灰钟馗一般咋咋唬唬地要劫道。盐背子们于是放下盐包也手持打杵严阵以待。打头的盐背子上前抱拳问道:“敢问大哥贵姓?”这其实是洪帮中对暗号的黑话,盐行掌柜为了自己的货一路走得安全通畅。一般都会向帮会组织交一些礼金以寻求保护。但眼前的这伙人显然听不懂,匪首恶狠狠地叫嚷道:“识相的盐坨子留下,捡条命从刀下过去。谁要是活得不耐烦,就试试爷这刀快不快!”打头的盐背子依然舰着脸拱手作揖,“这盐是掌柜的,我今儿要是从刀下过去了,明儿就过不去掌柜那刀了。”话不投机,双方剑拔弩张,眼看一场恶战在即,骡子叔一脚将骡子踹到了路边,自己随众盐背子挺起打杵就展开了生死搏斗。那打杵的底部都套有五六寸长的铁陀螺,走山路时扎在地上可以防滑,横起来却也不怯于长矛。那骡子被他叔一脚踢醒,撅起屁股就跑到山上一棵大树后躲了起来。转眼间,两伙人就刀杵相向血肉横飞,不多时就归于沉寂。半晌,骡子叔慢慢爬起来——他原本只是胸前被撩了一刀趁势倒下诈死的,准备寻了侄儿继续上路,忽然听见死人堆里有断断续续的呻吟。仔细查看原来有一个锅灰脸没断气。那锅灰脸也看见了他,那双凄惨黯淡的眼神令这个久经风霜的老盐背子也生了隐忍之心。他低下头,那锅灰脸说,他本是山前的田户,闹灾没了收成,家里都断炊了,有个三岁的儿子还病着,君子不记仇,麻烦转告他女人来收尸,好歹入土为安,免得在这里喂了虫狼。说完就咽了最后一口气。
叔侄俩往前走了七八里地。果真看见一户人家,门前一个玩耍的小孩满脸水疱,一看就是患了天花,不远处一个提篮的女人正蹲在地上寻着野菜。骡子叔想必就是这家了,于是上前招呼道:“妹子,你家大哥托我给你捎个信。”骡子叔进得屋里把事一说,那女人立即就瘫坐地上,人中掐了半天才嚎出一句“我的夫啊——”孩子不谙世事却也跟着嚎啕大哭起来。骡子叔冲骡子使个眼色,说:“你把娃儿带出去哄一会儿,我劝劝妹子别想不开。”骡子就抱了小孩出到院子里,只听得里屋那女人哭声越来越小,窸窸窣窣停顿了一会儿,渐渐地就变成了急促的喘息声。过了一会儿,骡子发现那女人送叔出来时已全然没有了悲伤,脸上反而有了一抹妩媚的红,而叔的黑脸也成了猪肝色。骡子叔边往外走边嘱咐女人:“天色不早了,还是明天去寻吧。”还亲呢地摸了一下孩子的头。叫了声“小山儿”。
一番耽误下来,住店已经赶不上了。叔侄俩就找了一个路碥上的岩龛歇了下来,那岩龛外还散落着木截柴炭,壁顶已被烟火熏得漆黑。一看就知道是住了不少回人的。叔侄俩就着那些木柴又燃起一堆火取暖。夜里醒来,骡子忽然看见隔火一丈开外晃荡着几双绿莹莹的眼珠,,遂惊恐地推叔,叔只是癔症了一句:“狼巴子,多加两把柴。”骡子又添了几根柴棒子却依然惊恐未尽,使劲撑着迷迷糊糊的眼睛直到那几点荧光随天边的星光隐去,这才合上眼。骡子被叔推醒时,才发觉变了天,阴沉的天空不时就滚过一阵炸雷。叔着急地说:“你在这守着,我去看看小山儿他娘。”说完就只身走了。骡子又睡了一觉,却依然不见叔回来。有心出
去寻叔,无奈眼前雾雨接地连天浑然一片,连脚伸出去都不知道在何处。好不容易挨到天晴,骡子连等带寻又是两天,叔依然杳无音信。第三天,骡子幸运地遇到了一伙同路的盐背子,一打听,那些盐背子们摇摇头苦笑道:“只怕不是被山洪冲走也是喂了野兽哦。”骡子只得大哭了一场随行走了。骡子叔失踪了。骡子每念及此事,只是喃喃地说,报应啊,叔那次是趁人之危行了龌龊之事的,不过,叔也是真心想成个家的。我作为旅游者也曾踏上过官封这一带的占盐道,昔日光滑的石板路连同打杵窝此时已长满寂寞的青苔,置身其中,山不见头,水不见源,林木不着边,不时一袭轻雾掠面而过跟前就是一片混沌,仿佛顷刻间整个世界就将自己抛弃。
骡子回去后就大病了一场,梦里时常说着胡话,不是猛地坐起身子喊救命就是瑟瑟发抖地推着女人叫叔,找鬼谷子算了一卦说是魂丢了,于是天天见黑女人就领着骡子到大柳树下去招魂,女人叫一声骡子应一声,如此半月方才踏实。不久骡子又拾掇起竹篓打杵重新上了路,没办法,牲口活着得喂食,女人孩子得吃饭,这就是命。只是此时的骡子已经没了初上路时的好奇和恐惧,走在路上也和别的盐背子一样伸着脑壳看着脚一步一步往前挪。两三趟下来背上的三包盐也变成了两包,生死苦难看得多了。骡子也想开了,中途也晓得偷偷地享受一下了,带回家的盐和钱也就越来越少了。有时候甚至去来净人,女人开始还体谅着,后来明白了就闹,推着他胸脯边往外撵边哭着喊着咒他“你个滚坡死的啊”,孩子看见大人动粗就哭,次数多了骡子也无动于衷了。终于有一次骡子回来竟然发现女人和一个野男人躺在自己的床上,愤怒的骡子举起打杵就要往女人身上砸,女人却没有丝毫的畏惧,也不躲闪,只是冷眼把骡子瞅着。半晌,无趣了的骡子悻悻地摔门而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三道街是条两三里长的石板街,也是盐道上的一处重要驿站,街上店铺林立,鳞次栉比,有盐行、客栈、染坊,当然也有妓院。来去的盐背子心里都盼着早点儿到此歇脚打尖儿,有的好顺便打听一下行情,交易一点随身的货物,也有的就图个快活。骡子初次随叔入川路过这里时眼前一亮,没想到深山老林里还有这么个繁华去处,感觉简直是进了世外桃源。那晚,叔叫骡子先睡自己出去一趟,去哪儿叔没说,后来骡子知道叔是去了春月轩快活了的。那地方骡子也是去过的,只是时间长了觉得那些婊子有钱掏钱无钱抠盐什么人都不认,太没意思。那时的骡子在盐背子中已经油了,在三道街也是熟唤的很。骡子厌倦了婊子的无情无义是因为对梅香起了念想,梅香个儿不高却生得白皙匀称,是三道街不远的庄户人家,男人前些年背盐时摔成半身不遂,天天直挺挺地躺在床上靠女人伺候,一个儿子还没长成器。骡子进得梅香屋里嘘寒问暖地就开始聊,都是过来人,几句话下来,梅香半推半就地大襟就解开了,两坨白肉颤颤地一露,骡子的头就蒙了,血往上一涌,干柴烈火地就着了。自古商杂流动之地都是笑贫不笑娟,男人在外挣钱不容易,女人在家偷缝儿摸空儿地裤带一松也能挣个油盐钱。再就是盐背子一年四季不落屋,外面也难免有几个相好的。有两个故事说是盐道上有户人家。女人和一个过路的盐背子在堂屋的板凳上刚媾和完,男人就回来了,问干什么的,女人答卖蜂糖的,男人用手指蘸了板凳上的淫液一尝,说幸亏没买啊,一点儿都不甜。还有一个是说两口子晚上睡觉,女的听到外面有动静,知道是野男人在约自己,于是说要出去小解,男人说披件衣裳吧,免得凉了,等再上床时,下身的淫液滴到男人脸上,男人一抹脸说,叫你批件衣服你不听,凉了吧,鼻涕都冻出来了。这种荤段子盐道上流传颇多颇广,也成了盐道上男人的插科打诨和男人之间的笑柄。此后,骡子就在梅香那儿安了个家,而梅香也算捡了个伙计。捡伙计是指男人丧失了劳动能力,女人再找一个男人帮忙自己干活养家,包括先前的丈夫,晚上行丈夫之实白天俗称伙计。
成了伙计的骡子依然干着盐背子的营生,越来越大的梅香的儿子从来不管自己叫爹,有事儿非得打招呼时就哎一声。梅香虽然也没说过开撵的话,洋芋坨苞谷糁有他们一口吃的也没少了自己一碗,日子一天天的过得还算安生。但骡子知道自己早晚是要离开这个家的,他养着这个家,但他在这个家里只是个没有地位的伙计。一旦这个家不再需要他,他就得从这个家走出去,至于走到哪里,他还没想过,半个月一趟盐他只顾得累了还来不及想。走在路上他也看到过冻死累死的盐背子,心想自己说不定哪天往路边一歪一辈子就了结了,这样拼死拼活地却不知道图个啥。此时的骡子年已不惑,已显佝偻的背脊一次也只背得动一包盐了。终于有一次骡子回来的途中一时贪凉伤了风寒,好不容易挨到家喝了几碗滚烫的葱根水卧床发了场汗,又歇了两天才下得地,中午坐在桌子上吃饭时骡子喝了几口苞谷糁,伸手去拿盐包时觉得有些不对劲,放到嘴里一舔才发觉是白火石,心下知道梅香是嫌自己在家闲的时间长了,在撵自己出门背盐了。于是说:“你给我准备点儿干粮吧,我明天就走。”到晚上吃饭时。桌子上就多了一盘金洋芋和一盘银苞谷。南山里没水田,一年到头除了洋芋就是苞谷。但是金洋芋和银苞谷却是洋芋和苞谷里面最金贵的吃法。洋芋切半指厚下锅放少许油煎二面黄所谓金,苞谷煮熟放到室外凌透再放到油里炸开花所谓银,这一般是过年才有的吃法,如今放在了骡子的面前,骡子心里是再明白不过,梅香的意思是要想在这个家呆,要想吃好的,就得干活。
第二天骡子就拾掇好家伙上路了,但他并没有走远,而是在三道街的一个客栈里和店老板吃着旱烟锅子闲聊着等伴儿。到傍晚上铺,看到铺上挤的人也差不多了,少说也有二十。看看行头是盐背子的也不少,心里塌实下来,遂燃起一锅烟坐了起来。这时屋里又进来一个麻脸的后生,沿墙放下随身的家什走到铺前望望满铺的人有些傻眼,一看就知道是没走过盐的毛头小子。骡子笑了笑,起身抽了根竹棍儿蘸了冷水往人缝里一拨拉,那两边的人激的一翻身立即露出一个空位,骡子示意那后生赶紧睡下。睡下后,骡子问:“是头一回走盐吧。”后生道:“是。”骡子问:“十几啦?”后生道:“十四。”骡子问:“家里几口人啊,怎么叫你出来走盐呢?”后生道:“就我和我娘,我娘种庄稼,前些日子又病了,我不出来不行。”骡子又问:“你家哪儿的。”后生道:“官封。”骡子又望了望那后生脸上的麻子,忽然想起了那段往事,算计了一下,于是问:“你叫小山子?”后生扭过头,有些惊讶:“你认识我?”骡子应道:“早年走盐路过你家,那时你还小,还在出天花呢。”小山子“哦”了一声。骡子正欲再问,小山子却已睡着了。
再上路时,骡子对小山子就有了注意,那小山子时而机灵如毛猴时而憨傻如崽熊,看到路边盛开的山桃花也忍不住折一枝把玩一番。一路上全然不知劳累,渲染得老气横秋的骡子也有了生气,骡子想自己的儿子也该有这么大了吧,那德行说不定也是这个样儿,想着想着就笑起来了。背盐时
骡子还是一包,小山子开始背了一包,耸了耸肩于是又加了一包。上了路不多时就得撅着屁股爬山,小山子依然提起打杵孱着头就往前走,骡子一嗓子吼道:“上七下八平十一啊,哪个多走一步是狗日的啊。”这是盐背子们协调速度的侃子,意思是几步一打杵。半晌过后,年轻的小山子气势也衰了下来,腰弯得更低,步履也慢了,走上三五步也不得不打上一杵了。第三天歇晌时。小山子回头眺望走过的路,上前天背盐的大宁厂边上的谭家墩竟然还依稀可见,小山子哇的一声就哭了。众人都笑起来,骡子没有笑,他忽然觉得那哭声中仿佛还有一丝未尽的奶腔,他想起了十来年前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的哭声,那哭声有恐惧有哀求,骡子的心一下子软了,他决定这趟盐下来无论如何也要回家一趟,不管儿子认不认自己都要回去,好歹骨肉相连,就是老了死赖着他他也不可能不给自己一碗吃的。于是劝道:“小山儿啊,别哭了,还没到哭的时候呢。”然后又扯起嗓子唱起来:“大宁厂哦,那个开盐行,累死了我湖北的好儿郎啊——”
过天池崖时,天气说变就变了,本来就上不见顶下不见底的天池崖,此刻更是云山雾海,一条细若游蛇的泥泞小路在脚下也是若隐若现。小山子此刻好像明白了骡子话的含义,他正揣摩着,一阵阴风夹着山桃花般大小的雪块就袭卷而来,顷刻间天地苍茫一片,小山子头一次看到三月下桃花雪,也是头一次负重走在这样的路上,他没有新奇却也没像骡子料定的那样去哭,他只有恐惧,稍一挪步就一趔趄,只好频频地打着杵脚步却畏缩不前。后面的人开始喊了:“走啊,再不走晚上都在这儿冻死啊。”骡子有些心疼了,说:“小山儿啊,叔来帮你背一包吧。”小山子看着骡子佝偻的背有些迟疑,骡子又说:“你放心吧,叔年轻时还背过三包呢,这会儿雪下得紧,权当压一压出出汗。”于是小山子小心翼翼地给骡子匀下一包,释了重的小山子腰杆儿挺了不少,一手拄着杵一手扶着崖壁,脚步慢慢地就挪开了。刚走不远,忽闻身后“啊——”的一声长啸,声音凄厉,转瞬即逝。小山子惊恐地回过头。就有盐背子喊:“骡子滚坡了——”小山子一下子痛哭起来:“叔啊——”众盐背子劝道:“走吧。走吧,这儿滚坡的盐背子多,不知哪个兄弟想骡子了,也邀他享福去了。”我到天池崖时也是个阴天——陪同我的朋友倒是来过很多次,在他的印象中,天池崖好像就没晴过。向上看依然是不见山顶只见白雾一片,朝下看依然不见底只见刀削般的悬崖和云海。这时的山路已经打成了两米多宽的水泥路,只是路面水渍很重,很多路段都青苔斑斑,路边没有防护栏,坐在车内感觉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一趟下来只顾着提心吊胆真是没有心思去浏览风景。
此后的小山子很是沉默寡语了些年,走在盐道上他和别人步调一致地打杵看路,也逐渐深谙盐路世事风情。俨然一个年轻的老盐背子。直到小山子二十六岁那年,发生了几件事,先是他母亲去世,安葬完母亲后,小山子忽然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单。并第一次有了成家的欲望,然后就是解放,路过红坪时,他突然发现世道变了,街上多了一块“房县红坪乡人民委员会”的牌子,而春月轩连同里面的婊子一起都不见了。来回走了一遭,他惊奇地看见春月轩的那个叫春桃的竟然就住在红坪街不远。那个晚上,小山子径直去敲响了春桃的门,屋内问:“谁?”门外答:“过路的,借宿。”屋内说:“前面不远有客栈。”门外答:“花不起店钱。”屋内说:“你到别处去吧。”于是不说话了。门外一个声音说:“算了吧,我们就睡扁担上吧。”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声音嘟嚷着:“你往里睡一下吧,挤得慌。”不一会儿鼾声就此起彼伏。也许是春桃觉得一根扁担上睡两个人稀奇,悄悄地起来把门开了个缝儿想看个究竟,但小山子趁机推门就进去了。事实证明,小山子的这次勇气和当机立断是多么的英明。不久,春桃就在房县城郊买了房子和小山子以夫妻的名义开始了新的生活,而小山子也彻底结束了他的盐背子生涯,只是他们一生没有生育,唯一的一个儿子是抱养的,但是以小山子的精明能干和春桃的聪慧贤淑还是经营得一家人殷实幸福。特别是土地分到户时,别人对政策都是犹豫观望不理解。他们则是率先买下了生产队里的手扶拖拉机搞起了运输,生活由此更加蒸蒸日上。他们这辈子,有人说是山爷享了春桃奶奶的福,也有人说是春桃奶奶享了山爷的福,总之村里人的眼睛在看他们时流露出的是羡慕。
但是山爷最终也死在他的盐上。上世纪末的九十年代,卤肉端上了人们的餐桌,并以其便捷和色香味俱全很快风靡起来。精明的山爷在家也卤了几次。但是色泽不是浅得发白就是深得发黑,后来听别人说卤菜店里是用亚硝酸盐上的色,便也去买了一些回来试着做。此招果然凑效,山爷看着自己做的卤肉比街上卤菜店里卖的还要鲜红,肉皮上透着红富士一样的光亮,得意之余不禁就多尝了一些。当人们发现山爷的尸体时,他的旁边还放着卤肉和没用完的亚硝酸盐。据卫生防疫人员现场抽样化验和调查。山爷做的卤肉亚硝酸盐超标近千倍。死因为食物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