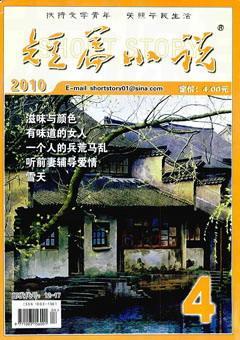雪天
郝 炜
一走出酒店,他就被雪包围了。雪,喧嚷着,嬉戏着,漫天飞舞,白茫茫一片。雪花很大,大得好像有了重量,落在身上却没有任何声息。他用手试了试,它们落在手上就化了,凉津津的。每个冬天下雪的时候,他都试图看清雪花的形状,每次都是徒劳。
好久没有下这么大的雪了,他想。
街道上行人稀少,这个时间,人们都回家去了,像飞鸟归巢。往天这个时候,他也坐在饭桌前吃着可口的饭菜,甚至喝点小酒。可是,今天从一开始就不对,从一开始就反常,连天气都显得不对和反常。下班的时候,他本来要回家,他已经武装好了一切。把围巾和手套都戴好了。小陈从门口走过,门开着,他看见了小陈,小陈也看见了他。小陈本来正匆匆走过,见他望见了自己,就带着有一丝游移和慌张,定住了。
小陈说,张处长,还没走?
他应了一声,说就走。
小陈说,和我们喝点酒去呗?
事实上,他清楚地感觉小陈只是路过,只是顺便问他一下,甚至没希望他去。可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答应。好像恰恰是因为小陈游移的眼神被他看在了眼里。使他一下子答应了,有些恶作剧的心理。
其实,他答应完就有些后悔。他知道他和小陈现在的关系只能说是一般,甚至是很一般。小陈是那种比较实际的人,以前的日子里,小陈对他还真是不错。小陈一直大哥长大哥短的,嘴显得很甜。可是自从一年前他调到了现在这个部门,小陈就淡了,甚至很少打电话和到自己的屋里来。这他也能理解。每个人在这个社会生活中都遵循着自己的道理,都有自己的求生方式,小陈从一个司机,一路走到今天。很轻易地就成了办公室副主任,人家凭的什么,还不是会看风使舵?这没什么可责怪的,尽管你在小陈过去的生活中多有帮助,可是你对现在小陈的生活还有什么作用?要说有用,仅仅是年底考核划票时有一点,一票而已。
一到桌子上。他就更为自己这个草率的决定后悔,他的感觉没有欺骗他。小陈今天请的是黄副总,黄总和他关系不好,小陈当然不会不知道,小陈可能也在为自己的草率后悔呢。他一坐在那里就不舒服,有一种被蒸烤着的感觉,尽管屋子并不热,尽管他们总共才五个人。黄总倒底是领导,很有心胸,很热情。倒是小陈显得心神不定、无所适从,好像不知道怎么说话好了。他知道如果他在场,今晚大家都不舒服。他正琢磨着怎么脱身的时候,手机十分善解人意、恰到好处地响了,他以为是妻子的电话,接起一听,是个陌生的女人,女人说,我是杨军的爱人,老杨出事了。杨军?哪个杨军?女人说,是杨军让我给你打的电话,老杨说,只要和你提他你就能来。哦,他还是有些莫名其妙,他问,杨军出什么事了?女人说,他出车祸了,刚送到医院,说着女人在电话里哭了起来。他根本想不起来这个杨军是什么人,也不知道这个给他打电话的人是谁,但他需要这个电话,需要脱身,他问,在哪个医院?对方边哭边说,中心医院。然后着急地说,你快来吧,我都蒙了,我还要去挂号呢,你快来吧。说着就撂下了电话。肯定特别着急。
他立刻有了借口,他冲大家抱抱拳说,不好意思,一个朋友出点事情。黄总关切地问,咋的了?他说。一个朋友出车祸了,我过去看看。黄总说,让小刘送你一下吧。小刘是黄总的司机,这时候显站起来的意思。他说,谁都不要动,你们喝你们的,我去去就来。车祸有医院,我也帮不上忙,就是过去看看。小陈说,要不我送你?他说不用不用,就赶紧退了出来,他知道只要他一出门,小陈就该松口气了,因为他自己也松了一口气。
他感觉刚才的电话肯定是打错了,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叫杨军的朋友。可是,他又想,也许自己生活中有过这个杨军呢,是不是这些年不联系,忘了,可人家还深刻地记得自己?杨军,一个普通的名字,也许有过。这些年总有一些聚聚散散的朋友,谁知道是不是呢?他忽然对自己把握不定。走出酒店,他本来很想回家,可是那个女人无助的声音使他很受震动,他想,也许真的认识呢?上出租车的一瞬间,他已经不再犹豫了。
司机问,上哪?
他说。上中心医院。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去医院。他觉得今天什么都有点不对头,从一开始就不对头。
车在大雪中穿行,根本跑不起来,所有的车都像蜗牛在爬。雨刷器嚓嚓地响着,雪像蝴蝶飞过来,在车灯下飞舞,死亡。他想,那个杨军究竟是哪一个呢?是什么样的车祸呢?是他自己驾车,还是被车撞了?这个鬼天气,怎么出了这样的事情。
他想到刚才的酒店,想到黄总和小陈他们,他想,他们也一定如释重负,他们和他的心情一样放松。他们已经端起酒杯,小陈他们正在开始向黄总敬酒。他们也可能在某一个空当说一下他的事情,甚至可能还要给自己打个电话,以示关切,会的,他们。他想。
司机是个爱说话的家伙,他不但把收音机开得很大,还叨叨咕咕地说着冰灯的事情。他说,用了好几百万搞冰灯,十几万平方米哦,你看了么?
他说,没看。在哪儿展啊?他知道这个城市有个冰灯展,他计划着要领孩子去看看,可事实上在哪他都不知道,他就是这么样的人。
司机说,世纪广场。这天真他妈要命。
他不知道司机把广场和天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他说,这天容易出车祸吗?
司机看了他一眼,好像对这个问话很反感。司机说,要我看。这样的天气才不容易出车祸呢,越是这天司机越是小心。车祸不分什么天。车祸就是该着。
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出车祸了。
司机说,是么?是开出租的,还是私家车?
他一下子茫然了,说:不知道。
司机不易察觉地笑了,开什么车你都不知道,还朋友呢?
他不确定地说,好像私家车吧。他又补充地说,他好像也不会开车啊。
司机说,哦,看来你们是很长时间没联系了。是吧?
他说,是的。
他发现自己已经逐渐地钻进了这个自己给自己编的圈套。他假设认识这个杨军。甚至这个杨军就是自己某一时期的朋友,他今天不幸出车祸了,不幸到什么程度他还不知道。他只是想去看看他,他摸了一下兜里,还行,还有几百块钱。他突然恍惚起来,我真的是要去看这个杨军么?
到了医院,他突然产生了错觉,医院倒好像是大街,入川流不息,他从未想过医院会有这么多人。他平时很少来医院,头疼脑热的就自己买点药,不知为什么,他对医院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恐惧。他问门口的导诊,刚才有一个车祸的人来抢救吗?
车祸?导诊的小姑娘说,有啊,有三个呢。都在急诊那边呢。
三个?他想。他怎么知道哪个是杨军呢?
这个莫名其妙的傍晚,这个莫名其妙的晚餐,这个莫名其妙的电话,加上这个莫名其妙的杨军。让一切都乱套了。
他顺着医院的走廊走向急诊室,不断地有人和他擦肩而过。急诊室门口乱糟糟的,的确是有两个人躺在活动病床上,他挨着个看了看。没有一个认识的,他捅了捅一个抻着脖子往里头望的人问,杨军呢?不料那个人翻愣了他一眼说,我他妈哪知道
谁是杨军,大夫,我们这个还有没有人管啊?
他看见这个人浑身是血,肯定是刚才抢救某个人了,他一眼看见那个移动病床上躺的是个女的。怪不得呢,心里正火着呢。
他知道这肯定不是杨军,另一个病床上更不用问了,是一个老年人,好像伤得也不重,在那里睁着眼睛哼哼。一个满脸横肉的年轻人说,你别他妈哼哼了,谁让你没事可哪儿走了。老年人立刻就不哼哼了。满脸横肉的人对另一个人说。你他妈别没事似的,扶着我爸点,给人撞这样,还鸡巴想踪,你他妈车咋开的?那个司机模样的人唯唯诺诺。恨不得给横肉跪下。哭叽叽地说,我眼看着老爷子往车底下钻,我根本就没有撞他,是他自己……横肉立刻火了,揪住司机说,你说什么?你还他妈这么说,现在是救人要紧,我不和你罗嗦,一会你要是还这么说,看我不揍扁了你。他冲司机恶狠狠地瞪了一下,司机立刻下意识地缩头。
他想,这个倒霉的家伙,撞人都不会撞,撞到这样一个无赖和凶神恶煞面前,指定是没好了。看来,正在屋里抢救的那个人肯定是杨军了。外面这么多人,他无法分清谁是谁的亲属,谁是谁的朋友,有了刚才的经历,他不太敢贸然相问了。他看着急诊室里的人进进出出,不一会,伤者被推了出来,好像是在这里进行了简单处置,然后被推向手术室。许多人和医护人员一起在推车,一个女的在旁边提着兜子跟着跑。他想,可能刚才打电话的人就是她,他已经看过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人了,可以确定,今天真的是搞错了,他真的不认识这个女人和这个叫杨军的人,这下他放心了,这个杨军的的确确和他的生活毫无关系,他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这时,酒桌上那边果然来电话了,一切好像都在按照他导演的进行。小陈已经有些酒意,问怎么样了,说桌上的人还等他呢。
他说,刚进手术室,正在抢救呢。
小陈说,那你还能回来不了?
他说,不行,我得在这里看看,挺严重的。
小陈说,那我们就不等你了。
他说,不用等了。
撂下电话,他觉得自己彻底松了一口气。他觉得医院太闷了,他走到外面,外面的雪依然很大。路灯下的雪花飞舞得十分醒目和耀眼。
一辆出租车嘎的一声停在他的面前,他没有犹豫就上了车。上车后,他掏出电话,按照那个号码拨了过去。响了半天才有人接,居然是个男的,他虽然觉得有些奇怪,还是忍不住他问了一句,杨军怎么样了?
那男的粗粗的声音说,什么杨军,你他妈是不是打错了?
他对着电话愣了愣,他想,也许真的是打错了。
雪依然很大,所有的车在路上都是慢慢地爬,蜗牛似的。这样的天打车十分困难,他站了半天才看到一辆空出租车,可是他刚一扬手,就被前面一对青年男女抢在了前面,那两个人嘻嘻哈哈搂抱着上了车。
他跺了跺脚,继续等。
他判断这雪是刚刚下,除了从地上落雪的程度,他更注重的是感觉,因为站在外面一点都不冷。一般地说,正在下雪的时候并不冷,气温是在落雪过程中逐渐降低的,和他走进酒店的时候相比,他现在倒是感觉还有一些微微的暖意呢,他知道这肯定是一种错觉。
他站在这里其实是有些焦急。刚才。他接到一个电话,说朋友杨军出车祸了,已经送到医院,正在抢救。他二话没说,穿上衣服就出来了。同桌的人问他出了什么事情,他说一个朋友出事了。大家都觉得有些扫兴,是有些扫兴,这样的天气,在一起喝喝酒是很幸福的事情,何况桌子上还有几个女人,都是刚刚熟悉的女人,他一直认为女人刚刚熟悉才有趣味,才能提起他的兴致,女人是需要探索的。可是,车祸是不管不顾的,这个杨军,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事……
凭他和杨军的关系他不能不去。估计杨军的女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把电话打给他。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不可能有太多的朋友,有的可能称之为朋友,你却只能和他在一起喝酒,喝酒的时候你甚至想拥抱他,可过了那阵你就想不起来他了。有的朋友,他在你的生活中电光石火地存在过,忽然消失了,他让你永远不能忘怀,你甚至有寻找他的愿望,可他就是永远地消失了,退出你的生活,在远远的地方注视你或者说是祝福你。也有的朋友,诸如杨军,他们之间就是一种比较绵长的关系,是男人和男人的那种关系,有点类似同性恋。拿他们自己的话讲,就是男男合作。但他们都不是同性恋,他的确遇到过一次有同性恋倾向的人。那个夏天,他在酒店稍稍喝多了点,酒店离他家不远。由于经常在那个酒店喝酒,老板也有些熟悉,就派一个服务生送他。说起来,在他的眼里那还是个小孩呢,一个个子高挑、瘦削的小男孩,他一直叔啊叔啊的和他说话,他就嗯嗯啊啊地答应着,可是快要到家的时候,那个小男孩的手突然就不老实起来,居然摸他的下体,他突然感到恶心和反感,一把推开了那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一脸惶惑地跑了,那小家伙回头回脑的表情,好像偷人东西被发现了,他在很久之后还感到恶心。他不知道真正的同性恋是什么样子,他主观地认为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有肌肤上的要求,恐怕不是同性恋也是有那个倾向。后来,再去那个饭店,他发现那个小男孩不见了,他没问老板,他想,他肯定也是不好意思了,这倒让他有些歉疚,一个举动就砸了人家的饭碗子,但他当时实在忍受不了。
杨军是性格很好的人,他的好脾气使他在生活中受益匪浅,他的朋友也很多,他觉得杨军很有意思。比如说生活是一个列车。杨军就永远是服务员的角色,他能够为任何人端茶倒水,把任何一个人都照顾得很好,所以杨军就积攒下了他人生之旅在各个时期积攒下来的朋友。他只是杨军这众多朋友中的一个。他是永远对杨军充满敬佩的人,他不是敬佩杨军处事方式,他敬佩杨军对人的真诚,在以往的日子里,他看到杨军所显示的力量,杨军曾经在他最最无助的时候,无私地帮助过他。
又一辆空车过来,亮着红色的灯,他再一次扬起了手,车停了。
他一上车,司机问,上哪?
他说中心医院。
司机在倒车,雨刷器唰唰响,前面一片迷蒙,雪越下越大,这是入冬以来这个城市下的头一场大雪。这种说法可能不确切。但他主观上是这么认为,因为前两场雪都没站在,阳光一出来就化掉了。天气预报上说,今天是零下二十五度。
杨军媳妇的这个电话让他立刻心乱如麻,他不知道杨军伤成什么样子。照理说,杨军不愿意摆弄汽车,他也不是对驾驭机器感兴趣的人,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在退休之后学起了驾驶。杨军一直生活在大家了解的状态中,但不知为什么,退休之后杨军反而不和大家联系了。
他感觉有些疲惫,在酒桌上他还没什么感觉,可是一上车他就感觉一阵疲惫。他在想杨军怎么样呢?杨军的确应该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他被分到了一个偏远的学校,原因很简单,他在学校搞对象,而那时学校是不允许搞对象的。这实际上是对他不听指导员劝导的一个惩罚。没办法,他那时木已成舟,他没有退路,只好置校方劝阻于不顾,毅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后来。是杨军
帮他运筹帷幄,摆脱了困境,居然从那么偏远:的学校,一下子调到了市教育局宣传科。再后来,经过他自己的努力就进了现在这个单位,一家报社。这些年,他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往来,比自己的亲属走动都频繁。因此,他很担心杨军这次车祸的结果。
他给杨军的一个朋友打电话,他说:杨军出车祸了。
对方说,是吗?真他妈的不巧,我在广州呢。
广州?他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广州没下雪吧?
对方说,开什么玩笑,这里阳光灿烂,热得要命。
他想象不出现在广州是什么样子,他还得回到现实中来。
他顺手又拨了个电话,这也是杨军的酒友,他对那个酒友说,杨军出车祸了。
酒友说,妈的,咋这么不巧,我在桦甸呢,早晨才过来,你替我看看吧。
他想真是不巧,这么多不巧都赶到一块了。
他说,桦甸下雪了么?
下雪?酒友说,市里下雪啦?大不大啊?
他说,挺大的。要不杨军能出车祸么?
酒友说,这个老杨,他哪会开什么车啊?你不是搞错了吧?
他说,我也寻思呢,不过刚才是他老婆打来的电话。
对方立刻叫了起来,哎,哥们,你疯了吧,他老婆去年就死了,乳腺癌啊。
他一下子愣住了,这个他还真不知道。他说,是真的吗?
什么真的假的,你多长时间没看到他了?
他想了想,可不是咋的,有两年没见到杨军了。他这才想起,那个电话的确可疑,一听是杨军他连问都没问清楚,就着急忙慌地上车了
他对司机说,停,停。司机莫名其妙。
他说,往回开。
司机说,怎么了。
他说,我他妈搞错了,那个出车祸的好像不是我朋友。
真他妈冷,司机说。
他一坐上出租车,就感觉碰上了一个饶舌的家伙。他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出租车司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见过。有的一上车他(她)就要和你搭讪,他不看你的脸色,尽管你一声不吭,他依然喋喋不休,自说白话,不管你愿意听不愿意听。有的一路都不和你说话,绷着脸,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你问一句,他勉强应付,不瞅你,好像不耐烦似的。坐在这样的车里你莫名地紧张,甚至想马上就下车。还有的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不多说一个字,惜话如金。这样的,一般脸上的表情都是平和的,热情的,甚至是快乐的,这样的司机讨人喜欢。他虽然不怎么喜欢饶舌的人,但他能理解,出租车每天都是和陌生人打交道,如果一点也不愿意交流,恐怕是会憋疯的。这样的人,无非是交流的愿望强烈一些罢了。
司机说,去看冰灯了吗?
他说,没有。
司机说,我听说这次政府可下老大功夫了。投了好几百万,冰灯面积有十万平米,乖乖,这他妈的不相当于盖房子么?
他还沉浸在刚才的电话里,没太拔出来。他没搭茬,他感觉司机说的和此刻他想的事情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司机说,要是有那钱投在路上,比啥都强,你瞧这路坑坑包包的。哎,我们是走解放路,还是走吉林大街?
他说,怎么走都行。
好嘞。司机说。
前面黄灯。司机没敢往前抢,把车停了下来,他拍着方向盘说,他妈的,这鬼天,车都不愿意动弹。同样给油,就是他妈的不走。
他有了点兴致,说:呵呵,车也像人呢。
司机说,可不是咋的。
司机像遇到了知音,说这车可不就是个活物么,你要拿他当人看待,它就好好给你干,你要是不屌它,呵呵,它就给你使性子,耍脾气。
司机说,你说现在这人这车啊,都他妈娇贵,才零下二十多度就受不了了。我们小时候,四十几度都有,那时候车咋跑了的?
他说,那时候才有几台车,大街上一天都看不到。再说,那时候都是解放车,抗造。
他想起小时候寒冷的冬天,那才叫冬天呢,他们戴着棉帽子,他们戴着手闷子,他们穿着大头鞋或者那种棉水乌拉,他们还要戴着口罩,把防寒武装到牙齿。滴水成冰肯定是那时候创造的词汇,他相信再过几年,这个词就会消亡,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夸张。他最近在网络上看了一部叫做《山楂树之恋》的长篇小说,很真挚,给人的感觉就是作者的回忆录,但是据说那些九零后们看了之后就大加挞伐,说简直是不可思议,是虚伪的爱情。他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虽然赶上了一个尾声,但他认为故事绝对是真实的,只不过是艺术性差了些,就此他还和比他年长的一位老兄做过争论。他们的观点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对文本的要求和解读不一样。他们都承认作品的真实,其实这就可以了,至今为止真实记录那段历史的有几人,很多人都是采取了回避的状态,中国的文人们大都愿意回避经历的痛苦,而制造或者夸大自己认为是痛苦的痛苦。还有一点他们不太一致。他认为和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那些人辩论他们没有的经历,简直是荒唐。
雪还在下着。是那种飘飘忽忽的雪,很大的雪花,是书里经常说的鹅毛大雪。
他知道这样的天气在北方已经很少了,他奇怪南方反而经常是大雪泡天,大自然最神奇的地方莫过于让人类失算,所有的预测都成为笑柄。比如地震,比如洪水,任何一次的预测都让我们对大自然的报复更加恐怖,对自己的能力更加失望。我们曾经对大自然有多么强烈的掌控和凌驾意识啊,事实上,即使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大自然都是个未知数。上了年龄以后,他迷上了一些科技知识。这让他对自然中许多曾经不以为然的生物充满了敬佩和崇敬,比如蟑螂,比如老鼠。他过去从来没有认为这些东西有生存的理由,他甚至认为这些东西是早晚要被人类灭绝的。可是后来他知道,它们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来到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比人类都长,只是人类自以为是,从来都把它们摆在从属的位置上,按照人类自己的想法去看待和划分它们。他还在网上看到,有人恐怖地预测,将来是昆虫的时代,若干个世纪后某一天人类已经消失,那些被人类随时就能碾死,就能生杀予夺的虫类,居然要在街上大摇大摆地发号司令……他虽然也觉得这是耸人听闻,也不免觉得很有可能,因为人类肯定会自己埋葬自己。
司机说,到了。
他说。到哪了?
医院啊,你不是说医院吗?
他说,我什么时候说上医院了?
司机诧然,嗨,你这个人哎,你上车就跟我说去中心医院,我还会听错?
他说,不对吧,我还没有说去什么地方,因为我还没想好去什么地方。一上车好像就是你说话了的。你唯一问过我是走解放路还是走吉林大街,对吧?
嗯?司机挠着脑袋说,是我糊涂了?哦,他想起来了。说:我刚才送一个人,他说去医院,说是他的一个朋友出车祸了。呵呵,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你去哪里?
他说,回家。
他说了个小区的名字,司机掉过头朝那个小区方向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