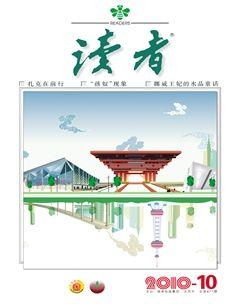永恒的爱
万科·萨利姆
一
他们都围在她的病床前,神情忧郁。最后一刻终于来了。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她都曾经扮演过那么重要的角色——母亲、姨妈、祖母、朋友和表姐。是她使他们每个人的生命变得与众不同。现在他们都来了,满怀忧伤,因为她就要永远地离开他们,留下一个无法填补的空缺。
她吃力地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把周围的人瞅了一遍。她还有那么多话要说,那么多事要做,多年来的记忆潮水般地涌来。她看到儿子站在面前,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结实强壮的男子汉,一位有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可是仿佛昨天他还是一个淘气好动的小男孩,吵吵闹闹地到处乱跑,跌倒了就爬起来,嘴角带着顽皮的笑,就像正在角落里玩耍的他的小女儿一样。
然后她看到的是女儿,现在女儿也已经当妈妈了。她曾经是个很难对付的丫头,动辄发脾气,摔盘子,又哭又闹。当然现在她不能由着性子来了,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调皮捣蛋的儿子。唉,真难为她了。
她还看到自己的好友在角落里默默地站着,神情悲痛。过去有多少时光她们是在一起度过的啊!早在少女时代她们就结识了,那时屋子里还没有这帮孩子。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还有她的外甥——一个可爱的年轻人。他时而紧张地低头看表,可能是担心午休时间快结束了。他一直是个有责任感的孩子。
她试图张口说话,想告诉儿子这算不了什么,要像她养育他那样把孙女养大。她还想叮嘱女儿做事要专注,要有责任心。她想把只顾玩耍的孙辈们喊过来,再抱抱他们。但是她已经没有力气做这些事情了,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咕噜声。外甥女抓住她那软弱无力、布满皱纹的手抚摩着。
她又闭上了眼睛,心想:什么也救不了自己了,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这些亲人花几天时间哀悼她之后,他们的生活还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就像她从来就没来过这个世界上一样。人生真可悲啊!她感到没有丝毫力气。外甥女还在揉她的手,这让她感到特别舒服,不由得有了睡意。我该知足了,她想,我毕竟来过这个世界,把孩子们都养育成人,他们很优秀。她还想到了好友。这让她又想起年轻时代,那是多么令人怀念的光阴啊,谁能想象她这样一个弱小的老太太过去曾做过那些疯狂的事情!想到这里,她在心里笑了。好了,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现在该休息了……
二
一个神情恍惚的陌生老人突然来访,打破了病房的沉默。他敲了敲门,拖着沉重的步子挪了进来,停下来环顾一周,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唐突,说:“对……对不起,这位病人是……”他说出了她的名字。
她的疲倦的亲友们相互看了看,都露出困惑的表情。她儿子正要走上前去探问,她的好友发话了:“是的。”接着对她儿子点点头,示意他这没有关系。
儿子退回到原来的位置,虽然心里仍然有疑问,但看在阿姨的分上,没有去阻止老人。
“请问,我可以……看看她吗?”老人几乎在哀求。
儿子看了看阿姨,她又点头同意了。
众人很不情愿地慢慢给老人让出一条道,老人一步一挪地走到病床前。一个年轻人主动给他让了一个座。
老人双手扶着扶手椅的两边,动作迟缓地坐下来,轻轻地叹了口气。
自从进来之后他还是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她。他好像忽然间僵住了,停止了一切动作,甚至包括呼吸。他的眼神很空洞,灵魂似乎被脑海中某个遥远的记忆攫住了,但是他又始终在盯着躺在病床上的她。他的眼皮不时地眨一下,流露出的眼神愈加悲哀、沉重和痛苦。他断断续续地咕哝着些什么,声音很低,外人几乎听不见。
他就保持着那个姿势坐着,一动不动,直直地盯着她,始终没有往别处看。他的面容似乎在讲述一个哀伤的故事,那种哀伤连他自己也无法理解。他陷入自己的内心世界里,然而又不时地把注意力聚集在她身上,好像她就是他一直寻觅的能够让他回到这个现实世界的唯一牵引力。
老人看上去好像要永远坐下去,但是最终还是把视线挪开了。人们发现老人的眼睛又红又肿。他把手伸进衣兜里,哆哆嗦嗦地掏出一张纸和一支笔,颤抖地写着什么。他不时地停下笔抬头看看她,好像这样才能进入她要带他进入的那个世界,然后又接着写。终于写完了,他把笔放进衣兜,小心翼翼地把纸条折叠起来,抬起头茫然若失地看了看众人,用苍老而沙哑的嗓音问道:“我可以把这个纸条交给她吗?”
有人开始怀疑他是否精神不正常,正欲反对,她的好友又出面了。
“可以。你该走了。”她语气坚决地说。
“我知道,”他无精打采地说,“我是该走了。”他低头看着被他紧张地捏在手里的纸条。这与其说是一个回应,不如说是自言自语。然后他就吃力地站起来,慢吞吞地挪到她的外甥女面前,因为她的手仍然被外甥女握着。
“别担心,我不会打扰她的。”他的声音在发颤。
他温柔地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把她的手指掰开。这时他的脸又颤抖起来,好像内心正经历着一场暴风雨。他的双眼红红的,但是很专注,很警觉。他的苍老的嘴唇似乎带着喜悦的微笑。终于他非常小心而又笨拙地把纸条塞进她的掌心。整个过程中的每一秒他都好像在用心回味,因为他的动作缓慢而从容,所以花费的每一秒似乎都是一个永恒。
他的眼神又变得空洞了,尽管她的手指还握在他手里。他脸上原先的那种近乎微笑的表情暂时被一种严肃而凝重的思索的表情所代替。接着,又现出一种万千思绪涌上心头的表情。当他的目光再一次聚集在她身上并且因此重回到现实中时,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痛苦。他很快合上她那只攥着纸条的手,不再像刚才打开它时那么从容。他终于松开了她的手,强迫自己转过身子,好像非常不情愿地把自己从此情此景中抽离。他穿过人群,目标明确地向门口走去,脚步显得比刚才轻松些,脸上呈现出坚定的表情。就要走到门边时,他突然转过身来,面向还没回过神来的众人。
“谢谢你们,”他用低沉喑哑的嗓音说,“你们都是好人,非常好的人。”
然后他转向她的好友,说:“谢谢你。”说完就走了出去,顺手把门带上了。
三
她在一阵骚动中醒来,发现儿子一副烦躁不安的样子,儿媳正在安慰他。外甥女仍旧坐在床边,但是不再抚摩她的手,一脸的困惑。另一边坐着她的女儿,似乎对什么感到十分有趣。
“怎么了?”她奇怪地看着女儿,眼神在问。
“一个陌生人来了,把一张纸条交给了你。”女儿说。
“是什么?”
女儿又读懂了她的眼神,充满好奇地读起纸条上的文字来:
阳光
太阳依旧需要升起,
花兒依旧需要开放,
它们仍然在等待,
等待你早晨慵懒的微笑。
虽然我现在衰老不堪,
你送的礼物却依旧新鲜,
它照耀着我的一生,
就像你早晨慵懒的微笑。
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停止过,
请不要离开……
这时她听到小外孙在后面重复道:“啊,阳光!”
“把纸条给我。”
这句话让他们吓了一跳,因为她已经好几天没有开口说话了。她的声音虽然微弱,但是听起来既像一个命令,又像一个请求,让人难以拒绝。纸条被放进了她的手里,她带着一种非同寻常的热切紧紧地抓着它。
“他来了?”她用微弱的声音问正低着头的好友。
“是的。”她轻轻地回答,仍然没有抬头。
她不再说话,目光注视着前方,眼睛里闪烁着已经消失多年的年轻的光芒。
这时又听到她那正在旁边玩玩具的小外孙笑嘻嘻地喊了一声:“阳光!”
而就在此时,街道某处有一个年迈的老人正艰难地走着,他边走边旁若无人地啜泣着,泪水从他那肿胀的眼睛里尽情地滑落。
(柳怀哲摘自《译林》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