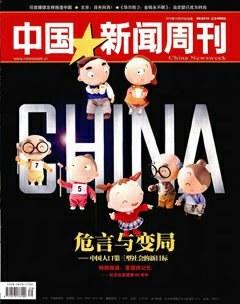借米勒的眼睛审视我们自己
陈晓萍
作为一名剧作家,阿瑟·米勒有着高度的文化和政治敏感。他两次来到中国, 1978年,作为中国对外友协邀请的客人,米勒以游客的身份随旅游团第一次进入中国;第二次是1983年,米勒获北京人艺的邀请,来华为人艺导演他的作品《推销员之死》。
米勒的两次中国之行,正值中国拨乱反正,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时候。米勒热切地想探究这片古老的东方国土上曾经发生过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
1978年,米勒应邀观看了话剧《蔡文姬》,并被要求点评此剧。他批评道:“剧作家在创作这个剧本时犯了个错误,是初学者通常容易犯的。”要知道,米勒批评的剧作家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而且当时是1978年,场面极为尴尬。英若诚在自传中记录了这件事,并写道:谢天谢地郭沫若当时不在场,他几个月前已经去世了。
在人艺排练《推销员之死》的一个半月时间里,米勒随身带着录音机,录下工作中的对话,于是有了这本《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直到最近,这本书才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排练之余,米勒拜访中国的作家朋友,包括杨宪益、华君武、张洁等,还和中国的戏剧同行座谈。他不断地提问、观察,即便在排练时的交流,他问演员对角色的理解,最终也是想弄明白,中国人对曾经的伤痛有何感受。
把《推销员之死》搬上人艺舞台,主要归功于当时的人艺院长曹禺和人艺导演兼演员英若诚。曹禺和英若诚都有着与美国相关的个人经历,重回舞台后,两人急于想把二战后的世界戏剧介绍给中国的观众。1982年,英若诚借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和米勒探讨了为人艺选择一台米勒的话剧,英若诚看中的是《推销员之死》,而米勒建议的是自己的另一部话剧《严峻的考验》。1978年访问中国时,米勒听到了许多中国朋友文革中受迫害的故事。英若诚对米勒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英若诚认为,如果只是以不公正的迫害为主题,没有多大意思。当时的中国,“伤痕文学”正当其时,文学作品大多揭露“文革”中人们遭受到的迫害和苦难,所以,在英若诚看来,《严峻的考验》并没有什么新意,而《推销员之死》却可以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1983年,对于中国演员来说,只能是在想象中完成自己对美国的理解。那么,如何能演好美国人?米勒对他们说,答案再简单不过,就是坚决不要尝试扮演美国人。米勒认为,要让中国观众接受这部美国话剧,只有让中国观众在角色中发现自己。
就在演员们努力寻找人性的共同点时,媒体却是以政治的眼光来解读这件事。
驻京的外国媒体提出了采访要求,他们提出的问题是:选择这出戏是不是一种批判美国社会的宣传?记者们甚至问到:这出戏会公演吗?戏票是公开出售还是只发给单位?而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则说:对《推销员之死》“特别热心的观众”——也就是反对美国的人——将发现,他们很难欣赏“这部杰作”,因为“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没有一个推销员”。时至今日,中美之间的政治误读依然存在,因为某些时候,某些事情,政治解读会显得高明和深刻。
这期间,中美之间发生了一件政治事件——胡娜事件,19岁的中国网球运动员滞留美国不归,而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宣布说,他本人愿意收养胡娜。这导致中国政府表示要取消一切与美国的文化体育合作。而《推销员之死》则如期售票公演并大获成功,掌声经久不息,观众涌向舞台。此后,美国的“推销员”留在人艺,而米勒也成为一个符号留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