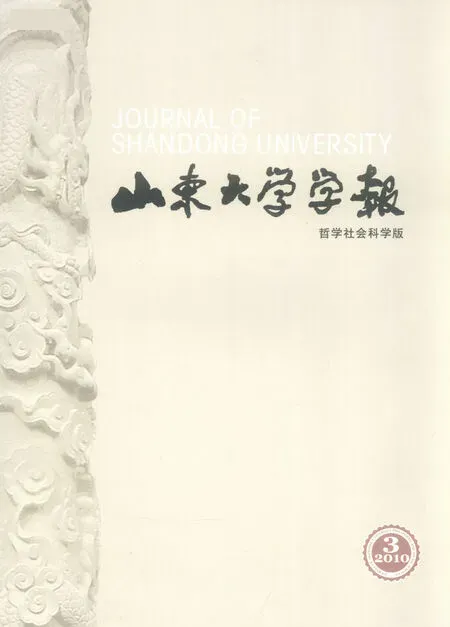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郭熙保 习明明
一、引言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发展经济学研究在各个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素福和斯蒂格利茨(Yusuf and Stiglitz,2003)针对发展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提出发展经济学已经解决的 7个方面的问题,尽管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小争议,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常规科学”领域和“共同智慧”的一部分。这 7个问题是:(1)什么是增长的源泉?(2)宏观稳定是否重要以及如何才能保持宏观稳定?(3)发展中国家应当实行贸易自由化吗?(4)产权究竟有多重要?(5)减贫是增长和资本积累的功能还是贫困网的功能?(6)发展中国家能够推迟或低估环境问题吗?(7)国家应当怎样严格管理和调控发展①赛义德·尤素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展问题:已解决的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见杰拉尔德·迈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编:《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 162-191页。。
不过,发展经济学家仍然面临许多挑战。随着全球化、区域化、环境退化、人口结构变化、食品与饮用水安全、城市化等趋势的发展变化,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尤素福和斯蒂格利茨(Yusuf and Stiglitz,2003)将其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多层治理与调控问题,要解决好当前出现的治理无力的问题,必须至少处理 5个问题,即参与政治、组织能力、权力下放、不平等和城市治理;另一类是与管理资源——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有关的问题,例如关于跨国移民、老龄化和资本供给、管理全球公共问题、食品与饮水安全问题等的研究。
阿德尔曼 (Adelman,2003)对发展经济学过去研究方法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主要存在 3个误区:(1)不发达只有一个单一的原因(无论其原因是低水平的有形资本、缺少企业家、错误的相对价格、国际贸易壁垒、政府的过度干预、人力资本水平不足,还是政府效率低下);(2)一个单一的标准足以评价发展绩效; (3)发展是一个对数线性过程。阿德尔曼认为,应该把经济发展看成是一个高度多面的、非线性的、路径依赖的、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互动方式的系统性转换,而这种转换又要求政策和制度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他提出了 4个命题:第一,发展过程绝非高度线性的;第二,发展道路不是独一无二的;
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慕克吉 (Mookherjee,D.2007)将其划分为 4个阶段:(1)对相关现象的描述性分析;(2)相关理论的构建,包括推导出可能预测到的潜在涵义;(3)对理论的验证和估计,并且可能修改或替换原有的理论,这一过程可以循环往复;(4)把实证检验最成功的理论应用在预测和政策评估上②迪利普·慕克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太少》,《比较》2007年第 28期。。根据这个划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正处于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对此,巴丹(Bardhan,P.2007)持相同意见,他认为当前的研究过分地关注量化分析,理论的研究还不够。例如:不完善的要素市场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如何随人口和技术环境而变化,经济过程与社会制度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如何才能超越现有的寡头垄断局部均衡模型,为寡头垄断经济中的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创建一个可行的理论;如何创建一个能将垂直产品差异、异质厂商、规模经济和国际竞争融为一体的理论;跳出低水平均衡这个过渡过程的动态机制有什么性质,等等。
发展经济学近十年的文献,大部分都侧重于实证研究,注重随机分析和工具变量的选择,如霍尔和琼斯(Hall and Jones,1999)③Hall,R.E.,&Jones,C.I.,W 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M uchM oreOutput PerW orker Than Other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114(1),83-116.,阿西莫格卢、约翰逊和罗宾逊 (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2005)等等④Acemoglu,Daron;Johnson,Simon and Robinson,James.The ColonialOrigins of Comparative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1(5),pp.1369-401.,巴苏(Basu,K.2007)将其称为“新经验主义发展经济学 (The New Empir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⑤考希克·巴苏:《新实证发展经济学:对其哲学基础的评论》,《比较》2007年第 28期。。以上三位教授都认为经验研究过多,而理论研究过少。但是也有很多学者持相反意见,支持经验研究。例如,班纳吉(Banerjee,A.2007)认为,当今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不是理论太少,而是理论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方向,因为实证研究者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都是来自于以前的理论,我们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反对实证研究,而应该考虑如何将现有的对问题的解释转化为理论,因此实证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有一天,这套新的理论会被定义为“新新发展经济学”⑥阿比吉特·班纳吉:《新发展经济学及其理论挑战》,《比较》2007年第 28期。。
理论和实证孰重孰轻?这个问题恐怕永远都不会有结论。不可否认,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自诞生以来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尤其是近二三十年,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发展,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受到了学术界前所未有的热捧。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后华盛顿共识”之后的“新发展经济学”,也就是发展经济学最近十年的发展概况。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对之前相关的文献做一些必要且简单的回顾。
二、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
法因 (Fine,2006)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出现和繁荣是对 1930年代“大萧条”和“萨伊定律”的反思,凯恩斯理论缩短了经济学与现实之间的距离⑦Fine,Ben,New Growth Theory:M ore problem than solution,in Jomo K.S.and Fine,Ben.(Eds.),The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London and New York:Zed Books.2006,pp.68-86.。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出现,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因为新古典理论假定个人偏好、禀赋和技术都是不变的。与此同时,很多其他的非主流经济学也得到了发展,例如新制度主义,新马克思主义。1940年代之后,东亚、南亚、东南亚以及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纷纷获得了独立,并积极寻求经济发展之路。发展经济学的出现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探讨的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稳态均衡增长和边际分析,新古典假设与市场和制度极度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格格不入。于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非主流经济学,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例如,罗森斯坦 -罗丹 (P. Rosenstein-Rodan)可能是最激进地偏离主流经济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G.Nurkse)则利用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阿林·杨(Allyn Young)的分工理论,强调与报酬递增有关的收入效应的作用。发展经济学的一系列政府干预政策如进口替代、贸易保护、出口导向、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等,在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然而,好景不长。19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涨”危机使得凯恩斯主义神话破灭,政府干预理论也受到了激烈的批评。1980年代末,拉美国家因陷入债务危机而急需进行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英国经济学家、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顾问约翰·威廉姆逊(John W illiamson)于 1989年在其《拉美政策改革的进展》一书中,整理出他认为当时华盛顿的政策圈(包括美国政府、国际经济组织如 IMF等)主张拉丁美洲国家应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包括与上述机构所达成的十点共识:(1)约束财政;(2)将公共支出转移到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上;(3)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和拓展税基;(4)利率自由化;(5)实行竞争汇率;(6)贸易自由化;(7) FD I自由化;(8)私有化;(9)放松管制,消除企业自由进入以及竞争的障碍;(10)保护产权。由于会议召开和国际组织都在华盛顿,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①Waeyenberge,E.V.,From Washington to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Illusions of Development,in Jomo K.S.and Fine,Ben,ed.,TheNew Development Econom ics:After theWashington Consensus,London and New York:Zed Books.2006,pp.21-45.。“华盛顿共识”反对发展经济学所提出的不完全竞争和政府干预观点,主张经济自由和个人行为的最优均衡,强调将政府干预减到最小。
然而,“华盛顿共识”在诸多方面的不切实际,以及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在经济上的失败,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根本没有增长,即使是被 IMF评为 A+的阿根廷也未能幸免于难。维因伯格 (Waeyenberge,2006)认为“华盛顿共识”的观点过于狭隘,并且只有在完美市场的条件下才能成立②Waeyenberge,E.V.,From W ashington to Post-W ashington Consensus:Illusions of Development,in Jomo K.S.and Fine,Ben,ed.,TheNew Development Econom ics:After theW ashington Consensus,London and New York:Zed Books.2006,pp.21-45.。阿罗 -迪布鲁(Arrow-Debreu)的一般均衡理论指出,给定个人偏好、初始禀赋和技术不变,竞争市场只有在不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自然垄断的条件下才会产生福利最大化或帕累托最优结果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而且每一个帕累托最优结果都可以通过市场达到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③关于福利经济学第一、第二定理,具体可以参考马斯 -克莱尔、温斯顿和格林的《微观经济理论》。。这就意味着市场对收入分配是中性的,政府的作用限定于收入分配和纠正市场失灵,增长的主要约束就是资本短缺,这也是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主要结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寻租与政治腐败、垄断与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共部门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crowds out)等,市场并不能有效解决增长和收入分配问题。《世界发展报告》(1989)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增长并没有解决贫困问题。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8)认为,“华盛顿共识”从最好的方面来看它是不完善的,从最坏的方面来看它是误导的④Stiglitz,J.,M 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moving towards the post-W ashington Consensus.W iderAnnualLecture,Helsinki,1998 January.。市场自由固然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但政治腐败更容易造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
尽管“华盛顿共识”遭遇各种困境,但并没有因此而消亡,支持“华盛顿共识”的学者对其在拉美和非洲国家的失败提出各种辩护。一般而言有 4种⑤丹尼·罗德里克:《诊断法:构建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比较》2007年第 33期。:(1)拉美和非洲国家没有实施充分的改革,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2)改革的收益还未充分体现,只要坚持最后必然成功;(3)这些国家的失败主要是源于糟糕的外部环境,例如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速度减缓;(4)东亚国家的成功实际上也遵循了“华盛顿共识”的建议,例如中国已经走向市场,并试图融入世界经济,印度已经实现自由化。
但是,这些理由都无法令人真正信服。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观点,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主要是因为缺乏资本。如果新古典增长模型是正确的话,那么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回报率就应该远高于发达国家,从而资本会源源不断地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世界各国的经济也将趋同。然而直到 20世纪末,这种流向仍然受到诸多限制。即便是 20世纪 90年代中期,资金也是以有限方式流向东亚增长最快的几个国家,大部分国家都面临严重的信贷约束问题。霍尔和琼斯(Hall and Jones,1999)的经验分析表明,最富的 5个国家劳均收入的几何平均是最穷 5个国家的31.7倍,而资本和劳动能够解释的只有2.2倍或1.8倍①Hall,R.E.,&Jones,C.I.,W 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M uchM oreOutput PerW orker Than Other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114(1),83-116.。也就是说,物质资本和教育只能解释跨国的收入差距很小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是由制度和政府政策决定的,即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因为它们构成了人们投资、创新、交流、生产和服务的经济环境。德兰亚加拉和法因(Deraniyagala and Fine,2006)认为,自由贸易从来都不是发展的问题和答案,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含糊和复杂的②Deraniyagala,S.and Fine,B.,Kicking away the logic:free trade is neither the question nor the answer for development,in Jomo K.S.and Fine, Ben,ed.,The New Development Econom ics:After theW ashington Consensus,London and New York:Zed Books.2006,pp 21-45.。现实经济的发展与“华盛顿共识”初衷或新古典理论的背离,引起了学术界大量的研究和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
斯蒂格利茨(1998)从“市场和制度失灵”的角度来反对“华盛顿共识”,他的“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被称为新发展经济学(the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③Stiglitz,J.,M 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moving towards the post-W ashington Consensus.W iderAnnualLecture,Helsinki,1998 January.。新发展经济学与旧发展经济学相比,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1)新发展经济学没有沿袭旧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思路,而是通过市场不完善的角度,试图回到古典的和统计的方法上,同时在研究发展的属性时它包括并拓展了主流经济学的方法。(2)新发展经济学继续以最优化的分析方法为基础,而没有考虑社会及历史结构,而后者正是古典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④Fine,Ben..Introduction,in Jomo K.S.and Fine,Ben,ed.,The New Development Econom ics:After the W ashington Consensus,London and New York:Zed Books.2006,pp.xv-xxi.。(3)新发展经济学大量采用新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变化和内生制度分析,特别是对人力资本的引进使得新发展经济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4)新发展经济学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例如,芒什 (Munshi,2008)从信息网络的角度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技术采用、生育率转移、教育与健康投资行为⑤Munshi,K.,Info rmation networks in dynam ic agrarian econom ies.In:Schultz,T.P.,StraussJ.(Eds.),Handbook of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4.Elsevier,Amsterdam.2008,Chapter 47.pp.3085-3113.。霍夫和斯蒂格利茨 (Hoff and Stiglitz,2003)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协调失灵、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⑥卡拉·霍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现代经济理论与发展》,见杰拉尔德·迈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编:《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 277-327页。。这些研究都背离了新古典主义假设,而且个人行为的扭曲最终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而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单一均衡。此外,他们认为不论是分配、技术、偏好和政策选择,还是制度,都应该是内生的。他们批判了新古典主义关于政府失灵的假定,他们认为政府并不总是失灵的,即使失灵也有程度的高低之分,作为政策决策者,需要一个表述清晰的理论,它能够解释政府为什么和在什么情况下失灵。
如果制度是内生的,那么为什么机能失调的制度能够长期存在?为什么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别那么大?制度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又是什么因素决定制度?阿西莫格罗等 (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 2005,以下简称AJR)区分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他们认为经济制度只有在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才会有利于经济增长:(1)政治制度在分配权力时倾向于那些以产权保护为广泛基础 (broadbased)的群体;(2)政治制度能很好地约束掌权者 (power-holders)的行为;(3)政治制度使得掌权者只能获得相对少的租金⑦Acemoglu,Daron;Johnson,Simon and Robinson,James.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In:Aghion,P.,Durlauf, S.N.(Eds.),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vol.1A.Elsevier,Amsterdam,2005,Chapter 6.。其所谓的经济制度主要是产权结构和市场的出现与完善,他们认为经济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影响社会的经济激励,将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部门,它决定谁将获得利润、收益以及剩余控制权。根据他们的观点,拥有能够促进要素积累、创新和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制度的国家将更加繁荣。在其研究以及众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中,经济制度是内生的,至少部分地由社会决定或由社会的一部分决定,因而研究为什么某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更穷,实际上就相当于研究为什么某些社会拥有更糟的经济制度。
尽管传统的关于制度或政治经济学的文献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能回答,既然制度是重要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制度,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制度?AJR(2005)在其研究中试图解答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制度是内生的,并由社会中的集体选择行为决定。但是不同群体对不同经济制度的偏好不一样,在选择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利益冲突,此时,不同群体的政治权力的大小就成为决定经济制度的最终因素。由于存在承诺问题(commitment problem),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无法协调,因为掌握政权的人不会承诺不使用政治权力来制定对他们最有利的资源分配,即使他们承诺了也是不可信的。只有群体自身掌握政治权力,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自己的利益。此外,政治权力的分配也是内生的,AJR将政治权力进一步划分为法理上(de jure)的权力与事实上(de facto)的权力。政治制度决定法理上的权力,而事实上的权力则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群体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能力;二是群体可利用的资源(即资源分配)。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当期法理上的权力和事实上的权力又反过来影响当期的经济制度和下期的政治制度,当期的经济制度又进一步影响当期的经济行为和下期的资源分配。
巴丹 (Bardhan,P.2003)从分配冲突的角度解释了发展中国家机能失调的制度为什么能长期存在,以及为什么集体行动会遭遇阻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关于变革成本的分担问题,即搭便车问题;第二,讨价还价问题,即关于分享变革潜在利益的争执。当提高生产率的制度变革中存在得益者和受损者时,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尖锐①普拉纳布·巴丹:《分配冲突、集体行动与制度经济学》,见杰拉尔德·迈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主编:《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 192-206页。。例如,当潜在的受损者的损失比较集中、比较明显,而潜在的得益者得到的好处比较分散和不确定时,制度变革和集体行动将变得更加困难。通常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办法是,国家发行长期债券来收买受损者,并且通过向得益者征税来使自身得到补偿。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的征税能力及其控制通货膨胀的可信性非常有限,证券市场也很薄弱。潜在的受损者还可能担心:在承诺没有得到遵守的情况下,放弃一个现存的制度可能会使他们无法再对未来的政府施加压力。因此,从得益者可能补偿受损者的意义上讲,受损者仍然会抵制可以带来潜在收益的帕累托改进的变革。
由于市场和制度失灵,“后华盛顿共识”主张政府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进行干预,但并不意味着其政策建议对于所有国家都是普遍适用的,一个国家有效的制度和政策移植到另一个国家未必管用。经济学尚未提供足够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以就特定领域的政策达成广泛共识,但有一种可以普遍接受的观点就是:各个国家可以自己试验,自己判断,去探索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策略。罗德里克 (Rodrik,2007)认为,贫困的国家之所以贫困,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缺乏、资本和资源使用效率低、制度落后、财政和货币政策波动、对投资和采用新技术的激励不足、信用度低、与世界市场隔绝等。“华盛顿共识”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它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可能是最关键的、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②丹尼·罗德里克:《诊断法:构建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比较》2007年第 33期。。因此,他提出“诊断法”作为构建经济增长战略的一种可行方法:首先,要进行诊断性分析以找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约束,他认为所有的病症都会显示出不同的、可供诊断的信号,或是产生经济变量不同类型的共振;其次,需要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政策设计,以恰当地解决已经找到的约束条件;最后,将诊断分析的过程和政策反馈制度化,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三、增长与发展理论的融合
很多人认为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是同一个学科,至少应该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但是直到 1980年代,这两个学科就像两个远房亲戚,互不来往,而且有时甚至还是相互对立的。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新古典增长模型强调的是稳态增长、规模收益不变和无弹性劳动供给等,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多重均衡、规模收益递增和有弹性的劳动供给等;其次,从研究对象来看,新古典增长理论研究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发展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再次,新古典增长理论关注的稳态的分析,所有经济变量按照固定的比率增长,而发展经济学关注的是非均衡状态,以及从一个稳态到另一个稳态的过渡;最后,新古典增长理论研究的是单一部门单一产品模型,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多部门多产品模型,或至少是两个部门,使用不同的技术。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结论显然没有得到发展中国家经验的支持,因为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不发达国家因缺乏资本,回报率高于发达国家,从而资本会源源不断地从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然而直到上个世纪末这种流向仍然非常有限,从而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研究,也终因面临种种窘境而逐渐进入停止状态。
1980年代中期之后,在增长理论沉寂了 20年之后,增长经济学再次变成了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热点课题。这种研究工作朝两个方向展开。一批学者试图修改和扩展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而保留规模报酬不变和外生技术进步这些基本假定。例如,曼昆、罗默和韦尔(Mankiw,Romer&Weil,1992,以下简称MRW),对内生增长模型的物质资本规模报酬递增或不变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将人力资本积累作为一个额外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结论表明即便维持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模型仍然能够足以解释跨国收入差距①Mankiw,N.Gregory;Romer,David andWeil,DavidN.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 ic Growth.TheQuarterlyJournalof Economics, 1992,107(2),pp.407-37.。由于假定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模型预测穷国的要素边际报酬高于富国,但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什么没有从富国流向穷国,MRW提出的一个解释是:穷国存在两种投资,一种是公共投资,一种是私人投资,公共投资收益低,私人投资收益高,但是私人不愿意投资,因为他们面临各种金融约束,并且也有政治风险,所以尽管穷国的要素边际收益高于富国,富国的资本也不会流向穷国。这一派经济学家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维护者。
另一批学者则想通过引入规模报酬递增并把技术变化模型化,从根本上否定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结论,这一派理论被称之为新增长理论。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复兴的增长经济学,与上世纪 50年代兴起的传统增长经济学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或者说一个最大的新奇之处是,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解释从不发达到发达的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例如加洛 (Galor,2005)用统一增长模型解释人类近 2000年的增长历史②Galor,O.,From Stagnation to Growth:Unified Growth Theory.In:Aghion,P.,Durlauf,S.N.(Eds.),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vol. 1A.Elsevier,Amsterdam.2005,Chapter 4.。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穷,一些国家的经济为什么比另一些国家增长得快等这样重要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主流增长理论研究议程的中心问题。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兴起和繁荣,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理论逐渐开始融合。这主要是因为新增长理论放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定和方法,并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同时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罗斯 (Ros,2000)认为,增长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应该融合在一起,至少应该是交往密切的两个邻居,对于增长经济学家来说,发展经济学家的很多见解不仅是有价值的,而且完全是可理解的,增长理论的某些模型也可以用来阐明发展理论中悬而未决的问题③Ros,Jaime,Development Theory and the Econom ics of Growth.Ann Arbor: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2000.。
新增长理论的诞生,主要是因为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理论假设与现实经济不符。法因 (Fine,2006)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归纳为四类:(1)新古典增长理论基于完全竞争与充分就业的假定;(2)新古典增长理论以稳态平衡增长 (steady state balanced growth)为归宿,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都以外生给定的速率增长; (3)新古典增长理论对索洛余值的分析严重依赖于模型包含什么投入要素;(4)最致命的缺陷来自于剑桥学派的批判或资本理论的争议,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一个经济只有一个部门,生产一种产品,这种单一部门单一产品的模型显然不能代表多部门多产品的经济。在这些方面,新增长理论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都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法因(Fine,2006)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新增长理论分析市场不完善和规模报酬递增;(2)新增长理论允许出现多重均衡解;(3)新增长理论将更多的变量内生化,并可以解释技术进步,增长率也不再唯一地由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决定;(4)新增长理论侧重于微观经济分析,大量地采用数理模型;(5)新增长理论假定资本和技术不能自由流动④Fine,Ben..Introduction,in Jomo K.S.and Fine,Ben,ed.,The New Development Econom ics:After the W ashington Consensus,London and New York:Zed Books.2006,pp.xv-xxi.。
新增长理论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很多基本假定不谋而合,从而新增长理论的许多分析方法都可以用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报酬递增和劳动剩余在 1940年代就被罗森斯坦 -罗丹强调了。而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内生技术变化、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可以充实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适度报酬递增和有弹性劳动供给结合在一起可能产生多重均衡,按照初始条件,不发达经济就可能陷于发展陷阱。例如,阿扎里亚迪斯和斯塔丘斯基 (Azariadis and Stachurski,2005)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由于偏好、初始禀赋和技术不同可能陷入贫困陷阱的多种机制①Azariadis,Costas and Stachurski,John,Poverty traps. In:Aghion,P.,Durlauf,S.N. (Eds.),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vol.1A. Elsevier,Amsterdam.2005,Chapter 5.pp.296-38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对稳态没有兴趣。发展经济学研究更加关注的稳态是低水平均衡陷阱,一个小的偏离使经济回到均衡状态,但大的震荡却会使经济累积性地偏离原始均衡状态,进入更高的稳态。
对于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融合,萨拉伊马丁(Sala-i-Martin,2002)认为,过去研究增长理论的学者都是从帕累托最优、完全竞争的新古典假定出发的,但是他们现在系统地放弃了传统的研究范式,继而研究各种制度的作用,但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从事二流的工作②ala-i-Martin,15Years of New Growth Econom ics:W hat HaveweLearnt?Journal Economía Chilena(The Chilean Economy),2002,5(2),5-15.。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家们也在不断将一般均衡和增长理论的各种方法和特性纳入到其研究中。班纳吉和杜夫罗 (Banerjee and Duflo,2005)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增长理论,他们认为,无论是新古典增长模型还是新增长模型,一般都假定存在一个总生产函数,而这个假定是否成立关键在于资源配置是否最优。但是,大量的微观研究文献表明,资源配置最优这一条件往往不能满足,因为一国之内的同一生产要素往往具有不同的收益率。为了更合理的解释各国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和增长率差异,他们构造了一个基于非加总 (non-aggregate)生产函数的增长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由于政府失灵、信贷约束、保险失灵、外部性、家庭动态以及行为问题等,投资没有发生在收益率最高的地方。此外,假如个人生产函数是具有固定成本的,则非加总的增长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穷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要低于富国,为什么穷国没有比富国增长更快③Banerjee,A.V.and Duflo,E.,Growth theory through the lens of development econom ics.In:Aghion,P.,Durlauf,S.N.(Eds.),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vol.1A.Elsevier,Amsterdam.2005,Chapter 7.pp.473-552.。
四、贫困陷阱理论的发展
国家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与传统增长理论的背离,穷国人民的生活与富国人民形成鲜明的反差。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穷国致富的秘方,从外国援助到直接投资,从发展教育到控制人口,从提供贷款到减免贷款。不幸的是,这些政策处方一直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伊斯特里(Easterly,2001)考察了非洲国家的外援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初始投资率很高且外援投资较高的国家,如几内亚比绍、牙买加、赞比亚、圭亚那、科摩罗、乍得、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却陷入经济衰退,而增长较快的国家,如新加坡、中国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初始投资率和外援投资数量都相对较少。此外,穷国更容易受外来冲击的影响而陷入贫困陷阱,例如自然灾害、饥荒、疾病等,从 1990-1998年,在全球发生的 568场大型自然灾害中,穷国占了 94%,在与灾难有关的死亡中,穷国占了 97%。从 1960-1990年,全球最贫困的 1/5国家中,有 27%发生过饥荒,而最富裕的 1/5国家中一个都没有。最贫困的 1/5国家中,超过 1%的人民由于自然灾害而成为难民,而最富裕的 1/5国家则没有。最贫困的 1/5国家中,11%的低风险人群携有 H IV病毒,而最富裕的 1/5国家这个比例只有 0.3%④Easterly,W.,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Cambridge.Mass.:M IT Press,2001.。
依照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如果资本和技术都是自由流动的,政策和市场都是有效率的,那么根本不会有贫困国家的存在。因为穷国总是可以通过采用富国的先进技术,引进富国的资本来获得发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穷国并没有完全采用先进技术,资本也没有大规模从富国流向穷国。此外,除了受到各种自然灾害、饥荒、疾病等影响外,穷国内在的各种体制弊端也层出不穷,例如政治腐败、治理缺乏、暴力动乱等,导致价格不能有效调节市场,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但即便是没有这些体制弊端的国家,如马里、加纳、以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一天生活不超过1美元。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体制弊端归结为贫困的根源,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在阻碍穷国通向富裕之路?在最近几年中,经济学家试图用贫困陷阱理论来解释贫困的根源以及如何跳出贫困陷阱的各种方法。
贫困陷阱有别于新古典模型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多重均衡的存在。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因为贫穷而没有足够的资金投资采用先进技术,新技术的不可获得使得该国继续陷入贫困,继而更缺乏资金,如此周而复始陷入低水平均衡;反之,如果一国因较富裕而大力发展研究并采用新技术,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从而收入也相应增加,使得该国更加富裕,继而不断向高水平均衡过渡。我们把一国经济陷入低水平均衡状态称其为贫困陷阱,一旦进入贫困陷阱,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不能自拔。只有通过强大的力量推动,才会跳出均衡陷阱,进入持续增长的路径,向高水平均衡前进。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导致一国经济陷入低水平均衡,还是向高水平均衡过渡的往往是相同的因素,只是作用的方向相反而已。墨菲、施雷弗和维什尼(Murphy,Shleifer&Vishny,1989)认为,导致多重均衡的因素一般有两个:规模收益递增以及信贷和保险市场失灵。由于技术和需求的不可分性,投资一般会产生一个固定成本,而正是因为固定成本的存在导致贫困国家的投资不足,进而陷入贫困陷阱。墨菲、施雷弗和维什尼讨论了在不完全竞争与总需求溢出的情况下的大推进理论,他们假定技术对于所有穷国而言都是可获得的,由于国内市场太小以及投资存在固定成本,穷国不会采用新技术。但是如果所有部门同时投资并且达到一定的比例则会有利可图。他们认为投资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经济才会产生多重均衡:(1)投资会扩大其他企业的市场或提高投资的利润,即投资具有外部性;(2)投资有负的净现值,即单个企业独立投资采用新技术是无利可图的。在他们的第一个模型中,尽管单个企业投资采用新技术无利可图,但是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从而增加了对其他企业产品的需求①Murphy,K.M.,Shleifer,A.,&Vishny,R.,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9,97(5),1003-1025.。假如这个需求溢出效应足够大,则会产生多重均衡。在他们的第二个模型中,投资采用现代技术改变了不同时期的总需求的组成,从而产生多重均衡。在最后一个模型中,由于基础设施和中间投入产品投资的协调问题,单个垄断企业投资基础设施是无利可图的,但如果所有的企业都投资则有利可图,从而也会产生多重均衡。
克雷默(Kremer,1993)从匹配的角度考察了贫困陷阱模型,他假定一个企业的生产过程由 n个不同的任务组成,并且将由 n个工人来完成,n是外生的,并且 n个工人的技术各不相同。工人的技术同时也可以看成是他们完成任务的概率,如果其中一个工人没有完成任务的话,则整个企业的产出为零。如果所有的工人都顺利完成任务,则有 n单位产出。有两个原因会导致这个模型产生多重均衡:第一个是劳动力市场的货币外部性,当更多的工人接受教育之后,工人匹配技术高的工人的概率也增加了,从而工人的期望收益也增加了,反过来促进工人更多地投资教育;第二个是不完全信息,由于工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技术工人之间的匹配依赖于技术工人的分布,工人的技术提高对其他工人的工资溢出效应非常大,从而会产生多重均衡②Kremer,M.,The O-Ring Theory of Econom ic Developmen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4),551-576.。
伊斯特里(Easterly,2001)从知识外溢与知识互补的角度讨论了不同层次——社区范围内、种族集团间、省域间、国家间——的贫困陷阱③Easterly,W.,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Cambridge.Mass.:M IT Press,2001.。甚至一个家庭或家族也可能是一个小的社会,也可能产生贫困陷阱。伊斯特里认为由于知识外溢和知识互补性会产生边际报酬递增,因而在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工人的平均工资也相对较高,而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工人的平均工资也相对较低。因为穷国的技术水平较低,工人不愿意投资来提高生产率,从而技术水平也不会提高。而且由于跨国收入差异巨大,穷国的高技术工人会倾向于流向发达国家。因此,穷国很容易陷入各种贫困陷阱。在马诸亚麻 (Matsuyama,2004)的世界经济模型中,所有的国家都在世界市场中竞争资本,一方面,他假定生产函数是严格凹的,从而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这意味着投资落后的穷国具有更高的收益,高收益吸引高投资从而促进高增长,各国的经济将趋于收敛;另一方面,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富国具有更多的抵押品,从而使得富国在竞争资本时,相对于穷国而言更具有优势,最终使得世界经济增长向富国和穷国两个方向发散,产生多重均衡④Matsuyama,K.,Financial market globalization,symmetry-breaking,and endogenous inequality of nations.Econometrica,2004,72,pp.853-84.。
阿扎里亚迪斯和斯塔丘斯基 (Azariadis and Stachurski,2005)概述了导致贫困陷阱的各种自我强我机制,例如历史和惯性自我强化机制,这些自我强化机制使得穷国愈穷,而富国愈富①Azariadis,Costas and Stachurski,John,Poverty traps. In:Aghion,P.,Durlauf,S.N. (Eds.),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vol.1A. Elsevier,Amsterdam.2005,Chapter 5.pp.296-384.。这些机制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来自于市场或制度失灵,并阻碍了穷国对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的获得。例如,在人力资本方面,当工人的技能是不可观察的时候,也就是说信息不对称的时候,高技能工人可能会被企业当成低技能工人而支付低工资,从而没有激励投资人力资本,而低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又反过来使得技能水平更低,低的技能水平又会减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在物质资本方面,在信贷市场上,富国比穷国拥有更多的抵押品,而穷国由于信贷约束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本,从而不能更多地投资,投资水平低导致穷国的收入水平更低,收入水平低又进一步阻碍投资。正是这些自我强化机制导致落后国家陷入贫困陷阱,使得落后国家的投资水平非常低,从而产生资本外流。
坏的制度要么会强化市场失灵,要么本身就是无效的根源(North,1991)②North,D.C.,Institution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1,5(1),97-112.。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坏的制度会产生路径依赖,促使贫困持续下去,这本身也是一种贫困陷阱。阿扎里亚迪斯和斯塔丘斯基认为腐败会从四个方面造成贫困恶性循环:(1)腐败会通过降低投资的回报而减少投资的激励,并且会增加投资收益不确定性;(2)腐败会阻碍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建设,例如公路与交通运输,从而严重影响现代部门的发展;(3)创新者在腐败体制下更容易遭受挫折,因为他们更需要政府的服务如许可、专利、执照等;(4)腐败会自我强化,因为腐败也具有互补性。墨菲、施雷弗和维什尼 (Murphy,Shleifer&Vishny,1993)指出了寻租的另一个潜在的互补性根源。随着寻租活动的增加,假如生产活动的收益下降的速度比寻租活动收益下降的速度快,那么即便是寻租活动的收益下降了,寻租活动仍然有可能增加,因为生产活动收益的减少降低了寻租活动的机会成本③Murphy,K.M.,Shleifer,A.,&Vishny,R.,Why is rent-seeking so costly to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83(2),409-414.。
穷国应该如何跳出贫困陷阱呢?伊斯特里 (Easterly,2001)认为政府干预可以引导一个国家跳出贫困陷阱。如果存在一个最低要求的投资回报率,那么知识匮乏可能会使得投资回报率过低,从而私人部门不会进行投资,政府可以通过对新知识投资进行补贴,从而引导这个国家走出贫困陷阱。此外,如果一个国家的贫困陷阱来源于恶劣的政府政策,那么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取消这些坏政策,然后对各种形式的知识和技术投资提供补贴④Easterly,W.,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Cambridge.Mass.:M IT Press,2001.。大野健一(KenichiOhno,2007)研究表明,低收入国家经常落入贫困陷阱,跳出陷阱有赖于各国的减贫战略,大野健一通过研究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政府治理水平与人均收入,表明二者之间呈严格的正向关系。大野健一认为,东亚的大多数国家之所以能够打破贫困陷阱,保持较快经济增长,得益于这些国家建立的威权发展模式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 m),其特点是:(1)强势而懂经济的领导人;(2)把经济发展当做国家目标;(3)有辅佐领导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技术精英集团;(4)政权的合法性来自经济发展的成功⑤大野健一:《东亚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比较》2002年第32期。。
经济的发展之所以需要一些“不够民主”的政府来推动,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是从一个很低的基础上起飞,需要快速而大规模地动用各种资源,而一个“民主”的政府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张夏准 (Chang, 2002)认为,“民主”不一定能够促进发展,尤其是在发展的初期。发达国家推荐的所谓的好制度:民主、“好”的官僚机构、独立的司法机构等;好政策:限制性的宏观调控、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私有化和撤销管制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并不会带来任何有利的发展,这些“好制度”和“好政策”是否真正适合发展中国家,还值得商榷。事实上,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初期也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些“好制度”和“好政策”。例如,美国独立的中央银行是直到 1913年才建立,“大萧条”后又开始放弃自由贸易政策,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瑞士在19世纪成了世界技术领袖之一,但它当时也没有专利法。发达国家之所以向发展中国家推荐所谓的好制度,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富国陷阱”,发达国家正在试图通过各种政策和制度“踢开”穷国登上富国的梯子 (Kicking away the Ladder)⑥Chang,Ha-Joon,Kicking away the Ladder: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London:Anthem Press,2002.。事实上,大部分发达经济体曾经采用的政策,基本上不同于他们向发展中国家宣扬的所谓正统做法。道格拉斯·诺斯等人(North et al,2007)认为,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失败往往是由于他们企图把开放准入秩序的元素——如竞争、市场和民主——直接移入有限准入社会中,而这些改革会威胁到维持社会统一的寻租体系,给整个社会的组织带来挑战。而当地的精英阶层乃至许多非精英分子会抵制、破坏甚至颠覆改革①道格拉斯·诺斯,约翰·瓦利斯,斯蒂芬·韦伯,巴里·温加斯特:《有限准入秩序——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思路》,《比较》2007年第 33期。。阿西莫格卢等 (2008)研究也表明,在控制一些历史的因素或固定效应之后,收入与民主之间并没有正向关系②Acemoglu,Daron;Johnson,Simon;Robinson,James A.and Yared,Pierre,Income and Democra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8,98 (3),pp.808-42.。
五、结束语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献只是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冰山一角,它只能代表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研究的一部分,由于篇幅所限,还有些杰出的、有开创性的文献没有包括进来。发展经济学眼下已然成为非常时髦的学科,过去很多主流经济学家都不屑于研究发展问题,但现在开始转到研究增长和发展理论,如理性预期学派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从 1980年中期开始就转到增长和发展理论的研究。纵观发展经济学近 70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近 20多年,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非主流的分析逐渐与主流经济理论结合,从理论构建到实证分析再到理论与实证的结合,从宏观到微观再到宏微观的结合,从发展理论与增长模型的分离到两者的结合,发展经济学 (包括增长经济学在内)走过了繁荣时代,也经历了黯淡时期,到目前又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热门学科。
尽管如此,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仍然存在不少缺陷,且面临许多挑战。各种针锋相对的理论让我们无所适从,很多理论都有待检验。但是,正是因为充满各种各样的挑战,发展经济学研究更加令人向往。巴丹这样评价道,“对我们而言,非常幸运的是,在我们的专业领域中,有卢卡斯这样伟大的人物,不局限于他对理性预期和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性贡献,在过去的20年中坚定不移地投入到增长理论的研究,使该理论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卢卡斯谦虚地说‘我并不想把我的后半生用来紧紧把着我前半生所做的事情’)。但是对我们这些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来说,如果要探索发展的制度障碍,就需要有更亮的指路明灯”③普拉纳布·巴丹:《强大但有限的发展理论》,《比较》2005年第 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