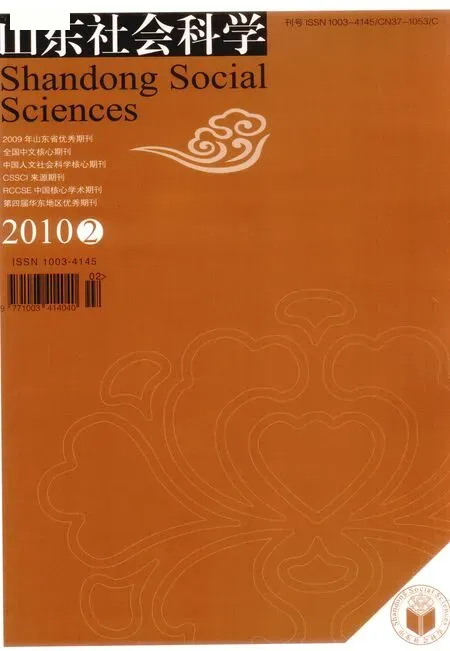观看之道
——桑塔格的女性主义图像观*
王建成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观看之道
——桑塔格的女性主义图像观*
王建成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以图像为主的视觉文化盛行,电视、电影、广告、报刊杂志、网络等使“观看”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行为,人们改变了传统的阅读方式,大部分时间是在“读图”而不是在“读书”,男性中心主义传统得以在图像领域继承。桑塔格作为西方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高潮中成长起来的女性知识分子,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揭示了“观看行为的不纯粹性”——“观看”是被父系伦理道德构建和阐释的。因此,桑塔格提倡女性主义的“观看之道”,主张作家艺术家必须反映女性主义的视觉文化诉求,打破图像领域的性别霸权,而不是将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牢牢钉在满足大众欲望的消费主义耻辱柱上。
女性主义;视觉文化;图像;消费主义
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1933—2004),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文学评论家、作家,女性主义者,是与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齐名的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作为女性主义者,她关注妇女问题,很多作品 (如剧作《床上的爱丽丝》、短篇小说《美国魂》)探讨了父系伦理道德观念对女性的束缚与压抑,探讨了争取妇女解放的途径。她于 1977年发表的《论摄影》是一本经典文艺批评著作,分析了摄影的捕食性和侵略性。桑塔格开始涉足图像领域后,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了男性中心主义传统对人们“观看行为”的塑造,指出图像已成为压抑女性的一种物质力量,因而必须倡导女性主义的“观看之道”,打破图像领域的性别霸权,为争取妇女解放张目。
一、桑塔格的女性主义立场
女性主义来自英文 Feminis m,最初译作女权主义,是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着很强的政治色彩 (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2年出版后,国内学术界大都认同了“女性主义”的译法)。1949年,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高潮的先驱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出版,该书从社会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出发,提出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形成的”观点,被誉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圣经”,为第二次女性主义高潮奠定了理论基础。1963年,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出版,书中分析了中产阶级上层妇女忘记了女权运动先驱的历史使命而成为“屋内的天使”,重新引发人们对妇女问题的思考,恰如当时《纽约时报》所点评,该书“点燃了当代女权运动,并因此永久改写了美国等国家的社会结构”。20世纪 60年代以来,美国的反越战游行、黑人的反种族歧视及争取公民权的运动引发了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 70年代的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高潮。在这次高潮中,美国激进女性主义崛起,不惜采取极端的态度,完全拒绝男性价值,从理论层面把父权制连根拔起,着力建立女性自身的主体空间,揭示了在私人生活领域也存在着男权压迫,喊出了“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口号。激进女性主义主要体现在颠覆异性爱霸权、抨击父权制和颂扬女性特质等方面。如组织“分离主义意识提高小组”,提倡“姐妹情谊”(Sisterhood)等。
桑塔格作为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其学术成长的关键岁月恰逢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高潮在美国爆发,对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压抑有着切身感受。桑塔格的女性主义立场是跟她的个人成长和时代背景分不开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桑塔格的女性主义立场。
首先,从桑塔格的个人婚恋来看桑塔格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桑塔格十六岁进入芝加哥大学,很快就凭着好成绩可以选修研究生课程。1950年桑塔格十七岁时,在旁听社会学教师菲利普·里夫的课时跟对方结识,十天后二人闪电结婚。但桑塔格婚后未改用丈夫的姓,仍保留自己的姓氏,“对里夫那传统的求婚方式的种种涵义,以及他对传统的五十年代家庭结构的期望,她一概不放在心上”。①[美]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铸就偶像》,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第48页,第61页,第188页 ,第168页 ,第128页。这说明桑塔格在少女时代就具备了不向男权社会低头的思想意识。而“里夫骨子是个保守主义者。在《弗洛伊德》第一版‘鸣谢’部分,他将桑塔格置于传统女性地位,向她致谢,在她的名字后加上她说她本人从未用过的夫姓”。②[美]卡 尔·罗利 森,莉萨·帕多克:《铸 就偶 像》,姚 君伟 译,上海 译文出 版社,2009年 版,第42页,第48页,第61页,第188页 ,第168页 ,第128页 。她喜欢无拘无束,从童年时期她就渴盼着自己能像成年人那样摆脱家庭的羁绊,一旦发现婚姻过于束缚人了,她就意识到婚姻仅仅是她的生活模式之一,丝毫没有停止远赴欧洲求学的脚步,尽管她当时已为人妻、人母。1958年年底,桑塔格从法国回国,毅然跟里夫离了婚,尽管里夫伤心欲绝。当她结束了起初热烈最后失败的婚姻之后,她又重拾童年时期的梦想,在纽约过一种自由作家的生活,而不是她一度在象牙塔内过的学究生活。其实在 50年代后期,她每年夏天都去巴黎进修,在那里通过听西蒙·波伏娃的课并成为她的密友。波伏娃认为结婚是“一种污秽,是把妇女置于从属地位的资产阶级原则”,她与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共同生活了51年,却始终没有结婚,桑塔格在个人婚恋方面是深受波伏娃影响的。桑塔格相信她作为一个随笔家能够写出她想写的东西,并以此来糊口。③David Rieff,Swimm ing in a Sea of Death,.New York:S IMON﹠SCHUSTER Press,2008,P20.这在当时她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刚刚离婚而又带着年仅 6岁的儿子,拒绝接受对赡养费的“理所当然”的要求,来到举目无亲的纽约,“她记得,当时仅有两只箱子和七十美元”。④[美]卡尔·罗 利森,莉 萨·帕多 克:《铸 就偶 像》,姚 君伟 译,上海 译文 出版 社,2009年版,第42页,第48页,第61页,第188页 ,第168页 ,第128页。即使她当时“身无分文,无家可归,没有工作,还有个六岁大的孩子要抚养”,她也“从未想过因为身为女人,她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就会受阻”,并且在“大家对她的单亲状况以及这样生活会有多么艰难唠叨个没完的时候,她很生气。毕竟,这是她自己选择的生活”。⑤[美]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铸就偶像》,姚君 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第48页,第61页,第188页 ,第168页 ,第128页。
其次,从桑塔格的同性恋身份来看她的女性主义意识。离婚后不久,挑战异性爱、跟女人亲密地结盟在桑塔格身上得到了很好地体现。桑塔格首先跟她在伯克利最要好的伙伴哈丽雅特·索姆斯结成“最亲密”关系。1958年二人曾结伴同游欧洲。桑塔格离婚后来到纽约,开始了她“征服纽约文学界的征程”。不久,桑塔格又跟哈丽雅特的好友——一个叫玛利亚·艾琳·福恩斯的古巴才女成为一对啧啧称羡的情侣。桑塔格不仅要闯事业,还要谈恋爱,一个接一个的情人 (多为女性)在她的生活中进进出出。自从 1963年与玛利亚·艾琳·福恩斯分手后,桑塔格不乏男女情人和求爱者,“在纽约有个 L先生 /女士,在米兰、罗马和那不勒斯又有个 C先生 /女士——在纽约还有一些别的”。⑥[美]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铸就偶像》,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第48页,第61页,第188页 ,第168页 ,第128页。1988年,桑塔格又跟纽约著名的时尚摄影师安妮·利布维兹 (Annie Leibovitz)建立了“亲密关系”,尽管安妮极力否认二人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她们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安妮为桑塔格本人拍了大量韵味十足的照片,也为她的著作拍摄封面,桑塔格则督促对方出影集、办影展,给她提建议。桑塔格的《照片不是一种观点,抑或是一种观点》就是为安妮的影集《女性》而写的。她们的恋情一直持续到桑塔格去世前夕。
第三,不做象牙塔内的学究、积极介入社会表明了桑塔格的女性主义立场。在某种意义上,桑塔格一直是一个政治型作家。⑦Leland Poague,Conversations with Susan Sontag,University Press ofMississippi,1995,Introduction.桑塔格是二战后成长和崛起的文坛新秀,幼年时她的生活就和政治运动紧紧连在一起,她从很小开始就崇拜居里夫人,曾一度梦想做一个科学家。“我一生的巨大改变,一个发生在移居纽约时的改变,是我决意不以学究的身份来苟且此生:我将在大学世界的令人神往的、砖石建筑包围的那种安稳生活之外另起炉灶”。⑧[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页。作为一个在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斗争岁月里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桑塔格拒绝只做象牙塔内的学者,拒绝“本来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所谓的专家”,拒绝“成为《老爷》杂志的专栏作家”,拒绝接受约稿,拒绝靠写书评就能大把赚钱的行当,而“有着巨大的勇气,去思考无法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的思想”。⑨[美]卡尔·罗 利森,莉 萨·帕多克:《铸就偶 像》,姚 君伟译,上 海译文出版 社,2009年版,第42页,第48页,第61页,第188页 ,第168页 ,第128页。她要以笔为枪介入社会,去做一个致力于维护自由思想尊严的“好战的唯美主义者”。
事实证明了她对自己许下的诺言。20世纪 70年代初期,桑塔格重新开始涉足她曾一度忽略的女性主义运动。在她执导的电影《卡尔兄弟》中,她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描绘了一个下层妇女如何虐待前情人的私生女以及一个已婚妇女身陷中产阶级婚姻的牢笼的情形。1972年她在《年龄的双重标准》(The Double Standard of aging)一文里指出,男人是如何长时间地拥有种种特权,他们又是如何能够吸引年轻女性的。年龄的增长和外表的丑陋对拥有财富或强权的男人来说根本形不成威胁。1973年,她又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上发表《妇女的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 ofWomen)一文,她发出了极其激进的、绝不向父权制文化妥协的女性主义声音,重申了自己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支持,指出还没有声称要采纳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政府真正解放了妇女——在她的字典里,妇女解放不仅仅意味着建立男女平等的法律制度,更主要的是要强制推行男女平等分享各项权利的方案。①Carl Rollyson,Reading Susan Sontag: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Herwork,Chicago:Ivan R.Dee,2001,P20。1968年 5月,美国对越南狂轰滥炸,桑塔格严厉谴责美国的暴行,应北越政府邀请访问越南,并写下《河内之行》来反思越南人是如何反抗美国强权的。同年,她还访问古巴,同情古巴革命,但这并不影响她反对卡斯特罗对古巴同性恋者的迫害。她反对强权政治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为营救许多遭到政治迫害的流亡知识分子积极奔走,也曾掷地有声地发出诸如“白人是人类的癌症”、“美国创立于种族灭绝”等声音。在塞尔维亚与波黑发生军事冲突时,她谴责西方对塞军种族灭绝的残酷战争袖手旁观,不顾生命危险在被围困的萨拉热窝逗留,在枪炮声中排演了贝克特 (SamuelBeckett)的名剧《等待戈多 》。“9·11”事件发生后 ,桑塔格在《New Yorker》(纽约人 )上发表了题为《Unsere Stärke wird uns nicht helfen》(强大帮不了我们的忙)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驾机袭击的伊斯兰分子不是“懦夫”,袭击不是对自由世界的打击,而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后果。②SteveWasserman.,Author Susan Sontag Dies,SeeThe los Angeles Times,December28,2004.桑塔格作为一个对抗平庸、对抗伦理上和美学上的浅薄和冷漠的战斗中的斗士,“她对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的揭露从来就没有动摇过”③[美]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铸就偶像》,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无愧于文学界的政治家的称号,用自己的政治实践兑现了“我坚定地认同我自己的女权主义者的身份”④Leland Poague,Conversations with Susan Sontag,University Press ofMississippi,1995年版 ,第210页。的诺言。
二、图像不仅具有真实性,更具有道德性、欺骗性、压迫性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以图像为主的视觉文化盛行,而且催生、构建了当代意义的图像符号系统,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了崭新的视听环境,打破了印刷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使图像凌越文字成为不争的事实,人们大部分时间不是在“读书”,而是在“读图”。相对于文字和绘画,图像具有无与伦比的真实性和现实性,观看起来省时省力,常常是“所见即所得”,但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它更具有道德性、欺骗性和压迫性。
图像毋庸置疑具有道德性。“在决定一张照片的外观,在取某一底片而舍另一底片时,摄影师总会把标准强加在他们的拍摄对象身上。虽然人们会觉得相机确实抓住现实,而不只是解释现实,但照片跟绘画一样,同样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⑤[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第3页,第55页,第21页。这种解释源自摄影师的头脑,照片蒙着“真实和现实”的外衣,只不过是在世人面前表演的木偶,而耍木偶的人正是摄影师或拍照者。摄影师或拍照者当然是一个具有道德意识的人,他的思想观念必然要符合他所在社会的文化标准,体现一定的意识形态和伦理观。正是摄影师的道德感使“照片是一种观看的语法,更重要的,是一种观看的伦理学”⑥[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第3, 55 21。,广大的受众透过相机源源不断地看到了“富人和有权势者的耗之不尽的魅力,穷人和被社会遗弃者的谜似的堕落”。⑦[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第3页,第55页,第21页。于是,广大的受众被摄影师牢牢控制,摄影师又听命于一定的意识形态或道德意识、价值观念,印刷文化里面的男权中心主义衣钵被“摄影”继承下来,又坐上了视觉文化的头把交椅。“摄影的工业化使它迅速被纳入理性的——也即官僚的——社会运作方式……照片被用来服务重要的控制制度,尤其是服务家庭和警察,既作为象征性物件,也作为信息材料”。⑧[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第3页,第55页,第21页。而男权社会恰恰是要把女性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这个“私人空间”,至于经国大业是男人的事。“在一个微波炉比萨的电视广告里,英俊的父亲和两个漂亮的孩子坐在一张布置得随意但很不错的餐桌旁。空气里透露出殷切的期盼。作为令人愉快的报答,妈妈捧着一份热气腾腾、诱人的比萨出现在门口。一家人开始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这块比萨显然是美味的。孩子们相视而笑,父亲看着母亲微笑,母亲向我们会心地微笑”。这个广告虽然是告诉大家这个比萨是由波特森公司制造的,但这个广告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贩卖的是一种愉悦的家庭生活,通过“波森特比萨”这个能指,喻示着“在理想的家庭中,母亲应该为家里买菜、煮饭、摆饭菜上桌,并且 (可能)还要清理饭桌”。⑨[英]理查德·豪厄尔斯 (Richard Howells):《视觉文化》,葛红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这样,一则大家耳熟能详的广告就建立了一整套“男人外出打天下,女人固守家庭”的社会秩序,把男性中心文化于不经意间贯彻得淋漓尽致;“照片不会制造道德立场,但可以强化道德立场——且可以帮助建立刚开始形成的道德立场”。①[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第83页,第177页。受众通过“观看的伦理学”在观看形式上也具有道德性,影像的形成和照片的观看形成具有同一道德意识的合谋。
图像具有意识形态欺骗性。桑塔格十分明了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设置的文化陷阱,敏锐地洞察到貌似价值中立、不偏不倚的男性文化同样在视觉图像里占据统治地位,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并且这种欺骗性在影像比真实还“真实”的情况下,具有不易察觉的隐蔽性。“拍摄即是创作”②[美]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第7页。,图像容易使我们相信“眼见为实”,但正像画家“作”画一样,摄影师在拍摄前“取景”,拍摄者的头脑决定了相机的“眼睛”所看到的并非全是真实,能让相机“说谎”。图像从来都不是超阶级的图像,图像暗含着等级的、文化的、种族的、殖民的、宗教的、性别的等诸多政治表达方式及象征意义,尤其对非西方主流文化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对一个以色列犹太人来说,一张有关耶路撒冷市中心‘斯巴罗’意大利餐厅袭击事件中一名儿童被炸碎的照片,是一名犹太儿童被炸碎的照片,是一名犹太儿童死于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的照片。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一名在加沙被坦克炮弹炸碎的儿童的照片,首先是一名巴勒斯坦儿童死于以色列炮火的照片。对好战分子来说,身份即是一切。所有照片都有待说明文字来解释或篡改”。③[美]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第7页。图像的虚伪性和意识形态欺骗性由此可见一斑。
信息时代的来临使文化传播方式、信息获取渠道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促使文学文本由激发想象、引起感情共鸣的描述方式向图像再现方式转变,人们离语言符号越来越远,放弃了对文字背后的人生感悟和理性主义思索,被逼真的视觉形象所吸引,不再去探求现象背后的东西,日益接受了以图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人们处于图像的包围之中,无所不在的影像似乎把一切经验都“平等地”让每一个人分享,人人在图像面前获得了完全的“民主”,正如桑塔格深刻地指出的那样:“摄影那超流动的凝视使观者感到惬意,创造一种虚假的无所不在之感,一种欺骗性的见多识广。”④[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第83页,第177页。既然图像具有道德性,图像的欺骗性也就不足为怪了,而欺骗性正是麻痹女性的斗志、使妇女乖乖听命于父权制的一贯伎俩。
图像具有压迫性。在信息时代,信息爆炸的主要症候便是图像的泛滥,图像越来越成为商业文化谋取利益、传播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商业文化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对财富的贪得无厌的攫取导致人的异化。在母系社会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市场经济,没有阶级压迫,当然没有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历史上的第一场阶级对立出现在一夫一妻制度中的男人与妻子之间,第一种压迫就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⑤[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在商业文化、消费主义的影像中,女性形象要迎合男性的观看目光,女人的性感撩人、风情万种、清纯美丽被蠢蠢欲动的大众作为欲望的对象被窥视,女性同样遭受压迫,遭受被物化的命运,商业文化背景下的消费主义跟女性主义是截然对立的。摄影发明以来,影像就成为媒体传达男性话语的视觉暴力工具,男性话语和父权制意识形态控制着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媒体沦为父权制话语压迫女性、维持女性传统形象的工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要求一种以影像为基础的文化。它需要供应数量庞大的娱乐,以便刺激购买力和麻醉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伤口”。桑塔格指出:“影像的生产亦提供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社会变革被影像变革所取代。消费各式各样影像和产品的自由被等同于自由本身。把自由政治选择收窄为自由经济消费,就需要无限地生产和消费影像。”⑥[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第83页,第177页。今天,影像是我们的主要消费模式,在这个消费模式中,妇女又被牢牢钉在了消费领域的欲望之柱上。男主女客的形象主导着父权制社会,在今天的消费社会丝毫不例外。
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男性书写的历史,女性的书写在人类的历史中长期缺席。“阴茎之笔”曾在人类历史的空白之页上肆意书写,相机作为阴茎的变体又在制造出大量的影像。“阴茎是钢笔的隐喻吗”曾引起女权主义者强有力的质疑,桑塔格同样质疑“相机作为阴茎,无非是大家都会不自觉地使用的那个难以避免的隐喻的小小变体”。桑塔格指出迈克尔·鲍威尔的电影《偷窥狂》是一部关于精神变态者的电影,主角在替妇女们拍照时,利用隐藏在相机里的武器杀她们。在消费社会里,女性也沦为一种物化的商品,一方面要充当商品促销员,如美女已成为汽车品牌的销售符号、选美已成为“美女经济”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要维护、遵守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不能越雷池半步,造成受众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就连广大女性自己也把这一戒律内化为准则。在这类影像里,女性不仅被呈现为固守家庭、相夫教子、贤妻良母、温柔贞顺、逆来顺受,更被刻画为成功男人的少奶奶、大款阔佬的二奶乃至自甘堕落、贪图享受的、精神空虚的妓女、三陪女、偷情女。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中男主人公的名字代表着正确与稳重:光荣、大山,也着意刻画了褚琴对石光荣、秋英对高大山的敬仰与服从。这恰如桑塔格所说“在一个社会里,妇女只是生儿育女者和帮手,她们没有任何仪式上的用处,而且代表着对男人的品格和力量的一种威胁”①[美]苏珊·桑塔格:《迷人的法西斯主义》,见《在土星的标志下》,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为了维护以男人为主导的社会秩序,相机 /阴茎就要以影像来书写消费社会的历史。
三、打破影像领域的性别霸权——反对消费主义对女性形象的包围和淹没
“后判断时代的精神特质汲取了消费主义的准则,正在社会上获得主导地位,摄影受到它的影响”。②[美]苏珊·桑塔格:《照片不是一种观点,抑或是一种观点》,见《重点所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页,第287-288页。桑塔格在为女性摄影家安妮·利布维兹的影集《女性》所写的序言《照片不是一种观点,抑或是一种观点》(1999)里一针见血地指出,摄影唯消费主义马首是瞻,图像领域仍然存在性别霸权,信息时代的到来并没有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带来真正的福音,消费主义对女性形象的压迫与歪曲不但没有丝毫削减,反而变本加厉。桑塔格认为,要想真正打破影像领域的性别霸权,抵制消费主义对传统女性形象的继承和包围,图像就必须告别父系文化的道德性、欺骗性、压迫性,就必须倡导一种女性主义的“观看的伦理学”——打破图像领域的性别霸权、为妇女解放张目,在以下几个方面开辟女性主义视觉文化的新天地。
首先,图像必须真正反映男女平等,塑造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形象。“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③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父权制建立以来,女性逐渐被限制在家庭来料理家务、相夫教子,干事创业、科技发明、艺术创造、智力创新都是男人们的事,妇女被禁止参与社会生产,只能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来从事家务劳动,这就造成“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对立”,任何试图闯入男人的公共空间从事社会生产的女人都是注定要遭受谴责和诋毁的。安妮·利布维兹的影集《女性》——一本有关女性的影集必须提出女性问题,刻画了许多杰出的女性形象,向我们传达了“女性如何克服长期以来的障碍、偏见和文化隔阂,在从没有涉足的领域取得成功”。桑塔格清楚,“一个男性被看作人类的一员,而一个女性被看作女性的一员。这些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改变,它们深深扎根于我们的语言、叙事、座次的排列和家庭习俗中。不论在什么语言里,‘她’从来不能代表包含两性在内的整个人类。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在文化上,女性遭遇不平等的待遇,男性似乎是受到偏爱的,男性和女性对自身的认识是不同的”。④[美]苏珊·桑塔格:《照片不是一种观点,抑或是一种观点》,见《重所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99页 87-88。桑塔格作为一个成功女性,仍然强烈地感觉到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压抑与歧视,大批影像正在重复这种过时的话语,在重新贩卖这种传统的女性形象,从而去压抑女性的远大抱负,“而抱负正是强调今天女性生活百态的影集要大声疾呼的”,桑塔格如是说,目的是要让视觉图像表达女性与男性同等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认同的诉求。
其次,图像必须将人类的本能作为一种自然的愉悦来反映,而不能借机宣扬色情暴力。人类的性欲是人类自身繁衍的生物基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西方教会信奉“上帝不羞于创造的,我们也不羞于宣讲”;孔子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父权制文化只将这些信条应用到男性身上,对人类的另一半则极力否认这一事实。父权制文化无限夸大男人的性能力,制造性领域的男性神话,将之作为控制女性的手段。信息时代的影像技术所释放的人类目光的视觉力量,日益演变成为父权制文化表达男性性别沙文主义和霸权的视觉暴力工具。在视觉图像里,男人在性行为中不仅有超强的能量,还是绝对操控者,将女人从生理上和心理上彻底征服,女人只能作为慰劳男人的尤物,逆来顺受、俯首帖耳。尤为可怕的是,男人不仅追求“征服”,还追求“暴虐”。桑塔格指出色情作品《○的故事》“继承着法国 19世纪出现的‘浪子’色情文学的传统。这些作品一般都以想像中的英国为背景,故事围绕着性虐待狂与受虐待狂的情节展开,男主人公是残忍的贵族,他们拥有巨大的性器及完善的性虐待器具”,“而女人在这里就是不折不扣的奴隶,是男人们用野蛮方式发泄并分享花样百出的兽欲的淫欲对象。房间里有皮鞭和锁链,女人一出现男人们就都戴上面具,壁炉中的炉火烧得很旺,然后是难以描绘的性侮辱、鞭打及其他闻所未闻的身体伤害落在了女人身上”。⑤Susan Sontag,“pornographic imagination”,inA SusanSontagReader,NewYork:Famar,Straws Giroux,Inc,1982,P216-217.当今的图像正是上述文字的视觉转换。不仅如此,图像还遮蔽、掩盖、否认女性有着正常的性欲,“在延续至最近的主流传统中,美貌将女性的性欲遮蔽了。即使是在赤裸裸的色情照片里,肢体和脸通常所表达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一个赤裸裸的女人躺在那儿,淫荡不堪,伸开四肢,或卖弄臀部,然而同时她还在看着你,脸上露出乏味的可爱的表情,像在拍一本正经的肖像”。①[美]苏珊·桑塔格:《照片不是一种观点,抑或是一种观点》,见《重点所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第290—292页 ,第298页。这深刻说明了女性的性欲一直被压抑且遭到歧视。针对这种状况,桑塔格指出“人类的性欲是一种天然的愉悦功能;而‘淫秽’是文化上的偏见,这一偏见虚构出性行为、性愉悦是令人不齿的神话并强加给社会”。②Susan Sontag,“pornographic imagination”,inA SusanSontagReader,NewYork:Famar,Straws Giroux,Inc,1982,P221.桑塔格要求图像必须将人类的性欲作为一种自然的愉悦来反映,如果图像走不出“道德的空间”,只能匍匐于父权制文化的脚下。实际上,图像不仅存在着道德的空间,还存在着美学的空间,快感的空间。正像桑塔格评论杰克·史密斯的电影《淫奴》所阐明的,《淫奴》“具有波普艺术的欢快、坦率以及免于道德说教的令人愉快的自由的特征……对生活中的某些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性快乐——不必采取什么立场”。③[美]苏珊·桑塔格:《杰克·史密斯的淫奴》,见《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页。
第三,图像必须揭示女性形象的多样性。随着后工业社会及信息时代的来临,消费主义大行其道,视觉图像凌越文字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媒体及各种传播媒介为人们赚取金钱提供了最佳方式,影像越来越成为商业文化谋取利益的有力工具,图像领域又形成了“男性观看、女性被看”的二元对立格局:女性形象是摄影师为消费者全力打造的性消费产品,作为男性欲望化客体而处于男性目光的笼罩之下,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替代品,成为林林总总的商品符号。于是,影像传达了刻板的女性形象:将女性与美貌和性吸引力等同。女性的“性与色”作为吸引眼球、赚取金钱的砝码,女性必须漂亮,女性的美貌就是一切。影像告诉我们,只有漂亮的女性才有可能进入比自己出身更高的阶层,才能在强势阶级那里钓得金龟婿,而美貌是可以人工造就的,女人自然要通过精心打扮,穿漂亮衣服、戴首饰、化妆、美容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而这正中广告商的下怀。“对女性的描绘着力表现她们的美貌,而对男性的描绘则着力表现他们的‘个性’……女性的特质应该是顺从的、温和的,甚至是忧郁的;男性的特质应该是有力的、观察敏锐的。男性不会愁眉苦脸,理想中的女性看上去并不会咄咄逼人”。这一切都是在执行男性的标准,正如桑塔格举小说《白衣女人》中的玛丽安·海尔科姆的例子所说明的那样,叙述者从背后和远处看到的是一个完全符合男性口味和标准的女性,当走近一看居然发现玛丽安·海尔科姆“长得这么丑!”④[美]苏珊·桑塔 格:《照 片不是一种 观点,抑或 是一种观 点》,见《 重点所在》,上海译 文出版社,2006年 版,第295页,第290—292页 ,第298页。尽管玛丽安·海尔科姆拥有每一种美德,惟独勾不起男人的欲望,且因过于聪慧、率直而缺乏“温柔和女人味”,结果给自己带来无尽的麻烦。这不由让人想起封建社会对女子“德言容功”的束缚。对此桑塔格有清醒的认识,呼吁大众传媒走出性别上根深蒂固的常规形象的怪圈,呼吁对女性的“公正”,“我们更喜欢那些讽刺性的、未被理想化的照片。得体被认为是一种伪装。我们希望摄影师无所畏惧,甚至目空一切”。⑤[美]苏珊·桑塔格:《照片不是一种观点,抑或是一种观点》,见《重点所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第290—292页 ,第298页。有广大作家艺术家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不随波逐流,不去迎合消费主义,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去揭示女性形象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倡导一种女性主义的“观看的伦理学”,而不是甘当消费主义的奴仆,这正是作家艺术家在当今信息时代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艳红)
J405
A
1003—4145[2010]02—0163—06
2009-11-11
王建成,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7级文艺学博士生,济南大学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