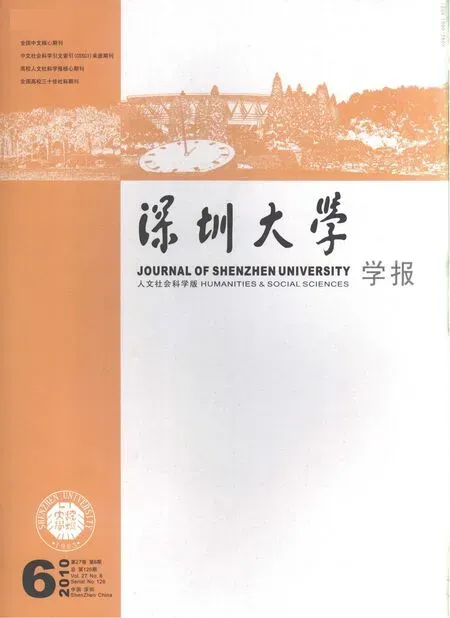理性超越性追求的本体论基础
宋清华
(河南科技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河南 郑州 471003)
理性超越性追求的本体论基础
宋清华
(河南科技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河南 郑州 471003)
人类理性总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层基上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这种渴求,是一种指向终极性的理性追求,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种终极性的关怀,并据此形成认识和评价尺度,来构建人类的理想世界,这种终极关怀就构成了本体论。本体论源于人类哲学的童年时代,与人类独特的生存状况或生存样式联系在一起,它体现的是人类对万物本源的终极追求,具体表现为3个方面:追求作为世界终极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反思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讯问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它们构成了人类理性超越性追求的本体论基础。
理性;本体论;理想
人类理性追求有其本体论基础,这种本体论基础正是人类理想不灭或者说永恒存在的深层原因。因为这是来自根源处的东西,是人类原初之相,是理想建构的根据或原型。人类理性只有在这种生生不息的源头中才能找到自身的本真,获得人生和社会的真意,构建人类理想的家园,为人类栖居大地奠定根基。
一
事实上,本体论肇始于人类哲学的童年时代,可直接上溯到古希腊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体现了西方对万物的根源的寻求,也就是说西方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在为万物寻找一个最终决定它们的东西,这是典型的西方思维形式。这种理性形式后来发展为对万物的本质、规律(逻各斯)的把握,也因此催化了近代科学理性的发育,以及理性主义的诞生,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对这种传统的探索,必须回到古希腊那里去。寻求万物本原、探求生活之真谛,是人类思维的必然趋向,是与人类俱生的,因而也可说是人类思维的本质特点之一。这是一种追根寻源、穷根探本的精神。在人类的最初阶段,靠着这种精神,人类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自然灾难,保存了自己的种族,在探索的阶梯上不断地攀登。然而,这样一个阶梯是无终止的,人们悬设的所谓“本原”、“真谛”,始终是一个追求的目标,永远不可能实现,但这正体现了人类对智慧的追求。最早提出本原问题的是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本原 (或译“始基”),按照亚里斯多德的解释,就是万物都是由它构成的,最初由它产生、最后又回归于它的那个东西。在柏拉图那里,本体又是和神话中的神相关联的,神话用言语编织自身的道路,并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现在、未来和从前的事。“凡事的开头最重要”[1],神话的作用在于打破起初的静寂,为人们传递神的语言,以展示宇宙的整体形象:谁能穿越这一静寂,回溯到源头,谁就能遇见神。这就为尘世获得神性和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也是理想主义的神性来源和根据。
本体论的产生与发展,首先是与人类独特的生存状态或生存样式联系在一起的。人类作为改造世界的实践——认识主体,其全部活动的指向与价值,在于使世界满足于人类自身的需要,把世界变成对人类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而具有展示人类本质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思维最根本、最切近的基础。基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人类理性思维,总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层基上或最完整意义上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并据此形成认识和评价尺度,来构建人类的理想世界,建构人类社会自身的完美形象,在人世间建立理想的天国世界。理性思维的这种渴求,是一种指向终极性的理性追求,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种终极性的关怀 (因为具体的物质形态终将毁灭,包括人及其生活的星球,乃至整个宇宙空间的物质存在都有生灭,没有能够永恒存在的物质形态,因此人们总是期望找到一种永恒的存在,使人与之相关联,从而使人类获得永恒不朽的价值,这乃是人类追求本体和终极实在、终极价值的原因,也是人为何要超越自身感性存在的原因。)这种终极性的渴求或关怀的理论表达方式就构成了贯穿古今的本体论。本体论是一种穷根究底、追本溯源式的理性意向式追求,是一种理性思维无穷无尽的指向性,是一种意在追求无限性的终极价值关怀。本体论的终极关怀包含三层基本内涵:追求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这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反思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 (这是知识论或认识论上的),讯问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这是作为价值论意义上的)。所以本体论是终极关怀意义上的存在论、知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
从对终极存在即世界的最高统一性的求索看,它体现的是人类对万物本原的终极追求,人们之所以把本体论界定为存在论——关于存在的理论,这是一种源于哲学史的说法。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哲学史上的本体论,其指向和寻求的“存在”,即不是“在者”,也不是海德格尔的“此在”,而是指总体性的存在或存在的总体性,即“在”本身。它对把握存在的人而言,是一种统一性的抽象或抽象的统一性。人类之所以要寻求这种抽象的统一性,是企图以此为根据去说明全部在者的生成、演化和复归。因此,这种存在对于人类理性所把握的世界而言,具有终极存在的意义。亚里斯多德曾指出,哲学的探索始于对大自然的惊异。当然,人之所以去探索、理解和认识世界,是因为这种惊异引起的好奇、敬赞。好奇心并非主观的,而是客观引发的(是被外在世界的神奇所诱发、所吸引),故是敬赞,是对世界的惊讶和赞美。世界的神圣性引发了我们的好奇心,这是知识的永久性。永恒的原因是第一性的原因,因此,研究神圣性引发了我们好奇、敬赞的根源,则为第一知识,第一原则、第一性哲学,即形而上学。因此,人类思维面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世界,试图寻求一种万物都由它构成,最初从它产生、消灭后又复归于它的存在物,把它作为实践之所以为实是的最终原因,这就是哲学思维在其童年时代所指向的终极存在。这种思维所关注和指向的终极存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体系,它研究的固然是“不变的”、永恒的问题,但仍不脱离可变的世界。而形而上学的特点也是其难点,在于它把世界作为一整体的把握。此种总体——“全”恰恰不是概念,不是抽象的东西,而仍是具体的。把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动与静综合起来思考,这才是全体、总体的真实含义。
至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惊赞、好奇,就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理智性的东西,是理智的直观、直观的理智。形而上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概念体系,不是一个由概念的逻辑分析推到出来的公式系统或理论系统;形而上学的方法不仅是分析的,而且也是综合的,是超越的,但又是包含着经验的,此种超越为经验之全,更准确地说是非概念的经验之全,所以是metaphysics,既是meta,又是physics。并不是有一个什么具体的东西在自然物理之后,或之前,也不是自然的、物理要有一个逻辑的条件。第一性、终极性存在问题既不是物理性的,也不是分析性(逻辑)的,而是总体性的。所以亚里斯多德的理论很好地揭示了形而上学所面对的神圣性、令人惊赞的世界。形而上学具有最高贵的性质,但它不是宗教信仰,而仍是一种科学性、理论性的体系。形而上学要用科学知识的形式——方式去把握那神圣的东西——终极存在,使神圣性被理论化,成为一门学问,不但是theology说神圣性的事,而且使此种说理论化、系统化,真正成为logos,成为一门与物理、自然有关的(尽管是在“超越、原、元”的意义上的关系)一门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即在theology,在“关于神圣性学说”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后世所谓形而上学,在亚里斯多德那里,正是theology,metaphysics即theology,是以理论的方式去把握physics中的神圣的部分,即永恒的部分。这个永恒的部分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是永恒的活、不死的世界,乃是神的世界,“不死”是希腊文“神”的中心意思,中文“神”字同样强调其活的一面。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神所指既非所有内容(材料、质料)的绝对形式的理性,也非受理性制约的自然,乃是活生生、活泼泼的但又是那样合度、合适、合规律、有秩序的世界。这个世界,才是最真实的世界——终极的存在,它不是概念的世界,是真理的世界。不难看出,这种本体的思启发着哲学家沿着对逻各斯的逻辑把握,去探寻世界的统一性即终极存在。这种哲学思路就是探寻对象世界的现象与本质的逻辑关系,把本体或终极存在视为超越经验而为思维所把握的理性存在物即共相的存在。这一思路也是由柏拉图提出的,柏拉图认为,现实存在的任何事物或现象,总是以其特殊性的存在或存在的特殊性而表现出诸种不完善性;从经验对象所获得的任何观念或知识,总是以其特殊性的内容或内容的特殊性而丧失其解释的统一性;因此,应该而且必须存在一个高于物理事物并且规范物理事物的“理念世界”,这个共相的理念世界给予并且显现物理世界的意义,因而也构成对物理世界的统一性理解和解释。这样,在柏拉图关于终极存在的探索中,已经显示出本体论的另一个重要的基本内涵——关于世界的知识性的终极解释[2]。
二
从人类寻求对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看,它体现的是人类对自身理性至上性的不懈追求。哲学家对世界本原或终极存在的追求和确认,不可能仅仅将本源或本体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必须对其进行逻辑分析和论证说明,使之具体化,成为知识形态的载体。而本体观念的具体化和知识化就是对本体的解释。本体观念指向的是世界的终极存在,本体观念的展开和论证,具有对世界进行终极解释的意义。事实上,作为终极解释的本体论,是以知识论形态为中介指向世界的终极存在,或者说,在其直接的理论形态上,不是表现为世界统一性的存在论,而是表现为关于知识统一性的认识论。亚里斯多德在总结古希腊哲学的基础上提出,哲学本体论所探求的是关于“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3],这种基本原理可以使人类经验中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得到统一性的解释,或者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的各种具体表现,从而达到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对此努力,黑格尔十分肯定,他赞同亚里斯多德所规定的哲学目标,认为整个哲学史所指向的正是这个目标。不过,他认为,其一,亚里斯多德及其后来的哲学家们把各种各样的现象提高到概念里面之后,却又使概念本身分解为一系列彼此外在的特定的概念,而没有给出作为“终极解释”的统一性原理;其二,作为终极解释的统一性原理,只能是形成于对人类所创建的全部知识和整个人类认识史的反思,而不是直接的形成于对各种各样的经验性对象的认识。正是从这种理解性出发,黑格尔指出:一是“要这样来理解那个理念,使得多种多样的现实,能被引导到这个作为共相的理念上面,并且通过它而被规定,在这个统一性里面被认识。”[4]二是要把哲学理解为“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即反思,并通过反思而使哲学的统一性原理获得系统的逻辑规定。在黑格尔看来,讲本体论所追求的统一性原理之所以具有对世界进行终极解释的意义,并不是因为它对世界作出最深层次的知识性解释,而是因为它要能够把全部知识和整个认识史扬弃为思维把握存在的逻辑,即人类思维运动的逻辑。由于这个逻辑具有充实任何真理性内容的功能,因而是人类全部知识得以生成和得以解释的统一性根据。黑格尔的这种理解和追求,是对整个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深刻总结。他以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哲学形式,唯心主义地实现了本体论所指向的终极存在与终极解释的统一[5]。
与亚里斯多德相比,黑格尔对知识论统一性的这种解释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人类理性由于自身的缺陷是不可能对人类经验中的各种事物给出统一性的解释的,康德对此作了经典的说明,康德把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前者只能在经验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是形成科学知识的基础,后者则适用于超验领域,即本体世界、道德伦理世界,体现了理性之形而上学意向的源泉。不过,康德对两种理性的划分是为了界定二者发挥作用的范围,以免相互越界,造成“不法的”行为或错误,因此,本体世界是不容许理论理性踏入半步的,否则必然产生先验的幻相,本体本身就是对理论理性的限定,或对理论理性所设定的禁地:“一个本体的概念,亦即一个根本不应当作为感官的对象、而是应当作为物自身(仅仅通过纯粹知性)被思维的事物的概念,……为了不使感性直观一直扩展到物自身之上,从而为了限制感性知识的客观有效性,这个概念又是必要的(因为感性直观所达不到的其他东西之所以叫做本体,恰恰是为了借此表明,那些知识不能把自己的领域扩展到知性所思维的一切之上)。……因我们有一种以或然的方式扩展到比现象领域更远的地方的知性,但却没有直观,甚至就连能够使对象在感性领域之外被给与我们,并使知性超出感性之外而被实然地应用的一种可能的直观的概念也没有。因此,本体的概念纯然是一个界限概念,为的是限制感性的僭妄,所以只有消极的应用。尽管如此,它却不是任意地杜撰出来的,而是与感性的限制相关联的。但毕竟不能在感性的领域之外设定某种积极的东西。”[6](P247)也就是说,本体世界的设定,目的是为了限制知性即理论理性的,那是理论理性的禁区,因为“纯粹的、纯然理智的对象的概念完全没有其应用的一切原理,因为人们想不出它们应当被给予的任何方式,而毕竟为它们留下一个位置的或然思想也只不过像一个空的空间,有助于限制经验性的原理,却毕竟没有自身中包含和显明经验性原理范围之外的某种别的知识客体。 ”[6](P250)
古典哲学家对理性能力的认知和对终极存在追求的体认,在后世得到了确认,理性是有限度的,它远远不能把握理性之外的事,因为面对:“异化和疏远人生基本的脆弱性和偶然性之感,理性面对存在的深奥而无能为力;‘虚无’的威胁以及个人面对这种威胁时的孤独和无所庇护的情况。很难合乎逻辑地确定这些问题的从属关系;每一个问题都在所有其它问题当中出现,而所有的问题都围绕一个共同的中心运行。只有一种气氛像刺骨的寒风弥漫于所有这些问题中:对人类有限性的强烈感觉。文艺复兴时期在人们眼中一望无际的地平线终于缩小了。说也奇怪,人发现自己是完完全全有限的——有人也许会说,从彻底的方面来看,是这样——这却是在人对自然的技术征服似乎不再有任何限制时发生的。但是这个关于人的真理决不存在于一种与另一种素质对立的素质之中,而要同时存在于两种素质之中。因此,人的弱点只是钱币的一面,他的力量则是另一面。唯一能防止力量由于冲昏头脑而崩溃的,也就是对有限性、对界限的认识。”[7](P36)这已成为西方哲学家的共识。而且20世纪的科学已经提供了使得理性主义的雄心显得过于自负的答案,这些答案本身表明人必须改进他那传统的理性概念。如果不是这样,科学就不可能有希望,因为科学家也是人,因此,他们同样有这样共同的精神,并且助长这种精神的生成。宗教、社会形态、科学和艺术是人存在的方式;而且我们越是认识到人的存在的短暂性,也就越发必须认识到那人类短暂存在籍以表现出来的所有这些方式里面和背后的一种统一性。
事实上,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在科学领域也非常明显,“科学,在其自身真正领域以内,也遭遇到人类的有限性这一事实。这一发现是在科学自身内部,而不是在关于科学的哲学探索中发生的。因此,更为确凿无疑,意义也更重大。 ”[7](P36-37)而且更加确定无疑的是那些出现在理性活动过程中之内的限度,出现在物理和数学等更为严密的科学中的限度。西方科学中最为先进的部分,物理和数学,在现代这个时代越发变得自相矛盾了。也就是说,这些学科已经到了引起理性本身自相矛盾的状态。200多年前,哲学家康德力图表明,理性有着不可避免的限度;但是,对于从骨子里来讲是实证主义的西方人来说,只有当这种结论出现在科学的研究结果之中时,才可希望他认真加以看待。随着海森堡在物理学中发现的测不准原理和哥德尔在数学中发现数学知识是无止境的,数学家永远也达不到其根基部,即数学家永远也无法证明数学的始终一致性。海森堡告诉我们,我们认识和预告事物的物理状态的能力有着本质上的限度。这一理论还使我们瞥见一个实质上也许是反理性而且混乱的大自然;无论如何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无法得知事实不是这样。海森堡的这个研究结果标志着物理学家们那个古老的梦想的终结,他们完全出于理性的独断,曾认为实在想必是完完全全可以预言的。而哥德尔的研究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它表明,即使在数学这一最为精密的科学中——在人类理性曾经是似乎万能的这个领域中——人也不能逃避他本质上的有限性:人所建立的所有数学体系都注定是不完整的。哥德尔已经证明,数学包含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而永远不能形式化为任何完整的体系。数学同人类生活一样都是未完成的。事实上,数学家们知道,从形式上讲,他们永远达不到系统化,因为数学并没有一个不依赖于数学家所进行的人类活动独立自在的实在。如果人类理性不能在数学领域中使之系统化,也就不大可能在任何其他领域中做到这一点。这就意味着,数学家永远无法证明数学的始终一致性,除非利用某些比他正在证明为始终一致的体系更靠不住的手段。所以数学家最终也不能避免与任何风险事业联接在一起的不确定性。由于数学在过去半个世纪遇到了一些非常麻烦的悖论,局面变得更加令人为难。数学就像一艘在大海上行驶而出现了某些裂缝(悖论)的船;这些裂缝被暂时堵上了,但是我们的理性不能得到保证不再出现其他裂缝。在这些理性学科中最可靠的领域中出现人的不牢靠感,标志西方思想中的一个新的转折点。数学家赫尔曼·威尔宣称,我们试图向天上发动猛攻,然而我们做到的只是垒起一座通天塔。这反映的是,数学家充满激情地表达了人类狂妄自大的垮台。而今,数学终于恢复了它作为有限的人的一种活动或存在方式的当然地位。直到此时,科学才终于赶上了康德,或者说证明了康德结论的正确性。
由此不难看出,人类对终极存在的追求和对知识的终极解释的寻求,都是人类自身超越自我有限性的体现,这种有限性既有生命的有限性、人自身的限制(感情、欲望、需求、无意识、本能等),也包括理性的有限性,而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及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的宿命——人无法达到这种终极性。无论是人们对终极存在的追求,还是运用理性对终极存在的最终解释,都是无法实现的。一方面,人类要超越自身追求终极存在,探求人类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人类理性的至上性也要求人对终极存在作一最终的解释,但这都与人自身的缺陷相矛盾,人类不具有达到终极存在和解释终极存在的能力,人只能以理想的理性建构去对终极存在作出解释——这种探讨和解释也无疑是有限的。因此,理想或理想主义也是人类的宿命,只要人类的实践存在,理想主义就将与之伴生。至于前述所言的理想主义失落问题,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即相对于人们纯正的理想价值追求有所偏离而已,或者说理想主义也有些异化了,需要重提和重建,以便使之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三
理性超越性追求的本体基础另一体现就是人类对终极价值——寻求意义的统一性的寻求,它体现的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价值的定位和评价,以及人作为在动物世界中位于最高序列的存在者,它在整个宇宙中的位置和最高评价尺度是什么。对于人类说,最感困惑的一个问题是人生是否有意义?如果有意义,那么,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生活?如果无意义,那么,人类的存在还值得期待吗?它和动物世界的其他存在者又有何区别呢?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人们,人们现在对解决这一问题仍缺乏自信。人们很容易受到形形色色的东西的影响,被无穷无尽的问题所困扰,而在这一片混乱和纷争中,很难看出任何统一的意义或目的。况且生活并非仅仅是无谓的游戏,它要求辛苦、劳作、克己、牺牲。这种辛苦和劳作是否有价值?全体或整体的利益能否补偿局部或部分的危险与损失?局部或部分的牺牲或损失是否有正当性?这些能否肯定地向我们证明生活值得一过?这不是个单纯的思辨问题,因为倘若没有对崇高理想的信念,就不会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为我们的生活中一切活动注入热情与欢乐,我们便不能获得生活的最大成功,也不能从中获得乐趣和幸福。当然,在某些时期,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潜在状态。我们的传统和社会规范为人们设定了确定的指导路线,摆在人们面前的目标的真确性是不容置疑的。不过,一旦有了问题,人们开始对支撑整个结构的假设产生了怀疑,信念的颓坏便如烈火肆虐,四处蔓延,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信念危机和意义困境。人们越是苦思冥想,问题越是变得复杂难解。当人们想去证明,生活虽有某种表面的混乱,但仍然具有某种意义和价值,而且可以满怀信心地宣称生活值得一过时,似乎显得愈加苍白无力。怀疑造成信念的瘫痪和理想的丧失,使人感觉到生活的虚无性,而生活的虚无性和无意义性则更为严重地吞噬着我们时代的灵魂,动摇着我们生活的信仰根基,侵蚀着人类心灵和精神的肌体,使我们社会的肌体也倍受腐蚀。人们所悟到的这一现象的明显证据在于下属事实:虽然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就和持续不断的进步,人们实际上并未感受到幸福。整个社会没有一种普遍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相反,倒产生了一种强调人的微不足道、藐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强调物欲主义或感觉主义的倾向,整个社会仿佛进入了拒绝崇高、否定理想、不要信念、什么都行、任其自然的时代。即使在仍保有理想和信念、确信生活仍有意义和价值的人们当中,冲突的价值观和生活取向也让人感到迷茫和沮丧。比如,可供选择的制度、理想,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乃至相互冲突,却同样要求人们去拥护。既然没有一个明显地、使人信服地优于其他的选择,相互冲突的倾向与标准便依然是当今社会的常态。在某人看来是至善,对另一个人则是绝对的恶;使一个人充满激情的东西,另一个人则认为对之如何谴责都不为过。因此,面对局部工作的丰富成果,我们却不得不处于一种甚为可悲的生活境地中,这使人们无法把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无法用一套令人信服的理想信念或价值观念来支撑人们的生活信念,解释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价值和意义,使人们对未来产生希望和充满期待,使社会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和趣味。一切似乎都变得不确定和充满风险 (因为没有了理想和信念,生活就像失去了航标和定向针,人们没有了评价行为价值的尺度,一切都模棱两可,无法判断和抉择,人们只能手足无措地茫然四顾)。甚至于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走的道路的性质都越来越没有把握。这种生活境遇使人们开始考虑这一问题,面对黑暗、怀疑和否定,人们是否还能够从生活中寻觅到意义和价值?冲突的要素是否终将会服从某种伟大的建设性理念。
然而要摆脱这种生活境遇,使生活是有意义的,人们就不能沉溺于流逝的瞬间,而必须追求某种包含一切的目标,追求理想,坚定信念,超越人类自身的特殊范围和有限性。因为人的生活和宇宙的生活无可解脱地联在一起,人必须确定它在宇宙中的位置,界定自身是谁,从何而来?去往何处?归宿为何?人要干什么,并据此来规范和调节其自身的活动,而避免沉溺于任何有悖于万物之理、有悖于他自身的诚实本性的幸福。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以下方面的限定性:其一,我们居住于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上,而无处可逃。我们必须在这个限制之下,借我们居住之处供给我们的资源而成长。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以保证人类的未来得以延续。这是个向每个人索取答案的问题,没有人能逃得了它的挑战。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的行为都是对人类生活境遇的解答:它们显现出我们心中认为那些是必要的、合适的、可能的、有价值的。这些解答都被“我们属于人类”以及“人类居住于此一地球之上”等事实所限制。当我们考虑到人类肉体的脆弱性以及我们所居住环境的不安定性时,我们可以看出,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为了全体人类的幸福,我们必须拿出毅力来确定我们的答案,以使我们的眼光远大而前后一致。这就像我们面对一个数学问题一样,我们必须努力寻求答案。我们不能单凭猜测,也不能希图侥幸,我们必须用尽我们能力所及的各种方法,坚定地从事此事。我们虽然不能发现绝对完美的永恒答案,但是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全部才能,我们必须不停地奋斗,来找出近似的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必须针对“我们被束缚于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上”这个事实,以及我们居住的环境所带给我们的种种利益和灾害。其二,我们并不是人类种族的唯一成员,我们四周还有其他人,我们活着必须和他们发生联系。个人的脆弱性和种种限制,使得他无法单独地达到自己的目标。假使只有他孤零零地活着,并且一向只凭自己的力量来应付自己的问题,他必然会灭亡掉。他无法保持自己的生命,人类的生命也无法延续下去。他必须和他人发生关系,此种关系是因为他的脆弱、无能和限制所造成的。个人为自己的幸福,为人类的福利,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和别人发生关联。因此,对生活问题的每一种答案都必须把这种联系考虑在内:他们必须顾及“我们生活于和他人的联系之中,假使我们变得孤独,我们必将灭亡”这个事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和目标是:在我们居住的星球上和我们的同类合作,以延续我们的生命和人类的命脉。我们要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和这个问题与目标相协调。其三,我们还被另一种联系束缚住。人类有两种性别,个人和团体共同生命的保存都必须顾及到这件事实。爱情和婚姻属于这种联系。每一个人都不能不对这一问题避而不答。这3个限定性的条件,构成了3种问题:如何谋求一种职业,以使我们在地球的天然限制下得以生存;如何在我们的同类中获取地位,以使我们能互助合作并分享合作的利益;如何调整我们自身,以适应“人类存在有两种性别”和“人类的延续和扩展,有赖于我们的爱情生活”等事实。基于此,阿德勒认为生活是有意义的,人类生活于“意义”的领域之中。不过,那些只属于私人的意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意义只有在和他人交往时,才有存在的可能。我们的目标和动作也是一样的,它们的唯一意义,就是它们对别人的意义。因此,他认为,所有真正“生活意义”的标志是:它们都是共同的意义——它们是别人能够分享的意义,也是能被别人认定为有效的意义。其次,奉献乃是生活的真正意义。所以生活的意义是对人类全体发生兴趣,并且也能够努力培育爱情和社会兴趣。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们想要增加社会利益的结果[8]。心理学家给我们提供了人类生活的意义的一种解答,或许这些答案是带有根源性的,所以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去追问这种意义的根源性,以寻求更为可靠的终极性意义尺度。正因为此,人类对终极价值有着与日俱增的兴趣,才有了对生命存在的本源性意义的探讨,以求对存在的意义作出解释和肯定。而人类对本体论的探讨体现的正是这种需求。
四
因此,本体论寻求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和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并不是超然于人类历史之外的玄想或空想,而是人类试图通过对终极存在的确认和解释的占有,来奠定人类自身在宇宙中安身立命之本,即寻求人类存在的最高支撑点。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的关怀,置身于人类对其自身存在的终极价值的关怀。所以海德格尔说,人类是唯一把自身存在作为问题来考察的实体,或者说:“所有物种中只有人类被称为存在之音,人类经历着所有不可思议之奇迹,这正是人存在的原因。”[9]而人类哲学的全部任务或秘密就在于研究人和解释人,“形而上学就是此在本身。因为形而上学的真理就寓于此深不可测的底层,所以就是最接近它的近邻也经常有把它认得大错特错的可能。”[10](P152)由是,在哲学史上,这一问题也成为人理解自身、理解世界的主题,“自然是人的法则”,“人是万物的尺度”,“上帝是最高的裁判者”,“理性是宇宙的立法者”,“科学是推动宇宙的支点”,“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认为自然立法”等等,这些表达特定时代精神的根本性哲学命题,就是哲学本体论历史地提供给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的支撑点。它们历史地构成人类用以判断、说明、评价和规范自身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也就是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从西方哲学看,从被黑格尔称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人物苏格拉底开始,人们就试图引导自身离开各种特殊的事例去思考普遍的原则,追究人们用以衡度自身言行的真善美的尺度。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求索,就是对人的终极价值的寻觅,这一主题贯穿了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中世纪哲学(如奥古斯丁等),直至康德、黑格尔等的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对此有精辟的概括:“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家们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或被用于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 ”[11](P11)“因此,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把自己看作是由科学、道德、艺术或宗教所提出的知识主张加以认可或揭穿的企图。”“哲学相对于文化的其他领域而言能够是基本性的,因为文化就是各种知识主张的总和,而哲学则为这些主张进行辩护。”[11](P1-2)海德格尔更明确地体认到这一问题,他认为,“形而上学奠基的难题在对人的此在的探讨中,即在对人的最内在的根据、对作为本质生存之有限性的存在领域的探讨中,找到了它的根。对此在的这一探讨要问的是,如此规定的存在者具有何种本质。就其本质在于生存而言,对此在本质的探讨就是生存论的探讨。但对存在者的存在的任何探讨,尤其是对存在者——其存在机制包含着作为存在领悟的有限性——的存在的探讨,都是形而上学。”[10](P119)所以寻求生命意义的根基,也就是寻求对人类具有普适性或普遍约束性、规范性、导引性的终极价值。这种终极价值是评价和判断人类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最高标准,而人类所追求的一切较小的目标都只能是达到这种终极价值的途径和手段。对终极价值的关怀,构成了哲学本体论追求的最激动人心的至上价值追求,也是人类全部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源泉。
所以本体论追求和承诺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既是理性指向的永恒目标,也是人类理性公开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对象。作为理性的永恒目标,本体论是在形而上层面上以理性的形式表达了人类理性对其建构的全部科学对确定性、必然性、简单性和统一性的寻求。比如化学探讨基本元素、物理学寻找基本粒子,生物学寻求细胞和遗传基因等,正是这种终极关怀的体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在寻求基本原理,这本身就是终极解释的表现方式。恩格斯强调思维是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认为:“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12]哲学本体论追求的正是植根于人类理性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至高的理想中。美国哲学家M.W.瓦托夫斯基也认为:“不管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推动力都是企图把各种事物综合成一个整体,提供出一个统一的图景或框架,在其中我们经验中的各式各样的事物能够在某些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13](P14)而这种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之所以无法拒绝,是因为人类“存在一种系统感和对于我们思维的明晰性和统一性的要求——它们进入我们思维活动的根基,并完全可能进入到更深处——它们导源于我们所属的这个物种和我们赖于生存的这个世界。”[13](P13)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本体论追求是不可避免的,也无法取消的。由是,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本体论所蕴含的这3种内涵,正是人类理性追求的形而上基础,它们互为前提,相互支撑,始终并存,构成了人类理想主义的最深刻的思想源泉。所以,作为人类理性超越性追求的本体论基础——其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其合理性在于,人类总是悬设某种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理性目标,否定自己和自身所处的世界的现实存在,把现实变为更为理想的现实。因此,本体论追求的意义就在于,它启发人们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永远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二者之间相互对峙,但又不相互取代,彼此从不打破这一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类打通了至上的形而上理想追求和世俗生活目标追求的通途,使崇高和尊贵的人性之美的高尚求索和平实无华的人生追求统一起来,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永远保有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这也是理想主义之所以能够保持其内在魅力、保持其常新性的体现,也是理想主义在保持自身对崇高性的追求时能够避免把崇高异化为某种僵死的存在的重要保证①。
注:
①本部分借鉴了孙正聿老师的著作《崇高的位置》和《哲学修养十五讲》中的一些观点。
[1][法马特.柏拉图与神话之镜[M].吴雅凌译.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4.
[2]叶秀山.“亚里斯多德与形而上学之思维方式”[A].永恒的活火[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196.
[3]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6.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385.
[5]孙正聿.崇高的位置[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23-24.
[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M].杨照明,艾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8]陈珺.心灵简史[M].北京:线装书局,2003.35-40.
[9]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42.
[10]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M].上海:三联书店,1996.
[11]查·罗蒂.哲学和自然之境[M].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中译本作者序及导论.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7.
[13]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M].杨春友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湜得】
Abstract:Human rationality always desires for an explanation of the world and confirmation of the status and values of man in the world at the deepest level.Such a desire is a rational pursuit of the ultimate nature,or is itself a kind of ultimate care,and accordingly it forms the epistemological and evaluation scale and build the human ideal world,which constitutes the ultimate concern of ontology.Ontology originates from the childhood of human philosophy,and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human conditions or survival styles unique to human beings.It embodies the human pursuit of the ultimate origin of all things,manifested specifically in three areas:the pursuit of the ultimate unity of the world’s ultimate existence;reflecting the ultimate explanation for the unity of knowledge;interrogating the ultimate value of unity of meaning.They constitute the pursuit of human reason beyond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Key words:rationality; ontology; ideal
Beyond the Pursuit of Rationalism With Ontological Basis
SONG Qing-hua
(Colleg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tudies,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engzhou,Henan,471003)
B 016
A
1000-260X(2010)06-0026-08
2010-09-07
宋清华(1968—),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河南科技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价值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