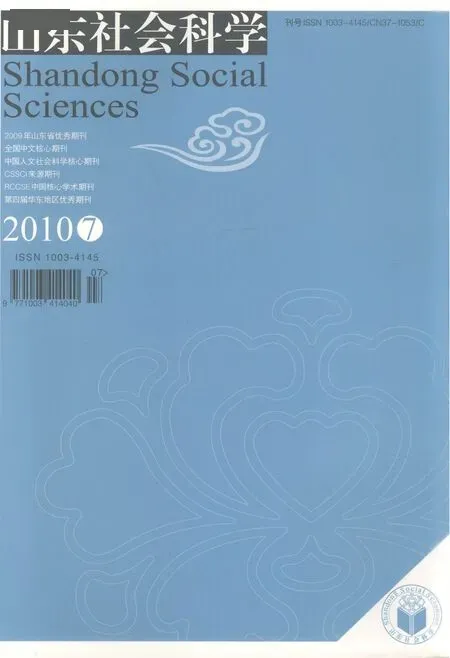沂蒙红色文化的文化生态学考究与辨析*
韩延明 魏本权
(临沂师范学院,山东临沂 276005)
沂蒙红色文化的文化生态学考究与辨析*
韩延明 魏本权
(临沂师范学院,山东临沂 276005)
借鉴和采用文化生态学的学科范式与理论方法,对孕育生成沂蒙红色文化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环境进行生态学意义上的考察,从“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角度,探讨沂蒙红色文化的特殊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与其它区域红色文化不同,沂蒙红色文化是以普通沂蒙大众为主体的红色文化,这与作为革命根据地的沂蒙山区独特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是密不可分的。
红色文化;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学;沂蒙红色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近年红色文化研究的基本学术取向
2004年,刘寿礼在《苏区“红色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研究》一文中正式提出了“红色文化”概念①刘寿礼:《苏区“红色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研究》,《求实》2004年第7期。,嗣后,红色文化的研究逐渐进入学术视野。从“革命文化”向“红色文化”概念的转换,意味着近年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革命精神、革命文化与革命道路等研究话语的重大转型,红色文化在新的学科背景和理论范式下,突破了以往革命文化史研究的思路,逐渐融入文化研究领域,并取得了较大的学术进展。
目前,学界在红色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功能,以及红色文化产业的开发与利用等问题上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综观目前我国关于红色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展开,可以发现学界基本沿着以下几个理路进行探讨。
其一,红色文化与红色教育。红色文化在政治教育、品德教育、文化传播、精神传承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决定了其自身的资源属性。因此,红色文化资源成为重要的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社会教育与公民教育的有效资源。②张泰城,魏本权:《论红色资源在当代中国公民教育中的价值》,《求实》2009年第4期。③陈世润:《论红色文化教育的社会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年第4期。将红色文化资源引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革命老区高校思政教育的一大亮点和显著特色。以中国革命道路、革命文化、革命精神为内涵的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红色教育”已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途径。伴随着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新的理念的提出,红色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提供了丰厚的“优质资源”。
其二,红色文化与红色旅游。红色旅游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④何光暐:《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推进三个文明建设》,《求是》2005年第7期。2004年 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就发展红色旅游的总体思路、整体布局和主要措施做出了明确规定,成为指导和推进红色旅游的纲领性文件。《纲要》中规划的 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将全国革命老区自然而有机地串联起来。学界对红色旅游的保护、利用、规划、开发的研究,对红色旅游特征、原则、发展路径的界定,以及红色旅游产业、红色旅游节会、红色旅游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的探讨,极大地推动了红色旅游业快速而健康的发展。
其三,红色文化产业开发研究。把红色文化产业开发纳入革命老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红色文化产业开发的需要,红色文化资源禀赋、区域红色文化资源赋存、红色文化资源评估、红色文化创意与产品演绎等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极大关注。
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红色文化产业开发,构成了当前红色文化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基本学术取向,但是红色文化研究仍然存在诸多缺憾和不足之处。目前,学界对红色文化的研究还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缺乏对红色文化概念的内涵外延、学科定位、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也缺乏对红色文化历史的细致梳理,更缺乏对红色文化研究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在此背景下,借鉴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深化红色文化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红色文化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需要建构新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概念的转换,本身就意味着需要创立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在深化和扩展红色文化研究理论方法方面,有的学者已从文化发生学角度进行了初步探索。文化发生学方法运用于红色文化研究,就是从红色文化发生根源、发生基础、发展环境、发生过程的角度,探究红色文化在革命区域如何与当地社会文化结合,衍生出新型的文化形态,并对此文化形态的动态过程进行考察描述,以获得关于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革新的规律。在此视角下,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楔入不同革命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必然结果,是中国近代不同区域文化发展演变与马克思主义相互结合的必然生成;由此才诞生了中国革命文化的不同形态——井冈山文化、延安文化、苏区文化、沂蒙红色文化等。①陈敬,魏本权:《红色文化的文化发生学考察:以沂蒙红色文化为中心》,《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但我们认为,沂蒙红色文化的文化发生学研究尚未回答沂蒙红色文化的特殊文化特征与文化模式和沂蒙地区生态环境的关系。以井冈山文化、延安文化、苏区文化、沂蒙红色文化等为代表的区域性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但它们在特定的历史境遇和区域环境下,形成了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共同性的个体差异性。如何认识这些红色文化类型的本质特征,需要借鉴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进行分析探讨。
本文拟尝试借鉴和采用文化生态学的学科范式与理论方法,对孕育生成沂蒙红色文化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环境进行生态学意义上的考察和分析,进而从“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角度,探讨沂蒙红色文化的特殊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源流。
二、理论与方法:文化生态学与红色文化研究
在文化生态学视野下,沂蒙红色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外来马克思主义与沂蒙区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沂蒙红色文化是中国红色文化的区域形态,是近代沂蒙人民在革命进程中的文化创造,沂蒙地区独特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人文生态造就了独特的沂蒙红色文化。以“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为主要体征的沂蒙精神是沂蒙红色文化的文化内核,体现出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不同的外在表征和内在品格。
沂蒙红色文化与其它中国红色文化相比,既具有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共性,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独特个性。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核心内涵的井冈山精神,是井冈山红色文化的“文化内核”,它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革命信念和勇于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巨大勇气,这是与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入农村、实现红色武装割据、建立中国革命基地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坚定的革命信念是这一精神的主题,体现了井冈山精神的最显著特征”。②孙翠萍:《西柏坡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内在联系》,《河北日报》2003-06-09。如果没有必胜的革命信念,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不可能的,井冈山文化的价值,最主要的一点即体现于此,它为随后 20余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提供了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以延安精神为主要内涵的延安红色文化,其内涵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敢于胜利,艰苦创业;其核心和主题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延安红色文化,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党政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延安时期所确立的抗战路线、延安整风、中共七大精神,以及毛泽东思想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所体现的正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根本思想路线。
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脉相承的西柏坡精神,是西柏坡红色文化的“文化内核”。西柏坡红色文化的特殊文化特征,集中体现在七届二中全会路线上。它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本质特征是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它所体现的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道德情操的高度要求和行为规范价值,是对延安时期党的思想路线的承继、弘扬与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贯穿在井冈山红色文化、延安红色文化、西柏坡红色文化中的核心理念,是党在不同革命状态下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对党的指导思想和思想路线的高度概括和总结。这些红色文化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革命状态下的精神选择与信念,是一种上层文化,是一种“政党型”的红色文化。沂蒙红色文化恰恰相反,大众性、基层性、平民性是沂蒙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爱党爱军”、“无私奉献”是沂蒙人民的崇高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它所体现的是人民对革命和党政军的热爱、支持与奉献;“开拓奋进”、“艰苦创业”体现了沂蒙人民不畏艰难困苦、不断创新创业的拼搏精神和顽强意志。因此,从区域红色文化的内涵来看,沂蒙红色文化体现为大众性、平民性、基层性,是一种“人民型”的红色文化。以红嫂、沂蒙母亲、识字班、英雄孟良崮、火线桥为符号和载体所显现的沂蒙红色文化,是以沂蒙人民对党、革命和人民军队的忠诚、热爱与无私奉献精神为基本品格特征的。这种水乳交融的红色情怀,虽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其它红色区域之内,但在沂蒙地区更为凸显,更为昂扬。
我们说,无论是苏区,还是抗日根据地、解放区,都是中国共产党依托的革命基地。然而何以在不同的革命区域内,形成了具有不同特征的红色文化类型,目前学界鲜有学者讨论这一问题。学界往往更多地关注了红色文化类型的不同特征,而忽略了形成这些不同特征的原因。本文就是想尝试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对此进行探讨。
从目前来看,在运用文化生态学对红色文化进行研究方面,仅见汤红兵从文化生态学视角对湘鄂西红色文化的形成原因所作的研究。他考察了湘鄂西红色文化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其中贫苦百姓对革命的渴望、大革命留下的革命基础、政府外公共权力——农民协会与渔民协会的作用,构成了湘鄂西红色文化形成的社会生态。①汤红兵:《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湘鄂西红色文化的形成原因》,《党史文苑》(学术版)2006年第12期。除此之外,将文化生态学运用于红色文化的研究,尚不多见。
文化生态学是 20世纪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它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来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的一种学说,是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之间的交叉和边缘学科。1870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 (Ernst Haeckel)最早使用“生态”概念,当时是用来指生物的聚集。1955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J·H·斯图尔德出版《文化变迁论》一书,首次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倡导建立专门学科,以探究具有地域性差异的特殊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斯图尔德提出“文化即适应”(Culture is adaptive)这一观点,也就是说,文化生态学正是要探讨人类的文化进化与自然、生态和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②杨文安:《斯图尔德与文化生态学》,《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斯图尔德完整地阐述了其主张的文化——生态适应理论,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 (Cultural Ecology)。重点阐明不同地域环境下文化的特征及其类型的起源,即人类集团的文化方式如何适应环境的自然资源、如何适应其它集团的生存,也就是适应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③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人文地理》2005年第4期。
可见,文化生态学是一门将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和系统论的思想应用于文化学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研究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与环境 (这里指广义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关系。因此,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是文化生态学关注的主要对象。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著名文化学家冯天瑜将文化生态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他指出:“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其使命是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适及内在联系。”作为文化生态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生态”(或称“文化背景”),主要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凭借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它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文化生态本身又构成一种文化成分。①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8页。因此,文化生态学关注的核心论题,是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即特殊的区域文化特征与其植根的文化背景之间到底有何关联。
三、文化与环境: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沂蒙红色文化
把“环境”纳入到文化研究之中,是文化生态学的最显著特征。一定的文化类型必然有孕育它的文化生态。1920—1940年代沂蒙地区的自然、社会与人文生态,是沂蒙红色文化形成的基础。错综复杂的地貌结构形态,久远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悲壮恢宏的革命斗争洗礼,与时俱进的社会实践创举,构成了沂蒙革命老区独具一格的地情生态特征。而沂蒙山区的生态背景又决定了沂蒙红色文化的独特性质。
1、自然生态
虽然,文化的不同不能直接归因于环境的不同,但文化本身不是静止的,对自然条件既能适应又能改变。文化区是在一个环境一致性的区域内发生的行为一致性的结构。因文化体现了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所以文化和自然区域一般有共同边界。②[美]J·H·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世界历史》1988年第6期。沂蒙山区这一特定区域生态就是沂蒙红色文化得以孕育生成的温床。
狭义的沂蒙地区,大致上相当于古沂州府所属地域,以今临沂市为中心。沂蒙地区,得名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山东省委在此创立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山东省委 (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山东分局)在胶济铁路以南、津浦铁路以东、陇海铁路以北、黄海以西地区,先后创建了鲁中、滨海和鲁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这些根据地的中心地带统称为沂蒙抗日根据地”。③崔维志,唐秀娥:《沂蒙抗日战争史》,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年版,第78页。在区域文化研究的视野下,沂蒙地区是指以沂蒙山区为中心,以现临沂市为主体的山东东南部地区。这一区域大体上包括今临沂市、日照市、泰安市、莱芜市和枣庄市的全部;淄博、潍坊和青岛三市的南部和济宁市的东部以及江苏省的北部。“沂蒙地区在地理环境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居山、顺河、临海”。④刘英华:《沂蒙文化发展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3页。其中,山地占总面积的 33%,丘陵占28%,平原占 36%,涝洼占 3%。地势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倾斜。山地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部,沂山、蒙山、鲁山、尼山四大山脉,计有大小山头 7000余座,海拔高度大都在 200—500米。此外还有不少由流水侵蚀造成的被称之为“崮”的桌状山,较为著名者即有 72崮之多。丘陵主要分布在沭河以东,沂河以西局部地区亦有分布,海拔高度多在 50—200米之间。平原以沂、沭河冲击平原最为著名,集中分布于本区南部的临沂、郯城、苍山等区县,并与苏北平原连为一体,海拔一般在 30—50米,盛产稻米,是沂蒙地区的重要粮仓,被誉为“山东江南”。区境内沂河、沭河、中运河、滨海四大水系,共有较大支流 1035条,中小支流 15000余条,流域面积占全区面积的 70%以上。流向区外的汶河、潍河、淄水将沂蒙地区与鲁西南平原和胶莱平原连结在一起。沂蒙地区的东部即是广阔的海岸线,濒临黄海,既有鱼盐之利,兼通华北苏浙,在革命时期的战略基地中,沂蒙地区的区位优势是难有与之匹敌的。
之所以选择在以蒙山、沂山为纵深的广阔区域建立革命战略基地,毛泽东曾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谈到:“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424页,第419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沂蒙山区的战略地位。早在 1938年 1月 15日,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指示山东省委: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方向,应以鲁中为中心,依托新泰、莱芜、泰安等地原有的工作基础,努力向东发展,尤以控制蒙阴、莒县等广大地区为重心。1938年 5月,毛泽东指示当时的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等人,抓紧创建沂蒙山区中枢根据地。
沂蒙地区的区位优势为创建鲁中、鲁南、滨海等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复杂的地质结构和类型多样的地貌,既为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天然的屏障,也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创造了条件;沂蒙地区的独特地理环境,连绵起伏、层峦叠嶂的山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广阔的战略纵深和回旋区间;南部粮仓为革命军民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纵横交错的河流形成革命根据地之间的区际屏障。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1939年沂蒙抗日根据地随之真正地建立起来。
2、社会生态
文化生态系统,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生计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它不只讲自然生态,而且讲文化与上述各种变量的共存关系。①苗红:《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庆阳农耕文化与区域环境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除了影响区域文化特征的自然生态因素以外,社会生态是更为鲜明的要素。文化的社会生态,是指文化形成的社会背景。
民国建立以来,沂蒙地区深受匪患、兵祸之困扰,造成社会经济凋敝,生灵涂炭,民生艰难,生计困顿。这一状况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始终没有大的改观。民国以后的北洋军阀之间历次战争,临沂必为兵掠之地。民国初年的莒县,(民国十五六年后)“市面情形为之一变,又兼各项税捐,有加无减,军队往来,供应浩繁,土匪纵横,抢架勒赎,商农交困,因之殷实商号闭歇时有所闻。至十九年高军之难,地方损失更不可统计,外商纷纷歇业,本商愈难维持。二十年后,世界经济之压迫,……本境商况,遂有一落千丈之势”。②庄陔兰:《重修莒志 》卷 38。临沂虽“地值温带,气候和煦,兼具大陆海洋二性质,故百昌怒生,矿脉纵横,为天然物之陈列场。然农学不讲,树艺无术,其开采诸煤矿者,亦第狃于土法不足胜算。故饥馑时告,乾没恒闻且来”。③《临沂县志》卷三·民风,1917年。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鉴于沂蒙山区特殊的战略位置、地理环境和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开创了以泰山、蒙山、抱犊崮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一经建立,各项建设随即展开。1940年 7月底,山东省联合大会在沂南县青驼寺召开,大会制定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大纲》,选举产生了全省统一的行政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 (简称山东省战工会),下设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教育、民众动员 5个组,战时的政治建设与抗日军事战争同步推进,极大地改变了沂蒙地区原有的政治生态。不久,按照三三制原则,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在临沂地区普遍建立起来,并形成了鲁中、滨海、鲁南三大战略区,揭开了沂蒙军民革命斗争历史的新篇章。当时的沂蒙有“小延安”之称,是我党华东和山东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山东党政军机关、华东局机关长期驻扎在这里,八路军第115师、八路军第一纵队、新四军、华东野战军长期在这里转战,山东省政府在这里诞生,《大众日报》在这里创刊,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在这里创建;革命根据地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工作,多是在这里先行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向全省其它地区推广的。
通过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合作运动和生产救灾运动,沂蒙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在保障战争供给的同时,改变了沂蒙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获得了沂蒙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响应,也极大地改变了沂蒙地区经济落后、政治混乱的局面。沂蒙人民从社会变革中体验到中国共产党给沂蒙地区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支持、拥护、爱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也就成为自然之举。沂蒙红色文化也由此获得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并逐步走向成熟。
3、人文生态
对长期处于封闭、内敛状态的沂蒙人民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全新的信仰和意识形态。沂蒙红色文化的孕育生长,离不开其母体——厚重的沂蒙文化。“沂蒙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它是指长期生活和活动在沂蒙山区及其辐射地带的人们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淀;是民族文化因受到沂蒙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历史人文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形态”。④于连凯,于澎:《沂蒙文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1页。底蕴丰厚的历史文化,为沂蒙红色文化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也造就了 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植入沂蒙大地的历史基因。
沂蒙大地,圣气灵人。宗圣曾子、书圣王羲之、兵圣孙膑、智圣诸葛亮、算圣刘洪等均诞生于沂蒙,因而也使沂蒙文化璀璨夺目、彪炳史册。沂蒙文化源远流长,连绵播迁,具有鲜明的原生性、经世性、交融性与连续性。从沂蒙地区方志的记载可以看出,沂蒙区域民风醇厚古朴,民俗崇礼尚仪。“临沂古为琅琊,代产名贤。……或名贤耆德,望重乡里;或孝友厚义,天性独醇;或文学艺术,足供欣赏;或挺身御寇,勇烈非常;或医术精通,济世活人;或旷逸流寓,足励末俗”。⑤《续修临沂县志》,临沂市地名委员会重印,1989年版,第207,第240页。“临沂近圣人居,敦诗说礼,渐染有素。女子多以德著,不以才显 ”。⑥《续修临沂县志》,临沂市地名委员会重印,1989年版,第207,第240页。
当时的山东大县莒县,“莒近鲁地,被周公之化,其人多重礼教,崇信义,士风醇厚,绝无奔竟,民性驯朴,号称易治 (《青州府治》)。其地襟淮带沭,据沂赣之上游,摄青齐之南鄙,士重礼节,耻奔竟,民朴而愚,不见粉华藻饰之习,饶五谷薪蔬,不当孔道,无支候送迎之费,素称易治 (《莒州题名记》)。莒俗雄博逊齐,啬守近鲁,得为远大,失为近小,庶民终岁袯襫,自食其力,士敦行宜,以夸毗为耻,土否瓦瓿,绮罗不御,盖其习惯,犹有古朴之遗风焉 (《刘柘山遗集》)”。①庄陔兰:《重修莒志》卷 42,卷 42。方志还记载,莒县“男女关系,尚属平等,女治内,男治外,其处分家事之权一也。男有继承权,而女有享用权,其有享受先人遗产之权一也。母多爱女,父多爱子,其见爱于亲一也(节录新河志)。莒俗近之,故处莒人家庭而倡男女平等之论,殊不合于事实。况嫁女而分财带产者,时有所闻乎 ”。②庄陔兰:《重修莒志》卷 42,卷 42。
处于沂蒙山区腹地的费县,“鲁论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汉书地理志其民有圣人之教化,又曰地狭民众,有桑麻之业,又曰其好学犹愈于他俗”。古俗谓费县“学校颇重士气,乡里犹有古风,守耕读,急赋税,婚姻不论财帛之多寡,设教不计束脩之厚薄,犹有先王之遗泽焉,但不尚积贮,中人以下多无三年之蓄,一经水旱,易至冻馁,又男耕而女不织,妇人往往坐食,亦俗尚之偏也”。③《费县志》卷一·疆域村社风俗。
在传统儒家思想观念熏陶下,方志所反映的近代以前的沂蒙人民崇尚礼仪、民风淳朴、务实持重,重视教育,男女地位相对平等。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沂蒙文化,造就了沂蒙人朴实、善良、勤劳、勇敢、智慧、自强不息的优秀品质,为沂蒙人民始终走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沂蒙人民逐渐从传统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中解脱出来,走出蒙昧和落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沂蒙人民固有的优秀思想道德和朴素的阶级感情转化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高度政治热情,激发起为翻身解放、实现革命理想而敢于战斗、勇于奉献的强大精神力量。在长达十二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沂蒙人民前仆后继,南征北战,十万英雄儿女血洒疆场,百万民众拥军支前。他们“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他们宁可自己吃糠咽菜、挨饿受冻,也要把仅有的粮食、被褥送给人民军队;宁可自己住茅棚、睡地铺,也要把房子、床板腾给人民子弟兵;宁可自己流血、牺牲,也要掩护、抢救伤病员战士。在沂蒙这片红色热土上,先后发生过大小战斗两万余次,可以说是“村村有红嫂,家家有烈士”。当时,沂蒙革命根据地共有 420万人,其中 20万人参军入伍,120万人参战支前,11万人战死疆场,为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经历了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经历了减租减息、抗击日寇、参军拥军、大生产运动、土地改革运动、支前运动之后,沂蒙人民扬弃了传统道德观,涌现出了用乳汁养育伤员的红嫂明德英、抚育战时革命后代的沂蒙母亲王换于等普通的沂蒙妇女形象。革命也动员起了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沂蒙百姓,以识字班为代表的沂蒙女性,组织妇救会,做军装、纳军鞋,送军粮、运伤员,用自己的行动践行对党和军队的无私奉献和无比热爱。沂蒙地区的男性青年,走出家门,走上战场。沂蒙六姐妹、火线桥、英雄孟良崮的故事家喻户晓……沂蒙地区的各个社会群体,以自己的行动印证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启蒙所带来的高度文化自觉,践行了“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几十年来,沂蒙精神始终伴随着临沂革命老区快速发展的每一个历史脚步,成为沂蒙红色文化中最深刻的特质与精髓。
“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的土壤联系着”。④陈绪新:《文化生态:以一种对话的视野回救现代性》,《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年第2期。正是沂蒙红色文化植根的土壤养育了勤劳淳朴、重礼尚义的沂蒙儿女,在革命的感召下才出现了无私支持革命、献身革命、支援战争的无数沂蒙个人和先进群体。在文化生态学“文化即适应”观点看来,置入沂蒙地区的外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适应了沂蒙地区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环境,造就了自身的特殊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作为一种沉甸甸的、血染的历史文化,沂蒙红色文化将继续闪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责任编辑:艳红)
G122
A
1003—4145[2010]07—0057—06
2010-03-10
韩延明 (1959-),山东肥城人,临沂师范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沂蒙文化研究;
魏本权(1976-),山东莒南人,临沂师范学院文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系副教授。
本文系 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09BKS04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