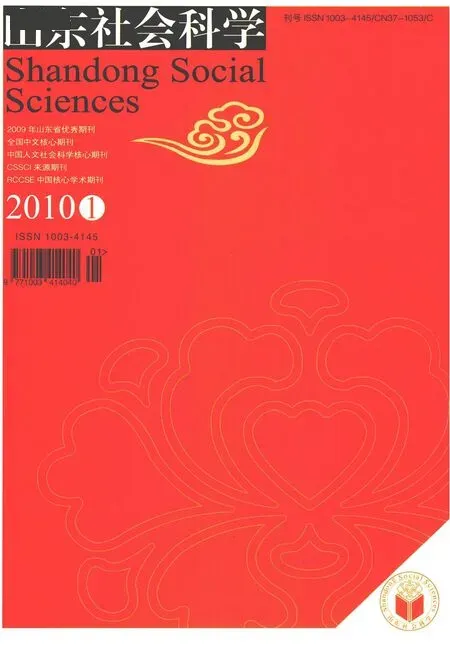三十年法治实践与法学研究的使命①
姜福东
(青岛科技大学政法学院,山东青岛 266061)
三十年法治实践与法学研究的使命①
姜福东
(青岛科技大学政法学院,山东青岛 266061)
根据衡量法治是否成熟的两个重要指标,法学研究被历史地赋予了两大使命:良法的创制与善治。从三十年的法治实践来看,我国法学研究的第一个使命——参与良法的创制完成得不错;但仍需努力。第二个使命——参与善治,尚未引起制度层面足够的重视,需要法学研究者加快学术成果向法治实践的转化。
法治;法学研究;良法;善治;方法论
一、法学研究的两大使命
2008年 2月 28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白皮书洋洋洒洒近三万字,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的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制度、依法行政与建设法治政府、司法制度与公正司法、普法和法学教育、法治建设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介绍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份我国政府首次发表的法治建设白皮书,给法学理论界系统回顾、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三十年法学研究工作的得与失,提供了权威的参照系。
法治有其丰富的内涵,学术界对此早已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相关文献可谓不可胜数,笔者无须赘言。但从法治的基本要义来看,无非是“良法”加“善治”。首先必须制定良法。这一点,正如著名人权专家徐显明教授所指出的:法治的要义在于依照公平正义原则平衡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合理配置权利与权力,并将其制度化。①徐显明主编:《法治与社会公平》,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代序第 2页。其次必须善于根据制定出来的良法进行治理,也就是冉昊先生所说的根据已知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稳定的规则来进行治理,其中特别强调法律规则所固有的程序性、普适性和恒定性。②冉昊:《法治和法学》,载张士宝主编:《法学家茶座》(第 1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 23页。而且,在此基础上要求动态地“善治”。因此,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成熟的法治国家,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是法律创制(包括法律制定、修改、废止)得好不好,二是法律实施 (包括执法、司法、守法)得好不好。
与之相适应,一个国家的法学研究也被赋予了两大使命。第一个使命是推动良法的创制,第二个使命是促进良法的治理。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法学研究,可以说第一个使命完成得不错,但仍需努力;第二个使命则尚未引起制度层面的足够重视,需要法学研究者奋发有为。
二、法学研究与法律创制
1979年,邓小平指出:“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我们的法律是太少了,成百个法律总要有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只是开端。”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89页。邓小平讲这番话时,我们的法律寥寥无几;到今天,我们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据《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介绍,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经制定了 229件现行有效的法律,涵盖了全部七个法律部门。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单从法律创制的数量角度而言,这已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为我们的法律是从无到有,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的。
在这辉煌的立法成就背后,不可忽视的是默默耕耘的法学研究者的心血和汗水。著名学者江平教授是我国民法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是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的主要起草人,也是《公司法》、《证券法》等一批法律的主要起草者之一,还是《合同法》起草组组长,他为改革开放头二十年法治发展呕心沥血,功勋卓著。著名学者江伟教授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早在 1979年,他就参加了《民事诉讼法》的起草小组,2003年又参与起草了《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为《民事诉讼法》起草、通过、修改和完善作出了突出贡献。还必须强调的是,“法治入宪”是与以中国社科院王家福研究员为首的法学专家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分不开的。1996年,王家福先生在中南海法制讲座中,专门阐释了《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我国最终确立依法治国方略提供了理论基石。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明确宣布,要实行依法治国。到 1999年修改宪法时,在宪法第 5条新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定 (宪法修正案第 13条),标志着中国从此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而“人权入宪”则与以徐显明教授为代表的广大法理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2004年修改宪法,在宪法第 33条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 (宪法修正案第 24条),中国的人权发展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实际上,这句话原本正是徐显明先生的提议。举世瞩目的《物权法》的创制,与以梁慧星研究员、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民法专家们的长期努力是分不开的。梁慧星和王利明先生分别带头起草了《物权法》草案专家建议稿,全国人大法工委就是在这两个建议稿的基础上,拟定了《物权法》草案并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②对 于《物权法》的起草经过,梁慧星在其著作以及讲座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参见梁慧星:《生活在民法中》,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第85-86页。从1979年《刑法》到 1997年《刑法》,刑法典的创制和日益完善更是凝聚了高铭暄等一批刑法专家学者的心血。一句话,《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附录中所罗列的 229件现行有效的法律,无一不是包括法学研究者在内的广大法律人、法治建设者们三十年智慧与汗水的结晶。
如果从良法的尺度来衡量,法学研究第一个使命的完成情况可谓有得有失。虽然白皮书指出: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和立法质量不断提高,法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确保国家权力正确行使等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不过,这更多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实际上良法的创制还存在诸多不足。的确,过去三十年的法学研究对法律创制作出了重大贡献,通过参与专家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许多法学研究的成果被转化成为现行法律。在法学家们的帮助下,我国制定了一批可称为良法的法律,尤其是近年来修改或者制定的《婚姻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足以与发达国家的立法相媲美。例如《物权法》历经 13年起草,草案前后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审议,才最终由全国人大通过并付诸实施。其间还发生了公法学者巩献田教授舌战民法专家,导致《物权法》推迟审议通过的戏剧性一幕。这种专家立法使得《物权法》的科学性、民主性、专业性大大增强。在某种意义上,说《物权法》是一部良法,是法学研究者们的杰作并非过誉。③这 从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一书中,可得到充分的证明。但是,也有许多法律存在着令人遗憾的地方。例如,违宪审查的法律规定、法律解释的法律规定等已经落后于时代潮流,还有一些事关公民自由的法律没有出台,例如《新闻法》、《出版法》等。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法学研究比较薄弱,致使出台的一些法律存在着观念陈旧、笼统简单、操作性较差的缺点。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法律漏洞、法律空白、法律冲突越来越严重。从整体上看,我们距离良法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而权利、正义等法治文化的启蒙工作,还不能说已经彻底完成。
正因如此,徐显明教授主张:“中国当下法学研究的使命仍然在于权利文化的启蒙与推进,在于制度正义的校准与改善。”④徐显明主编:《法治与社会公平》,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代序第 3页。笔者认为,这是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法治实践,尤其是法律创制的经验基础上,对法学研究第一个使命的完成状况的正确判断。就法律创制特别是良法的创制而言,的确可以说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是,笔者同时认为,徐显明先生对于法学研究第二个使命,未免有些强调得还不够。中国法学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方法论的时代。中国当下法学研究已经面临第二个使命,亦即加快法学方法论或曰法律方法论的系统研究,并将研究的成果及时向法治实践层面转化,以促进“善治”。
三、法学研究与法律实施
应该说,三十年来,法学界对人权、法治、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现代文明理念的研究和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很好的启蒙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更多致力于法律特别是良法的创制,法学研究对法的本体论、法的价值论更为重视。这在法理学界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法是什么”、“法应当是什么”的本体论和价值论追问,占领了法理学界研究的主阵地。①有关这段时期国内法理学的研究状况,请参见张文显等:《中国法理学二十年》,《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 5期。纵观改革开放头二十年,我国法理学研究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公民权利文化的启蒙和法治理想国的奠基方面。体现在法治制度实践层面,则以“法治入宪”和“人权入宪”为典型代表。除法理学研究外,部门法研究的许多学者,出于对注释法学的不满,也转向了部门法本体论和价值论的研究。部门法哲学研究成果纷纷涌现,这种风气甚至一直延续至本世纪。②例 如,宋功德:《行政法哲学》,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刘远:《刑事法哲学初论》,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年版;江国华:《宪法哲学》,商务印书馆 2007年版等。
然而,单凭法哲学意义上的苦苦追问,法治国家的建设永远是纸上谈兵,即使这种追问是极具价值的。同样,单凭静态意义的法律而无动态意义的善治,是实现不了法治的,即使创制出来的法律都是良法。良法的呼吁与创制是法治的重要前提,而法律的有效实施和良好运行才是实现法治的关键所在,对法律实施过程中的技艺和方法的探寻和掌握才是重中之重。如何使通过法律 (大体上是良法)“预设的价值、规范在事实的运动场上跑起来,让它们在舞动中获得新生或延续生命”,③郑永流教授的妙语。参见[德]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附录,第 285页。这实属一门科学。尤其是当制定法还存在漏洞、空白、甚至矛盾冲突的时候,通过方法既实现个案正义同时又能维护法治的基本精神,就更是一门独特的学问,有些学者已经较为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学者们日益意识到,应该超越对法治价值及其必要性的呼唤,对法治的研究进入到如何操作的阶段。而法治与法律方法,实有至为密切之关联。法治理想之实现,端赖方法之完善。所以,法律方法论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和关注的重要论题。”④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 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63页。大约在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在三十年法治实践的后十年,法学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开始逐渐增强,方法论研究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受欧陆、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法学方法论的影响,国内民法学界早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前就出现了方法论意识的觉醒。梁慧星先生的《民法解释学》是中国大陆几乎最早的系统研究和介绍法学方法论的专著。梁先生后来出版的《裁判的方法》更是风靡一时,多次重印,成为法学界和法律界的畅销书。随着国外和台湾相关法学著作的翻译和引介,法学方法论在中国大陆日渐成为显学。几乎在民法学界方法论意识觉醒的同时,法理学界也开始了法律方法论的探索。早在 1994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制及其意义——法律解释问题研究》一书中,陈金钊教授就对法律解释学进行了初步探讨。在法理学界,他比较早地提出了:法理学应该率先更新观念,进行从宏观到微观领域的改革,突破口的选择就是方法论。法理学要通过对方法论的深入研究来回应现实。⑤陈金钊主编:《法理学——本体与方法》,法律出版社 1996年版,前言第 1页。法理学界从 2000年起已举办了多次方法论学术会议,对于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已渐成星火燎原之势。⑥有关法理学界法律方法论的研究状况,请参见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 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63页以下。刑法学界对方法论的研究虽然晚于民法和法理学界,但其取得的成就还是比较突出的。我国 1997刑法典制定得较为完善,因此刑法学界起初主要满足于刑法典的法条注释。后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新的情况和案例不断涌现,需要理论界、实务界对刑法适用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于是刑法学界的方法论意识日渐浓厚。2004年在深圳召开的首届刑法方法论论坛,标志着刑法学界开始关注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以陈兴良、张明楷等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刑法方法论研究方面走在了学界前列。⑦例 如,陈兴良主编:《刑法方法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梁根林主编:《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等。另外,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研究近年来也开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方法论问题。⑧例如,范进学:《宪法解释的理论建构》,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黄竹胜:《行政法解释的理论建构》,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等。中国的法学研究在以往本体论、价值论研究的基础上,似乎出现了向方法论的转向。
于是,在我们眼下总结和反思三十年法学研究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命题需要我们作出解答,这就是:法学研究,到底要研究什么?瑞典法学家佩策尼克 (Aleksander Peczenik)认为,法学研究有不同的类型,如法史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哲学等。这些类型运用的是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的方法,而它们都是“非法律的方法”。还有一种法学研究的类型,其所运用的方法是“法律方法”,该方法是对私法、刑法、公法等具体法律进行体系性的、分析与评价性的揭示。这种法学研究就是欧陆国家尤其是德国流行的所谓法教义学研究。①Aleksander Peczenik.On Law and Reason.Boston:KluwerAcademic Publishers,1989,p17.法教义学是以实在法规范为研究客体的,因而被认为能够给法治以最大限度的支持。如芬兰法学家阿尔尼奥(AulisAarnio)指出:法教义学所关注的乃是某个具体的法律秩序,它是典型的解释性学科。它有两个功能:体系化与解释法律规范。体系化是法教义学的理论面向,而法律解释是法教义学的实践面向,它主要指向实践的目标。②Aleksander Peczenik.On Law and Reason.Boston:KluwerAcademic Publishers,1989,Introduction,p2-3.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教义学就是狭义上的法学,就是规范法学。法教义学方法论就是规范法学的方法论,亦即法学方法论或曰法律方法论。笔者赞同陈兴良教授的主张,倘若我们把法学界定为一门规范学科,即以法律规范为研究客体,则法学自有其独特的方法论。只有在狭义上的法学即规范法学的意义上,我们才可能确立法学方法论。③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载梁根林主编:《刑法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页。我们认为,狭义法学亦即法律教义学的研究将越来越成为主攻的方向。今后,我们应在“广义上的法学”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加强“狭义上的法学”研究,加强规范法学研究、法教义学研究、法律 (学)方法论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从法律运行特别是“善治”的角度而言,法学研究者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要更加积极地、及时地将其研究成果向法治实践层面推广,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目前,由于民法和刑法是最受重视的两个部门法,民法学界的法学方法论研究和刑法学界的刑法教义学研究,对于法律实施已经开始产生有益的影响。特别是以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解释学和以陈兴良、张明楷为代表的刑法教义学研究,对法院、法官司法过程中的法律适用起到了一定的方法维新的作用。相比之下,法理学界的法律方法论研究由于和部门法研究脱节以及与法律实务界缺少沟通机制,其研究成果尚未产生实际效应。当然,对于实务界的一些法官也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孔祥俊、王纳新等知名法官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尝试运用法律方法论的最新理论资源。至于其他如宪法学、行政法学的方法论研究,因为刚刚起步且受制度制约,影响力更小。总的来说,从对法治实践制度层面的影响力来衡量,法学 (法律)方法论研究,迄今为止还远远不及传统注释法学、法伦理学、法哲学、法社会学所施加的影响,从《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里也看不出这一根本性问题已经引起制度层面的高度重视。这种“漠视”无疑是对法学方法论研究者的一种鞭策,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完成法学研究第二个使命任重而道远,需要狭义法学的研究者们奋发图强、有所作为。
D920.0
A
1003—4145[2010]01—0064—04
2009-12-01
姜福东,男,青岛科技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法律方法论。
本文系“青岛科技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周文升 wszhou6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