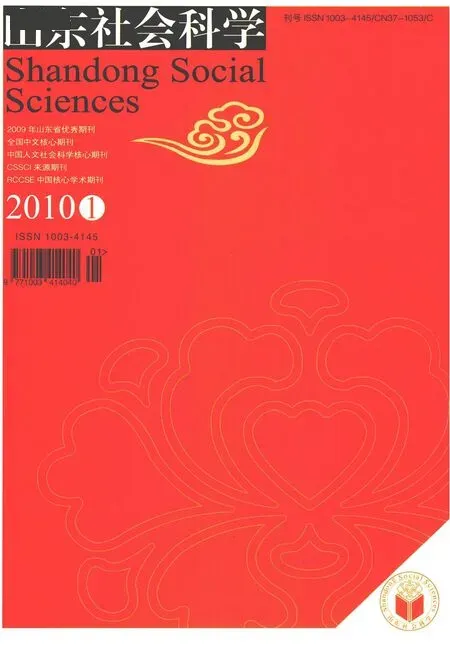当代民间工艺的语境认知与生态保护
——以山东惠民河南张泥玩具为个案①
张士闪 邓 霞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研究所,山东济南 250100)
当代民间工艺的语境认知与生态保护
——以山东惠民河南张泥玩具为个案①
张士闪 邓 霞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研究所,山东济南 250100)
民间工艺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创造、传承和演变都是在特定语境中发生的,因而民间工艺研究的前景就在于呈现它与所属整体民俗生态的互动关系。本文以此为思考基点,借重整体语境的研究方法,对山东惠民泥玩具进行“还鱼于水”式的深描,并试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讨论中国民间工艺与乡土语境的内在关系。这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大致建立、首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普查已基本结束的今天,对于进一步探索更富有实效的文化生态保护理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民间工艺;语境;生态保护;河南张泥玩具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民间工艺长期受到上层文化的轻视甚或漠视,被视作游戏小道、奇技淫巧。在历代艺文志、风俗志、游记之类文献中,提及民间工艺时,往往只述其艺,不见其人。即使是一些受过皇封御赐、声名显赫的民间工艺,也不过是描述其工艺技术稍为详致而已,而对艺人主体以及所处民俗语境基本上都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20世纪的中国民间工艺研究成果显著,尤其是在近 30年来,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方法的更新,皆前所未有。然而,重技术、轻语境的痼疾仍然普遍存在,多数学者继续以对民间工艺的“发现”与细描为己任,沉浸于对其工艺技法的条分缕析。比如民间玩具,就主要是作为造型别致的特色工艺品而进入研究视野,研究者关注和分析的往往是不考虑时代政治因素、剥离了地方性语境的工艺本体。也有少数学者,从功能论的角度联系当地生活与劳动的直接功用予以简单阐释,或煞费苦心从地方革命历史中找寻材料,将琐细的工艺描述链接到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之中。上述对民俗语境的忽视或对现成理论生搬硬套的做法,从根本上削弱了研究的学术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间工艺研究的学术品位,影响到该领域的知识积累、理论成熟和学科独立。
笔者认为,民间工艺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创造、传承和演变都是在特定语境中发生的,与特定社会语境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密切相关,并由一个个富有个性的个人来制作、展销、欣赏,故其意义和生机不仅在于它对于区域文化特征的物化表现,更在于民众在当下社会生活中如何不断地予以创造、展示和接受。对于当今民间工艺研究而言,过份偏重于对工艺技法描述方面的精雕细凿与热衷于理论的生搬硬套,都有失偏颇;还鱼于水,从民间艺人主体的行为实践出发,以其艺术行为、口述资料与社会事件为观察基点,以历时性的地方社会变迁为线索,将民间工艺置于当下民俗语境中,才能使之得到真正的理解与阐释。可以说,民间工艺研究的前景就在于呈现它与所属整体民俗生态的互动关系。放眼当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乡土社会正酝酿着前所未有的巨变,附着其上的许多民间工艺出现了严重的传承危机。本文正是以此为思考基点,借重整体语境的研究方法,对山东惠民泥玩具进行“还鱼于水”式的深描,并试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讨论中国民间工艺与乡土语境的内在关系。这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大致建立、首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普查已基本结束的今天,对于进一步探索更富实效的文化生态保护理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火把李与河南张:村落之间的分工与互动
“河南张,朝南门,家家户户做泥人。”这句远近流传的俗谣,是对惠民河南张村泥玩具当年曾盛极一时的集体记忆。河南张村位于沙河南岸,村里 4个姓氏 (张路孙洪)中张姓占多数,2006年该村有 70余户,330口人,耕地 770余亩。据村民说,该村泥玩具制作已有 300多年的历史。在 20世纪上半叶,全村男女老少几乎都能制作泥玩具。如今,靠这门手艺吃饭的人家越来越少。根据我们近年来的持续调查,2005年制作泥玩具的有近 20户,2006年为 10户,2007年、2008年均为 9户,2009年略有增加,达到 12户。显然,这一民间工艺目前面临着较严重的传承危机。
谈到河南张泥玩具,就不能不提及相邻的火把李村。两村都属于惠民县城西南部的皂户李乡,相距约 6公里。火把李村是个杂姓村,包括崔王李刘等姓,共 188户,750人,耕地 1510亩 (根据 2006年的统计),以农为主,其地貌都是浅平洼地,是黄河改道或决口的河间地带,由静水沉积而成,其土壤质地大部分中壤和重壤,盐碱地较多按照村民的说法,明初有李忠、李孝兄弟由河北省枣强县迁居于此,因立村处靠近一座长春寺,故最初村名长春寺。此地曾为元明交替时期的征战之地,丧生于此的军卒、士民很多,无人安葬,入夜常见磷光闪闪,状如火把,村名遂改为火把李。①邓霞:《惠民河南张泥塑:庙会语境中信仰与艺术的互动研究》,山东艺术学院 2009届硕士论文。农历二月初二,是民间所谓“龙抬头”的日子,火把李村一年一度的庙会就在这天举行,村民视之为“第二遍年”,此俗传承至今。
火把李庙会作为周边乡土社会的公共空间,将两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村民的记忆中,以前的火把李庙会首先是个“香火会”,然后才是个集贸市场。现在则以经济贸易为主,兼具文化娱乐的功能,作为一种定期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活动,已经成为当地乡土社会中一种“生活形式”。②刘铁梁、赵丙祥:《联村组织社区活动——河北井陉县之调查》,载于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205-257页。造型古朴的泥娃娃是火把李庙会中最具影响的“吉祥物”,其影响之大,从河南张村俗称“娃娃张”、火把李庙会俗称“娃娃会”中可以想见。近年来,塑料娃娃、毛绒娃娃、葫芦娃娃、套圈游戏、投球游戏、扎气球游戏、综艺表演等大量的现代商品及当代流行娱乐活动麋集于此,泥娃娃生产则处于日渐萎缩的状态。但一提起火把李庙会,人们总是将之与泥娃娃联系在一起,显示出区域民俗惯性与文化根性的巨大力量。显然,河南张泥玩具通过火把李庙会进一步凸显其吉祥寓意与审美价值,火把李庙会则因为有了河南张泥玩具的扎根而富有个性,火把李庙会与河南张泥玩具已经不可分割。
二、摊主、商品与顾客
据火把李村的老人说,自古以来庙会这天的生意一直特别好,除了河南张泥玩具很受欢迎外,以前主要卖的是条子筐、玩具、蒲墩子、纺车子、大镐、锨、檩条等生产生活用具,故又叫“买卖会”。坐地行商各种生产生活用具的摊主来自四面八方,而销售河南张泥玩具的则全部是河南张村艺人,属于自产自销。
色彩艳丽、造型古朴的河南张泥玩具,在火把李庙会上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它以红粘泥为原料,经设计造型、制坯、晾干、摩拭加工、涂粉、着色、涂胶等工序加工制成,有的玩具内装有哨子或弹簧、引线,能构成音响和局部活动。其品种很多,既有小巧玲珑的小玩具,也有高达一两尺的大泥娃娃。有在莲花上的“坐孩”、“躺孩”,有在肚子里内置哨子或小棒可以发声的“响孩”,以及狮、猴、鱼、鸡、桃、杏、葡萄等几十种。概括夸张的造型,艳丽的色彩,以及喜庆吉利的寓意,是其显著特色。如一个泥娃娃要用十几种颜色装饰,但在其背部和底部仍要刻意露出泥坯的本色,这在当初也许是偶然如此,而在后来却成为泥娃娃朴实无华风格的有意凸显。传统民间工艺,从来就是顺循民间生活之需与民间信仰观念而为民众服务的。民间艺人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有着鲜明的功利性追求,这种功利性不仅指向当地生活生产之需,也指向包括信仰心理在内的民众精神需求。以火把李村为中心的周围村落,有着当地特殊的信仰形式,民众希冀“一年不倒”,祈望亲人平安健康。河南张艺人便用自己独特的工艺技法予以表达,于是众多“富贵娃娃”、“吉祥娃娃”带着祝福走进火把李庙会。如今“栓娃娃”仪式的灵验尽管普遍受到怀疑,但当地赶庙会的村民和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仍然将窄窄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穿行于村头巷尾五颜六色的泥娃娃等泥玩具制品中,于熙熙攘攘摩肩擦踵之中品评各式各样的泥娃娃,交流人生体会,体验到一种莫大乐趣。临近中午,捎几个泥娃娃回转家门,似乎就将幸福平安带回了家门,将某种神圣感从庙会带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
从河南张泥玩具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民间信仰的精神力量为泥玩具制作提供了强烈的原动力,泥玩具是民众的信仰与艺术的奇妙结合。庙会上造型多样、朴实美观、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工艺,丰富了这一带民众的节日生活,使得日常生活不再那么单调乏味。
在村民的回忆中,火把李庙会风雨无阻,从来没有间断过,即使在“文革”期间亦然。当时,县政府、公社干部专门在路口设卡,拦截村民不准赶会。但摊主与顾客似乎心有灵犀,总是偷偷绕道而来,在庙会大街上完成交易。这实际上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家政治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政治征服与反征服的表现。一方面,火把李村庙会作为这一地区的中心,吸引着周边民众前来“朝圣”,不断整合着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面对来自恶劣的自然气候与特别紧张的政治压力,民众反而更加激发出某种体验自我力量、分享公共领域生活的强烈诉求。此时的庙会,就是以商品为媒介,摊主与顾客之间共同营造的“草根庆典”。
三、庙会与泥玩具:信仰与艺术的合奏交响
河南张泥玩具出现在火把李庙会,即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显扬在乡土社区的公共生活空间之中,成为一种被神圣化的民间工艺。正是借助于赶庙会、制销泥玩具的活动,火把李和河南张两村在周边乡土社会中结成了某种相对紧密的网络关系。一村以神圣的名义,面向周边乡土社会搭建起一个宗教、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庙会平台,而另一村则将富有特色的民间工艺植入其中,并逐渐成为庙会中的“主角”。人们赋予河南张泥玩具以祈子、佑子、祈福等功能,其实是基于现实生活之需而对民间信仰的有意贴近,而销售地点之落脚于被周边乡土社会视为信仰中心的火把李村,也就并非偶然。
火把李村庙会最初就是依托长春寺而成为以祈福、祈子为号召的庙会。人们选择在二月二庙会之期前来购买泥娃娃,实际上是在实施一种求子的巫术。哪家妇女若是婚后无子,就会在家人的陪伴下来赶庙会,在市场上买一个漂亮可爱、精神饱满的泥娃娃回家。比较讲究的人家则会悄悄地拿一根线到庙里跪求神灵,然后花更大的价钱从长春寺僧人手里“栓”走一个娃娃。显然,火把李庙会上泥娃娃的盛行,是以庙会所积累的神圣资本为依托,以当地人们信仰观念中泥娃娃所具有的“交感”功能为支撑,希图借此达到祈子的实用目的。以前,这一带医疗卫生条件差,人们对于不孕不育的现象难以解释,束手无策,赶一场热热闹闹的庙会,抱造型可爱的泥娃娃回家,意味着家里又“添”了新的人口,象征着子孙满堂、家族兴旺;也有的买来送人,借以表达美好祝愿。庙会中最受民众喜爱的是一种“不倒娃娃”的造型,这可能与过去新生儿的成活率较低有关,人们用这种“不倒娃娃”寓意为旺盛的生命力和健康壮实的身体,祈望自家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图个吉利。赶庙会,抱泥娃娃回家,由此成为这一带传承悠久的乡土传统。后来长春寺被毁,所有的泥娃娃都一律摆放在街面摊位上待价而沽,其神圣意味却并未随着寺庙的毁坍而消散无存。
其实,我国各地的许多民间工艺都是在民众信仰与艺术的互动中凝结而成,这甚至成为中国民间工艺的独特景观:艺术常常打着信仰的旗号,试图增强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合理性与权威性,而宗教信仰则需要借助艺术表演以扩大影响。艺术借助信仰而增值,信仰经由艺术而强化。无论是泥娃娃制销还是赶庙会的活动,我们都可以视为民间信仰在乡土社会现实层面的表达形式。庙会中的民间信仰,构成了民间工艺活动的重要语境。
河南张泥玩具既由民众所制,民众的生活实践活动和情感表达模式便决定着其艺术语汇和造型手段的选择,因而具有浓郁的乡土色彩。在数百年来的传承过程中,这些造型古朴、憨态可掬、形象逼真的泥娃娃,已经积淀了当地历史社会与文化的诸多内涵。如单单一个“不倒娃娃”,就蕴含着祈子、佑子、江山不倒、官位不倒、事业不倒等,成为社会各阶层人们心中的吉祥物。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河南张泥玩具的文化内涵具有多义性,才使得它在 300多年来一直保持了阐释的张力,并由此蕴具着生生不息的精神活力。
结语
民间工艺是遗产还是传统?置身于乡土田野之上,我们常常对此感到困惑。毫无疑问,问题的答案应是指向后者。民间工艺不是“文化遗留物”,而是掌握在村民手中的乡土传统,并作为活生生的文化现实与当下社会语境中的多种民俗事象杂糅共处。鉴此,我认为有如下两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走出对于民间工艺的认知误区:民间工艺不是所谓的“纯艺术”,而是与民众生活世界交织在一起。河南张村村民的泥塑工艺以及所制作的泥玩具,并不是每天每时都在进行,而表现为以年度为周期的季节性生产。就此而言,这些村民不是职业的“艺术家”。同样,当他们操持起农业生计,如春种秋收、夏做冬藏等,即不从事“艺术创造”的时候,我们也很难认定此时他们就是绝对的“农民”。民间工艺生产的节令性特点,使得众多民间艺人多是复合性人才。而民间工艺品中浓郁的乡土色彩,正是民间艺人在工艺活动与农事活动的双重劳作中涵育而成。我们在对民间工艺进行制度性保护的时候,就要注意创造一定条件,让民间工艺生产重新回归到一种与村落日常生活相联结的、充溢着精神创造旨趣的“副业”活动,而不是仅仅选择几个艺人给予生活补助、商业包装即算大功告成。基于此,我们需要保护的就不仅仅是民间工艺活动本身,更要注意保护民间工艺所赖以存身的文化生态。如果没有了后者的依托,民间工艺永远只能是表层的技术的存在,是一种没有心灵、随处飘荡的无根浮萍,直至成为存照归档的“遗产”。
我注意到,在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急剧升温的大背景下,河南张泥玩具早在 2006年便进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无论是在技艺传承还是在制作规模上,河南张泥玩具的衰落状态依然难见起色。受制于目前申报制度中对于各项非物质文化类别的精细分割,在申报过程中对于保护方案的设计以及后来对保护方案的实施,都难以将河南张泥玩具销售所依托的火把李庙会文化空间包括在内,难以形成整体、有效的保护,可能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因而,无论是调查、研究还是进一步的开发工作,我们的视野都应指向民间工艺的“活动”过程及所属的整体性文化空间,而不仅仅是几样定型的制品。
注重对民间工艺人人文关怀:对民间工艺人不应满足于拉网式的普查和抢救式的“立此存照”,更应抱持“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对民间工艺传承人实施人文关怀。关注民间工艺的现状,以现代田野作业的理念调查民间工艺,以种种现代手段保存技艺、建立档案,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更应注意对于民间工艺传承人的人文关怀,创造条件让他们走上现代社会的前台,更直接地参与到现代社会的发展与运作的过程之中。可以说,民间工艺在当代的复苏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这里面最突出的是来自政府的主导作用、来自学者的“主脑”作用和来自民间工艺传承人的主体作用。而学者研究、政府引导的作用,最终是要落实在民间工艺传承人自觉的文化传承意识与文化创造行为层面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今学者不应满足于从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的角度去研究民间工艺,更应该关注正在经历着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的民间工艺正在发生了什么,以此达至对于民间工艺传承人的“同情之理解”,推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中人文关怀方面的制度建设。
一言以蔽之,当代语境中的民间工艺,并非仅仅是传统农耕文化所遗存下来的“古俗”,而是一种容纳着丰富的历史社会信息、具有情感交流与生活交际价值并因之常在常新的文化形式,是一方水土表达集体情感与意志的比较稳定的物化载体。我们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对之实施保护,是因为它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推进力量。产品的不断创制与销售,既是在对传统的再造中对于群体意志的一再彰显与强调,同时也表现为对个人情感的优雅重温与新的培育,人类生活由此而生出许多韵味。特别是当今全球化、都市化的超速发展,使得民间工艺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连根拔起脱离乡土,但连根拔起的遭遇也可以是遍地开花的契机,脱离的同时即意味着超越的可能。当代民间工艺无可选择地置身于传统与当代、乡土与都市相杂糅的当代语境,当它在涵化现代文化成分后获得新活力,遵循自身发展逻辑奔向未来,就是它在新时代破茧重生的开始。斯时,其意义将不再局限于为一时一地提供某种经济资源,也不仅仅是延续一方水土的文化传统,而将久远地滋养、温润着无比广阔的社会疆土,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支撑。
J528
A
1003—4145[2010]01—0034—04
2009-10-12
张士闪,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邓霞,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生。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山东民俗生态与相关文化产业的区域发展模式研究”(编号:07BSHJ01)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