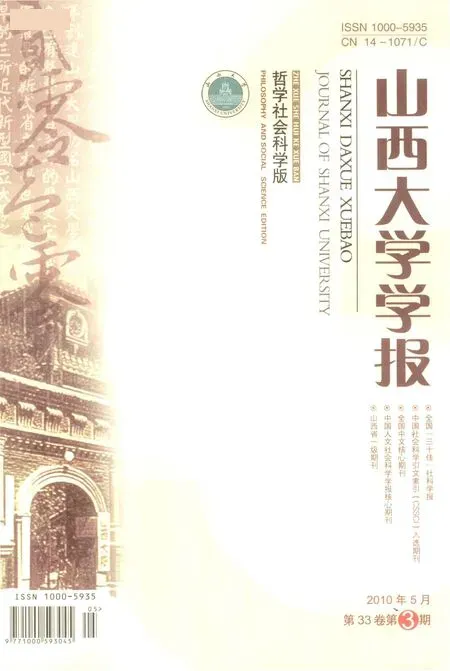鲁迅小说的人物与音乐
——鲁迅小说的跨艺术研究
许祖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鲁迅小说的人物与音乐
——鲁迅小说的跨艺术研究
许祖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文章所论的问题不是鲁迅小说的人物是否涉及音乐的问题,而是从音乐的艺术规范与艺术效果方面跨艺术地探讨鲁迅小说中人物的音乐性与鲁迅对人物描写的音乐性及其审美效果,也就是从音乐艺术的角度探讨鲁迅小说中人物生命迹象与生存状况的音乐性、人物内在生命诉求的音乐性以及人物感觉的音乐性三个问题。
鲁迅小说;人物形象;音乐性
鲁迅小说的人物真切、生动,内涵丰富,无论是现实形象还是历史人物,其艺术个性鲜活显豁呼之欲出;其个体生命迹象与生命诉求以及各种人生感受中常常包含了普遍而深邃的历史、社会、文化和人生意味。从不同的艺术角度进行阐述,我们都可以在一个宽广的平面得到可以言说的话题,其中,从中外小说艺术的角度展开言说,学界同仁已奉献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本文拟从音乐的角度对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展开跨艺术的研究,以期开拓鲁迅小说研究的新领域。
一 人物外在生命迹象与生存状况的音乐性
由于人物外在的生命迹象及其生存状况是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最直接、最感性的内容,因此,从音乐的角度透视鲁迅小说的人物,首先阐述人物外在生命迹象与生存状况的音乐性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鲁迅小说对人物外在生命迹象与生存状况的音乐性描写,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动态状况的描写,一种是静态状况的描写。动态状况描写的音乐性多具悲剧意味,静态状况描写的音乐性则常显喜剧意味。这两种状况的音乐性描写,在鲁迅小说的众多人物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应该分析的是在现代小说《祝福》中对祥林嫂的描写与历史小说《出关》中对老子的描写。小说对这两个人物外在生命迹象与生存状况的音乐性描写,虽然形式不同、意味迥异,但魅力却同样深邃,其阐释的空间也都十分广阔,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显示了鲁迅小说对人物外在生命迹象与生存状况音乐性描写的艺术匠心,也显示了鲁迅小说多样性的艺术手笔与繁复、隽永的艺术神采。
《祝福》中对人物外在生命迹象与生存状况的音乐性描写主要表现在对主人公祥林嫂形象的塑造。其中,对祥林嫂第一次在小说中出现时的外在形态的描写,又是最为直接、最有代表性的:
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这段描写是典型的“白描”,用鲁迅自己的话说,白描最出彩的是对人物眼睛的描写。而这段对人物眼睛的“白描”,特别是对“那眼珠间或一轮”的白描,在传神地刻画出人物状貌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节奏,一种由表面的生命现象构成的具有音乐性的节奏。这种节奏在强度上很轻软、柔和,使用的是纯粹白描的手法,没有形容、比喻,也没有进一步地展开和说明,但在功能上则强劲有力、深沉隽永,尽管它没有声音,表面上仅仅只是关于人物“活着”的生命迹象的一笔生动描写,但在直观地揭示出人物生存状况的悲剧性和鲁迅对人物生命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倾向的同时,也形成了音乐节奏所具有的强大功能和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音乐的节奏作为“音高和休止在时间中的一种流程”,它“能把音乐的音高材料或‘音响事件’有逻辑、有秩序地组织起来,从而产生有意义、有性格、有特点的组合,进而形成音乐主题”[1]。小说中所写祥林嫂“那眼珠间或一轮”的节奏,同样有这种艺术上的结构功效与主题功效。这一“节奏”,尽管反映的只是祥林嫂现在这一时段的外在生命和生存的悲剧性状况,只是对人物描写的一个片段,却有效地勾连起了祥林嫂整个生命的历程,它虽然是不变的,但由于描写的基点是动态性的,是从“改变”的角度与意义上对祥林嫂外在生命状态的巨大变化的描写,揭示的是祥林嫂人生命运的巨大不幸,因此,“那眼珠间或一轮”的节奏虽然不像音乐的节奏具有展开性,但在艺术逻辑上却导引出了一系列丰富而充满变数的悬念,一系列在内容与结构上都不能不回答的悬念,一些在审美上不能不让人追问的悬念,诸如:既然祥林嫂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那她原来是怎样的呢?她的生命与生存境况又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导致她发生如此变化的客观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她主观上的原因?等等。由此,“那眼珠间或一轮”的节奏,就不仅仅只是人物还是“一个活物”的直接证明,只具有显在的实证的作用与意义,而且还成为进入人物生命历程的一个通道,一个内在地被开通了的通道,这个通道的艺术路标指向人物生命与生存状况的过去及导致其变化的原因;这个通道的思想路标则指向小说的主题,其功效具有双重的特性,从而使“那眼珠间或一轮”的节奏成为关于人物的命运乃至整个小说创作意图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艺术结点,在有力而生动地勾画出了人物生命迹象与生存状况的巨大变化之后,小说悲剧性的主题也就水到渠成了,或者说是被“那眼珠间或一轮”的节奏,像音乐的节奏一样,通过自身保有的内在逻辑,有秩序、有规律地组织起来并被凸现出来了。所以,这句生动、传神的描写,虽然是用文字完成的,在形式上没有音乐节奏的分明形态,但却与音乐节奏在审美效果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比之音乐的节奏更具有可资分析的深刻内容与多样的艺术效果。更何况这其中还包含了惊讶、同情等种种复杂的情绪,也包含了清醒的时间意识,从时间的线性规律中写出了人物令人吃惊的变化,既表明了鲁迅对人的生命与时间关系的哲理性认识与判断 (时间本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生命无法抗拒和超越时间,所以,在无法停止的时间的流逝中,人的变化是无法避免的),同时也在艺术的层面切中了人的生命与音乐的种种联系(因为人的生命迹象中本来就有音乐的元素,如脉搏的跳动、举手投足等)。
与《祝福》中对人物生命与生存状况的动态性描写不同,《出关》中对人物生命与生存状况的描写主要是静态的,这些描写没有节奏,却具有音乐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请看下面的描写:
老子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
这是整个小说开篇对老子生命与生存状况的描写。
一过就是三个月。老子仍旧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
这是小说第二部分开头对老子生命与生存状况的描写。
两段重复的描写突出展示的是老子生命与生存相对静止的状况。对老子生命与生存的这种静的状况的描写,从音乐艺术的角度看,颇似音乐休止手法的运用,其情感倾向的表达与艺术效果正与休止手法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音乐作为声音的艺术,主要依靠声音的魅力来表情达意。但作为声音艺术的音乐也常常反其道而行之,用无声来表情达意,用休止的手法构造“大音希声”的审美境界。鲁迅这里对人物“毫无动静”与“好像一段呆木头”的生命与生存状况的描写,就颇似音乐休止手法的运用,它们以“无声”的状态传神地表达了小说的意图,以“大音希声”的审美效果,在一个特殊层面上显示了鲁迅小说的魅力与神采。
从小说的意旨来看,小说要揭示的是老子出函谷关的必然性,所要表达的是对老子行为和生命价值的否定。从小说提供的内容看,老子的出关,当然与孔子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孔子不断地向老子请教,将老子的所有都获取了,老子深感与孔子在一起时自己已经没有任何优势,自己在此地的存在虽然还可能得到孔子的尊敬,但自己在此地的存在价值却已经与先前不可同日而语了。更为重要的是,老子的出关还与自己的信念与行为有更为直接的关系,或者不妨说老子最后的出关是自己的信念与行动之间无法协调的矛盾的必然结果。按鲁迅自己的观点,孔子与老子虽然都是尚柔的,“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子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2]539-540也就是说,老子虽然感到了孔子的威胁,可他又是一无所为的,无法也不愿意用行动与孔子抗衡,因为,他一有所为,那么,就正如鲁迅在《<出关 >的‘关’》中指出的一样,“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2]540,也就是老子的行为就会与自己所恪守的信念相背离了。所以,老子这种生命状况的“静”,正是老子的信念与行动之间无法协调的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其没有任何行动,也无法采取任何行动的生存状况的直观表现。对老子这种无法调解的内心矛盾的揭示,鲁迅在小说中虽然没有展开进一步地描写,也没有借用近代小说细腻的心理刻画的手法用大的篇幅直接描写老子的心理和思想活动,只用了实写的笔法反复地描写了“老子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的生命与生存的状况,却使人透过老子这生命与生存状况的“静”,透过这表面静的描写,感受到了老子内心激烈的斗争,体味到了老子当时对自己去留利弊的反复权衡以及在权衡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之味。而也正是在这种音乐般休止的状态中,我们也分明感受到了鲁迅对“徒作大言的空谈家”的否定性的情感倾向以及鲁迅“毫无爱惜”送老子出关的创作意图。小说“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喜剧性艺术效果也就在这种音乐般休止的生命状况的描写中力透纸背地显示出来了。
当然,鲁迅小说对人物生命与生存状况的静态描写也并非只有喜剧效果,如《阿Q正传》第二章中对阿Q“睡着了”的生命与生存状况的静态描写,则既具有喜剧性,也具有悲剧性,是喜剧与悲剧两种审美倾向的完好结合,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和将无价值的东西撕开的创作意图的生动表现。其“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与音乐的休止一样,有很多可资分析的内容。就其悲剧性而言,阿 Q生命与生存的静止状况的出现实际上是阿 Q身上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以后的结果。在他“睡着”之前,他曾经为自己赢来的一堆钱在一片混乱中失去了而痛苦、烦躁,流露出少有的对失败的真情实感,这正是阿Q身上有价值的东西;而当他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还自认为是打了那抢去了自己的钱的人并欣欣然睡着了之后,便将自己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全部消解了,其喜剧性的意味也就在阿 Q“睡着了”的生命与生存状况中形成了。面对阿 Q这种“睡着了”的生命与生存状况,我们仿佛看到这样一种情景:犹如音乐的休止一样,万籁俱寂,只有“精神胜利法”的幽灵在天空徘徊,冷眼审视着“睡着了”的阿 Q。悲剧的、喜剧的意味也就在阿 Q这种生命与生存的静止情景中以一种混合的状态呈现出来,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多样情感,也在这种状况中体现出来了。
二 人物内在生命诉求的音乐性
有学者曾经指出:“音乐的表达更注重人类的内在生命。”[3]人的内在生命主要是人作为人的精神本性,音乐所表现的人的内在生命,也就是人的精神本性。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正是人的内在生命的欲求催生了声音的奇葩——音乐。英国民族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 (John Blacking,1928-1990)在《人的音乐性》一书中曾经指出,“很多 (即使不是全部)产生音乐模式的基本过程,都可能在人类的身体构造以及人类社会中的相互作用模式中被发现。”[4]24这也就告诉我们,音乐不是谁后天给予人的,而是人固有的基本精神特性,不仅人的外在生命迹象具有音乐性 (如身体构造),而且,人的内在生命诉求也同样具有音乐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对音乐特性的研究当然也就是对人的某种本性的研究,起码有助于对人的本性的研究。正如马英珺和陈铭道两位在译校《人的音乐性》的《译者前言》中十分中肯地断言的一样:“如果我们对包括音乐创作在内的音乐结构进行研究,并从整体上去学习一些关于人类相互作用的结构知识和人类思想核心性质,那么,人类赖以生存的一些结构准则也会昭然若揭。”[4]20他们不仅认可了约翰·布莱金的音乐是人固有的精神特性的观点,而且认为音乐的结构与人类赖以生存的一些结构几乎是完全相通的。上述观点虽有显然的绝对化倾向,其说法也似可推敲,但却显示了一种从个体的人与人类出发研究音乐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的严谨思路与开阔视野,不仅为人们解读音乐与人的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观念、范式,也为我们解读鲁迅的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一个从人出发来探讨小说音乐性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切入鲁迅的小说,一片新的天地展示在了我们面前。
鲁迅小说对人物内在生命诉求的音乐性描写,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对人物显意识诉求的描写,另一种则是对人物下意识欲求的描写,还有一种是对人物情动于中而形于外的生命诉求的描写。这三种描写的音乐性不仅与音乐的功能相契合,而且具有音乐所无法达到的人性高度。
人的显意识诉求往往是目的明确的生命诉求,一般说来,目的明确的生命诉求是不太适应用音乐的形式来表达的,因为音乐所表达的意义往往比较泛,不是很明确,但正如我国现代音乐家黄自先生指出的一样,“有的人说音乐的意义泛,使人不易揣摩。可是音乐的妙处,正在此点……音乐泛,耐人寻味,你如此去想它也可,如彼去想它也可。”[5]201也就是说,在审美领域,音乐意义的“泛”更耐人寻味。在鲁迅的小说中,鲁迅不仅借助语言文字的优势鲜明、生动地揭示了人物显意识的生命欲求,而且在揭示人的内在生命的音乐性的同时,使对人物显意识生命欲求的描写具有“耐人寻味”的音乐的审美效果。如《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热恋的时候,有这样一些描写: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子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
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
这是描写涓生等子君来的情景与心理活动的几段文字,它们形象生动地揭示了涓生显意识中强烈的生命诉求。这些描写,不仅揭示了涓生对声音感觉的音乐性,而且表现了涓生内在生命欲求的音乐性。音乐作为声音的艺术,其音的强弱、高低、快慢等往往通过人的耳朵在人的感觉中形成具有不同情感内涵的所指,正如我国古代的音乐学著作《乐记》中指出的一样,“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感于物而动。”[5]192-193也就是说,音乐的声音本来没有什么喜怒哀乐之性,也没有明确的意义所指,音乐所表之情与所达之意主要是人感觉的结果,或者说是人的内在生命的欲求赋予了音乐音响以意义。就小说中所写的“履声”而言,这履声原也无所谓情,无所谓意,但在特定的情景中涓生对它们的感觉却使它们变成了有情有意的音响,变成了流淌的音乐一样的有意味的形式,或者说,是涓生此时此刻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和生命的欲求,使这些时近时远、时强时弱、时清时浊的履声,具有音乐声响一样的表达人的内在生命欲求的功能,具有音乐音响一样的情感所指、意义所指。从审美的角度看,这些描写也的确“耐人寻味”,很富艺术的匠心。首先,涓生对子君在起初爱得多深、多真、多痴情,这本是模糊而难以量化的,即使借助语言的优势用几个形容词或者比喻句等来直接描写与形容,也很不容易获得言简意赅、生动具体的审美效果,而小说却用涓生的感觉,而且是用涓生对不具有诗情画意的“履声”的感觉,描摹出了涓生起初对子君的一往情深,其描写具体、传神,其意蕴以小见大,写的虽是平凡的事件揭示的却是人物内在生命中最有诗情画意的追求,它们虽然没有量化最难量化的男女之情,但却在逻辑上形成了通过想象可以揣摩的一个刻度:既然涓生对子君的“履声”都如此敏感且刻骨铭心,那涓生对子君的兴趣、爱好等更本质的东西会怎样?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小说开头的这些描写,不仅用人物对声音的具体、细腻的感觉揭示了人的内在生命本质的音乐性,而且在艺术上也为小说最后的悲剧预先涂上了一层对比强烈的底色,使“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悲剧有了具体、强固的支撑,从而也为水到渠成地导引出小说的主旨,小说所包含的“一个良心枯萎的社会是爱情天敌”的理性判断和小说所要表达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的深刻、睿智、清醒的认识,铺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这段显示涓生对子君一往情深的音乐性的描写,也为全文涓生的真诚忏悔提供了依据。正因为涓生曾经如此深情地爱过子君,所以,当子君最后因涓生的原因而离开涓生并抑郁而死后,涓生的忏悔才显得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忏悔,也正因为有了真诚的忏悔,涓生才没有成为现代的陈世美,没有成为一个被否定的人物。
在对人物下意识的生命欲求的音乐性描写方面,鲁迅小说也具有同样的艺术魅力。一般说来,人的下意识欲求不仅不受伦理的约束,而且也与喜、爱等情感无关,按照下意识学说大师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1856-1939)的观点,人的下意识活动及其欲求是纯肉体的人的本能的欲求,它有“心迹”却无“心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音乐在这方面就显示了自己无与伦比的优势。钱中书先生曾经从音乐时间性的本质存在方面指出,“音乐不传心情而示心迹”[6]。匈牙利杰出的音乐家李斯特 (Franz Liszt,1811-1886)曾从功能方面指出,音乐“它能够不求助于任何推理的形式,而复制出任何内心运动来”[5]263。鲁迅杰出的讽刺小说《肥皂》对主要人物四铭的下意识欲求的描写就正具有音乐对人的“心迹”描写的特点,也具有音乐一样的审美魅力。
四铭本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物,当他在小说中刚刚出现的时候,呈现在人面前的却是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但随后,小说对其三次下意识活动的描写,就逐渐撕碎了这副道貌岸然的面孔。第一次是四铭在街上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乞丐后回到家,当其愤愤地指斥当今学生如何没有道德的时候,突然冒出了“孝女”两个字。第二次是当其训诫儿子时也突然来了一句“学学那孝女”。第三次是同道来征求“移风文社的第十八届征文题目”,在征集“诗题”时,四铭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孝女行”。这三处描写,不仅彻底地暴露了这个假道学的丑恶嘴脸,也完整地揭示了其下意识中对女乞丐肮脏的邪念,其艺术的手法则颇似音乐对人的心迹的传达。
音乐在显示人的心迹时,既通过音的高低、快慢、强弱等表达心迹的变化,也常常采用重复的手法强化心灵的欲求,变是过程,而心灵欲求的表达则是目的,所以,万变不离其宗。在形式上,则是变化始终围绕主旋律,而主旋律则总不断被重复。如:我国现代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既用各种变化的手法表达了男女主人公爱的心迹,也用主旋律重复的手法,强化了人物“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死不离的爱情追求。鲁迅小说《肥皂》对四铭心迹的描写,虽然不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样以撼动心灵的悲剧情怀展示人物心迹的美好、圣洁,而是以尖刻的讽刺、否定揭示人物心迹的龌龊、肮脏,但在艺术手法上则是异曲同工的。四铭对女乞丐下意识的心迹虽然也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总与其邪念相关,他三次本能地提到“孝女”并堂而皇之地进行解说,并非真的被孝女的行为所感动,更非真的认为孝女的行为有匡正所谓社会风气、为人楷范的作用,不过是其心灵深处被压抑了的邪念的自然流露,是自己邪恶本质的自我暴露。所以,小说对其下意识心迹的每一次描写,都使其本质得到一次自我显露,人物自身的虚伪、可鄙的属性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在重复中被放大、被强化,小说尖刻、深沉的否定性主旨也就在人物下意识内容的多次重复中被凸显、被完成了。
与以上两例人物内在生命欲求的描写相比,《铸剑》中人物的内在生命诉求的描写则是另一种景象。如果说上两例人物内在生命的诉求所表现的音乐性还是一种隐性的音乐性的话,那么,《铸剑》中人物内在生命诉求的音乐性则不仅具有隐性特征,也有显性的特征。
《毛诗序》中曾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 (咏)歌之”,揭示的是人之所以“唱歌”的内在缘由,这种内在缘由就是人在表情达意的过程中,当人类创造的世界上最神奇的花朵——语言都无法承载表情达意这种人的生命的内在需求时,人就用歌咏的形式来表达。《铸剑》中写了“黑色的人”和眉间尺的头颅在特定场合下的歌唱,这也是鲁迅小说中少有的直接用歌唱来揭示人物内在生命诉求的描写。从功能的角度看,这些歌唱正如《毛诗序》中所描摹的一样,有让人物表情达意之功效,是人物情动于中而形于外的直接表白;从审美的效果来看,则不仅仅如此。按鲁迅自己的观点,小说中人物所唱的这些歌“我们这种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7]因为,这些歌的歌词是模糊的。从上下文的关系,我们固然可以揣摩出这些歌词的意思:无非是人物力图除暴复仇心迹的表白,也可以理解鲁迅如此写的艺术意图 (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因为是奇怪的人和头颅唱出来的歌,所以自然模糊、难解),但如果从音乐审美的角度看,这种用模糊的歌词表达人物内在生命诉求的描写,不仅切合了人的内在生命诉求的某些特征,也切合了音乐表情达意的特点。人的内在生命诉求虽然往往是明确的,但其“度”却是模糊的,如我在上面所分析的涓生、四铭的生命欲求就是如此,涓生对子君爱到什么程度,四铭的邪念到了什么程度,都是模糊而难以量化的。同样,《铸剑》中人物的除暴、复仇的生命诉求达到了什么程度,同样是模糊的,难以量化的,即使是用比喻性的文字也难以形成清晰、适应的刻度,而音乐正是人为了表达情感模糊的度和模糊的情感而创造出来的。从审美的意义上讲,正因为音乐表情达意具有模糊性,所以,对音乐表达的情与意也就有了多样解读的可能。同样,《铸剑》用人物模糊的歌唱表达人物内在生命的诉求,也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根据不同的环境、语境、心境对人物内在生命的诉求进行不同的解说,形成更为丰富的意义判断,如:对“黑色的人”第一次的歌唱,我们既可以从积极的方面理解黑色的人歌唱是在抒发除暴的豪情,是人物英雄气概的显露,具有从正面刻画人物之功效,同时,我们又何尝不可理解黑色人的这次歌唱是人物在为自己除暴的行动提神,为自己义无反顾地慷慨赴死壮胆并以此来抚慰自己内心的怯弱?因为,黑色的人也是人,他也有人的弱点,从艺术描写的真实性方面看,这样的理解也似乎更有说服力,不仅不会解构小说反抗强权的意图,相反还能更有效地发现小说真实性的艺术品质,从另一个层面拓展小说审美的空间。
三 人物感觉的音乐性
鲁迅小说中的很多人物的感觉都具有音乐性,如涓生、九斤老太、祥林嫂、女娲等等,其中,“我”这类人物的感觉的音乐性又是最为突出的,他们感觉的音乐性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艺术魅力,更赋予小说以很鲜明的哲理意味,所以值得重点分析。
鲁迅小说中的“我”具有多重的角色与作用,他既是作品中的一个独立的具有充分个性的人物形象,又往往是作品故事的叙述者。作为客观存在于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形象,他自身的生命状况与行为本身往往就具有音乐性,如《祝福》中的“我”,《故乡》中的“我”,《在酒楼上》中的“我”,《孤独者》中的“我”;而作为叙述者,其叙述的内容往往具有很强烈的音乐感,或者说是“我”在对象身上所感受到的音乐性。如《祝福》中的“我”。小说中有这样一些描写与叙述的内容:
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
这是对鲁四老爷的生命与生存状况的叙述与判断。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变化,单是老了些……这是对一群人的生命与生存状况的叙述与判断。
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是如此。这是对鲁镇“祝福”习俗的描写。
前两段的叙述与判断虽然简约,主要揭示的是现实中生活的人们变与不变的生命与生存状况,但在主体的角度上表达的却是“我”的音乐感。就现实的情况而言,小说这里对鲁四老爷与“他们”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的叙述与判断,其潜在的指向是人物的本质没有变化;而“单是老了些”的叙述,虽然指向人物的形态,但潜在的含义则是对时间的客观属性的认可。后一段对鲁镇祝福习俗的描写,则直接地表明了一种时间意识。不管是前两段中的感觉,还是后一段中的感觉,从主体的情况看,这些感受都是音乐的,不仅是音乐的,而且是与音乐的深层本质吻合的。
所谓音乐感有两个方面的所指:一是指对音乐的基本因素——声音和节奏、音高、音强等存在形式的感觉;二是指时间感。前者是显在的音乐感,是人通过自己的感官直接感受到的;后者是深层的音乐感,是流淌在人的生命与意识中的感觉,是对音乐存在的本质的感觉,或者说是契合了音乐存在本质的感觉。上面所举《祝福》之例的音乐感很显然与前者关系不大,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但却与后者关系密切。
从绝对的意义上讲,时间,是音乐存在的基本形式。小说所叙述的那些人与事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时间,是“我”从自己的角度对人与事的某种时间感觉,这些时间的感觉从表述到判断虽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如认为鲁四老爷和“他们”“单是老了些”,就表明了时间不可逆的本质特点,但更多的感觉却不是一种线形的时间感,也不是物理学赋予的客观时间感,而是主体抹平了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情况与客观情况后得出的时间感,是纯粹主体自我的时间感,不具有客观性,如认为鲁四老爷与“他们”比先前并“没有大改变”,虽然加了一个“大”字似乎承认他们还是有一点“变”的,认可了时间的流逝对人的客观的制约性以及人无法离开时间而生存的规律性,但从其潜在的意识与主体的价值认可来看,“我”想要表达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以及价值意识的保守性与恒定性,即不变性。如果说,前两段中所包含的时间意识的纯粹主体性还是差强人意的话,那么,后一段书写的关于祝福习俗的情景,其包含的时间意识则是地道主观性的,彻底地剔除了时间的客观性,完全抹平了时间过去、现在、将来的界限,表达的是年年岁岁花相似的循环时间感觉,是没有差异的时间感。这里所说的“年年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不仅不合物理意义的时间状况,也与我们经验的事实及感受相左,因为,今年的“祝福”虽然和以前一样是“祝福”,但形式与内容上的相同并不能说明规律上的相同,更无法说明时间意义上的相同。正如我们先人所说的,万物皆变,无事常恒,这是事物存在的规律,祝福作为一种习俗虽然年年存在,它每年也都总有一定的变化,也不可能跳出“变”的规律,只是变化的幅度也许太小人们感觉不到而已。至于时间的无法停止性和不可能中断的特性,更在绝对的意义上使今年的祝福与以前的祝福不可能不发生变化,最直观的事实是:今年的祝福在物理时间中已经让去年的祝福成为了历史,这既是常识,也是自然的规律,正如希腊哲人所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但,这种革去了时间的客观属性纯粹以“我”的内在感觉为基础形成的时间感却正与音乐本体内在于人而外在于己的时间性有着惊人的一致。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小说的音乐性特征不仅加强了、突出了,而且魅力也更为丰富多彩了。
作为时间艺术的音乐,因为没有空间形态的实体,所以它只能在不断地发生而又不断地被否定的时间过程中存在,在绵延的过去、现在的时态中显现自己的生命与活力,组构自己的整一性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它唯一能被人直接感知的音响,总是具有当前性的“现在”的音响。它过去的音响已经逝去无法返回只能以知觉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回忆之中而无法成为在场者;它将来的音响还只存在于可能之中不具有任何意义的现实性,只有当将来的音响向着现在生成,成为新的现在才具有了实在性。所以,当前化也就成了音乐形成自己时间规范的最基本的倾向,在场性则成为音乐本体的基本时态与基本的时间属性。小说中“我”认为鲁四老爷和“他们”与先前相比“没有什么大变化”,其简朴的言说以及形成的判断,既是人物一种现在状况的描述,又让人物的过去生存的时间以“我”的回忆的方式出现于“现在”生存的时间中,甚至让人物的将来也在这种不变中得到了某种具有价值意味的暗示:如果其思想观念与生活意义不得到改变,明年,甚至几十年以后他们也不会有“大变化”,其小说的主旨也就在这种看似不起眼的简单的叙述与判断中,在小说展开主要内容叙述之前就已经被点染出来了,也为后面主要内容的叙述定下了一个基调;而“我”身处今年鲁镇祝福的情景中所形成的与过去鲁镇的祝福情景相比“今年自然也如此”的判断以及所表达的时间感,则既是对祝福这种习俗当今状况的描述,也让过去的时间以前提似的形式当前化了,至于“年年如此”的判断,则是一种以想象的方式让将来存在于现在中的时间感,一种强烈的在场性的时间意识。这种“当前化”与“在场性”时间的感受,既是海德格尔(Matin Heidegger,1889-1976)指出的人在生存中对时间的最基本、最原始的感受,也是音乐给人的最切近、最直观的感受;这种时间感既包含了深沉的悲剧性的精神内容,揭示了人物与鲁镇社会面貌与精神面貌的停滞不前,表达了“我”的哀戚之情以及深刻的理性意识,摹写了无聊、无奈的“我”在鲁镇这个“我”的故乡的实际的生活处境,又吻合了音乐本体“现在”的时间性存在特征,构造了一种主体始终“在场”的音乐情景。在这种音乐情景中,“我”这个独立的人物的面貌及实质也得到了清晰的映现:“我”已经不仅是一个鲁镇的“他者”了,也不仅仅是当前和后面祥林嫂悲剧命运的见证者了,而是鲁镇里第一个觉醒了的先驱,第一个从鲁镇中出走而“变”了的人,第一个获得了深刻的理性精神的启蒙者。也是在这种音乐情景中,作为叙述者的“我”的作用与意义在得到了应有的肯定的同时,也得到了提升:我不仅在叙述故事,我更在评判故事的性质;我不仅是我,我还是创作主体。同样,小说第一自然段与第二自然段的作用与意义也就不仅仅是交代背景和人物了,那些看起来似乎是与主人公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的叙述与描写,也不仅仅只起到引出“我”见到主人公祥林嫂的作用,它们实际是为整部小说深刻主题定调的一组文字,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小说描写自我感受的文句,虽然没有一句话,甚至一个字提到音乐,更没有像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1929-)那样自觉地按音乐本体时间性的规范、特性来结构小说的开头,但自我时间意识与音乐时间性的存在本质的深沉吻合,却使其小说开头的强烈的音乐感在这些文句的字里行间力透“我”的悲凉的心境表现出来,从而在文字勾画的“我”的清醒、理性的精神境界与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显出一种音乐的情趣、音乐的时间,表达了一种语言所没有表达也难以表达的音乐的心绪。
时间性虽然是音乐的本质,但这种本质它不是抽象、虚化地存在着的,它往往在音乐最基本、最主要的艺术形式——节奏中得到直接而感性的再现。节奏除了音的高低、对比、强弱等规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艺术规范,这就是音的周期性循环,即重复。小说中“我”对人们与祝福习俗无变化、年年如此的主观感受,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讲,揭示的也是一种循环,一种重复,是现在向过去的循环,将来对现在的重复。这里引用的对人物变与不变的叙述以及对风俗不变的描写所构成的重复,尽管没有节奏等音乐的外在形式,主要是时间性的本质的重复,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这种重复在与音乐时间性的基本存在方式吻合的同时,也构成了与音乐一样的同质、同类的因素的重复、循环。这种重复、循环,与音乐节奏的同质、同类的重复、循环不仅是吻合的,而且其在时间的展开中构造的相似的情景及其效果也是异曲同工的,都有力而有效地凸显了主体的某种感受、某种意味,强化了作品的主题,深化了主体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某种精神性诉求。就我上面所引用的小说中的“我”的叙述与判断来说,这种循环、重复的时间感,在凸显了“我”的寂寞感、孤独意识以及批判意识的同时,也将主体鲁迅改造国民性乃至改造整个社会的精神诉求曲折地表现出来了。这正是小说中“我”的音乐感的思想与艺术价值之一。
[1]彭志敏.音乐分析基础教程 [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98.
[2]鲁 迅.《出关》的“关”[M]//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沈致隆,齐东海.音乐,文化与音乐人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4.
[4][英]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M].马英珺,译;陈铭道,校.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24.
[5]汪 流,等.艺术特征论 [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6.
[6]管建华.中国音乐审美的文化视野[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4.
[7]鲁迅全集 [M].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53.
The Characters andM usic in LU Xun’s Novels——The Cross-art Studies of LU Xun’sNovels
XU Zu-hu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azhong Nor m al University,W uhan430079,China)
Instead of discussing whether the characters in LU Xun’s novels are related to music,this paper,from the aspect of the artistic specification and the artistic effect,probes into the musicalness of the characters in LU Xun’s novels,the musicalness ofLU Xun’s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aesthetic effect in a cross-artistic way.In otherwords,it expounds the musicalness of life signs and living conditions,the musicalness of characters’internal life appeals and the musicalness of character’s feelings.
LU Xun’sNovels;the image of characters;musicalness
book=31,ebook=301
I210.97
A
1000-5935(2010)03-0031-08
(责任编辑 郭庆华)
2010-03-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鲁迅小说的跨艺术研究”(08BZ W070)
许祖华(1955-),男,湖北仙桃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