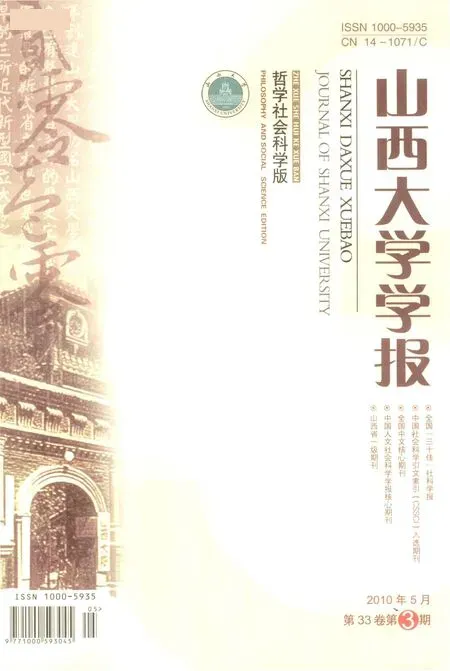《长恨歌》文体异说
徐翠先
(山西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山西忻州 034000)
《长恨歌》文体异说
徐翠先
(山西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山西忻州 034000)
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以他文史大家的卓识,提出“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的新说,并准确地指出《长恨歌》为“言情小说文体”的诗歌部分。其实就《长恨歌》与《长恨歌传》这两部具体作品而言,两者都是小说,一用诗体,一用传体,《长恨歌》就是诗体小说。
《长恨歌》;诗体小说;陈寅恪
总之,陈先生是把传与歌捆绑在一起,“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从而形成所谓“文备众体”的小说的整体。在贞元元和间也确有此等风气,除陈先生举出的元李之莺莺传及歌,陈白之长恨歌传及歌,似应再加入白行简之《李娃传》与元稹之《李娃行》。元之《李娃行》属于歌行体,与《长恨歌》相当,虽然只留残句,但从“髻鬟峨峨高一尺,门前立地看春风。”“平常不是堆珠玉,难得门前暂徘徊。”“玉颜婷婷阶下立”。[2]这五个诗句就可以推见描写李娃形象之生动。陈先生认为只有把歌传结合起来,才是“新兴之文体”即小说,似乎有些拘泥于见“史才,诗笔,议论”的定见。其
一 问题的提出
人们向来把白居易的《长恨歌》归类为叙事诗,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是往深想一想,叙事诗这一诗歌类型能否恰当地概括《长恨歌》的叙事艺术特征?就以白居易的另一篇与《长恨歌》齐名的叙事诗《琵琶行》作比,二者之间在叙事艺术上的差异恐怕就只能用“文体”这个尺度来衡量了。因此,《长恨歌》究竟应该归属哪种文学体裁类型,就有必要做一番探究。最早于叙事诗的笼统说法外提出异说的是陈寅恪先生,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一扫陈说,“别进一新解”:“鄙意以为欲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1]2陈先生所谓“文体关系”实启于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中一段众人皆知的话:“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1]4-5据此,陈先生说:“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虽非如赵氏所言是举人投献主司之作品,但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此种文体之……优点在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备具众体。既明乎此,则知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之部分,陈氏之传当之。”[1]13这种看法的确有点“异”,但他认为《长恨歌》是这种“新文体”即“小说”的诗歌部分却是“新”而又确的观点。
不仅如此,陈先生还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对《长恨歌》作了进一步的文体阐释。其一是关于《长恨歌》的情节增饰,实,就拿《长恨歌》与《传》来说,它们是对同一故事题材的不同语体表达,完全可以分离开来,陈先生自己也说“就文章体裁演进之点言之,则长恨歌者,虽从一完整机构之小说,长恨歌及传中分出别行,为世人所习诵,久以忘其与传文本属一体。”[1]11从作品实际与陈先生的论述,完全可以提出另一异说,《长恨歌》是诗体小说。就《长恨歌》之本文看,无论主题之统一,故事情节之曲折完整,人物形象之丰满灵动,作为小说都是上乘的。本文拟从三个方面略陈鄙见。
二 题材源于民间故事
长期以来,关于《长恨歌》主题的争论都与一个基本事实有关,即作品所据题材的来源及性质。凡是主张《长恨歌》的主题是揭露帝妃婚姻腐朽本质的,都把“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长恨”题目撇在一边,认为帝妃之间本就没有什么爱情可言,何况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结合又建立在新台之恶的基础上。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不仅忽略了自己是在研究文学作品的基本立场,而且也忽略了作品题材来源的基本事实。笔者认为《长恨歌》及《传》的创作题材至少不完全来源于李杨婚姻的宫闱秘闻,而有民间故事的成分,或者干脆可以说是民间故事化了的宫闱秘闻和道教神话故事的结合。
首先看作品题材的来源。最早提到这个问题的不是别人,正是为《长恨歌》作《传》的陈鸿,他在《长恨歌传》的结尾写下这样一段话:“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歌恨》……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3]明刻《文苑英华》此文后附出自宋人张君房所撰《丽情集》的一篇,结尾一段话与此有两处不同:一处是“质夫于道中语及于是”,另一处是“予所据,王质夫说之尔”[4]。两文互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长恨歌》所写的题材不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 (即陈鸿所谓《玄宗本纪》),而主要是王质夫所讲的故事。
为了有利于说明问题,有必要对王质夫和陈鸿二人的情况作一说明。王质夫是白居易的友人,交谊甚厚,《白氏长庆集》就收有不少投赠王质夫的诗,如《招王质夫》、《祗役骆口因与王质夫同游秋山偶题三韵》、《赠王山人》、《翰林院中感秋怀王质夫》、《寄王质夫》、《王夫子》、《和王十八蔷薇涧花时有怀萧侍御兼见赠》、《期李二十文略王十八质夫不至独宿仙游寺》、《酬王十八李大见招游山》等。从这些诗,结合陈鸿《长恨歌传》可以考见:王质夫,山东琅琊人,排行十八,至少在白居易于元和元年四月底任周至县尉前已隐居县南三十里仙游山之蔷薇涧。后出山入剑南东川节度使幕府,死于元和十四年 (819),年龄小于白居易。陈鸿,字大亮。他在《大统记序》中说:“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贞元 [乙 ] (丁)酉岁 (按,贞元无丁酉年,据下文登第后即修《大统记》,七年即元和六年辛卯始就等语,此丁酉为乙酉之误,乙酉为公元 805年)登太常第,始闲居遂志,乃修《大统记》三十卷……七年书始就,故绝笔于元和六年辛卯 (811)。”[5]元和元年(806)即乙酉之第二年,《长恨歌传》说他“家于是邑(即周至)”,《序》言“[乙 ](丁)酉岁登太常第,始闲居遂志”,在家闲居,又在周至,可见他就是周至人。这样,白居易、陈鸿、王质夫才能聚在一起,才能有元和元年冬十二月的同游仙游寺之行,才会出现创作《长恨歌》及《传》的文坛佳话。
两种版本合参,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杨生死婚恋的故事,特别是杨贵妃化仙的道教神话故事,是王质夫讲给白居易和陈鸿听的。《丽情集》本自不待说,就是通行本的结尾所言,其意也不出此。《传》曰:白居易、陈鸿与王质夫“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是谁“话及此事”?从王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等举止言语看,“话及此事”的人就是他。这说明王质夫不仅提供了题材,而且促成了歌与传的创作。我们说《长恨歌》及《传》的题材来源于民间故事,也可从陈鸿的郑重声明中看出。他说:“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可见他不是写历史,他只是把《长恨歌》改写为传奇,而《长恨歌》的题材是王质夫讲的李杨故事。
陈寅恪先生认为:“此种故事之长成,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体会陈先生的话,意思是杨妃化仙上蓬莱山的故事是白歌陈传的创造,而且是“从汉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1]13创造的基础就是方士招魂术与汉武帝李夫人故事的文化历史资料。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可能,但它不大符合《长恨歌传》所述的事实与逻辑。就作品本文而言,《长恨歌传》的传文应到“元和元年十二月”之前结束,之后是后记,说明题材来源及歌、传创作过程的。其中“话及此事”的事,当然包括歌、传、人天、凡仙的整个故事情节,陈先生所引汪立名也说:“论诗须相题,长恨歌本与陈鸿王质夫话杨妃始终而作,犹虑诗有未详,陈鸿又作长恨歌传。”[1]12话说的是很明白的。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包括杨妃化仙情节的李杨生死婚恋故事是从哪里来的?是王质夫的编造还是来自民间?笔者的结论是来自民间的传说故事。这一点甚至连古人也早已看了出来,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作过如下论述:“惟方士访至蓬莱,得妃密语,归报上皇一节,此盖时俗讹传,本非实事。”他进一步认为,玄宗自蜀还长安,居兴庆宫,还有外人进见。至上元元年迁于西内,宫禁严密,内外不可通,“即方士能隐形入见,而金钗钿盒,有物有质,又岂驭气者所能携带?此必无之事。特一时俚俗传闻,易于耸听,香山竟为诗以实之,遂成千古耳。”[6]这说明《长恨歌》及《传》的题材的来源就是“俚俗传闻”。
三 杨妃化仙神话考索
现在应当回答一个问题,诗的题材包括史事和神话两种性质不同的故事,史事基本上与客观事实相符,而杨妃化仙的故事则纯属子虚乌有,那它是怎么“长成”(陈寅恪语)的呢?是不是汉武帝李夫人故事的唐代翻版呢?
杨妃化仙的故事是道教神话,自然是道士制造出来并流传民间的。这个结论是有迹可寻的。《长恨歌》写这一段是这样开头的:“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陈鸿《传》则作:“适有道士自蜀来,知上皇心念杨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术。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驭气……”歌、传相较,传文多了一个曲折,即道士以招魂术索之,不至,才用“游神驭气”术去访寻。唐玄宗的奢望也就是像汉武帝一样,见一见杨妃的魂魄身影而已,但道士招不来,这才有了在蓬莱山见到杨太真的动人一幕。这个道士是谁?他的招魂和神游驭气是在何时何地进行的?杜光庭有一篇神仙传《杨通幽》给我们透露了一些信息。传出《仙传拾遗》,收入《太平广记》卷二〇。文曰:
杨通幽,本名什伍,广汉什邠人。幼遇道士,教以檄召之术,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无不立应。驱毒厉,剪氛邪,禳水旱,致风雨,是皆能之。而木讷疏傲,不拘于俗。其术数变异,远近称之。玄宗幸蜀,自马嵬之后,属念贵妃,往往辍食忘寐,近侍之臣,密令求访方士,冀少安圣虑。或云:杨什伍有考召之法。征至行朝,上问其事,对曰:“虽天上地下,冥寞之中,鬼神之内,皆可历而求之。”上大悦,于内置场,以行其术。是夕奏曰:“已于九地之下,鬼神之中,遍加搜访,不知其所。”上曰:“妃子当不坠于鬼神之伍矣!”二日夜,又奏曰:“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间,虚空杳冥之际,亦遍寻访而不知其处。”上悄然不怿曰:“未归天,复何之矣?”炷香冥烛,弥加恳至,三日夜,又奏曰:“于人寰之中,山川岳渎祠庙之内,十洲三岛江海之间,亦遍求访,莫知其所。后于东海之上,蓬莱之顶,南宫西庑,有群仙所居,上元女仙太真者,即贵妃也。谓什伍曰:‘我太上侍女,隶上元宫。圣上太阳朱宫真人,偶以宿缘世念,其愿颇重,圣上降居于世,我谪于人间,以为侍卫耳。此后一纪,自当相见。愿善保圣体,无复意念也。’乃取开元中所赐金钗钿合各半,玉龟子一,寄以为信。曰:‘圣上见此,自当醒忆矣!’言讫,流涕而别。”什伍以此物进,上潸然良久,乃曰:“师升天入地,通幽达冥,真得道神仙之士也。”手笔赐名通幽,赐物千段,金银各千两,良田五千亩,紫霞帔,白玉简,特加礼异。[7]
杜光庭是唐末五代时的著名道士,中和元年 (881)随唐僖宗入蜀,遂留成都。后事前蜀王建父子,赐号“广成先生”。他曾漫游巴蜀,著作甚丰,收入《正统道藏》的就有二十多种。《仙传拾遗》四十卷 (残)是《墉城集仙录》之外的另一仙传作品。从时间上来说,收录于《仙传拾遗》的《杨通幽》自然晚出于《长恨歌》一百余年,但从作品的内容看,有两点应引起注意:第一,杨什伍为玄宗访寻杨妃之事,不在龙驭返京之后的廷掖,而是在狩蜀期间的“行朝”,“行朝”即行在,是玄宗幸蜀期间的跓跸之所,而且不是杨什伍找上门来,而是“近侍之臣,密令求访方士,冀少安圣虑”,才找到会“考召之法”的杨什伍的。这些过程不仅合情而且合理,因为玄宗“属念贵妃,往往辍食忘寐”,恐怕在蜀期间为更甚。第二,搜访杨妃的魂魄有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首先是在“行朝”内设置道场,作为招魂之所;其次详述访到杨妃的过程,一日入地二日上天,均未找到,说明马嵬驿事变之后,杨妃既没有为鬼,也没有成神,这就隐含着一个可能——她并没有死。那她哪儿去了?那就只有成仙一途了。果然,第三日在蓬莱仙山找到了她。这个过程能说明什么问题?杨什伍其实是个骗子,他根本不会什么“考召之法”,更不会“神游驭气”之术,他只能编出第一日入地、第二日上天都找不到杨妃踪迹的谎言暂时搪塞唐玄宗。他根本就招不来,但是玄宗是君王,他总得有个交代,弄不好是会掉脑袋的,因此,第三日才以杨玉环曾度为女道士赐号太真的事实,编出了在蓬莱山找到已回仙宫的“上元女仙太真”,玄宗本为“太阳朱宫真人”、“开元中所赐金钗钿合各半,金龟子一”等貌似合理的神仙故事来交差。当然这是聪明的作法:杨妃既是“太上侍女”,自然不可能像鬼魂一样招来相见,而且这也投合了玄宗的心意,因为玄宗认为“妃子当不坠于鬼神之伍”。这样一来,杨贵妃化仙的神话就被制造出来了。
事情虽发生在蜀地“行朝”,但此等故事在道教盛行的当时,杨什伍为自高身价,当然会流布于蜀地民间,流传增益,越来越完善,待到杜光庭入蜀,漫游蜀地,便搜集起来;同时,它也必然随玄宗龙驾返京,而从宫廷流传于民间。在之后的将近五十年中,民间口耳流传,便形成一个完整的民间故事,可让王质夫来“话”一番了。王质夫对此感兴趣,我想应有两点原因:一是他隐居仙游山之蔷薇谷,身居民间,有机会搜集到此等生动有趣的民间故事;二是王质夫是道教神仙观念的信仰者,白居易《赠王山人》诗云:“闻君减寝食,日听神仙说。暗待非常人,潜求长生诀。”[8]即为确证。这样一位隐居的山人,虔信神仙之说,并修炼“减寝食”的内丹,当然更会主动搜求民间的神仙传说,并深信不疑,以为谈资了。
四 《长恨歌》小说叙事的基本特征
虽然杨妃化仙的神话是道士杨什伍用自神其术的方式编造出来的,可是传到民间就逐渐民间故事化,融入了人民群众的理解;传到王质夫耳中,神仙信仰加上士大夫文人的神仙伴侣的审美理想,讲给白居易、陈鸿听时,整个故事已成为一个以“情”为核心的“希代之事”了。因此,王质夫认为必须由能够理解这个故事内在价值 (即所谓“多于情”)的白乐天来写成诗歌,以便流传于世。
笔者认为李杨的婚姻悲剧与杨妃化仙的道教神话原来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独立的故事,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既是民间熔铸的结果,也是白居易的艺术创造。在作品里,杨妃化仙的故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白居易的《长恨歌》能够在当时和后世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感染力,关键的一环就是他运用了这个民间流传的道教神话,激活了李杨婚恋故事的爱情基质。英人马林诺夫斯基研究托伯兰岛人的文化,把他们的神话传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说,叙述过去的事,常作为信史;二是民间或神仙故事,用以娱人娱己;三是宗教神话,反映其宗教信仰、道德以及社会结构的基本因素。[9]白居易对于杨妃化仙的故事的态度,除“娱人娱己”外,也反应了民间对于爱情婚姻的道德观念。他用李杨忠贞于爱情这一主线酝酿主题,构思作品,反映了人民群众和时代风尚对于男女婚恋的社会理想,突出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超时空的爱情永恒观。不管白居易的文体意识是否自觉,而作品的事实是他确实围绕杨妃化仙的道教神话,吸收传奇作品的艺术经验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表面的事实是,他完成长诗的写作后,主动要求陈鸿把《长恨歌》改写成传奇,就是一个明证),突出一个“情”字,把李杨的婚姻悲剧改造成一个人天仙凡紧密相连的表现纯美爱情的传奇故事。
《长恨歌》是诗体小说,因为它至少在三个方面运用了小说的叙事方法。
第一,故事情节的合理安排。所谓合理就是更加艺术地表现主题,白居易为此对素材作了两点大的调整:一是删去了玄宗夺子寿王瑁妃杨玉环为自己的贵妃这一乱伦之举的历史材料。过去的诗论家往往以为尊者讳作解释,其实从小说叙事艺术的角度看,这是为了突出作品的主旨而对分散枝蔓的剪裁。诗人用“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叙李杨的结合,那就是一段最自然不过的人间婚事了。一个“重色思倾国”的君王,一个深闺待字的丽人,因缘巧合,成为一对深情的夫妇,这就是作品开始奠定的主题基础。二是把杨什伍招魂的神话从蜀地的“行朝”移到回京之后,虽隐去了杨什伍的姓名却保留了临邛道士的身份。这一移花接木的调整意义重大,它不仅为玄宗龙驭返京之后的凄凉晚景和孤灯挑尽的苦恋留下了描写的无穷空间,而且直接揭示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长恨”主题。
第二,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处理。我们说《长恨歌》是一篇诗体小说,它取材的前半——李杨婚姻悲剧,虽然基于史实,但进入作品后,在道教神话故事的折射下发生了变化,成为一个爱情故事的框架,李杨本身也成为这个爱情故事的文学人物,与其说他们是帝妃,毋宁说他们已转化为理想爱情的符号。李隆基也好,杨玉环也罢,在诗人笔下都是忠贞于爱情的典型,如果说马嵬驿事变之前,两人迷恋于爱情的描写带有浓厚的帝妃生活的奢靡色彩,使人不免产生“荒淫误国”的感觉,那作品的主体——马嵬驿事变之后的描写就只有真情流露了。应当说,诗人对玄宗和杨贵妃都做到了个性化处理:一个封建帝王能做到“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确实不容易。正因为如此,杨贵妃死后,他才如此痛心,如此痛苦,蜀道的凄凉,南宫内的孤独,一位太上皇在爱情悲剧的折磨下,长夜难眠,梦魂不到,只好求助于道士的招魂术,那是一种什么景况!至于杨玉环,从入宫到赐死,作为一位美丽柔弱的女性,在玄宗的笼罩下,其个性淹没在宫廷的华彩欢宴之中,只有在蓬莱山独处仙宫才摇曳多姿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从形容到心理作为一个爱神的形象进入中国古代文学形象画廊之中。在人物描写上,诗人发挥了诗歌的特长,把抒情镕铸于叙事之中,把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
第三,叙事视角的选择。现代叙事学十分重视小说叙事视角的研究,因为它不仅规定着叙事对象以什么面貌呈现在作者的创作视野之中,而且影响着各种描写手段的运用。唐传奇文体的确立,其中一个重要的艺术因素就是叙事视角艺术的成熟。白居易生活在传奇从成熟走向创作繁荣的中唐时期,其弟白行简、其友元稹、陈鸿都是著名的传奇作家,他在叙事诗的写作中有意无意借鉴小说的叙事艺术经验是十分自然的事,何况《长恨歌》这种小说体裁的作品呢!《长恨歌》采用的是小说的叙事方法。首先,从整体上看,诗人采用全知视角,把以唐玄宗为主角的全部故事情节置于客观呈现和发展的角度,诗人只作客观描写,即使是蓬莱神话也是由玄宗引出来的。只有这种全知视角才能让诗人把李杨二十年的故事从结婚到婚后生活到马嵬驿悲剧到蜀地惨状到晚年孤苦再到求道士寻访,从宫内到宫外,从乐极到生悲,从行在到回宫,方方面面,尽情地写了出来。其次,他也使用了限知视角。临邛道士寻访到蓬莱仙山,叩响了西廂玉扃,从“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之下,便把太真仙子置于道士的视线之下,无形之中转成了限知视角,杨太真的形容、表情、动作、语言都是道士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这就增加了神话的真实性。
此外,在叙述顺序上运用了倒叙法,“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是一段倒叙。本来七月七日在长生殿两人的誓愿完全可以写在前面的适当地方,但诗人没有这样做,而是用倒叙法写在了结尾处,把它作为道士真正见到杨太真的确证,这就不仅是个次序先后曲折的问题,而是事关主题的宏旨了。当然不少考据家考出,长生殿在华清宫,是祭神之殿,非言私情之所,而且玄宗幸华清宫均于冬日,从未在热天临幸过,那就纯属历史了。而白居易在写小说,他生当中唐,去盛唐未远,不会不知道这些,这样“违背历史真实”正说明他在自觉地写小说。
结论:陈寅恪先生于数十年前,就以他文史大家的卓识,提出白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是歌传合璧的新兴小说体裁,也准确地指出了《长恨歌》是“言情小说文体”的诗歌部分,但是囿于“经国大业”之文章观,他认为只有用《长恨歌传》结尾的“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来补充《长恨歌》戛然而止的开放结构,才算完整。其实就《长恨歌》与《长恨歌传》而言,两者都是小说,一用诗体,一用传体,而且诗体的《长恨歌》比传体的《长恨歌》更具叙事艺术的优长,题材处理更简洁,人物刻画更形象,心理描写更生动,语言更富诗情韵味,无怪其具有永久的艺术生命力。
2001.
[2]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698.
[3]鲁 迅.唐宋传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74.
[4]周绍良.唐传奇笺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68.
[5]陈 鸿.大统记序[M]//全唐文:卷 61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2738.
[6]赵 翼.瓯北诗话[M].霍松林,胡主佑,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43.
[7]李 昉,扈 蒙,李 穆,等.太平广记:卷 20[M].北京:中华书局,1961:138-139.
[8]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97.
[9]李丰茂.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论集[M].中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138.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D ifferent Views on the Style ofSong of Never Forgetting
XU Cui-xian
(Chinese Departm ent,Shanxi Xinzhou Nor m al College,Xinzhou034000,China)
Decades of years ago,Mr.Chen Yin-que,a master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advanced that novels during the year form ZhenYuan to YuanHe in TangDynasty are of a new style,and"The Story of YingYing"and the Song by YuanZhen and LiShen in the year of ZhenYuan,and the Song and Story ofNever Forgetting byBaiJu-yi and ChenHong during the year of YuanHe are of a new style.He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Song of N ever Forgetting is the poetric"love story".In fact,as far asSong of Never ForgettingandStory of N ever Forgettingare concerned, both of them belong to novels,with one in poetry style,and the other in biography style.Song of N ever Forgetting is poetry-style novel.
Song of Never Forgetting;poetry-style novel;Chen Yin-que
book=26,ebook=276
I226.3
A
1000-5935(2010)03-0026-05曰:“若以唐代文人作品之时代,一考此种故事之长成,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此故事既不限现实之人事,遂更延长而优美。然则增加太真死后天上一段故事之作者,即是白陈诸人,洵为富于天才之文士矣。”[1]11-12这段论述杨妃化仙情节为“白陈诸人”“增加”尚容别议外,陈先生完全肯定了这一情节增饰的必要性,因为它使作品的故事“更延长而优美”,从而认为此种“创始”“洵为富于天才”,评价是很高的。其二是关于作品中的爱情细节描写,曰:“又宋人论诗,如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之类,俱推崇杜少陵而贬斥白香山。谓乐天长恨歌详写燕昵之私,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无礼于君……殊不知长恨歌本为当时小说文中之歌诗部分,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而详悉叙写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尔,而为元白所擅长者。如魏张之妄论,真可谓‘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也。”[1]12细节描写自然是小说叙事的本质特征之一,而“详悉叙写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尔”,真是高人之论。
(责任编辑 魏晓虹)
2010-03-06
徐翠先(1956-),女,山西原平人,山西省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唐代文学研究。
——笔画设计